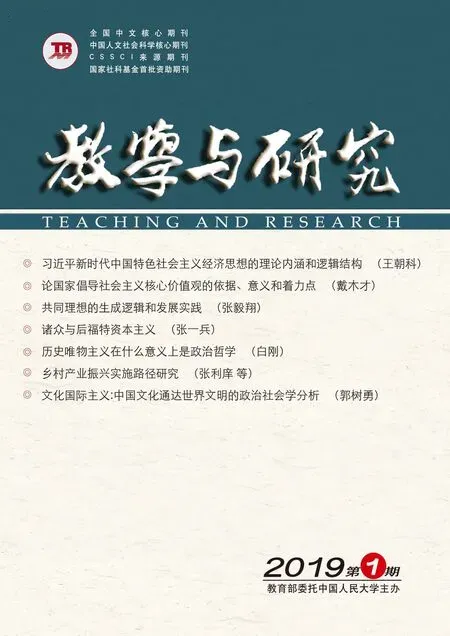诸众与后福特资本主义
——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解读
维尔诺[注]维尔诺 (Paolo Virno, 1952—):意大利哲学家,左翼运动旗手。1979年因牵涉红色旅事件被捕,1982年被判刑十二年,维尔诺上诉获释候审;1987他最终被无罪释放。1993任乌尔比诺大学哲学教授,1996年任蒙特利尔大学哲学和传播伦理学教授,现为罗马大学哲学教授。代表作为:《诸众的语法》(2003),《诸众:创新与否定之间》(2008)等。是意大利当代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中最有思辨能力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2003)[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he MIT Press,2004. 中文版:[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此书为维尔诺任卡拉布里亚大学传播伦理系主任时,于2001年所做的三次专题讲座整理而成。一书,是讨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时代的主体——诸众问题最重要的文本。可以看到,维尔诺在讨论诸众的主体性特征时,总是将其与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体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在《诸众的语法》一书的最后,维尔诺提出了诸众与后福特资本主义之间关联性的十个问题。这也是本书中最重要的理论研讨部分。其中,他将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对未来超越性社会解放的憧憬,直接翻转为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方式,其核心是劳动时间和物质生产模式的根本性解构,创造财富的活劳动被指认为雇佣劳动方式中的一般智力运用。维尔诺甚至认为,后福特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和对待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后福特:马克思的预言的翻转
维尔诺认为,诸众是后福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产物,诸众的生成基础是由“后福特制的当代生产的性质”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则的体现。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资源(primary productive resource)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交往能力之中,存在于人类特有的交流和认知能力(活力、动力)的综合之中”。[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27、126-127页。这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新的断言了。依维尔诺的看法,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资源的转移,聚焦为马克思在“机器论断片”中指认过的“一般智力”。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一般智力性质,决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诸众之异化存在的特征。也是在这里,维尔诺给出了关于诸众异化存在状态定义域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经典表述:
像陌生人[stranger (biosxenikos)]那样活着是常态;讲话中的“共同之处”要比“专门”之处更为流行;智力像这个社会生产支柱那样重要的辟邪装置(apotropaic device)应有的公开性;没有终端产品的活动(精湛技艺);以个体化为原则的聚合;对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物尽其用;无所不能;语言非指涉性(non-referential)方面的过度膨胀(闲聊)。[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27、126-127页。
这就是维尔诺眼中的诸众。诸众的生存不像传统社会宗法关系中的凝固化奴隶状态,也不像泰勒—福特制流水线上的无法脱身的固定熟练工位,它的存在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自己,就是一种永远自我异化的陌生状态。一般智力的共通能力、没有产品的精湛技艺、空洞的闲聊和好奇,展现出诸众消极状态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或潜能性”。在维尔诺看来,这正是诸众在历史学、现象学和存在论上的表现。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后福特资本主义与诸众的关系,他提出了理解二者之间关系的十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排序是任意的,相互之间会有交叉和聚合。可以说,这是维尔诺对自己诸众理论最重要的一次小结。但遗憾的是,维尔诺对这十个问题并没有给出深入的理论分析。
首先,维尔诺强调了诸众在意大利的出现,是“1977运动(Movement of 1977)”[注]“1977运动”是意大利当代左翼力量的一次重要革命运动。这也是继法国红色五月风暴之后,当代西方左翼社会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77年,因一名意大利自治主义学生在罗马遇害,导引出左翼学生先后接管了罗马、佛罗伦萨等多地的大学。运动席卷意大利全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与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特定历史产物。这是维尔诺研究诸众问题时,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原则。在他看来,诸众作为后福特主义的产物,“在意大利是由受过教育的无稳定工作的流动性劳动力的骚动引起的”,他们不同于那些泰勒制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再将“在工厂里制造耐用消费品”的稳定工作看作自己的生活方式。维尔诺认为,“1977运动中集体倾向的转变(退出工厂,无视稳定就业,善于学习和网络沟通),即转向专业化的新概念(机会主义、闲聊、精湛技艺等):这是意大利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最珍贵的成果[‘反革命’的意思不是简单地复辟到先前的状态,而是相反的革命(revolution to the contrary),即为了重启生产力和政治统治的一次经济和制度的彻底创新]”。[注]
按维尔诺的观点,劳动者从1977运动开始的走下流水线,退出固定工作是与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相一致的反向革命,这个运动本身虽然并不带有“奴性(servile)”,可是它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却是符合后福特主义的。这可能是转变中的诸众自己也没有意料到的事情。维尔诺1996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还记得反革命吗?》。[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p.29,pp.241-259.在这篇文章中,维尔诺指认这种反向革命的实质是:“反革命总是反方向的革命(revolution in reverse)。换句话说,它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激烈创新(impetuous innovation),它巩固了资本的指令(capitalist command),并再次使它畅行无阻。反革命,正像它的对立面一样,改变了一切。它创造了一个漫长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其中,事件的时间序列似乎被压缩了。它积极地创造了自身的‘新构序’(new order),塑造新意识、文化习惯、品味和习俗——简言之,一种新的共识。”[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p. 241.中译文参见黄晓武译稿。诸众的出现是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但这种改变的本质是资本的构序方式创新,正是这种创新导致了整个劳动者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这就是诸众。
其次,后福特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经验实现。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的著名表述[注]维尔诺在这里引述的马克思的原文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维尔诺此处加:机器的自动化系统)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中已经预言了今天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机器的自动化系统”,它造成了财富新的巨大源泉,然而,这却铸造了一个“几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抽象知识—科学知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趋向于同主要生产力平起平坐,还将重复性劳动降至残余的位置(residual position)”。[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0页。中译文有改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p. 100.恐怕,不是重复性劳动被降到残余的位置,而是机器人承担了重复性劳动,劳动者在自动化生产中付出的监管作用被弱化了。维尔诺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后福特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中,一般智力已经成为财富的源泉,这样,马克思自己所坚持的基于体力劳动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律”,就已经“被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瓦解和驳倒”。因为,自动化生产中的一般智力对象化与马克思的产品的劳动时间计量公式之间出现了矛盾,并且,马克思自己预言,由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维尔诺认为,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确是马克思上述断言的经验实现,可是它并“没有带来任何解放的后果”。知识所起的作用与渐成次要的劳动时间之间的不均衡并不是孕育危机的温床,却催生了新的、稳固的权力形式。生产观念的激进蜕变,一如既往,属于老板手工作的范畴。要说“片断”(“Fragment”)是暗指胜利在望,却更像为社会学家准备的工具箱。“片断”描述了一个横在我们所有人眼前的经验现实:后福特制结构的经验现实。[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1页。
维尔诺的意思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对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本质的分析,已经成为今天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真实现实,但这种新的现实并没有如马克思所期望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危机和解构,反倒生成资本家全新的统治权力结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曾经期冀的一般智力运用所将迎来的解放可能性,已经被资本所吸收和消化,成为“老板手中”的新的生产力和新型统治的工具。
再次,诸众与劳动社会危机(the crisis of the society of labor)。维尔诺在上述第二个观点中,已经指认一般智力在自动化生产体系中的运用并没有导致马克思预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反倒生成了新的统治形式,然而,这并不是说维尔诺不承认后福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新的社会危机。维尔诺认为,新的社会危机恰恰出现在诸众自己的劳动生存之中。他说:“当科学、信息、一般知识、合作,所有这些都体现自身为生产的关键支撑系统”时,看起来,这是一种对传统劳动社会的超越,可是在新型的劳动主体诸众那里,则会出现一种新的贫困状态:“工资补偿、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由投资带来,而不是由于缺乏投资造成的)、无限灵活地使用劳动力、等级制度的扩散、古代训诫措施的复兴、对个人的控制手段不再受工厂制度规定的制约。在现象学的层面,这是为了‘超越’而允许的磁暴(magnetic storm),[注]磁暴(magnetic storm)现象:当太阳表面活动旺盛,特别是在太阳黑子极大期时,太阳表面的闪焰爆发次数也会增加,闪焰爆发时会辐射出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及高能量的质子和电子束。其中的带电粒子(质子、电子)形成的电流冲击地球磁场,引发短波通讯所称的磁暴。矛盾的是这种超越恰恰是在那个被超越的对象的基础上发生的”。[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2、132、134、135页。
这也就是说,当科学技术和一般智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基础时,看起来脱离了生产流水线的诸众得到某种生存论意义上的解放,可是,弹性工作时间,灵活的就业和多样化工资形式,这些超越传统劳动社会的所有解构在另一种层面上重新成为资本控制的力量。所以维尔诺认为,这种“劳动社会的超越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形式中产生的”。[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2、132、134、135页。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灵活性生产形式,都必然“体现为不朽的雇佣劳动(perpetuation of wage labor)!”[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2、132、134、135页。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现实中,每一种新的技术革命和工作方式的解放都成为诸众被压迫、被奴役的力量。看起来获得自由的诸众的贫困是看不见的贫困。
二、劳动生产时间的精神错乱与生产模式的多样化共存
在维尔诺看来,后福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中边界清晰的劳动活动和一般活动、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等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首先是后福特资本主义现实中劳动与活动的同质化。一方面,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边界是固定的,而在今天的后福特主义时代,由于一般智力在生产中的运用,“劳动和非劳动显示出相同的生产力形式”,与体力劳动支出一样,“语言、记忆、社交、伦理和审美爱好、抽象思考和学习等”这些过去被认定为非生产性的能力,也都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在数控机器旁边监管,在电话机前提供咨询,在办公室里设计营销方案,这些不同的劳动者的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一般智力导致了后福特时代所有工作的同质性(homogeneity)。另一方面,与过去生产劳动总是发生在工厂车间内不同,今天的工作往往出现在工厂和办公室之外,它既包括了复杂的经验和学问,也内含着在生产劳动活动之外的各种合作。在家承担分包任务的编程人员、提供房产信息的售房小姐、跑在各地的导游,虽然都不在固定的工厂车间和办公室里工作,向生产过程提供的服务也不同,却都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相对于马克思原先界定的生产性劳动,“后福特制劳动也总是成了隐性劳动(hidden labor)”。在维尔诺看来,“隐性劳动,首先是指不获取报酬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各方面都像劳动活动,然而,不被计入生产力”。[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2、132、134、135页。后福特制时代劳动与活动趋同、隐性劳动的泛化,都将导致传统劳动观念的根本改变。
其次,后福特资本主义中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差异弱化。维尔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区分了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比如在农业生产中,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生产时间中,直接的劳动时间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在后福特时代,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是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变成了“监管和调整(劳动时间)机器的自动化系统(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定义为生产时间)”,工人的劳动时间在自动化生产时间之外,即“监管和调整的现代活动,却自始至终处在自动化处理过程的旁边(alongside)”。[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6、137、137、137-138、138页。二是“在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时间’包括非劳动时间(non-labor time),而社会合作正是扎根于这段非劳动时间之中”。[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6、137、137、137-138、138页。机器与人之间不会出现交流性合作,而处于监管职能的劳动者之间发生交流恰恰在生产过程之外。依维尔诺的观点,这种新的情况必然要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重塑,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来自剩余劳动,即来自必要劳动(补偿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而承担的开支)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差值。那么,不得不说,在后福特制时代,剩余价值首先取决于以下两者的差距,即并不像计算劳动时间那样计算的生产时间和依照劳动时间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计算的劳动时间的差距”。[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6、137、137、137-138、138页。
当然,维尔诺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说明是不够精准的,被延长的工作时间与必要劳动的差值只是绝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而相对剩余价值的基础是资本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维尔诺这里的意思是说,后福特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的来源,已经转到突破了传统劳动与活动、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边界的新的弹性劳动—生产时间中。
维尔诺认为,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第二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生产模式的多样化。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作场所之外整个社会生活都被一般智力所同质化,这造成了“多样化生产模式的共存(co-existence)”。[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6、137、137、137-138、138页。维尔诺认为,福特主义的劳动组织通常是参差不齐的,其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并没有在全部生产领域普及,但是,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通过一般智力,通过计算机数据通信技术,通过包括非劳动时间在内的生产合作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语言知识成为主要生产力时,却造成了所有生产内外各种活动的同质化。所以,维尔诺说:“后福特制重新编辑了整部劳动史,从大众劳工的群岛(islands)到专业员工的飞地(enclaves),从再次壮大的自主劳动(independent labor)到重新设置的个人实力形式。在这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各种生产模式仿佛按照世界博览会的标准互相随着重新同步(synchronically)登场。”[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6、137、137、137-138、138页。
维尔诺刻意使用了劳工的“群岛”和专业员工的“飞地”这样的概念,来表征同质化活动中诸众的存在状态。当然他也承认,站在“不同参差不齐的生产模式的对位声部(counterpoint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ve models)”上,软件工程师、菲亚特工人与临时工之间存在差异,但在一般智力的泛化之下,诸众的“情感色调、兴趣、心智和期望值”却是共同的。
三、作为活劳动在场的一般智力和大众知性
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般智力虽然并不直接融入固定资本,但它却成为创造性的活劳动。为此,他仍然不赞成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的观点,即将一般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仅仅视作对象化为“固定资本、机器系统在内的‘客观的科学力量’(objective scientific capacity)”,而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便遗漏了今天绝对卓越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一般智力本身就作为活劳动在场(the general intellect presents itself as living labor)”。[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9页。中译文有改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p. 106.如果今天的活劳动已经是一般智力的活动,言下之意,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就会是一般智力活动。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严重质疑。
为了支持自己对马克思的这种批评,维尔诺强调,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首先,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已经出现了所谓“第二代自主劳动”。比如在意大利梅尔菲的菲亚特汽车制造工厂,资本家对自动化机器系统的操作程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工人现在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摆脱了过去福特主义流水线上疲惫不堪的状态,作为数控机器人作业的监督和管理者,男女工人都可以通过一般智力在相互之间发生交流性的“语言合作”,实现了新一代的自主性的劳动。维尔诺并没有交待第一代的自主劳动是什么。他认为,“在后福特制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概念和逻辑构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概念和逻辑方案是不能被置于固定资本中的、不能与多元化的生活主题的复现相分离的。因此,一般智力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维方式和‘语言游戏’。在当代劳动过程中,有着思想和话语,它们起着像生产性‘机器’那样的功能,无须采取机械体或电子管那样的形式。”[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9-140、40页。中译文有改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p. 106,p.107.
这的确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无法想象到的情况。但是,维尔诺将后福特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中决定性的活劳动,仅仅归结了作为机器运行监督和管理者的劳动者之间的主观交流是有问题的。因为,真正对创造性的设计、制造概念和构序性的“逻辑构架”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根本不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旁边的劳动者,而是在微软和苹果公司大楼中被盘剥的另一类智力劳动者(如软件工程师和编程人员)。这恐怕也是解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题的一个科学入口。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后出现的极其复杂的新问题。
我觉得,维尔诺进入不了这么复杂的理论构境层。在这里,他转而批评了哈贝马斯的劳动观,即将没有互动的劳动与“相互承认、具有共同信仰的”互动性的“交往行动”区分开来。维尔诺显然不同意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他认为,“今天,雇佣劳动(被雇佣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互动(interaction)”。[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39-140、40页。中译文有改动。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p. 106,p.107.这打破了哈贝马斯所设定的边界。因为,在今天后福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沉默寡言的,而是侃侃而谈”。维尔诺甚至认为,今天的劳动者的任务就是将“个人的劳动与他人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联系做得更好”,“正是劳动活动的这种反射性(reflective character)强调了劳动中语言—相互联系方面(linguistic-relational aspects)日趋重要;它也强调了机会主义和闲聊成为非常重要的工具”。也是在这个构境意向中,维尔诺声称:“后福特制领域,黑格尔的‘精明’已被海德格尔的‘闲聊’所取代”。[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1、141页。
其次,与这一观点相关,维尔诺还认为,如果更准确地定位,体现在后福特资本主义的活劳动中的一般智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大众知性(intellectuality of the masses)。维尔诺承认,大众知性并不直接等同于一般智力,“我不会认为今天的工人是分子生物学家或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专家”,但是,大众知性的形式体现了一般智力,其中“存储了不能在机器系统中具体化认知和交往技能”。这包括:“最通用的思维能力、语言的能力、爱好学习、记忆力、进行抽象化和相互关联的能力、倾向于自我反思。大众知性与思想行为(如书籍、代数公式等),是与思考和语言交流这些简单的能力有关。语言(如同理解力或记忆力)比脑子里所想到的东西要更具扩散性,更少专业性”。[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1、141页。
其实,维尔诺的这个界定并非十分有力。因为,在福特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者是否就不具有维尔诺这里所列举的大众知性呢?可能,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每一个阶段上,劳动都会具有一定的“思考和语言交流这些简单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是不是真的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
再次,也正是在这个构境层面,维尔诺再一次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马克思。这一次,他认为后福特主义时代出现的诸众,已经“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理论(theory of proletarianization)抛在了交往群体之外”。维尔诺强调,他刚刚讨论的大众知性观点是无法还原到马克思对“非技能”的简单劳动和“智力”的复杂劳动的分界中去的,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大众知性是复杂劳动,可是“这里的‘复杂’劳动是不能简化为(not reducible)‘简单’劳动的”。[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当然,今天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以高科技知识为支撑的复杂劳动是否能简化为简单劳动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可是,维尔诺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过于简单化的。他认为,“鉴于后福特制时代的劳动都是复杂劳动,不可以再化约为简单劳动,也就意味着确认‘无产阶级化理论’今天已经完全离开了交往群体”。这是因为,大众知性为主的劳动已经在“借助人类通用语言认知能力”时,马克思针对“人民”概念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化理论’便失效了(fails)”,诸众不再是过去的无产阶级。[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
维尔诺的最后结论是:“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Post-Fordism is the ‘communism of capital’)”。[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在他看来,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局面,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资本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f capital)”。这应该是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之后普遍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维尔诺说:“人们用这个称呼来指国家在经济周期承担决定性的角色、终止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由公共产业做计划指导的中央集权管理、全面就业的政策、福利制度的兴起。资本主义对十月革命和1929年危机的反应是庞大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或者说得更好些:国有化)。”[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
当然,是不是用“资本的社会主义”来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可以再讨论,但应该承认,维尔诺这里的观点可能是我所看到的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象所做的最好的历史分析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都没有认识到,凯恩斯革命的历史意义正是对十月革命的现实和理论深刻反省,维尔诺对这一历史变革的精准历史定位和具体定性论断是令人惊讶的。
维尔诺告诉我们,如果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革命是走向资本的社会主义,那么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社会制度的蜕变则可以指认为资本的共产主义。
如果说,福特制用自己的方式吸收并重写了社会主义经验的某些方面,那么,后福特制则已经从根本上摒弃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它在一般智力和诸众之间所起的铰接作用那样,后福特制以其自身的方式(in its own way)提出了典型的共产主义要求(typical demands of communism,取消工作、解散国家等)。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
维尔诺甚至认为,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对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回应,而60年代和70年代,在欧洲也出现了“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这也是“反对雇佣劳动”的失败的革命。[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应该分别是指法国的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的“1977运动”。维尔诺说:“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斗争表达的是非社会主义(non-socialist)的要求,甚至是反社会主义(anti-socialist)的要求:对劳动的激进批判、对差异的偏爱,如果还想说,那就还有完美的‘个体化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不再是占有国家的欲望,而是保护自己免受国家的侵害,解除国家束缚这样一种能力(aptitude,当然,有时有点暴力)。”[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
请一定注意,这是维尔诺对“五月风暴”和“1977运动”最重要的一次比较性历史说明;并且,维尔诺认为,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或者说‘资本的共产主义’是对这次失败了的革命的回答”。[注][意]维尔诺:《诸众的语法》,第143、144、144、144、146、146、147、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