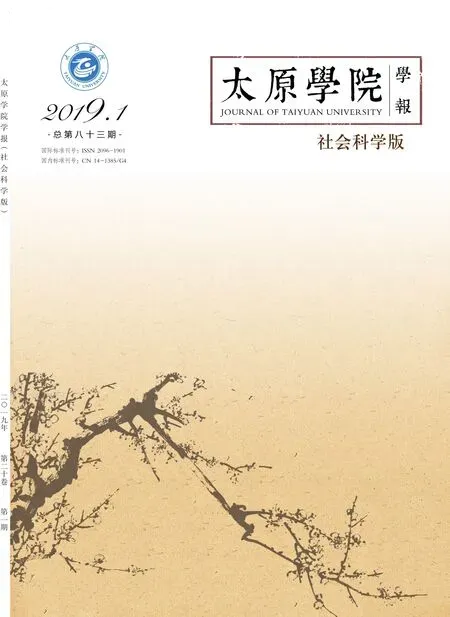论梦窗词的抒情结构①
姜晓娟 蒋 蔚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723000)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其词以密丽沉郁、幽邃绵密的风格,在宋词词坛卓然一家,独树一帜。尽管其词作在意象与典故的使用方式上因如“七宝楼台”[1]16般不成片段而饱受后人诟病,但作为在南宋末期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吴文英将个人的“沉着之思,浩瀚之气”(《蕙风词话》)[2]4447雕刻在梦窗词繁杂多变的结构形式中,使词作章法一丝不乱而又脉络井井。吴振华先生认为,梦窗词中存在一种“包裹式抒情结构……梦窗词卷起是圆,展开为线……这样的结构是梦窗词中的重要结构”,[3]所谓“包裹式抒情结构”,是指词作以浑然圆融的主题情感贯穿始终,词人在抒情过程中以跳跃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使作品外在形式上呈现出“意象奇特浓密,且时空常转换跳跃”[4]3的艺术特色。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梦窗词的这一抒情特色多持批判态度,一方面是其通篇堆砌罗列的意象典故使作品表面看起来跳荡无绪、杂乱无章,另一方面,凄迷朦胧的意境加大了读者对梦窗词的理解难度。学界对梦窗词结构的关注多是从作品章法入手,周永忠先生《雕缋满眼,灵气盈篇——梦窗词章法结构剖析》一文指出梦窗词在结构上兼具词作布局谋篇常见的线性结构与回环结构;罗弘基先生《梦窗词结构艺术初探》一文则从梦窗词整体布局、层次过渡以及意象组合三个方面,分析其结构艺术,而鲜有学者从抒情结构入手,研究梦窗词的抒情特色。所谓词作的抒情结构,是指词人通过对词心、词境等美感材料的处理,将个人审美体验传达给读者的结构方式。本文拟从梦窗词抒情的内、外结构入手,探究词心、词境对梦窗词抒情的影响,以及在这两种抒情结构影响下梦窗词呈现出的审美内涵。
一、内结构——词心的深幽朦胧
词作为抒情文学,其抒情结构是和诗不同的,核心是审美主体勃发的、强烈的、不可抑止的情绪状态和深层心理体验。[5]51词体的抒情核心是构成作品的内在骨架,也是作品的灵魂,词人创作是围绕主题思想的不断填充与扩展,作为词作抒情核心的主题思想,融汇着作者对某一事件强烈的主观情感,这种情绪作为贯穿词作全篇的主线,有时是词人借助外界客观景物进行抒发,有时是词人“缘事而发”。词作为以抒情为主要目的文体形式,受篇幅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词人在具体创作中很难将事件或情绪生成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清楚,如果后人不了解词作创作所涉及的本事,就很难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现的情绪从何而来,故而大部分词作的抒情核心呈现出深幽朦胧的审美特质。吴文英作为南宋词坛善于雕琢词句的代表人物,以其细腻的情感体验,借助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作品抒情表现出飞扬的神思,具有笼罩全篇、而又不易琢磨的深幽朦胧的艺术特质。
(一)“用意不可太露”的创作宗旨
邓乔彬先生认为:“大多数词人思路易于寻迹,形象与主题的关系清晰可见。吴文英则不然。他的词往往表面意义与内在意义有较大距离,题旨藏的深。”[6]289此语意在指出梦窗词词意飘渺无端、不易为读者探寻的特点。梦窗词中很多作品涉及词人个人情事,但他出于各种原因并不想将他的这段感情展现得过于直白,于是,时空混乱颠倒、意象错综繁复、典故晦涩难懂便成为梦窗词的一大特色,从侧面折射出吴文英“用意不可太露”的创作宗旨。
首先,吴文英在恋情词创作中喜好借物喻人,表面看词人在咏物,实则是在更深层次上借外物描摹隐喻自己内心对昔日恋人的怀念。如代表作《琐窗寒·玉兰》:
绀缕堆云,清腮润玉,记人初见。蛮腥未洗,海客一怀凄惋。渺征槎、去乘阆风,占香上国幽心展。遗芳掩色,真姿凝澹,返魂骚畹。 一盼。千金换。又笑伴鸱夷,共归吴苑。离烟恨水,梦杳南天秋晚。比来时、瘦肌更销,冷薰沁骨悲乡远。最伤情、送客咸阳,佩结西风怨。[7]1
单纯从词题来看,本词的主题应该是歌咏玉兰花。然而,词人上片在描写玉兰花的同时,也将玉兰花赋予了人的情态特征,以花喻故人,赞美花也就是在凸显故人的美丽。开篇将花之初见比拟为人之初见,借花之明艳暗喻人之美丽,将故人身世与玉兰之来龙去脉合为一体,这一“借花返魂”的艺术构思巧妙地为情感抒发蓄势。转至下片,通过对与故人以往幸福生活的短暂回顾,时而写花,时而写人,以感性视角将花与人交叉重叠来写,从最初“返魂骚畹”带给词人的短暂喜悦,到最后“冷薰沁骨悲乡远”的凄凉结局,委婉点出与恋人不得不分离的结局,从而在咏物词中巧妙镶嵌了对故人的思念之情。总体来看,词人情感的爆发是在二人被迫分离,对故人的怀念之处,为了这一情绪的抒发,吴文英借对玉兰花的描写做了很多铺垫,上片以玉兰花的描写为主,以花喻人,到了下片,玉兰花更多是意象意义上的存在,抒情主人公的地位逐渐凸显,而吴苑、咸阳等多个跳跃空间的组合出现,在不了解词作本事的情况下,初读极易给人造成恍惚迷离之感,这与词人“安排篇章又常不以理性而以感觉印象为线索”的创作习惯紧密相关,[4]14从而给人造成支离破碎,不知所云之印象。在咏物的过程中隐喻人事生活,以个人极强的感性逻辑随意走笔,是吴文英隐藏情感的重要手段。
其次,梦窗词用典较多,意象的跳跃性也很大,生僻典故的运用加大了梦窗词的阅读难度,后人对此批评的声音较多。王国维先生在评价梦窗词时有“映梦窗,凌乱碧”之语,[8]108即言梦窗词“意旨飘忽,意象凌乱,缺乏深沉之思而徒有外在形式之炫目耳”。[8]109王国维对梦窗词的评价有失偏颇,他只看到吴文英在作品外在形式上所做的繁复雕砌,而忽视了作品内在思想上的艺术内涵。梦窗词之沉郁表现在词人生长在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固有的家国之痛,作为一位布衣终老的文人,面对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的政治现状,梦窗自然不会如辛弃疾般以战斗的笔法揭露社会现状,家园破碎、情感生活不如意,使词人表现出慷慨悲凉而又无可奈何的态度,这就形成了梦窗词“莫不有沉着之思、浩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尽。”(《蕙风词话》)[2]4447如《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乔木生云气)一词,创作于南宋朝廷国势日渐衰微之时,词人借追忆当年英雄陈迹之事点出对当时国家形势的隐忧,词中“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7]1691“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7]1691“怀此恨,寄残醉”[7]1691等句一改梦窗词以往千回百转的抒情特色,有直抒胸臆,不吐不快的沉痛气息郁结其中。吴文英虽以讽喻为本篇词作创作宗旨,但通篇写得都很隐晦,在以南宋政治局势为主题的创作中,吴文英都喜好以“以小见大”的笔法,将沉痛的时代悲怆感寄托于作品中,具有“言外寄慨,出之温婉”[6]304的独特艺术个性。
梦窗词抒情结构的凌乱与吴文英本人“用意不可太露”,即故意隐藏个人情感经历的创作宗旨有很大的关系。吴文英既想在作品中塑造深情多才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又不想将自己当年情事以及对时政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导致作品深幽朦胧的审美特质。后代词评家批评梦窗词结构混乱,通篇雕砌的弊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词人苦心孤诣隐藏于作品中的不宜为外人表露的思想情感。而梦窗词中弥漫全篇的沉郁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连接梦窗词各种跳跃空间与凌乱意象的必要工具,词心的深幽朦胧是构成梦窗词抒情结构的重要表现。
(二)“句断意不断”的情感脉络
所谓“句断意不断”的情感脉络,是指吴文英在词的创作过程中因强烈丰满的主观情绪表达需要,不断变换景物书写,如果读者单纯从意象和景物转换入手解读梦窗词,那么跳跃的语言表达很容易造成词意的中断,若能把握梦窗贯穿作品全文的情感脉络,则会发现,吴文英通过浑然圆融的主观情绪抒发,将与之相关的事件串联在一起,频繁的片段事件书写构成梦窗词“句断意不断”的包裹型抒情脉络。梦窗词是“感情的组合,不是外在世界的场景再现,甚至不是对外在世界经验的具体体现。回忆提供了现实世界和景象的短片,这些形象同人的情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根据感情的内在世界的规律,又重新被组织起来。”[5]71只有剥开梦窗词外在华丽的辞藻与繁复的意象,读者才能接近吴文英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情感内涵。
词体是以抒情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当吴文英以“句断意不断”的情感脉络连接词中涉及事件时,事件的叙述对情感抒发起辅助作用。尽管词人强烈、密集的主观抒情使作品中事件转换频繁,但以情感为主线贯穿全文的抒情脉络往往能成为词中潜在的抒情线索,为读者提供解词脉络。如梦窗恋情词代表作《莺啼序》(横塘棹穿艳锦),“是他借咏荷而抒写了一生的恋爱悲剧,是梦窗词体大思精的杰构之一。”[4]120本词的“体大思精”主要表现在抒情主题的确定性,即梦窗通过对当年情事的怀念,抒发对所爱之人的思恋之情,在这一显性主题下,辅助表现抒情对象的事件叙述却具有极大的时空错乱性,其时间不限一时,地点分属多处,甚至苏、杭二姬形象也有诸多重合模糊之处,这体现了吴文英在作品中以主观情绪抒发为主,无论是事件的叙述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亦或是意象、典故等创作素材的安排,都是以传达自我意绪为第一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尽管这首词是梦窗词中晦涩的代表,但词中充满香艳色彩的情事书写却并不妨碍读者理解吴文英大致想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意犹未尽的情事、曲折回旋的时空跳跃、主题叠现的笔致,共同展现了梦窗词的“空际转身”之妙,不独本首词为然,吴文英大部分作品均是以此种笔法,以细致周密的谋篇,将叙事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看似不合情理的突转,实际藏有词人句断意不断的独创精神,意脉不断,而又离合变幻,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言:“梦窗词之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仅不是‘不成片段’,而是每一片段与每一片段之间有着‘钩连锁接’之妙。”(《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9]180无论是词作的创作宗旨还是情感脉络,都是构成作品骨架。吴文英对词作主题的表达受社会环境与个人性格的影响,并不像其他词人那般直接,其抒情内结构具有深幽朦胧、难以琢磨的美感,这是梦窗词在抒情上的一大特点。
二、外结构——词境的紧密罗列
词心只是抒情美学的发端,它还必须和身外之境(景)融合为一才能达到抒情美学的终点:词境。[5]74词作的抒情主题确定后,作者还需要塑造一定的境界,使作品情感的表现符合词体温婉柔媚的抒情特质。将外在客观景物融入到作者主观情思的过程,就是作品中意境塑造的过程。吴文英在词境塑造方面喜好以个人丰富的想象,借梦境书写表达内心情思,意象的叠加、过于繁密的用典以及繁复的辞藻修饰,使得吴文英“在艺术上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虚构出许多离奇虚幻的审美境界。”[8]285
(一)意境塑造的层层关联
梦窗词的包裹型抒情结构首先表现在意境塑造的层层嵌套方面。梦窗作为南宋词坛以擅长“空际转身”笔法而闻名的词人,在一首作品中可以塑造出多个层层关联的词境,诚如邓乔彬先生所言:“梦窗词常常是看起来似离题旁涉,实际上四面盘旋,仍然紧扣主题。”[8]294梦窗词中的很多作品具有多重意境,这也是吴文英作品一个显著的个性特征,后人讥讽梦窗词“雕砌满眼”之弊病,很大程度源于词人在意境塑造方面的巨大跳跃与多次堆叠,这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繁琐复杂,细细品味却层层关联的意境塑造方式。
首先,从梦窗词的意境组合来看,吴文英喜欢借梦境塑造书写多种情感,梦窗词的这一特征早已成为学界对梦窗词研究关注的热点。唐圭璋先生认为:“南宋词学大家,稼轩、白石皆尚疏,惟梦窗尚密,三家分鼎词坛,信乎各有千古也。”[10]204即言梦窗词在辞藻、意境组合、意象使用方面喜好以多取胜的特点。词人在对梦境进行书写的同时,喜好从梦境出发,以丰富的想象力生发出与之相关的其他情境,借梦境隐喻过往经历,具有虚实相生的效果,这是吴文英虚实结合的抒情手段之一。吴文英在南宋词坛有“词中之商隐”的称号,即言词人在词作中情感表达具有如同李商隐般朦胧绮丽的特点,梦窗这种词体风格的形成与多种朦胧意境的繁复组合有着密切关系。吴振华先生指出,梦窗词中频繁出现以“梦”为主题的意境塑造,不仅梦的种类十分丰富,“梦的形态与运作过程更加变幻莫测”。[3]在梦窗词中,无论是“新梦”“旧梦”,还是“晓梦”“残梦”,每种梦境的描绘都是词人心境的折射。吴文英对“梦”意象的偏爱促使其整体词风呈现出奇幻缥缈的艺术个性,将这些各具千秋的梦境联系在一起,便形成了梦窗词在抒情上“美梦难成”的效果。
其次,从梦窗词意境脉络来看,吴文英喜好以上下映带、突接突转的写作手法,将各种多而杂的意境融汇在一首词中,同时,词人以个人细腻的柔情对细微之景进行深度刻画,其中蕴含词人隐含其中的“无限深情,无限怅惘”。[10]207如词人节日忆亡姬的《霜叶飞·重九》一词,以“断烟离绪”之无限伤情笼罩全篇,而后,在这样凄迷忧愁的意境下,进一步雕琢出亡姬在世时二人重阳节登高的歌舞之乐,这种快乐在“吊古”的伤逝之痛与“寒蝉”的悲凉之声中已经显现出的凄凉结局,词人在充满自我无聊、沉痛的身世之感与时代意绪的今情抒发之前,借对往昔凄凉情境的回忆直接将接下来“缘愁万缕”这样心灰意懒的情绪的渲染不断造势,从而更有助于将今情直接推到极致,词人往昔与亡姬重阳登高,今年自己独自一人未能登高,于是只能在对往日的回忆中抒发悲凉情绪,同时,结尾不忘憧憬“但约明年,翠微高处”,这种隐性时间穿插方式使作品时间线索清晰,表面上看,往日之落寞与今日之惆怅同属一种凄凉之境。往日的悲凉因故人的加入还有些许温情,而今词人却孤身一人,这种情绪配之以梦窗词绮丽婉转的辞藻,加深了作品飞扬的神韵。词人借外界环境的细微变化暗喻人事沧桑,这种景物与人事的变化具有内在外在一致性,体现了词人上下紧密映带的写作逻辑。
在层层关联、相互包裹的意境结构下,梦窗词显现出紧密而又不乏逻辑性的情感表达特点,加之吴文英心中郁结的恋情之思与家国之痛具有密丽幽深的情感特质,这就使得梦窗意境塑造更有助于千回百转的情绪抒发。
(二)典故引用的浑化无迹
梦窗词不乏用典。从抒情的角度看,典故的引用有助于作者情感表达;从叙事角度看,词是以抒情为主要内容的文体形式,事典的运用有助于节省作品叙事笔墨,最大限度保留作品抒情空间。典故的引用有助词人借他人酒杯浇一己之块垒。
吴文英喜好在词作中用典,但与其他词人不同的是,吴文英用典目的似乎并不是让读者更加清晰地领悟其内心所要抒发的真实情感,而是故意使个人情感经历更加模糊朦胧,读者若不能熟悉梦窗词中的用典,便会觉得梦窗词很难理解。晦涩难解的典故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梦窗词抒情意境的曲折性。如梦窗词中以用典繁复、难解著称的《高阳台·落梅》:
宫粉雕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上黄昏,月冷阑干。 寿阳空理愁鸾。问谁调玉髓,暗补香瘢。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离魂难倩招清些,梦缟衣、解佩溪边。最愁人,啼鸟清明,叶底青圆。
作品表面咏梅,但在咏梅的同时借多个与人相关的典故的引用兼及怀人之意,“金沙锁骨连环”化用美妇人——锁骨菩萨死葬传说暗含哀悼之意;“寿阳空埋愁鸾”“调玉髓”“补香瘢”“缟衣”“解珮”涉及寿阳公主梅花妆、三国吴孙和误伤邓夫人后治灭瘢痕、郑交甫遇江妃二女等典故。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此词典故引用极为频繁复杂,一首简单的咏梅词中涉及诸多与女性相关的典故,一方面是词人借这典故写梅花形态,另一方面,将梅花、梅树这样的客观外物赋予人的思想感情,其中隐喻对已故爱姬的怀念之情。这种在咏物词中借频繁用典暗喻多种幽微情绪的抒情方式,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斧凿痕迹,加之各个事典本身并无太大关联之处,很容易让不明典故和对词人生平不甚了解的读者产生“不成片段之感”。然而,这些看似不相关联、格局个性化的典故背后有一共性:即这些用典均以表现女性温婉柔媚、似梅花般明艳的特征,与梅花相关的典故大量运用到咏梅词中,在表现梅花特征的同时,也肩负了词人对梅花般已故恋人的怀念。恰如有评论者所言:“锁骨、寿阳、孤山、解珮诸事,在看似不相连属的字面深层,流动着脉络贯通的情感潜流,它们从不同的时空、层面,渲染了隐秘的情事和深藏的词旨。”[4]141这一评价即指出多条典故背后的关联之意。浑化无迹的典故引用增加了词境的曲折,深化了吴文英作词的迷离态度。
(三)语言风格的密丽深幽
梦窗不但炼字、炼句,而且都能和炼意相结合。[4]17典雅、华美的词作语言使梦窗词大有北宋清真词风,体现了宋词雅化的审美特点。梦窗词意境本身以繁复典雅著称,配之以密丽深幽的语言,词作的抒情结构便更加婉转含蓄。
吴文英作词,一直恪守“用字不可太露”的创作原则,沈乐府在《乐府指迷》中云:“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意味。”[2]277意在指出词人在词作中的炼字造句应以婉转回互章法结构来间接抒情。吴文英作词深谙此道,如《采桑子》:
水亭花上三更月,扇与人闲。弄影阑干。玉燕重抽陇坠簪。 心期偷卜新莲子,秋入眉山。翠破红残。半簟湘波生晓寒。[7]1621
此词以相思为主题,但在写法上,“作者用景物来渲染,用动作来刻画,但就是不肯直写主人公的内心”,[4]165这样一首颇带香艳色彩的小令词中,词人将大量篇幅来安排写景,营造出夜晚优雅静谧的气氛,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作者对抒情女主人公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刻画:水畔自照、整理妆容、借莲子占卜、占卜后愁容满面,一系列动作下来,尽管词人并未直接指出女子心中所愿究竟何事,但此时女主人公思念之人不得见的惆怅情绪却已呼之欲出。全词以景物描写开端,又以景物描写作结,在章法结构上首尾呼应,在语言上百转千回,密丽深幽,将所要抒发的情绪恰到好处地暗含于周遭的环境描写与女子的动作刻画中,生动形象的人物刻画与辞情优美的语言艺术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词境作为承载词体抒情外结构的部分,是承载作者情感的重要媒介,在对词境的处理上,景物描写与抒发情感相关的典故引用以及词人的语言风格都将对其形成深刻影响。吴文英作为一位个人情感经历丰富的文人,在南宋末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将个人对恋情的追忆之苦和对国家危亡政治局势所引发的黍离之悲,隐喻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个人主观情绪的意境当中,辅之以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段,构成了梦窗词在抒情外结构方面回环往复、层层关联的特点。
三、梦窗词抒情结构的审美内涵
吴文英“其词烹炼精湛,密丽幽邃;而大气盘旋,脉络井井;故能生动飞舞,异样出色。”[10]204梦窗词中表现出的唐圭璋先生笔下井然有序的脉络结构主要是通过词作中看似繁复、杂乱的空间转换与景物描写对抒情主题的聚合作用而产生的。尽管晦涩难解是梦窗词为后世公认的、典型的艺术个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吴文英作为一位在宋末词坛颇负盛名的词人,其作品在主题意蕴方面具有不冗不碎、神韵天然的审美风貌,正因如此,梦窗词尽管晦涩朦胧,但读者却不难从中管窥词人寄寓其中的沉痛家国之思与普世的爱情主题。
(一)沉痛家国之思下一唱三叹的深度无奈感
梦窗词中涉及到家国之思的作品尽管数量上不如恋情词丰富,但作为在南宋末期特殊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文人,梦窗词中这一主题的书写从侧面折射出报国无望的部分文人对国家残破局势的深沉感慨,其作品中隐含的沉痛的家国之思具有深沉悲慨的无奈感,梦窗词中的此类题材作品喜好借助外物进行含蓄的示意,在抒情结构上具有一唱三叹的结构特点。
词人想将隐晦情感的抒发寄于物,必然涉及多种外物描写手段。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价梦窗词:“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筋骨珊珊,洗脱凡艳。幽索处,则孤怀耿耿,别缔古欢”[2]3803吴文英作为一位未被正史记载,却颇有才名的南宋文人,无法像辛弃疾那般以充满战斗力的笔触寄托自己为国效力、收复失地的愿景,只能将沉痛的家国之思放在对外物的吟咏上。如《古香慢·赋沧浪亭看桂》一词,表面上是在咏沧浪亭的桂花,实际是借助拟人化的手法,将桂花放置在重阳节前衰瑟的意境中,表达“秋澹无光,残照谁主”般“濒于危亡,国事无人管的沉痛”;[4]177受危亡政治局势的影响,吴文英词作中面对家国之痛表现出的情感更多的是无法反击的无奈,很多时候词人在悲愤情绪无从抒发的情况下,往往不顾读者接受能力,而过度强调自己主观情绪的喷发,以时间、空间巨大的跳跃为依托,借词意、章法的快速转换表现自己因物兴悲之情。如《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下片,词人写到:“伤春不在歌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癯?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7]1312这几句词涉及的空间十分丰富,抒情主人公将个人愁绪寄托在“灯前”“雨外”“游船”“临流”“西湖底”“柳绵”“平芜”等多重物象之上,频繁的空间转换与时间跳跃下包蕴的是词人眼见之处皆是愁这样一种始终萦绕满篇的个人情绪,吴文英表面在伤春悲秋,实际上,撷取这些春天中衰败之景,“所象喻的正是当时黯淡衰落的国运”,[4]138吴文英借咏物之机,在词作不易为人察觉处寄托家国情怀,这不仅仅是词人单纯对国事的隐忧,更有个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极强的身世之感,加之梦窗词中以家国之思为主题的作品大都作于词人晚年,此时南宋王朝垂危已成定局,作为一名文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情绪始终裹挟着他的创作,使他无时无刻不在各类题材的作品中书写这种情绪,因而,他的作品笼罩着浓郁的家国之思和深度的无奈感。
也许是因为处于没落时代,而词人又有着曳裙王门的坎坷生涯,词中流溢着一种深沉而悠远的伤感之情。[11]890《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意无穷也。[12]106借词体这种内倾型文学表情达意,委婉含蓄是主要的风格特征,吴文英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将个人层出不穷的意绪隐含于词作中,有一唱三叹,别具一格之妙。
(二)普世情爱主题内虚处传神的高度概括性
词作中的情爱主题具有普世的情感价值。尽管梦窗词中与其恋情相关的作品大多晦涩难解,难以找到具体爱情实指,但吴文英对昔日恋人浓郁的思念之情的表达却总能激起读者内心强烈的认同,产生心理共鸣。梦窗词中以情爱为主题的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柔情与细腻,它表现出吴文英对具有普世意义的情爱主题的高度概括性,这也是尽管梦窗词晦涩凝昧、充满雕砌色彩却依旧深受后世读者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词人通过个人对情爱这一主题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主观描写,使恋爱生活中情侣的各类心态萦绕在作品之中,即使读者对梦窗词中很多典故意象摸不着头脑,也能从片段的细节描写中大致领悟作者所要表现的细腻情感。
首先,梦窗词中以怀人为主题的恋情词往往喜好以悲欢更迭的前后对比,以渐次凝重的笔势引出当下之别恨。恋情之所以美好,在于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时相处足够温馨,梦窗与一姬一妾的具体情事尽管无从考证,但从其词作中的片段描写中,读者不难拼凑出这两段情事所包含的无限深情。如《望江南》:
三月暮,花落更情浓。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 恹恹醉,尽日小帘栊。宿雁夜归银烛外,啼莺声在绿阴中。无处觅残红。[7]1618
上片追忆往昔暮春三月与情人相见的场面,表面写景,无情事具体细节,但词人在静谧环境下通过对“人去”“马停”“画船空”这样场景的刻画,加之“情更浓”三字的点醒,暗示此时相爱的两人正在幽会,这是一幅极富温情而又充满浪漫气息的画面。下片词人笔锋陡转,原来,他年的欢情与浪漫不过是为当今落寞作铺垫,在恹恹的情绪下,词人流露出“事同春梦不多时,人似飞鸿无觅处”[4]167的寂寞心境,昔年欢愉与今昔落寞的强烈对比下,折射出词人内心对昔日恋人哀婉绵邈的怀念之情。
其次,吴文英写恋情,还喜欢以画面的补充对比暗喻抒情主人公与恋人两下不得团聚的遗憾,词人不喜欢直接抒情,却以恋爱双方同样千回百转的相思之情产生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新雁过妆楼》(梦醒芙蓉)中,既有词人自己“夜阑心事,灯外败壁哀蛩”的思人之苦,也有料想被思念对象“行云远,料淡蛾人在,秋香月中”这样孤单寂寞的生活处境,词人的悲伤与思念不仅仅是自己一人所感,对方也同样承受着与词人相同的凄凉与困苦,吴文英在词作中故意运用这样的画面补偿,遥想对方与自己情感两相呼应,在抒情结构上具有互为补充、互为衬托的作用。尽管吴文英在很多作品中故意将情事隐去,或是写得扑朔迷离,但其想要表达的分离双共同哀怨的情感却很容易使读者感同身受,具有摄人心魄的审美力量。
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评论吴词得失时有语:“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2]278这是对梦窗作词得失比较公允的评价。吴文英上承周邦彦,而后以飞扬的深思与深邃的艺术创造力在词体审美风貌上另辟蹊径,以极强的跳跃性思维与才力将绮丽繁复的空间堆叠罗列起来,形成梦窗词迥异于前人的艺术风貌。[13]梦窗写恋情,之所以在事件指代不明的情况下仍旧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在于其善于通过对恋人心理的描绘,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吴文英写恋情词这种虚处传神的抒情方式在普世爱情母题下具有高度概括性。
综上所述,受时代背景与个人坎坷恋情经历的影响,吴文英在梦窗词中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裹挟着词作的内外结构。内结构词心的深幽朦胧与外结构词境的紧密罗列共同构成梦窗词在抒情方面秾丽而不失典雅的特色,在这一抒情结构下,梦窗词中以家国之思与离情别恨为主题的作品对抒情主题具有充分的聚合作用,从而显得脉络井井,具有独特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