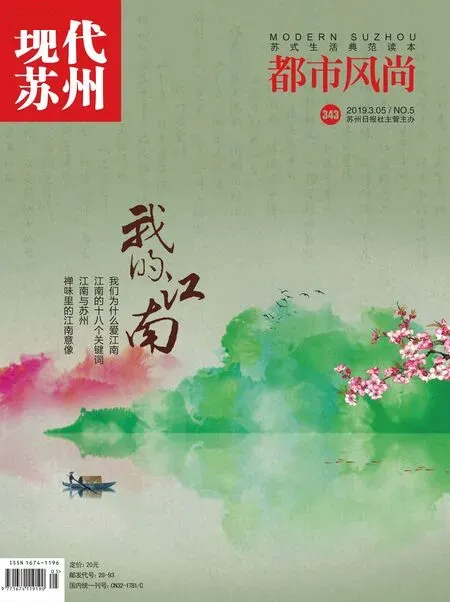江南好
谁都可以说江南,但惟有苏州能把江南说的最动听最好。
如果说声音是来自天地万类的话,苏州的声音比其他地方总是多那么一点点。
别处有鸟声,苏州有山花野鸟之音;别处有雨声,苏州有雨打芭蕉之音;别处有风声,苏州有竹风度曲之音。而比起其他地方,更令人艳羡的是,苏州的声音里有唐朝的音,宋朝的音,甚至有周朝的音,有杜甫当时的声音,有李白当时的声音,也有沈三白当时的声音。
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苏州人拥有八个音来述说江南的美好。更何况,每个字的音,苏州人还有能力将其分为头腹尾,像品尝一条上好刀鱼一样将它涵咏得细细微微,意态悠长。
刀鱼是江海派出的刺客。真正的苏州吃货,会在上桌前,将其脊骨完整剔出,做一道脆炸龙骨,香酥可口。一条龙骨,节节贯穿,刀鱼便能像一把匕首般直穿江涛暗旋之中。苏州的声音,世人都听到的是水性的千回百转,骨子里却是有刺客精神的,明明晃晃,顺畅爽利,浪里白条,收字归韵都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而且吴地之音里有着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浊声。苏州音并不单单是粉嫩的,而是含蓄的,含蓄里有收有放,收中还有放,那丹田发出的浊声,勾天雷动地火,那是中华的元气在苏州声音里面的流转暗藏。
江南好,是因为江南有华夏的心气流转。
有声乃有气,有气即有意,有意便有心。而要体味这一脉气息,初唐于苏州任职的刘禹锡是行家。他调素琴,阅金经,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为什么要没有丝竹和案牍,因为丝竹乱心,案牍扰形。宫商角徵羽中,丝为徵音,能通心,案牍入脑,思虑过多,外侵身形。没有丝竹喧杂的环境,放下思考的脑筋,才能抚琴诵经。为何我觉得是吟诵呢,因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经典需要直接用身体体悟。丝竹毕竟还隔了一层,古琴需调,金经亦然,需用心来调,身心合一的,才能体验气脉流转精微之情境啊。
如果一个人,每天能有这样精细的感觉,那就是自觉之人,也一定能觉察出江南的静好了。为什么张爱玲能写出平常生活里的不平常,就是这奇女子能静,能放松了体会,体会那些日常细节里的戏剧滋味。打个比方,吃螃蟹,唯有苏州人懂得品一品蟹爪尖里的肉,那叫“蟹人参”,韧且鲜。也只有苏州人明白绿豆芽里嵌肉糜的恰好,雅中俗。这和一个人富贵贫穷不搭界,和懂不懂体味生活有关。或者说,体味生活也是一种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懂得什么层次的生活。
一支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唱这支曲子的苏州人,一定是缓板而歌,放松自己体会渔夫之乐和吴地音韵的变化,其实就是体会天地之气的变化啊。这一支曲子,有三层意思。一是音韵的变化,二是气息的变化,三是阴阳的变化。渔夫多快乐啊,在天地里,乐而忘返。音韵也美,用苏州话来读就明白了,每一字都是一首歌。平上去入,平,是地球的公转自转,也像一颗子弹,但却有着旋转的弹道;上,是黄宾虹笔下一根S线;去,是一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的反弹;入,就像丢入湖面激起层层涟漪的一粒鹅卵石子。入声,是出口即停的,可是体味久了便不觉得它收藏的短促了,塞、白、箬、笠、绿、不,这些字,就像一个颤巍巍的水泡,一条清溪里飘过的穿条鱼,一片含情飘落的桃花,在气息里发出一团柔软而又明白的光芒。
能察觉江南好的人,一定是懂得体会气息的人。天地有元气,洪荒时混沌一气,和孩子一样,脐带剪了,才有一呼一吸。气,是物质,也是虚无,虚无不是真无,当然也不是假无,那是在有无之间,恍恍惚惚。气,是一个讲不清,写不明的江南话题,就和江南的好一样,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但是身在江南,我们无处不能感受到它。
江南好,能静了,才知江南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