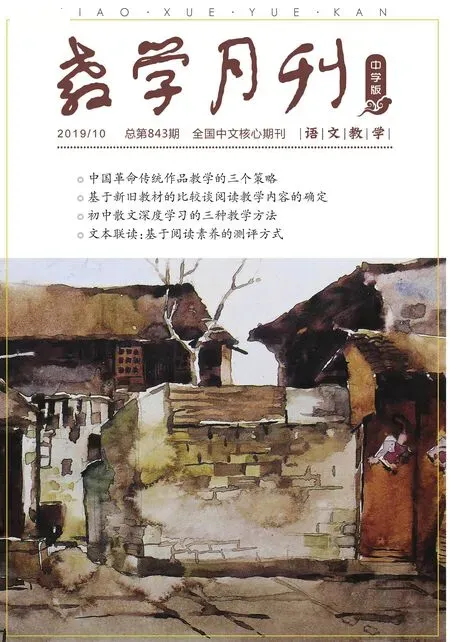“说书人”的文化隐喻
梁 娟(安吉县高级中学,浙江安吉313300)
《说书人》是现代作家师陀于1942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入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在果园小城这个虚构的空间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种建筑交相辉映,共同赋予这个社会空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就如鲁迅先生营造的鲁镇,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说书人的故事很简单,三次出场即为一生,没有背景交代,也没有性格摹刻,但是细品小城环境下“说书人”的遭际,小说中的每一笔似乎都是人与城的相互喻说,都在表达着作者的感性情怀、理性态度和文化诉求。
一、说书人的穷途末路隐喻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
“说书”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形式之一,是乡土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在没有义务教育、知识不普及、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它承担着丰富人们娱乐生活、引导民众向善向美、弘扬忠义、传道教化等文化功能,尤其受到乡土社会底层民众的欢迎。正因如此,说书人大多能识文断字,且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文学功底,也经常被称作“先生”,先生者,“为人明知强记,博览图籍”。
小说中的说书人:“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他说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让“我们全被迷住了”。而“长衫”是那时先生的行头,穿长衫的人自然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是,凭此糊口的说书人又历来是“人家看不起的”,“连家谱都不能上的”,他从事的“无疑是一种贱业”。说书人实实在在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小说借一件长衫说出了人物的命运变迁。
于是,在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中,他从“穿一件蓝布长衫”到“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最后“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伴随着长衫,破损的,是说书人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脸很黄很瘦”“时常咳嗽”到“更黄更瘦”“咳嗽,并且吐血”,最后“时常发病,不能按时开书”。他的生活被日渐挤压,逐步困窘,尽管身着长衫,但生命的存在方式却已近于一个乞丐了。“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这样的际遇,似曾相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和说书人一样都是可以随意被人欺侮的。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家人,无人关心,无人祭奠,都成为这个小城的“多余人”。
但长衫是一种文化符号,穿着长衫的说书人并不多余,他曾经带给小城民众快乐,让“我”的童年无比幸福。说书人的生命价值正是小城文化价值的体现,这位有着古典文化与评书艺术文化标识的人的死亡,无疑是小城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悲哀。
这种文化没落还体现在说书场所的变化上。城隍庙算是小城民众的多功能活动集区,是承载小城文化的最有活力的空间场所。在最后一次来到小城听“说书”时,“我”发现“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俱乐部”是个现代化的名字,这意味着果园也城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迫接受外来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冲击。但是,外来文明并未给小城民众的精神带来现代性。在丢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后,没有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文明品格,那么民众在外力冲击下的精神贫瘠一望可知。“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师陀的立意是“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那么小城民众的特质正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众的民族特性。果园城繁华不再,小城民众思想荒芜,传统文化衰落,现代化没有带来真正的文明,作者的留恋与不满、反思与批判都隐藏在对“说书人”长衫的描述中了,“他的破长衫……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
这种反思是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作者弱化了说书人故事的背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经济破败物价飞涨等),而突出表现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的悲剧命运。联系当今社会,身处科技革命、文化冲击而陷入迷茫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再阅读价值。
二、侠义精神的远去隐喻民族性格的怯懦和作者对民族生存的焦虑
小城里的听书人基本上都是小城中的底层老百姓,这从说书场所在城隍庙以及说书人微薄的报酬可以看出。同时代有名的江南书场,倒也有有权有势的书迷光顾,或者请那些著名的说书人到家里去说书。不过,“说书”毕竟是民间技艺,说书人是“混江湖的”,不入流,这种形式就成了适合中国广大底层民众的最具代表的消闲方式。消闲方式表面上只是一段时间内进行的一项活动,实质上还包含着一种心境,这种心境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习俗、常识和文化。所以果园小城中人们的某些消闲方式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姿态,从中也就可以窥探人们的现实境遇和生存状态。
小城的人们喜欢听书,当说书人“从傍晚直说到天黑”,“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听客们忘记了时间,沉醉于说书人营造的奇幻世界。虽然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构的,但是说书人被“特许”“撒谎”。因为现世太苦了,挣扎其中,难以自救,只好用短暂的精神愉悦去稀释现实的痛苦,摆脱重负寻找片刻的自由快乐,获得了这样的心理安慰,似乎才可以支撑着大家继续活下去。
正像说书人死去后,“我”感叹“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小城的人们确实向往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希望现实中有“刘唐”“武松”杀贪官惩恶吏劫富济贫,却缺乏自救的勇气。侠义精神并没有带来启迪,却让人们在一次次的自我麻醉中,渐趋怯弱、消沉、麻木,成为灵魂空虚的盲从和庸众,成为“铁屋中沉睡的人”,呈现出一种毫无价值的状态。而人性中无法被启蒙的怯懦,无疑就是那个时代整个国民的性格特征。
听“说书”,是一种娱乐,而娱乐永远只能是娱乐,并不能发生精神启蒙的奇迹。
说书人死了,这个事件隐喻着侠义精神的彻底死亡,因为宣讲这种精神的人已经入土,但他的死并没有引起众人的重视或同情。虽然也有老听客多给钱,但大家更多关心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听他说书取乐。两个杠手(或许也是曾被感动过的听客)回答“我”的问题时表现出令人心悸的平静和淡漠,甚至“嘲弄”地说:“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当然,这里的“嘲弄”可能并非贬义的“嘲讽捉弄”之意,此情此景,更有可能是一种淡然的“调侃”(调侃说书人和他自己)——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兴许,死了才是解脱吧。死亡是一种结束,令读者回味的是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结束后,果园城将会如何?更值得回味的是,人们对这种结束的冷漠态度,让人怀疑这种文化有没有发生过价值和意义。
在说书人没死前,一个“卖汤的”就占据了书场(也就一张桌子大小),这可以理解为物质享受战胜了精神追求。要知道,精神、自由、情感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这些都是生命领域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地理或者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神空间的被挤压被消亡。蒂里希说:“人之存在的焦虑源于‘无空间性’,空间性之占领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而空间性之丧失意味着存在之丧失。”[1]听客们越来越少,离开小城谋生的越来越多,孤独的说书人带着自己的“精神天地”死去,小城人们的生存焦虑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焦虑。作者没有给说书人具体的名字,“无名”,无法命名的方式,赋予小城一层模糊的屏障,但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清晰——乡土中国整个民族的众生的生存景象。
关注人类生存的作品,大多书写各种生活样式人物生存的焦虑。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记录呼兰小城普通人生命的琐碎卑微,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描写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挣扎与沉沦。师陀曾在《我的风格》一文中说:“我只是刻意描写社会和人。”“刻意”的表现,也正表明了作者对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焦虑和悲悯。
三、说书人的命运隐喻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最先感知小城文化、社会经济的衰败并因此而受到伤害的就是文化人。说书人并非没有抗争,他始终穿着长衫,哪怕破旧依然标识着与“短衣帮”的不同;虽然讨要说书钱时近乎乞丐的口吻,但他终究没有沦落成一个乞丐。可是,他讲英雄人物,传播侠义精神,最终也只是在挣扎中陷于自我安慰的桎梏。就如穿插于《果园城记》中的知识分子“我”,既是马叔敖,也是孟安卿,更是师陀们。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能够看到民族性格的怯懦,渴望寻找疗救的良药,但是在传统与现代共存、新与旧互渗、中西结合、城乡融合的社会磨压中,失去了精神、自由、情感的空间,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焦虑”,只好不停地寻找可以让精神上岸的地方。
师陀曾说:“人们永远有个不能满足的欲望,因此就常年地从那里到这里,从这里又到另一个地方。”[2]因中原小城的荒凉,师陀离开故乡到北京,北京虽是厚重的文化场,但它的懒散沉闷又让他来到上海,可是上海的现代文明更让他浮躁,沦陷区的生活孤独落寞,最后只能在孤岛中构筑“故园”。当然“我”回到“果园城”,发现它并非故园,师陀也一样,归来意味着再离去,永远“生活在别处”。这种“离开—归来—再离开”的写作方式和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样,都把近代知识分子的游子情怀和故园意识写尽写透了。
说书人最后死去了,这似乎预示着知识分子的结局。“我在旁边看着,毫不动弹地站着。”这种无能为力之感让人伤感,“我”最终选择逃离小城,师陀也再寻找不到精神家园了。在这里作者强力表达着一种忧患意识:个人和民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同时代很多优秀作家也在不停地追索、探问。不过,就像离开故乡湘西来到北平的沈从文,离开东北辗转各地的萧红,师陀在身体远离故乡后,心灵上却更加靠近故园,也更能理性地看待和审视故园。师陀“感受着新旧时代夹缝的无根和乡土式微的悲情,文化焦虑与身世之感契合,孤独和悲凉的情绪不断积累,并指向社会、文化和生命本体意义的索解,具有了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1]。
当然,作家的无力感还来源于人类共同拥有的悲剧性命运——时间流逝中一切皆会消亡。小说结尾处说:“凡是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前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是啊,时间让美好的生命凋零,让文化消亡,让小城陷入死寂,时间可以让我们忘却痛苦,但也终将带走我们的一切欢愉。最痛苦的是,在时间面前,没有什么不能改变,但你无法逃遁,更无法停留,甚至不能证明你曾经存在过。这一点加深了小说人物的悲剧性,也使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广。
由此看来,师陀是把小城作为主人公来书写的,“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而“说书人”就成了这个空间中最普通也最独特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对说书人的文化隐喻的探究中,我们感受到了师陀在深刻的理性反思与批判中饱含的悲悯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