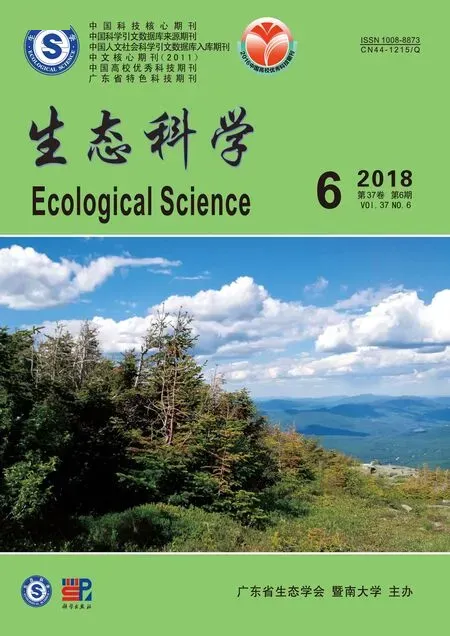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周静, 万荣荣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周静1,2, 万荣荣1,*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08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 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对区域乃至全球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进行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对湿地保护管理、规划利用以及湿地治理有重要科学意义。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关键在于评价方法选取与指标体系构建。文章在介绍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内涵及健康评价发展过程的基础上, 重点总结回顾了国内外几种常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方法, 归纳、剖析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 并对目前湿地生态健康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与展望, 包括健康标准、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多时空尺度的综合以及湿地健康评价的应用等问题。
湿地; 生态系统; 健康评价; 指标; 阈值
1 前言
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 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1], 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自然综合体, 成为各种能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换场所。湿地因其具有强大的水文循环功能、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 以及丰富的资源潜力, 被誉为“地球之肾”[2]。湿地的特殊性, 决定了湿地生态系统容易遭到干扰与破坏, 且难恢复, 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对区域乃至全球生态平衡, 以及人类健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 世界各地湿地生态系统健康面临严重威胁, 各国高度重视湿地保护与健康研究。近十几年来, 美国环保署(US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对全国湿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健康诊断和评价, 基于不同尺度, 形成了3个层次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3]。1946年, 英国成立野生鸟类和湿地基金会(The Wildfowl & Wetlands Trust, WWT)。2000年, 欧盟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WFD)实施, 为湿地等水生态系统的评价与恢复提供指导框架, 该指令提出了基于植物群、底栖无脊椎动物、鱼类等生物要素以及水文形态、物理化学等因素的指标体系[4]。澳大利亚于1997年颁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湿地政策》(The Wetlands Policy of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湿地保护与管理[5]。
上个世纪90年代生态系统健康成为区域环境管理的一个新目标和新方法[6],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受到了许多组织和学者重视, 已成为当前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的核心内容[7]。其中, 评价方法的研究已成为热点, 其科学性对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有深刻的影响。同时,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研究也面临挑战, 关于评价的方法选择、指标构建以及健康标准、评价尺度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二十多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湿地健康评价的方法、体系展开了许多研究。本文在介绍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内涵及评价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了国内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方法及特征, 最后对今后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2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
“健康”原是医学上的概念, 被定义为“无疾病, 或没有生理机能失调”。苏格兰医学家、地质学家James Hutton于1788年首次提出健康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认为地球是一个大的能够自身维持的有机体。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最早可以在Aldo Leopold[8]的著作中发现, Leopold首先定义了“土地健康”, 认为健康的土地是被人类占领而没有使其功能受到破坏的状况。随后, 国内外学者Costanza[9]、Schaffer[10]和Rapport[11–12]等从不同学科视角以及功能、结构等不同角度定义了生态系统健康, 并从最初生态学的角度考虑——以Costanza[9]的定义为代表, 倾向于自然生态方面, 认为生态系统健康就是没有疾病, 即生态系统的组织未受到损害或减弱, 并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加入人类健康因素——认为生态系统健康依赖于社会系统的判断, 还应考虑人类福利要求, 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逐渐得到发展, 以Rapport等[12–13]的定义最为典型。回顾历来的研究, 许多学者通常用健康的特性或测量标准来诠释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 把稳定性、恢复力和抵抗力等作为健康的重要特性。同时, 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人们认识及研究目的的差异性, 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远未统一。
湿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系统, 因此更难给出一个精确明晰的关于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定义。目前, 认为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的定义和崔保山的定义表述较为完整[14–15]。前者表述为: 湿地生态系统稳定且可持续发展、无疾病反应, 即指生态系统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并维持其组织及自主性, 在外界胁迫下容易恢复。此定义从湿地生态系统内部定义健康的概念, 但没有将人类因素考虑在内。后者认为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既能够提供特殊功能, 也具有维持自身有机组织, 从不良环境胁迫自行恢复的能力, 即指湿地生态系统在一定的时空尺度内对各种扰动能保持着弹性和稳定性。该定义包含了湿地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 反映了湿地健康与社会经济系统间的联系, 是当前较为完整的定义。
3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概述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人类面临着合理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的问题, 因此科学家针对生态系统不健康的现实, 展开人类活动与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等问题的整合研究, 确定生态系统在胁迫条件下产生不健康的症状和机理, 探讨其恢复对策, 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提供参考。生态系统健康及评价研究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13, 16]。所以,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全面研究生态系统在胁迫下的特征,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规律, 进行系统诊断, 找出生态系统退化或不健康的预警指标, 从而为湿地管理提供目标依据, 以便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湿地生态环境[17–18]。Aldo Leopold[8]第一个进行了“土地疾病”症状的分析, 包括侵蚀、肥力丧失、水文反常、某些物种非经常性的数量爆发或莫名其妙的局域性灭绝、农林产品质量的退化等。对于湿地生态系统, 其偏离正常边界、功能紊乱的症状有水质变差、水文反常、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Rapport[13]表示, 评价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可以从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等三个主要特征来定义。许多学者基于这一思想通过分析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压力、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改变、生态系统服务丧失与社会经济指标反应间的联系, 开展生态系统健康评价。Karr[19]认为生态系统的退化是人类过度干扰造成的, 生态系统健康就是生态完整性(Ecological Integrity), 并率先在对河流的评价中建立使用了生物完整性指标(IBI), 随后广泛应用到了水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实践中。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实际上是描述湿地的现状与管理目标所设定的理想状态间的差异程度[17], 也就是说需要确定一个湿地生态遭到破坏的最低阈值, 而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确定出衡量偏离健康状态程度的合理指标及测度方法[18]。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主要包括:湿地健康概念的理论问题、诊断指标、评价方法以及研究尺度等问题[20–21], 而目前的侧重已从理论上的概念争议转移到实践中定量评价方法的探讨。因此, 评价方法是湿地健康评价研究最具前景的研究方向: 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是客观评价的基础, 对于湿地这一复杂系统, 正确且客观地进行健康评价面临很大挑战, 在评价方法方面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尚待解决, 因而极具研究前景。
4 国内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概述及比较分析
作为湿地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近年来发展迅速, 国内外学者已运用多种方法对此进行了探索, 并随着3S技术的开发应用、统计学方法的完善进步, 许多新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 但也由于各种方法出发点不同, 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适用对象存在差异, 因此各有优缺点。基于这种现状, 本文对目前常用评价方法进行分类, 可归纳概括为两大类: 生物法和指标体系法。
4.1 生物法
鉴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我们经常通过研究单个物种或指示类群来反应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22]。首先确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特有物种、濒危物种或环境敏感物种, 然后采用适宜方法测量其数量、生物量、生产力、结构功能指标及一些生理生态指标, 进而描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23]。一般来说, 在一些自然生态系统中指示物种法比较适用, 利用这种方法对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的工作已有很多。硅藻、海草、鸟类、鱼类以及底栖无脊椎动物等被作为评价湿地健康程度的可行指标[24]。Montefalcone等[25]利用海草建立了3类综合指标来评价滨海湿地的健康程度。郑耀辉等[26]指出海蛙作为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中唯一的两栖动物, 开展其环境指示功能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总体来说, 在国内指示物种法应用较少, 但由于其比较容易测度、花费低等优势, 这种方法在在湿地健康评价中有很广泛的应用。但它也存在很明显的缺陷: 筛选标准不明确, 有些采用了不合适的类群[27–28]。另外, 关于指示物种的减少是否能全面反映生态系统的变化趋势仍存在争议。Boulton[29]发现指示物种的变化与整个生态系统功能、性质的变化相关性很小, 而且指示物种法不考虑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等因素, 难以对湿地健康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4.1.2 生物完整性指数法
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概念最先由Karr[30]在1981年提出, 用鱼类来评价河流的质量特点, 随后, 美国学者将其推广到湿地健康评价中。IBI方法的实施过程: 在对待评价区湿地类型进行划分的基础上, 开展野外调查收集区域内土地利用和栖息地信息, 建立人类干扰梯度; 然后, 筛选并确定生物类群及各类生物属性, 对多数生物种类而言, 一般采用8—12个对人类干扰敏感的生物属性来构建多测度指标[3]; 最后, 根据一定规则进行打分, 得到该湿地的IBI值。在北美大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中, 研究人员每年对1500个监测样点的植物、鱼类、鸟类、两栖类和底栖无脊椎动物五大生物类群以及水体环境展开野外调查、数据采集, 构建其生物完整性指数。项目组依据IBI指数的评价结果形成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生态系统评价报告, 美国环境保护局据此进行大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管理与保护。例如, 多年来监测及IBI数据分析显示, 大湖周围农业污染导致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下降, 该研究结果提示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业污水排放等的管控[31]。另外, 有研究显示芦苇在许多地区有持续扩张趋势, 对大湖湿地的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 采取喷洒除草剂、火烧、刈割等措施控制芦苇的蔓延[32]。因此, 基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IBI方法, 对于理解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建立生态安全预警起到重要作用。除北美大湖, 世界上许多湖泊湿地已开展了生物多样性监测, 包括加拿大, 欧洲国家。Petesse等[33]建立了亚马逊河泛滥平原区湖泊湿地的生物完整性指数, 并进行健康评价, 研究发现指标得分有显著的季节性差异, 与亚马逊河的洪水周期相吻合, 且这种方法能有效区分参照湖泊与受损湖泊。Breine等[34]基于鱼类构建IBI, 参考生态标准和统计分析对挑选的9个指标进行打分进而评价佛兰德斯上游河流湿地的健康状态, 结果显示能很好地区分采样点受干扰程度, 符合WFD提出的标准。我国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还处于探索和起步发展阶段, IBI法在国内应用较少。
生物完整性指数法相对其他方法劳动强度较大, 需实地采样调查, 故适用于小尺度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该方法能提供一种直接测量水生植物和动物的方法, 从而有效地确定胁迫反应的阈值, 有助于相关部门指定管理目标与决策[19]。
4.2 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 也称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通过选取能够表示生态系统主要特征的指标, 并确定其在生态系统健康中的权重系数, 进行综合评价来反映湿地的健康程度。相比于物种指示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涉及多领域、多学科, 考虑了生态、景观、社会经济等因素, 因此更综合全面, 在国内应用较多。但也存在指标选取重复, 权重确定过程中主观性强等问题, 评价方法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4.2.1 评价模型(指标体系)
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是湿地评价的基础。随着对生态系统以及湿地科学的深入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诊断指标由最初集中在生物、化学指标上(水、沉积物和有机物的化学组成, 物种组成和多样性, 生态系统生物量和生产率等), 逐渐加入了物理指标、压力指标, 并将社会经济因素考虑在内, 使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不断完善[15]。
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 会根据不同类型的湿地生态系统(湖泊、河流、沼泽以及人工湿地等)选取不同评价指标[35]。由于环境背景和研究目的的差异, 指标体系将无法得到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 而且在评价过程中, 对不同指标分别评价是很繁杂困难的工作, 因此需要构建整体的评价模型, 将湿地类型所具有的共性提取出来进行指标的确定。Friend和Rapport[36]提出PSR模型, 以因果关系为基础, 考虑压力、状态、响应3方面,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指标体系框架。各学者从自身研究出发对PSR模型进行调整, 得到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驱动力-状态-响应(DSR)模型等[37]。基于Costanza健康指数的活力-组织力-恢复力(VOR)模型也被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所认可。随后, 各国进行指标体系框架的积极探索,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的学者考虑环境背景、环境变化趋势以及社会经济3个方面建立了流域健康诊断指标体系, 取得较好成果[38–39]; 国内学者崔保山和杨志峰[35], 从生态特征、功能整合性、社会政治环境三方面构建了评价模型; 由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从水环境、土壤、生物、景观、以及社会5个方面进行考虑评估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40]。
此外,也可开展乡镇级别的幼儿教师培训,让教师们充分了解幼儿一日活动的基本理念及详细规则。培训中可以就某些集中问题进行分组讨论,例如幼儿的晨间锻炼运动有哪些具体的要求,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教师应该做什么工作,具体怎么执行等。在讨论的基础上,让教师们撰写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如何才能够将幼儿一日保教活动执行得更好,真正地理解并做到幼儿教师规范细则。
4.2.2 健康标准
为合理地定量评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需要确定构建指标的阈值范围。已有的研究在健康标准的分级上仍存在许多争议。针对不同的指标体系, 确定合适的指标阈值对健康评价结果有很重要的影响。一般地, 通过搜集相关历史背景资料, 参考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和国内外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经验判断来制定评价标准[41–42]。大部分研究学者将指标分级标准划为很健康、健康、亚健康、不健康和病态等5个等级。
4.2.3 评价方法
归纳目前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常用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如表1。
多指标综合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评价的结果是多种因素(评价对象、评价目标、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组合所决定的。传统评价方法对此缺乏理性标准, 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43], 同时, 可能出现使用不同评价方法得到评价结论差异较大的现象。基于这种现状, 利用综合集成的思想,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加以改造并结合得到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成为了当今评价领域及湿地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在面对复杂的评价系统, 且决策目标具有模糊性、难量化等特点时, 将一般综合评价方法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 引入模糊数学的隶属度和灰色系统理论的灰度概念可达到更好的效果。例如, 朱卫红等[44]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图们江下游湿地健康进行评价, 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此外, 一般评价方法与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的集成, 以及模糊数学与人工神经网络的结合已经得到较好地发展和运用。
5 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势
5.1 健康标准的问题
目前, 关于生态系统的健康标准或参考状态仍存在争议: 一些学者提出未经人类干扰的原始状态, 也有学者认为是演替的顶级状态, 还有学者提出生命诞生前的热力学平衡状态, 但这些将某一特定状态作为健康标准的看法均缺乏理论依据, 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65]。根据生态系统的“自然”程度或者说受干扰程度来判定生态系统健康是否科学?简单来考虑: 如果以一种合理、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生态系统, 新的生态系统是否一样可以保持健康?说到底生态系统的健康标准是一个人类标准。其次,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具有模糊性, 涉及到生态系统、景观、流域等多种尺度的湿地健康。不同尺度下, 其状态特征、表现行为存在差异, 在小尺度上常表现出非平衡特征或“瞬变态特征”, 但在更大尺度上则可能表现为极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66]。因此, 生态系统健康标准、评价指标的确定是否需要考虑健康的时空差异性。

表1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常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比较与汇总
5.2 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问题
综合评价是运用各种数学方法对具有多属性体系结构的对象系统进行整体性、全局性的评价, 即通过对多个指标信息的赋值, 得到其优劣排序的一种评价方法[43, 67]。随着数理统计等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越来越多。但由于评价方法机理各异, 适用范围不同, 在面对不同类型、不同环境背景的湿地生态系统时, 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准则去选择评价方法也是当前湿地健康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5.3 时空尺度及差异性问题
我国目前只有少数湿地开展了相关监测工作, 现有监测体系的分布和代表性尚不能满足区域尺度上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需要,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多局限在单一湿地上, 缺乏在区域/景观水平上对某一类型的湿地进行大范围、全面的评价[3]。而在EPA的组织下, 美国已开展了大、中尺度的湿地健康评价研究工作, 有学者利用大型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的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了明尼苏达州的100多个低洼湿地[68], 其评价结果对湿地监测工作和湿地管理工作有实际指导意义。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仅关注某个单一尺度, 可能漏掉来自其他尺度生态、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有关信息, 而且如果采用的尺度显著大于或小于某些因素的特征尺度, 很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5.4 未来发展趋势
针对上述问题,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未来的研究可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受到自身演替、自然干扰及社会价值变化等的制约, 即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存在差异。因此在确定参考状态、健康标准或划分健康等级时, 要用异质性理论和发展的观点对评价指标的安全阈值或健康状态等级进行辨识和划分。同时, 不能过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自然程度”, 或拘泥于理想状态, 而应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和更新能力来把握湿地的健康, 预测湿地的未来趋势。其次, 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时, 重点考虑对评价结果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控制指标, 实现少量指标或单一指标的健康风险预警, 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的未来趋势。
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时, 移植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 不断引入新的评价方法是有效开展今后评价工作的基础。另外, 借助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 对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集成、组合研究, 将有利于消除单一方法产生的误差, 增强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使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具有智能性、交互性和通用性。
在多尺度上开展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多尺度评估使得我们可以根据较小尺度的研究结果对较大尺度上得出的结论进行独立验证, 并在较大尺度上为较小尺度的研究结果建立一种参照背景。尺度的推绎或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叠加或线性还原, 因此, 不同尺度(生态系统和景观尺度)的结合问题是未来尺度研究的核心与挑战。其次, 完善我国湿地监测工作, 在湿地监测采用的指标体系、野外数据的采集方法以及数据的分析与管理等方面做到科学规范、可操作性较强, 同时在实践中对监测方案的各个环节不断优化, 从而建立成熟的区域甚至国家尺度的湿地监测体系。
[1] 吕宪国, 刘红玉.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2] 邱彭华, 徐颂军. 人工次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以广州南沙区万顷沙湿地为例[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
[3] 陈展, 尚鹤, 姚斌. 美国湿地健康评价方法[J]. 生态学报, 2009, 29(9): 5015–5022.
[4] ORTEGA M, VELASCO J, MILLAN A, et al. An ecological integrity index for littoral wetlands in agricultural catchments of semiarid mediterranean regions[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33(3): 412–430.
[5] 孙丽君, 杨可书, 周烨, 等. 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浅谈[J]. 中国经贸, 2011(14): 106–107.
[6] COSTANZA R, NORTON B G, HASKELL B D. Ecosystem health: new goal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M].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1992.
[7] 傅伯杰, 刘世梁, 马克明. 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内容与方法[J]. 生态学报, 2001, 21(11): 1885–1892.
[8] FLADER S L, CALLICOTT J B.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9] COSTANZA R. Towar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ecosystem health[J]. Ecosystem health: New goal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2(14): 239–256.
[10] SCHAEFFER D J, HERRICKS E E, KERSTER H W. Ecosystem health: I. Measuring ecosystem health[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88, 12(4): 445–455.
[11] RAPPORT D J. What Constitutes Ecosystem Health?[J].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 Medicine, 1989, 33(1): 120–132.
[12] RAPPORT D J, WHITFORD W G. How ecosystems respond to stress: common properties of arid and aquatic systems[J]. BioScience, 1999, 49(3): 193–203.
[13] RAPPORT D J, COSTANZA R, MCMICHAEL A. Assessing ecosystem health[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1998, 13(10): 397–402.
[14] 李文华. 生态学研究回顾与展望[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4.
[15] 崔保山, 杨志峰.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进展[J]. 生态学杂志, 2001, 20(3):31–36.
[16] 任海. 恢复生态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7] PANTUS F J, DENNISON W C. Quantifying and evaluating ecosystem health: a case study from Moreton Bay, Australia[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5, 36(5): 757–771.
[18] 袁兴中, 叶林奇.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群落学指标[J]. 环境导报, 2001(1): 45–47.
[19] KARR J R, FAUSCH K D, Angermeier PL, et al. Assessing biological integrity in running waters: a method and its rationale[J]. Illinois Natural History Survey Special Publication, 1986(5): 1–28.
[20] 武海涛, 吕宪国. 中国湿地评价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世界林业研究, 2005, 18(4): 49–53.
[21] 杨波. 我国湿地评价研究综述[J]. 生态学杂志, 2004, 23(4): 146–149.
[22] HILTY J, MERENLENDER A. Faunal indicator taxa selection for monitoring ecosystem health[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0, 92(2): 185–197.
[23] 孔红梅, 赵景柱, 马克明, 等.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初探[J]. 应用生态学报, 2002, 13(4): 486–490.
[24] WANG Y K, STEVENSON R J, SWEETS P R, et al. Developing and Testing Diatom Indicators for Wetlands in the Casco Bay Watershed, Maine, USA[J]. Hydrobiologia, 2006, 561(1): 191–206.
[25] MONTEFALCONE M.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using the Mediterranean seagrass Posidonia oceanica: a review[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09, 9(4): 595–604.
[26] 郑耀辉, 王树功, 陈桂珠. 滨海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诊断方法和评价指标[J]. 生态学杂志, 2010, 29(01): 111–116.
[27] VITOUSEK P M, MOONEY H A, LUBCHENCO J, et al. Human domination of Earth's ecosystems[J]. Science, 1997, 277(5325): 494–499.
[28] 马克明, 孔红梅, 关文彬, 等.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与方向[J]. 生态学报, 2001, 21(12): 2106–2116.
[29] BOULTON A J. An overview of river health assessment: philosophies, practice, problems and prognosis[J]. Freshwater Biology, 1999, 41(2): 469–479.
[30] KARR J R. Assessment of biotic integrity using fish communities[J]. Fisheries, 1981, 6(6): 21–27.
[31] SCHOCK N T, MURRY B A, UZARSKI D G.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Drainage Outlets on Great Lakes Coastal Wetlands[J]. Wetlands, 2014, 34(2):297–307.
[32] TULBURE M G, JOHNSTON C A.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romoting Non-native, Expansion in Great Lakes Coastal Wetlands[J]. Wetlands, 2010, 30(3):577–587.
[33] PETESSE M L, SIQUEIRA-SOUZA F K, FREITAS C E D C, et al. Selection of reference lakes and adaptation of a fish multimetric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to six amazon floodplain lakes[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6, 97: 535–544.
[34] BREINE J, SIMOENS I, GOETHALS P, et al. A fish-based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for upstream brooks in Flanders (Belgium)[J]. Hydrobiologia, 2004, 522(1/3): 133–148.
[35] 崔保山,杨志峰.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理论[J]. 生态学报, 2002, 22(7):1005–1011.
[36] 麦少芝, 徐颂军, 潘颖君. PSR模型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的应用[J]. 热带地理, 2005, 25(4): 317–321.
[37] ZHANG F, ZHANG J, WU R, et al.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based on DPSIRM framework and health distance model in Nansi Lake, China[J].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Risk Assessment, 2016, 30(4): 1235–1247.
[38] WALKER J, REUTER D J. Indicators of catchment health: a technical perspective[M]. CSIRO Publishing, 1996.
[39] 张晓萍, 杨勤科, 李锐. 流域“健康”诊断指标——一种生态环境评价的新方法[J]. 水土保持通报, 1998, 18(4): 57–62.
[40] 钱逸凡, 楼毅, 初映雪, 等. 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价值评价[J]. 湿地科学, 2016, 14(4): 516–523.
[41] 高永胜, 王浩, 王芳. 河流健康生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水科学进展, 2007, 18(02): 252–257.
[42] 李浩宇, 周利军, 李凯. 流域生态健康指标评价标准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5, 14(15): 125–127.
[43] 陈衍泰, 陈国宏, 李美娟. 综合评价方法分类及研究进展[J]. 管理科学学报, 2004, 7(2): 69–79.
[44] 朱卫红, 郭艳丽, 孙鹏, 等. 图们江下游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生态学报, 2012, 32(21): 6609–6618.
[45] 孟庆生. 信息论[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7.
[46] 邹志红, 孙靖南, 任广平. 模糊评价因子的熵权法赋权及其在水质评价中的应用[J]. 环境科学学报, 2005, 25(4): 552–556.
[47] 陈卫, 方廷健, 马永军, 等. 基于Delphi法和AHP法的群体决策研究及应用[J]. 计算机工程, 2003, 29(5): 18–20.
[48] 杨丽芳, 钟艳霞, 李小宇. 基于PSR模型的鸣翠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水生态学杂志, 2015, 36(03):38–43.
[49] 李春华, 叶春, 赵晓峰, 等. 太湖湖滨带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生态学报, 2012, 32(12): 3806–3815.
[50] 金菊良, 魏一鸣, 丁晶. 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J]. 水利学报, 2004, 35(3): 65–70.
[51] 贾慧聪, 曹春香, 马广仁, 等.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湿地科学, 2011, 09(3):209–217.
[52] 胡永宏, 贺思辉. 综合评价方法[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53] 帅红,李景保. 基于投影寻踪的洞庭湖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11):1477–1483.
[54] WEBB-ROBERTSON, B-J M, JARMAN K H, HARVEY SD, et al. An improved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a Bayes factor termination criterion for sequential projection pursuit[J]. Chemometrics and Intelligent Laboratory Systems, 2005, 77(1): 149–160.
[55] BROWN M T, VIVAS M B.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dex[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05, 101(1): 289–309.
[56] 林波.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及其应用[D]. 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0.
[57] FENNESSY S. Review of rapid methods for assessing wetland condition[M]. EPA/620/R–04/009/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 2004.
[58] MILLER R E, GUNSALUS B E. Wetland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 (WRAP)[M].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Division, Regulation Department, South Florida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 1997.
[59] HATFIELD C A, MOKOS J T, HARTMAN J M, et al. Development of wetland quality and function assessment tools and demonstration[M] Rutgers University, 2004.
[60] SPENCER C, ROBERTSON A I, CURTIS A.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 rapid appraisal wetland condition index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8, 54(2): 143–159.
[61] PARKER K, HEAD L, CHISHOLM L A, et al. A conceptual model of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in the Shellharbour Local Government Area,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 2008, 86(1): 47–59.
[62] MO M, WANG X, WU H, et al.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of Honghu Lake wetland of China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pproach[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09, 19(4): 349–356.
[63] 薛亮, 冯超. BP神经网络在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的应用[J]. 林业调查规划, 2009, 34(5):47–50.
[64] 毕温凯, 袁兴中, 唐清华, 等.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湖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 2012, 32(8): 1984–1990.
[65] 张志诚, 牛海山, 欧阳华.“生态系统健康”内涵探讨[J]. 资源科学, 2005, 27(1): 136–145.
[66] 崔保山, 杨志峰.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尺度特征[J]. 应用生态学报, 2003, 14(1):121–125.
[67] 王晖, 陈丽, 陈垦, 等.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及权重系数的选择[J]. 广东药学院学报, 2007, 23(05): 583–589.
[68] GENET J A, OLSEN A R. Assessing depressional wetland quantity and quality using a probabilistic sampling design in the Redwood River watershed, Minnesota, USA[J]. Wetlands, 2008, 28(2): 324–335.
Advances in methods of 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evaluation
ZHOU Jing1,2, WAN Rongrong1,*
1.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Ge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Wetlands are considered as the kidney of the earth. Healthy wetland ecosystem has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logical balance. Thus,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has great significances in terms of wetl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treatment.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are key points to evaluate the wetland ecosystem. Based on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ing history of evaluation methods of 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this paper made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common methods of wetland health assessment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respectively. Finally, problems existing in processing 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establishment of health standards, sel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s, correlation between multi-spatial-temporal scale data,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evaluation.
wetland;ecosystem;health assessment;metrics;threshold
10.14108/j.cnki.1008-8873.2018.06.027
X171.1
A
1008-8873(2018)06-209-08
2017-09-19;
2018-04-0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4022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07); 江西省水利厅科技项目(KT201503)
周静(1994—), 女, 山西吕梁人, 硕士, 主要从事湿地生态与环境响应研究, E-mail: jingz7886@163.com
万荣荣, 女, 副研究员, E-mail: rrwan@niglas.ac.cn
周静, 万荣荣.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研究进展[J]. 生态科学, 2018, 37(6): 209-216.
ZHOU Jing, WAN Rongrong. Advances in methods of 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evaluation[J]. Ecological Science, 2018, 37(6): 20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