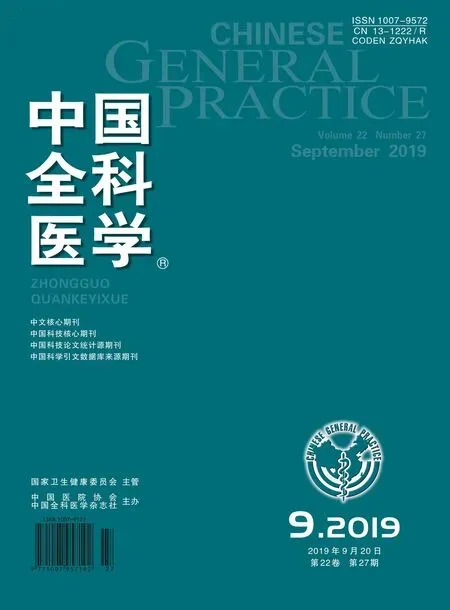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呼吸系统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张立涛,赵静,韩虎
人的皮肤、阴道、呼吸道和胃肠道中生活着数万亿的共生细菌,主要包含6门: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变形杆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和蓝细菌门[1]。然而,这些门的相对丰度,特别是属水平上不同部位的细菌组成存在显著差异[2]。其中,胃肠道的细菌定植密度最大,重量约为1.5 kg,数量是人体细胞的10倍、基因组的100倍,对代谢、内分泌、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影响重大。肠道菌群失调是一系列胃肠道疾病的潜在病因,并且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一些非胃肠道疾病(如肥胖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精神疾病同样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3-4]。
宿主肠道菌群对远端器官免疫功能的影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最近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组成和功能的变化与宿主免疫反应的改变以及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本文综述了健康胃肠道和呼吸道中常见的微生物种类以及对肠道和肺之间免疫学联系的新认识,即肠-肺轴,并且探讨肠道菌群和呼吸系统疾病相关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
1 肠道菌群和宿主免疫功能
肠道微生物群是在人出生后1~3年内形成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相对稳定[5]。早期肠道微生物的形成与产前微生物的垂直转移、分娩方式、喂养方式、感染、抗生素的使用以及肠道环境有关,并影响人的健康状况[6]。
迄今为止,胃肠道仍然是宿主相关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最深入的系统,原因为其微生物丰富,微生物群可以通过粪便标本进行检验,很容易获得。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度不仅沿着肠道的长度变化,而且在每个区域的黏膜和肠道管腔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不同[7]。这些差异受环境的影响,包括pH值、胆汁酸浓度、消化滞留时间、黏液特性和宿主防御因子[8]。从数量上讲胃肠道是人体细菌定植最密集的表面,细菌载量达到1014个[9]。拟杆菌门是最丰富的门,其次是厚壁菌门。在健康成年人中,拟杆菌、粪杆菌和双歧杆菌是最常见的属[10]。此外,肠道菌群可根据个体存在的优势属分为3种:拟杆菌(1型菌群)、普雷沃特菌(2型菌群)和反刍球菌(3型菌群)[11]。环境因素、饮食、使用抗生素、化疗、胃肠道感染和宿主免疫状态的变化会短暂或永久地改变肠道生态系统,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表现为有益菌种数量减少和/或其他菌群的生长或种群转移。肠道菌群失调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身体健康,如条件病原菌的生长、宿主代谢谱的改变和/或炎症的增加。
肠道菌群通过以下机制调节宿主黏膜免疫功能。肠道微生物提供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作为肠上皮细胞(IECs)管腔或基底外侧表面不同toll样受体(TLRs)的配体,TLRs激活信号级联,导致转录因子激活和基因转录,增强细胞屏障,进一步刺激固有层中的免疫细胞。肠道细菌及其衍生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直接刺激IECs或被树突细胞(DCs)和巨噬细胞吞噬,在肠系膜淋巴结(MLN)促使B细胞和T细胞成熟和分化。其中B细胞变成浆细胞并产生IgA,IgA随后被分泌到肠腔内。而T细胞分化为Th17和Th1,其具有促炎倾向,能激活其他效应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导致细菌被清除。某些特定种群如脆弱拟杆菌、婴儿双歧杆菌、梭菌群可以促进调节性T细胞分化,通过刺激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的产生来抑制过度的炎性反应,维持肠道内稳态[12]。
肠道菌群可调节肠道内及远端的宿主免疫,通过几个关键途径影响全身免疫应答,如介导肠道外T细胞群的扩张和分化[13]。肠道菌群产生的各种SCFAs,尤其是丁酸盐,可以通过激活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和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影响免疫细胞迁移、黏附、细胞因子表达、细胞增殖、活化和凋亡,发挥广泛的抗炎活性[14-15]。
2 呼吸道菌群
呼吸道是许多微生物和颗粒(如病毒、细菌或真菌)的主要和连续的入口。从上呼吸道开始,鼻孔中的细菌以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为主,厚壁菌门、变形杆菌门和拟杆菌门在口咽中普遍存在[16]。传统观点认为正常的肺内是没有细菌的,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基于直接扩增和分析16S rRNA基因的技术揭示肺部存在不同微生物群落定植。健康肺中最常见的细菌门是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和变形杆菌门,优势属包括普雷沃特菌、韦氏菌、假单胞菌、梭菌和链球菌[17]。CHARLSON等[18]使用双支气管镜取样的方法研究6名健康个体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的微生物群,以避免污染的风险,结果发现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微生物群生物量明显减少,肺组织样本中每1 000个人类细胞中含有10~100个细菌细胞,下呼吸道细菌谱系较上呼吸道丰富,肺的微生物群同鼻子和口腔微生物群更相似。“生活在南极洲”模型[19]描述了影响肺微生物群的三要素:(1)微生物进入呼吸道;(2)微生物从呼吸道消除;(3)呼吸道内微生物的相对生殖率。任何肺部微生物群落的变化,无论是在健康还是在疾病状态下,均是这3个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亚临床微量吸入咽部分泌物是肺部微生物移入的主要来源[20]。微量吸入上呼吸道分泌物是正常的,尤其是在睡眠期间。因此,健康的人肺微生物组是短暂存在的,这些菌群可以被正常的肺防御机制清除。其他影响微生物进入呼吸道的因素包括从空气中吸入的细菌和沿呼吸道黏膜表面直接迁移的细菌。微生物的清除是通过黏膜纤毛清除、咳嗽和宿主免疫防御(先天和适应性免疫)来完成的。炎性反应对于呼吸道微生物的生殖率十分重要[21],主要是通过影响区域生长条件来实现的,如营养利用率、温度、pH值、氧张力。炎性反应可增加呼吸道的血管渗漏,为细菌生长提供重要的营养元素,如碳源、氨基酸、维生素和铁。上皮细胞损伤可形成基底膜基质暴露区,促进细菌黏附。而健康时,区域生长条件一般不支持细菌的旺盛生长,导致细菌的生长相对较少。
肺微生物组在维持肺内稳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肠道菌群相似,肺部菌群也可能被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促进出生后肺部幼稚T细胞从Th2表型向Th1表型转化,从而保护新生儿避免哮喘和过敏性疾病的发生[22]。新生儿肺部细菌由变形杆菌门和厚壁菌门向拟杆菌门的转移与肺部Helios阴性T细胞的发育有关,可抑制过敏原过度的炎性反应,直至成年[23]。而动物实验也证明肺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以促进M2肺泡巨噬细胞分化,从而对流感引起的肺部致命炎症起到保护作用[24]。而肺部菌群失调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持续进展相关[25]。
3 肠-肺轴
微生物群在维持定植器官或组织的稳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局部菌群的变化也会影响远端组织的免疫功能,如肠-肺轴。
组织胚胎学研究已经证实肠道和呼吸道结构来源是相同的,原肠的前肠分化成肺与气管,原肠内胚层分化出呼吸道上皮与腺体,其黏膜内壁实际上是连续的。肠道和呼吸道由柱状上皮细胞组成,微绒毛(肠道)或纤毛(呼吸道)突出,均通过杯状细胞分泌黏液,同时分泌免疫球蛋白A,起到物理屏障和免疫屏障的作用,在很多病理改变中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肠道微生物群通过启动肺泡巨噬细胞在宿主防御肺炎链球菌诱导的肺炎方面发挥保护作用[26]。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肠道分节段丝状细菌(SFB)可能通过促进肺感染后中性粒细胞的分解,对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提供保护,以对抗肺炎链球菌感染[27]。肠道菌群同样可以在免疫调节细胞的参与下对抗流感病毒感染[28]。反之流感病毒可以通过Th17细胞介导,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引起肠道免疫损伤[29]。局部诱导的肺部过敏反应也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30]。而短双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减少了COPD模型小鼠肺部的病理改变[31],减少体外暴露于香烟烟雾提取物的巨噬细胞的炎性反应[32]。而肠道细菌的发酵产物,即SCFAs,通过调节免疫功能,可预防过敏性气道炎性反应的发生[33]。
我国中医藏象学说中也有“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其最早记载在《黄帝内经》中,如《灵枢·本输》云“肺合大肠”[34]。从临床治疗效果来看,肺病患者从肠论治以及肠病患者从肺论治均能达到显著疗效,一定程度上也论证了肺与肠之间的相关性。
因此,目前的理论认为肠-肺轴是双向的,类似于可以从两个位置刺激的循环,但是具体免疫调节作用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潜在的途径。进入肠黏膜的微生物群及其产物被巨噬细胞或DCs吞噬,通过抗原提呈细胞(APC)转移到MLN,刺激T细胞和B细胞的活化。一旦激活,随着合适的趋化因子受体(CCR)如CCR4、CCR6的表达,这些细胞可以通过淋巴循环和血液循环重新迁移到原始部位(肠黏膜)或远端位置,如肺上皮细胞和肺淋巴结,直接作用于目标细胞或继续刺激其他免疫细胞[35]。另一方面,由于患者肠道和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加,来自肠道黏膜的细菌可以通过血液循环移位到肺部[36]。根据SAMUELSON等[37]的肠-淋巴理论,肠道黏膜下层或MLN包含的存活细菌、细胞碎片或细菌的蛋白质部分随肠道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0、IL-6、转化生长因子-β、干扰素γ)和趋化因子逃逸,沿着肠系膜淋巴系统进入乳糜池,随后进入体循环。进入肺循环后可能导致DCs和巨噬细胞活化,以及T细胞的启动和分化。细菌代谢产物(如SCFAs)也会通过血液循环被运送到肺部调节免疫功能。相反的,从肺到肠可能存在同样的机制,但是肺微生物群对肠道菌群和肠道免疫的影响知之甚少。
4 肠道菌群与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临床研究
多项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多样性与哮喘之间存在相关性,母亲在妊娠期间使用抗生素,包括头孢菌素、大环内酯类和青霉素,会增加儿童患哮喘的风险[38-40]。在生命早期4种肠道菌属包括:粪杆菌属、毛螺菌属、韦荣球菌属、罗氏菌属能够减轻气道炎性反应,降低哮喘的发生风险[41]。对于2~7岁的儿童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可以导致放线菌门减少,拟杆菌门和变形杆菌门增加,哮喘患病率增加[42],而通过益生菌治疗恢复改变的肠道菌群可以降低这种风险[43]。这些数据支持了微生物在生命早期发育阶段定植可预防儿童哮喘的假设。一项为期10个月的随机、双盲、平行和安慰剂对照研究评估了长双歧杆菌BB536对520名2~6岁健康马来西亚学龄前儿童腹泻和/或上呼吸道疾病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BB536对儿童腹泻没有显著作用,但是10个月后BB536组和安慰剂组肠道菌群差异显著(P<0.01),具有抗炎、免疫调节作用的粪杆菌属丰度显著升高(P<0.05),同时患儿咽喉痛时间减少46%(P=0.018),发热时间减少27%(P=0.084),流鼻涕时间减少15%(P=0.087),咳嗽时间减少16%(P=0.087)[44]。证明长双歧杆菌BB536对上呼吸道疾病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对于反复发生肺炎的患儿研究发现:其粪便中双歧杆菌数量以及双歧杆菌和大肠埃希菌含量的比值(B/E)均低于急性组及外科组(P<0.05),而大肠埃希菌数量高于外科组(P<0.05),与急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反复肺炎患儿血清D-乳酸值较急性组及外科组均增高(P<0.05),B/E与D-乳酸值呈负相关(r=-0.539,P<0.05)[45],提示患儿反复肺炎可能与肠道菌群紊乱、肠道黏膜通透性明显增加有关。肠道菌群同样与囊性纤维化(CF)有关,CF患儿早期肠道微生物是呼吸系统疾病进展的决定因素,CF恶化与肠道微生物组成有显著相关性(P=0.03),而益生菌能够使患者获益[46]。
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COPD和哮喘患者常伴有胃肠道症状,并且与严重程度高度一致[47]。EKBOM等[48]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COPD患者溃疡性结肠炎〔风险比(RR)=1.83〕和克罗恩病(RR=2.72)的风险均显著较高。其具体机制可能与COPD患者代谢需求高,存在肠缺血-再灌注损伤,进而肠通透性增加有关[49]。相反的炎症性肠病患者虽然没有急性或慢性呼吸道疾病史,但是多达50%的患者出现肺功能损伤[50]。以上研究表明COPD与肠道疾病可能具有相关性。
益生菌作为一种活的非致病性微生物,可以保护肠道屏障,抑制病原菌过度生长,减少细菌易位,防止感染。两项Meta分析比较了肠道益生菌对肺炎发生率的影响,其中一项包含28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Meta分析显示:围术期接受益生菌/合生元治疗的患者感染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OR=0.35,95%CI(0.24,0.50)〕,其中肺炎发病率明显降低〔OR=0.44,95%CI(0.28,0.68)〕,但ICU住院时间和死亡率无显著差异〔OR=1.19,95%CI(0.52,2.74)〕[51]。一项纳入2 972例患者共30项RCT的Meta分析显示,益生菌可显著降低感染并发症发生率〔RR=0.80,95%CI(0.68,0.95),P=0.009〕,并可以显著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率〔RR=0.74,95%CI(0.61,0.90),P=0.002〕,但是对患者死亡率、住院时间或腹泻的发生无明显影响[52]。由于临床异质性以及潜在的发表偏倚的限制,对最后结果的认可还需要谨慎。采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对H7N9病毒感染者肠道菌群进行分析发现,大肠埃希菌和粪肠球菌是有害的,与此相反,普通型拟杆菌、卵型拟杆菌、柔嫩梭菌、肠道玫瑰布里亚菌、真细菌、长双歧杆菌和副流感嗜血杆菌可能在这一特定的生物学背景下产生有益的影响,同时发现H7N9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肠道菌群成分变化主要是病毒感染及相关治疗所致[53]。无论H7N9感染患者是否接受抗生素治疗,其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均有所下降。然而,包括抗病毒药物、益生菌和抗生素在内的治疗似乎有助于增加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肺和肠道微生物组与肺结核感染同样有关,但相关临床研究较少,对1名曾接受多种口服抗生素治疗的耐多药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的粪便样本进行分析显示:肠道细菌数量和组成明显较低[54]。动物研究显示肠道微生物组对免疫系统的调节可能与预防结核病感染、减少潜伏期进展、减轻疾病严重程度以及降低耐药性、感染并发症发生率有关[55]。
重症患者的肠道菌群同样发生明显变化,脓毒症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丧失。研究发现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的比值(B/F)与院内死亡率有关,B/F>10的患者死亡率明显增加[56]。对68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收集的100份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标本中的细菌群落进行了测序,并将这些群落与7例健康志愿者的细菌群落进行了比较,发现肠道来源的拟杆菌属在ARDS患者的肺泡灌洗液中数量丰富,其相对丰度和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浓度明显相关(P=0.01),与肺泡TNF-α浓度无相关性(P>0.05),而变形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和肺泡TNF-α浓度呈正相关(P=0.003)[57]。这一发现表明,ARDS患者中肠道菌群在肺部富集,即存在细菌移位,这与急性全身炎症的严重程度有关。肠-肺细菌转移和肺部微生物的改变可能是脓毒症和ARDS发病的共同机制。
5 总结
人体表面70%以上的细菌种类无法通过现有的技术进行培养,传统的培养技术已不再是微生物研究的金标准。包括16S rRNA基因在内的识别细菌序列的先进技术,使人们对微生物学和相关疾病的研究不断深入。为鉴定细菌菌群组成,常用16S rRNA基因作为细菌特异性保守基因,扩增16S rRNA基因的9个可变区域(V1-V9)中的V3-V4区域[58]。相对于传统的Sanger测序方法,新一代测序技术(NGS)能够以99%以上的准确率快速评估大量的碱基(1~10亿个读数),适用于分析在同一个时间或样本中各种各样细菌的DNA。但是NGS中每个序列的测序精度可能低于Sanger测序方法[59],NGS (MiSeq)只能检测属水平,而Sanger测序方法可以检测种水平的所有细菌亚型[60]。
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的概念认为黏膜免疫系统是一个全身性的器官,免疫细胞在不同黏膜组织之间相互作用,而肠-肺轴很可能是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的一部分[61],但是不同黏膜位点是如何进行沟通的,以及这一过程涉及哪些免疫细胞及分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肠道和肺的微生物群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同时对肠-肺轴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临床研究较少。肠道的细菌成分和代谢产物具有调节局部和全身免疫的能力,影响哮喘、COPD和呼吸道感染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微生物群和肠-肺交互作用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作用,而不仅是相关性,并有可能促进发现新的和有效的治疗途径。
本文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和Google Scholar近5年的相关文献以及本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检索关键词为:Gut microbiota,Gut-lung ax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