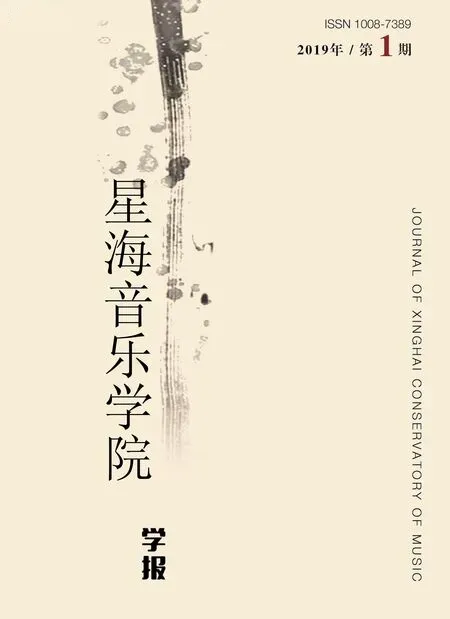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中的音乐史学理论探析
汪 静
梁茂春先生作为音乐史学家、音乐评论家,毕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科研、教学与评论工作,其史学著作在我国音乐理论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据笔者了解,目前对其著作的研究多以《百年音乐之声》[注]① 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中国当代音乐》[注]② 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为主。其中有关《百年音乐之声》的主要文献有:石一冰《百年大写意——评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注]③ 石一冰:《百年大写意——评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黄钟》2005年第1期。、张晓农《纳世纪之百川 坦真诚之灼见——评梁茂春音乐著〈百年音乐之声〉》[注]④ 张晓农:《纳世纪之百川 坦真城之灼见——评梁茂春音乐著〈百年音乐之声〉》,《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3期。、董晓婷《百年中国 音乐百年》[注]⑤ 董晓婷:《百年中国 音乐百年》,《音乐周报》2001年03版。等;有关《中国当代音乐》的主要文献有:于林青《一本有史有论的佳作——读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注]于林青:《一本有史有论的佳作——读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这些文章大多以书评的形式对其著作进行研究探讨,主要从著作内容、结构,作者写作风格、治史态度等方面对梁茂春的史学著作予以评析。然而,遗憾的是从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对他的著作予以关注的文章还未发现。梁茂春的音乐史学著作不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厚度而言,都是他奉献给社会的具有一定份量的精神财富。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丰富的史料资源,更看到了作者严谨的治史理念。
笔者通过对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以下简称《边角》)的学习,发现在这本史学著作中,体现了他多元的史学观念、新颖的研究方法与独特的研究视角。所以,有必要对梁茂春的音乐史学研究观念、方法予以关注,在充分了解其音乐史论著的基础上,对其史学研究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笔者选择《边角》一书为研究基础的原因有三:
首先,《边角》出版于2015年9月,是梁茂春先生较新的学术著作。是书不论从作者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方法的拓展,都是其史学观念升华之体现。从时间上看《边角》更贴近梁茂春当下的史学研究观念。
其次,“边角”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角落,应当有人去收集、研究。梁茂春通过对音乐史中的“边角研究”, 对一些少为人知而又在历史进程中起积极作用的史实进行梳理,对以往研究中被歪曲误写的史料重新整合。所以,《边角》是对“重写音乐史”这一话题的积极呼应,是新史学研究的实践成果,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其三,内容深入浅出、鞭挞入理,丰富翔实的史料与条理清晰的逻辑体现了作者坚固的史学根基与成熟的治史理念,可作为笔者对其史学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有力支撑。
一、史学观念
“历史研究离不开人的理性思维。音乐史实只有通过音乐史学家本人心灵或思想的冶炼,才能成为史学。因而治史必须要有观念,也必定受观念的支配。”[注]田可文:《音乐历史观及研究模式的求证》,《黄钟》1987年第3期。历史观是史学家对历史事实这一客观事物的主观阐释,体现了史学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的科学认知与写作历史的价值观念。也正因为不同的史学观念,才造就了各不相同的史家学派。通过对梁茂春早期史学著作的学习,以及对《边角》的研读,笔者认为,他始终秉承还原历史真貌、填补历史空白这一治史观念。然而,世界万物是变化的,音乐生活是发展的,永远会有新资料的发现和新观念的提出。这些变化与发展必然会对史学家的历史观产生影响。梁茂春的音乐史学观念自不例外,从主流音乐史研究转向支流音乐史研究,从中心人物研究转向边角人物研究,这样的转变也正体现了他历史观念的嬗变。
(一)历史观的坚守
1.还原历史原貌
史学家的任务与责任应当是尽己之力去接近真实的历史,梁茂春的史学研究始终坚守着这一史学观念,并以此作为《边角》一书的写作宗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其发展初期,大多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政治的偏见代替了理性的认知。由于受地域、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影响,许多本应被历史铭记的人物、事件被淡化或遗忘。在看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这一弊端后,梁茂春怀揣还原历史原貌的初心,本着对音乐历史生命尊重的态度,铸就了一部相对真实、理性的史著。书中十八章内容大到历史音乐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小到一张图片、一个数据都是作者经过层层筛选、考证、比对后才纳入其中的。正如梁茂春自己所言:
我们的艺术史有许多可以称之为“鹦鹉艺术史”,音乐历史著作往往在权威面前嗫嚅失语。“音乐史的边角研究”只求让音乐历史拂去尘埃,重新拉开历史的厚重幔幕,还原音乐历史的真相。[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5页。
真实的历史不会被时间揭穿,书写真实的历史应当是每一位历史研究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2.填补历史空白
《边角》中收纳的大多是一些新的音乐史料,其中涉及边角人物、边角事件、作品等。许多为历史作出卓越贡献的音乐人物没有被历史铭记更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以书中第十二章“韩悠韩研究”为例,相对于大多主流音乐人物而言,韩悠韩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属于“留白”的研究领域。在看到这一历史空白后,梁茂春通过近十年的时间,对韩悠韩这一韩国作曲家的资料进行大量搜集,其中涉及韩悠韩在中国期间创作的作品及组织的音乐活动等。作者以搜集到的研究资料为基础,对其音乐贡献进行历史分析。进而将一位“边角”人物较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掷地有声的史料依据为这位边角人物在历史的空白处留下足迹。
(二)历史观的嬗变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沉淀,梁茂春的史学观念也逐渐变化。他不再囤于传统治史观念的窠臼,而是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面向浩瀚的音乐史料,其史学观念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从主流历史向支流历史转变和从中心人物向边角人物转变两方面。
1.从主流历史向支流转变
梁茂春的史学研究开始由主流历史研究转向支流历史研究,关注主流历史中被忽略的领域。例如,书中对于“天津乐事”的研究。作者将搜集到的大量碎片化的图片、文字等资料组合比对,通过对天津公共乐队、清末新军军乐队、津郡乐工学堂、天津音乐体操传习所、天津工商学院管弦乐队、天津水师学堂军乐队、李映庚的《军乐稿》及天津青年会合唱队演唱《圣诞曲》的研究与探索,逐渐将天津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历史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对原本陌生的天津音乐历史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天津本身在中国音乐史上就是一个边角”[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7页。,由于地理位置、政治因素等原因,许多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堙没。作者将研究视野从所谓的“主流”转向这些被忽略甚至遗忘的“支流”,通过大量有理有据的史料搜集与音乐学分析,力图拂去历史的灰尘,让这些被埋没的、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重见天日。除“津门乐事”的研究外,作者还将视野转向杭州“春风乐会”“福建乐群”等领域。通过对这些相对陌生的历史进行研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起到了补充与细化的作用。
2.从中心人物向边角人物转变
在《边角》一书,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人物研究。其中涉及到的大多是一些历史上的“边缘”人物。他们或是不曾被熟知,或是因各种原因没能被载入史册,例如书中对华丽丝的研究。作为一位外国音乐家,华丽丝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典型的边缘人物。作者对华丽丝的研究集中在其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方面,通过对华丽丝艺术生平、艺术歌曲分析及其写作背景原因等综合考证,得出“华丽丝的艺术歌曲,应该是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收获”[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这一结论,并认为历史不应将华丽丝忘却,她不仅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更对青主的音乐创作有过帮助并培养了廖辅叔、廖玉玑两代音乐家。
再如对邓丽君的研究。邓丽君作为人尽皆知、家喻户晓的人物被作者放置到了“边角”研究中难免让读者觉得匪夷所思,然而,细读文章才深知作者的良苦用心。作为流行音乐歌手,邓丽君因种种原因完全被正统音乐史排除在研究范围外。作者期望通过对邓丽君的研究,让主流音乐史能够对流行音乐歌手及作品予以关注。在音乐史的研究中,不应将研究视野局限于一方一隅,而应带着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对人类历史进程中作出过贡献的音乐家都纳入研究范畴。只有史学家以多元的治史观念撰写历史,才能铸就具有鲜活生命力、符合社会发展的音乐史著。
纵观《边角》一书,十八章的内容涉及了区域史(“津门乐事”“春峰乐会”“福建乐群”)、人物史(霍尔瓦特夫人、华丽丝、金律声、廖辅叔、黎锦光、王君仅、韩悠韩、陈田鹤、黄桢茂、王洛宾、瞿希贤、邓丽君) 、专题史(中国交响乐队、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百代国乐队)等。这些研究对象中,不论是时间长度上的跨越还是空间高度上的纵横,其丰富性都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多元的治史观念。梁茂春音乐史学观念中所体现的坚守与嬗变,是其对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发展的思考与反思之结果。而这一反思结果似乎更多地受到“重写音乐史”[注]“重写音乐史”论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近年来的重大事件。自1988 年戴鹏海第一次提出至今,数位音乐理论家积极参与讨论。思潮的影响,正如作者在《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一文中所言:“没有自觉的‘重写音乐史’的学者,就不是一位称职的学者;没有以‘重写音乐史’为职责的音乐史学家,就不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音乐史学家。”[注]梁茂春:《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黄钟》2002年第3期。作者认为自己早期的音乐史著述缺少独立的思考与话语,将之比作鹦鹉学舌,深刻剖析自我的背后,也正是作者意识形态、史学观念升华的体现。
二、史学方法
所谓史学研究方法,指史学家在其研究过程中所用到的系统的研究手段,是联系史学家及其研究对象的媒介,是帮助史学研究者接近历史真相的工具,“是研究者的学术个性、知识结构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料品质的相互适合”[注]王小盾:《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4页。。史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学术水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关系密切。
“历史”一词 ,可分为两层含义。居其宏将第一层历史含义定义为“历史的实在性存在”[注]居其宏:《历史本体论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音乐研究》2014年第3期。,第二层定义为“历史的观念性存在”[注]居其宏:《历史本体论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音乐研究》2014年第3期。。“史实”是历史的实在性存在的载体。“史料”则指当下现实生活的人以及后人对客观存在的历史所作出的带有主观情感的解读与重构,是历史的观念性存在的载体。史学家的责任是尽可能搜集、挖掘散落的碎片化的史实与史料,并通过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以求真实贴切的还原历史。下文将以《边角》为研究基础,从史料搜集、史料分析两个方面对梁茂春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探讨。
(一)史料搜集
孔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史学家在写作之前的首要工作,应是尽可能的搜集一切有关史料。“史料”与“史实”既相同又不同。相同在于,“史实”一定是“史料”,不同在于,“史料”中有真伪之分,需要史学家加以辨别,去伪留真方能使用。
我们考量一位史家笔下某部历史著述之史学价值如何,最重要的不是评价其历史观以及从历史对象中提升出的结论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音乐艺术规律,而是看他所运用的史料史实、所梳理的历史脉络、所描画的历史图景、所构建的历史意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或者接近了历史的实在性存在,是否较为真切可靠地重现出实在性历史存在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其历史架构在整体上是否可被称之为“信史”等。[注]居其宏:《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多元史观与普适性原则》,《音乐艺术》2004年第3期。
梁茂春在其史学研究中做到了面对史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求古本之真、求事实之真。严格恪守了史料第一性、史实第一性原则。
1.史料第一性原则
史料的丰歉与贫瘠是衡量史学家治史功力是否扎实的关键。作为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基础,史料范畴的宽广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深浅。梁茂春的史学研究始终将史料的收集放在第一要位。不论是地域史、人物史还是专题史研究,作者都以丰富的史料为研究基础,这些史料涉及图片、音响、谱例、文献等,其深度与广度,也同时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史学思维与开阔的学术视野。以“百代国乐队”研究为例,作者在对这一研究对象的相关史料尽可能详尽搜集的基础上,先是对“百代国乐队”前期后期成员资料进行整合,对乐队成员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后,又对乐队创作的“四大名曲”进行逐一分析。作者以清晰的逻辑思维包裹着丰盈的历史史料,这些史料涉及歌曲演奏名单、乐队演出请柬、乐谱谱例、相关文献等等。正是依托这些丰富的史料,“百代国乐队“在作者的笔下才得以清晰地展现。
2.史实第一性原则
“史实”指已经确定存在并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实在性历史。其中包括图片资料、谱例等。在将研究范围内相关史料尽可能悉数搜集后,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辩证则体现了史实第一性原则。
“史料第一性”原则是贯彻“史实第一性”原则的材料基础,没有丰厚、扎实的史料基础做支撑,后者的考证和辨伪工作便失去了对象;“史实第一性”原则贯彻是“史料第一性”原则的目的,未经严格考证和辨伪的史料,即便再多再丰厚,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依然是存疑的,也就减弱了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史学价值。[注]居其宏:《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多元史观与普适性原则》,《音乐艺术》2004年第3期。
梁茂春史学研究中所秉承的史实第一性原则在《边角》一书中处处都得以体现,如对中国第一首管弦乐第一说之史料辨析、对王洛宾具体出生日期之史料辨析、对李叔同信中用词准确度的辨析等。作者在详尽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及敏锐的学术洞见对史料进行反复考证、面对史料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以独立的辩证思考为基础对史料进行分析、考其流传、辨其真伪,进而求得历史之本相。
(二)史料分析
史料分析方法应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时,对其进行分析考证并将其取舍、分类就需要对众多史料有一定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找出相似之处,通过严谨的分析将各种无限的可能性逐渐推导至不可信并得出结论。笔者将梁茂春的史料研究方法归纳为比较法、搜集排比法、实证法、形态分析法。
1.比较法
正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边角》一书中作者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进行比较。针对《怀旧》《新霓裳羽衣舞》《哀悼进行曲》这三首管弦乐作品何为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这一问题,作者以搜集到的史料为研究依据,通过在对史料层层梳理将有争议的三首作品进行比对,并运用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得出《哀悼进行曲》应为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的结论。
2.搜集排比法
历史上的事件,很多是一件件分开的,单独看是不存在什么逻辑,因此史学家研究历史则应该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关联起来,进行排比研究,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边角》中天津公共乐队的研究正是这一史学研究方法的鲜明体现。作者将雷穆森对天津公共乐队的研究材料与韩国鐄对北京赫德乐队的研究相联系,发现1885年赫德曾在天津办过军乐队培训班,训练者为比尔格。1886年将在天津学成的八人调往北京继续培训其他学员,而留在天津的学员则在1887年组成天津公共乐队,北京的学员于1888年组成12人的赫德乐队。比尔格则来回穿梭于天津北京之间担任指挥及教练,为两支乐队提供了技术上的指导。“历史的蛛丝马迹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些令人惊喜的缠绕和勾连”[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4页。,正是作者将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史料连接起来进行解析,天津公共乐队的历史面貌才得以展现。
3.实证法
所谓实证法,既“考据”方法。是一种强调以可靠证据为支撑论述观点的方法。梁茂春在《边角》的撰写中大量运用了实证研究法。书中共引用127张图片,45个谱例,正是这些丰富且可靠的论据,使得其论点拥有了强大的说服力与支撑,是其史学研究真实性的保障。例如对霍尔瓦特夫人的研究,作者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音乐报纸杂志、霍尔瓦特夫人工作过的单位保存的相关资料及已出版的霍尔瓦特夫人当年的同事或学生的传记著作,搜集到有关于霍尔瓦特夫人的照片及信息。通过对照片拍摄时间、地点等背景分析进而作为研究霍尔瓦特夫人的有力依据,这些有理有据的照片与信息,也正是霍尔瓦特夫人作为中国早期声乐专业教育开拓者之一的印证。
4.形态分析法
“形态学方法,就是从音乐艺术及其各门类的独特形态特征、技术手法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工艺学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注]居其宏:《音乐学文论写作教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47页。形态分析法在梁茂春的史学研究中,占用一定的分量。也正是对这一史料分析方法恰如其分的运用,才使得其对人物、作品进行研究时,不仅限于普通的学理探究,更从技法层面对作品进行音乐形态学分析,从而给予历史人物、事件以科学客观的评价。例如,对杭州春峰乐会的研究。作者在对乐会成员介绍的部分中,对他们的作品也逐一进行曲式分析,通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质量的探究,作者提出春峰乐会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能够代表“五四”这一时代声音,因为音乐作品往往能更深刻准确地反映时代的特征。除此之外,作者对王君仅、韩悠韩、黄桢茂等音乐家进行研究时将他们的代表音乐作品也都进行了技术层面的分析,使读者通过音乐作品对这些音乐家有更深入的了解。音乐形态学分析方法是音乐史学著作研究的基础,只有将作品本体进行技术分析,才能将潜藏在音乐中的时代背景发掘并以此作为史料依据,从而更深刻全面地对历史进行分析。
诚然,《边角》除以上涉及的比较法、实证法、形态分析法、搜集排比法以外,作者还运用了一些其他史学研究方法如推理法、存疑法等,笔者仅以这四个运用较多、涉及范围较广的方法论为研究切入点。在对这些史学研究方法做简单梳理后,我们发现正是作者辨析史料过程中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研究对象的结构,将历史思维与逻辑思维辩证统一,使其史学著作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三、独特视角
(一)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音乐史写作的一个新视角,“口述音乐史”这一历史研究方法贯穿于《边角》一书。梁茂春最初的音乐家采访开始于1979年前后,其中涉及贺绿汀、杨荫浏、刘雪庵、曹安和、黎锦光、丁雪松、王洛宾等老一辈音乐家及其家属友人的采访记录。这一系列访谈录大多属于“口述音乐史”的范畴。正因有这些一手资料的掌握,使得作者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梁茂春在其文章《口述史漫议》一文中将“口述史”定义为:
音乐史的一种“口头文本”,它区别于音乐史的“书面文本”;这是音乐史的“民间文本”,因而区别于“官方文本”。“口述史”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话语系统与主流意识形态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一定全部符合标准答案。这应该是可以容许存在的。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应该是官方文本和民间文本同时并举,才可能突破大一统的格局,从不同的方面去接近真实。[注]梁茂春:《口述史漫议》,《福建艺术》2014年第4期。
简单理解,口述音乐史是以访谈性质进行,以对话形式构建,以录音录像方式保存,充斥着听觉与视觉双重效果的历史研究。口述音乐史为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使音乐史的研究充斥着活力。梁茂春对廖辅叔、黎锦光、王洛宾三位音乐家进行过多次的采访。从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正因为作者亲自对音乐家进行的访谈使其对这些音乐家的记录中带有更多的真实情感,同时也为读者呈现出更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从而使音乐家的形象鲜活,并使读者从丰富完善的史料中了解到更加真实的音乐家。
口述音乐史更能够对非主流音乐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一些被忽略的边缘群体。把普通人民的经验纳入到历史中,书写出更接近于历史原貌的大众历史著作应是每一位史学家所承担的责任。“口述”过程中生动的语言是极具价值的史料,和其他“笔述”史料一样,它同样需要经过考证才可以使用。这一当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更预示了多元化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行文风格的特殊性
梁茂春是音乐史学家,同时也是音乐批评家。在其音乐史学著作中,除对史料的忠实记载,带有作者主观情感的批评语言是其史学著作的一大特色与亮点。
因为要研究当代音乐史,就不能不把研究与评论结合起来,不能不大面积的接触当代音乐生活的实际,不能不大量的熟悉当代作曲家、演奏家,不能不密切关注当代音乐生活的发展与走向。[注]张苏琴:《我追求直言的批评——梁茂春访谈录》,《音乐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3期。
《边角》一书,大部分章节末作者都附以“小结”。“小结”中的内容,多是作者对客观历史所作出的主观性阐述。这也正是作者撰史过程中秉承“秉笔直书”式的叙史原则与“发潜阐幽”式的批评文风之体现。例如对陈田鹤的艺术歌曲研究中,作者感慨“即使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人们对音乐的需要也是多元化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音乐的历史,就应该给各种另类的音乐以生存的空间”[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这段对陈田鹤艺术歌曲的评价,不仅映射出了作者的宽容历史观,更折射出作者发潜阐幽的治史风格。语言与观念的匹配度越高,文章的思路才会愈加清晰。纵观全书,沉稳凝练、鞭辟入里的语言行文将一桩桩历史事件、一位位历史人物生动清晰地还原在读者面前。不论是对文章框架的宏观把握,还是言语措辞的微观处理,都足以体现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与睿智独特的批评理念。除此,研究中参入自己的诗句,抒发历史情怀也是梁茂春文章的一大风格。比如在对廖辅叔的研究中他作诗《廖师素描》:“缓缓地低吟/苦苦地追寻/静静地奉献/默默地耕耘/纯真的书生/旷远的诗心/万古的师表/飘逸的妙文”,以此诗抒发对廖先生的敬佩。《边角》中还有不少作者或即兴,或深思后的小诗,这些也构成了梁茂春以诗抒情的写作风格。
(三)写作情怀的特殊性
梁启超说“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芜城废殿,从瓦砾堆中搜集断椽破甓,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页。。通过对梁茂春史学研究成果的再研究,笔者深感史学家治史过程的艰辛。这是一个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的“苦差事”。
只有那些凭兴趣并超越了利欲之心的人才能从荒凉的“边角”中获得内心的快乐,才能发现深藏着的历史魅力,穷通自乐。[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6页。
梁茂春十年如一日对史料的重视与关注,才使其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而这也正是他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之体现。
梁茂春将“以人为本”视为理想音乐史著述的准则。例如,对韩悠韩的研究中,作者不仅仅将视野放在其音乐作品中,更以现实关怀为基础对韩悠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予以重视,通过资料搜集解决这些疑问,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韩国音乐家做铺垫。再如,对邓丽君的研究中,作者坦言所有的音乐都应是为人性服务的,不论是艺术音乐、流行音乐还是传统音乐,它们的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作者对音乐作品、音乐家是否能被载入音乐史提出了这样的标准:“看这首作品或这位音乐家是否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尤其要看是否表达了底层草根阶层的心意和声音。这是人本主义音乐史的基本理念”[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404页。。所以,音乐史的写作中应秉承以人为本的治史理念,将一切对人类精神文明做出过实际贡献的,对音乐文化发展历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音乐家都纳入其中。抛开政治、地域等外界因素的桎梏,在有限的自由中求创造,在创造的实践中突破束缚音乐史写作的各种限制。将人本主义精神贯穿于音乐史的创作,逐渐推动多元化音乐史观的发展。基于作者丰厚的人文素养,“以人为本”这一命题才在作者的文章中得以显现和延续,而这也正彰显了作者对音乐史学发展的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四)研究视野的特殊性
我们音乐史上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件和人物,往往被人为地湮没在历史的深处,被视为弃履,人为地被历史省略,音乐史上被人为地设置了许多历史盲点和禁区。而“边角研究”则重视让历史不断找寻恰当的再现,还原真实的形态。[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9页。
边角研究是梁茂春史学研究视野的新突破,作者以边角研究为切入点,从历史的微观之处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以从未走入主流历史或被主流历史冷落的音乐人物、作品、事件为主。边角研究强调从历史的细微入手、从历史的旁侧入手。正如作者言:
边角研究并不追求音乐历史的宏大叙事,只注重微观的专题研究。多元的音乐生活应该有多彩的音乐史著作来反映。边角研究提倡叙述音乐历史的多种方法,提倡音乐史学家的个人叙述风格。[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页。
典型的边缘人物韩悠韩、金律声,神秘的霍尔瓦特夫人,勇敢的反思者瞿希贤,诗意盎然的杭州春峰乐会……正是秉承这种不偏中心、不废边角的史学理念,这些被长期忽略的“历史边角”,在作者的努力下才得以回到音乐史的研究视野中。
在《边角》的绪论中,梁茂春对“边角研究”这一独特研究视野的阐释可见其容纳多元史学观念的胸怀。边角研究可以恢复音乐历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增加音乐历史的细节叙述,边角研究更加注重音乐史上的凡人小事,提倡音乐历史的多种写法与风格,同时可以提高音乐历史研究的独立思考精神。历史永远处在变化与发展中,今天的边角亦可能成为明天的中心,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历史,本着宽容的历史观给予各种历史生命以生存的空间,我们的音乐史才能突破大一统的局面,才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结 语
通过以上对梁茂春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梳理,对其《边角》一书的史学研究及成果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与认识。从史学观念而言,他对还原历史的坚守与研究方向的延伸体现了多元的治史观念。从史学方法而言,他严格恪守史料第一性、史实第一性的搜集原则并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分析史料,体现了科学的治史方法。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行文风格、写作情怀的特殊性而言,体现了他成熟的史学风格。
“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史学家在忠实记录音乐史的过程中,因价值观、形态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正所谓“文如其人”,读史书的过程同时也是读史学家的过程。笔者认为,梁茂春以求真务实的撰史准则,鉴空衡平的治史态度对音乐史事进行忠实记录,这是其“史德”之体现;以“专而精”的专题史为研究基础,是其“史学”之体现;以“读史得间、独具匠心”为研究策略,是其“史识”之体现。
“大道多崎,音乐史应该是一门大道,多崎是它的本质”[注]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6页。,正基于作者对多元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容纳胸怀,才使得其宽容治史理念在书中得以显现与延续,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日趋完整的结构体系,也折射出作为年轻学科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在多元化的大环境下旺盛发展的趋势。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