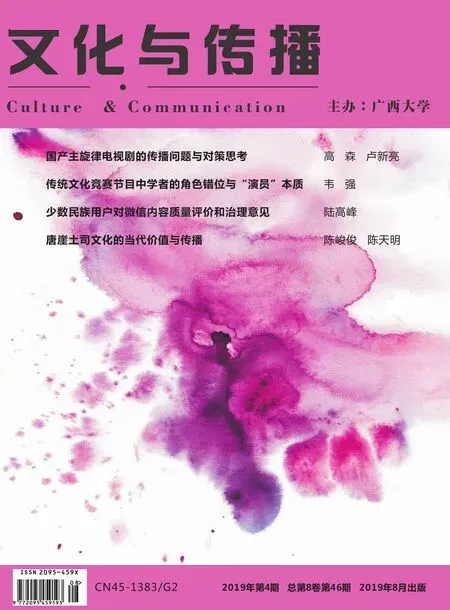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伦理
——以《蓝》《白》《红》三部曲为例
周星宇 袁智忠
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在1993年到1994年这一期间创作的影片《蓝》《白》《红》三部曲虽各有侧重,但也都是关乎人类社会存在、生命精神欲求的伦理思考。《蓝》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它表明了“人格缺陷”对自我觉醒的特殊影想,是三部曲共同的潜在前提,同时也饱含着对“自由伦理”的社会吁求和个体假设。《白》是失衡文本的突出表达,是反映背负精神包袱的个体面对生存抉择的矛盾化阐释。《红》无关对错,是关照个体生存,守望幸福自我,回归人道主义关怀的人间大爱。影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依靠其理性和良心,根据目标和法则,独立感官冲动和爱好,决定了主人公生活的能力”。[1]基耶斯洛夫斯基给三部影片的主人公都赋予了“人格的缺陷”,这种广泛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内的精神内容首先为“三部曲”的伦理叙事提供了艺术前提。
在“三部曲”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善于去假定社会内容,故事在极度抑郁的基调下依然藏有讴赞生命的主线。《蓝》《白》《红》都是融入进“生存悖论”和“个体重构”的叙事文本,也都是涵盖着“自由伦理”和“人格缺陷”的艺术内容。在影像的空间内,基耶斯洛夫斯基假定了另一种社会现实的可能,镜像了具有缺陷性人格个体的生存样态。一定意义上,其作品的特定叙事伦理表达也是对社会道德层面的“可能性”展现。这种“可能性”的艺术隐喻是作用于生命意义本身的诗性美学表达,其对艺术空间文本的“可能”探寻,也是对现实伦理内容的“可行”追问。
一、“生存悖论”的个体无助与形成原因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部曲”在直观上看来,光影与色彩的配合运用是他影片能够切身让观众感受到的显著特性。其影片中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如象征悲伤的蓝色、表现冷漠的白色、引申纯情的红色等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思想叙事的重要标志。并且我们熟知,起源于尼德兰的红、白、蓝等三色的旗帜也正是许多欧洲国家国旗中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然而,基耶斯洛夫斯基并没有让他的作品回归于与之相关的宏大政治叙事,甚至在影片的思想表达上还刻意的回避继而重构了新的艺术命题。他为那些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文明注入了个体的生命元素,在质疑社会的发展价值、反思人类现存状况的同时,也勇敢的解构传统群体价值、直面的探讨个体“生存悖论”的内容。
个体的“生存悖论”是依托“人格缺陷”而产生的。心理学意义上,普遍存在的“人格缺陷”有别于病态呈现的“人格障碍”。“人格缺陷”是个体人格特征相对于正常而言的一种亚健康状态,多与黄、赌、毒等恶习彼此相关或互为因果。这种介于人格健全与人格障碍之间的特殊状态,实质上也是一种不良的人格发展倾向。个体的抑郁、自卑、怯懦、孤僻、冷漠、悲观、依赖、敏感、自负、自我、多疑、焦虑或对人格敌视、暴躁冲动、破坏等,都是人格缺陷的不良心理呈现。个体的“人格缺陷”内容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活动效率、有碍正常人际交往,同时也会给个体精神空间蒙上消极、阴暗的色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艺术时空,《蓝》《白》《红》的基调十分突出。影片中蓝色是难以抉择的忧郁、白色是无法权衡的无助、红色守望自我的苦痛。并且,让人忧郁、难以取舍、无法承受的“蓝”一度是贯穿于三部曲始终的内容。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历史和政治反复强调的绝对自由,也许正导致了个体的迷狂无助和无所适从,大多数人都在弱化个体体验的过程中掉进了丰裕物质时代下社会伦理精心编造的陷阱。社会的舆论使得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了历史记忆下的人类自由,但自我的真实情感体验却一度重压于每个普通人的胸口。
在《蓝》中,当偶然的车祸导致朱莉失去至亲,家庭的破灭在带给她伤痛时也让她彻底卸下生活重担。朱莉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便其丈夫是著名音乐家,但国家也并不能“指导”朱莉重新生活。朱莉仍要重新思考她的“生存原则”、面临他的个体选择。朱莉负担的完全缺失,导致她本人成为了一个半真的存在,任何事情在她眼中都流于了无意义的“自由”陈述。《蓝》的个体无助呈现,也是“囚”的自我真实体验。从社会角度看,也正是情感和记忆的长期固着和不对等造成了这种“人格缺陷”。并且,也正是这种“人格缺陷”使得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失去了自我的精神信仰。影片《白》的卡洛和多米尼克一度面临自我价值和现实生存的考验,他们在自我追寻的路上受权、色、情、欲等多重因素影响,也陷入到了充满悖论的生存状态中。剧情中纯洁爱情的背后也潜藏着每个个体的迷失和伦理抉择,这也或多或少的展示了现代社会的生存荒诞。当夫妻情感在利益面前成为了“性满足”和“金钱”的一种利益交换,最终沦为互相“报复”的手段,影片中多次闪回出现的温情婚礼镜头就在整体的主线对比中构成了基本的情感悖论呈现。与前两部不同,《红》更侧重呈现个体的精神空间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真实状态,这种生存的悖论和个体无助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既定伦理导致的。主人公瓦伦蒂娜总是与近邻奥古斯特遗憾错过,影片中的她尽管满怀希冀,但夜阑人静其也只能独守空房,将男友米歇勒的红色夹克抱在怀中。社会的发展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却也加剧了人与人之心灵的疏离。不论是瓦伦蒂娜和米歇勒,还是片中瓦伦蒂娜偶然认识的老法官,抑或是瓦伦蒂娜抱憾错过的近邻奥古斯特,都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人际失衡和生存伦理的失范。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许多电影中,大多数的故事都讲述了人身上存在的缺陷。[1]《蓝》《白》《红》的主人公都是具有“人格缺陷”的个体,他们的遭遇使得自己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长期面临自我的矛盾选择,不断的进行着潜在的个体思想重构。这不仅是影片整体叙事和“生存悖论”得以延续和呈现的前提,也是确立影片基调,反映个体无助的重要内容。
二、“自由伦理”的文本缺陷与现实之问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文本叙事总是服膺于其艺术时空的交合,在完满呈现“人格缺陷”的同时,“自由伦理”的观念也交替其中并不断参于着影片的主观叙事和文本表达。直面的探讨《蓝》《白》《红》关于“自由伦理”的呈现,是基于现实伦理的发问,毕竟肉体依然要存活于现实之中。从社会现实意义上看,“三部曲”的“自由伦理”缺陷在于:在具有偶在性的现实生活中,人并不能够充分证明个人“自由伦理”意识的存在内容。并且,在私人的情感中,人类也不一定能够充分的享有自由理想。换而言之,每个个体的生存空间、生活样态都不同于他人,它是有着十足的合理性和偶然性。我们对于“自由伦理”的误判,往往是因为混淆了现实和艺术的边界。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没有人确切的知晓对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3]在充满“自由伦理”的叙事下,《蓝》《白》《红》中的色彩都不再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时代隐喻,也不再作为宏大的社群“自由”的象征,而是着重从去寻求和表现个体追随自我理想道路中的艰辛旅程。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朱莉的痛苦实质上是来自于其自我的“人格缺陷”与美好生活理想的差距。《蓝》的“自由伦理”叙事围绕朱莉的个人命运展开,通过朱莉追求自由理想的过程,我们也可以透析人类生活的“自由伦理”矛盾。在影片《蓝》中,朱莉最终未能够找到了“个体自由”或是“生存原则”,她一直在没有结果的自我抉择中悲惨徘徊。影片的叙事依托于朱莉寻找“个人自由”的故事,也正是因为影片伊始就让朱莉脱离了现实家庭的社会关系束缚,才使其个人的“自由伦理”意识在慢慢觉醒中架构和呈现了整个影片的叙事完满。在《白》的故事呈现上,影片也将对“真”“善”“美”的终极叩问置入到了家庭荒诞剧式的虚空中,个体出于自身无奈和自我欲求不得不向“他者”妥协。整个影片在闹剧式的呈现下直面探讨婚姻伦理价值,卡洛尊严曾被践踏处于生死边缘、多米尼克由主动离婚变成被动求爱,在这场“性能力”的比拼中无关胜败,夫妻双方都身处毫无伦理依托的生存悖论之中。虽然直面社会偶在,很多时候男性主人公个体落魄、痛苦、甚至失去尊严都是服膺于现实的被迫而为,但是在“自由伦理”的语境下,也都是从属于个体生命选择和基本人格缺陷的内容。《红》亦是如此,社会大环境中的瓦伦蒂娜从属于群体规约,参与着自我选择却又无时不刻的限制着自我的真实情感。个体带着过去的“包袱”圈定着他者的言行,夹杂人心疏离、回归于孤独苦痛,而在瓦伦蒂娜照顾被自己撞伤的老法官的牧羊犬时又让影片回归于博爱。主人公的主体性情在剧情内容的“碎片”呈现上来回多变反复,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自由伦理”在面对“现实伦理”的必然波动。当个体生存的选择在多种认知并存的迷茫中无所适从,最终也必然压抑心灵绝对自由,继而回归到社会大环境之中。个体的绝对自由在现实社会无疑是“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是现存伦理的无价值诉求,但电影本就擅于造“梦”,“三部曲”在故事的文本架构上,就已经将主人公推入到了“自由伦理”的虚空。
影像的世界是时空复合、时间延续的世界,“自由伦理”是一种相对社会现实伦理而言的意义探寻。在复合的、延续的艺术世界,个体长期拥有着绝对的主体自由性和社会流动性特点,但它也仅仅是能够存在于特殊的文本表达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叙事是想寻求一种艺术时空的可能,它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艺术性,同时也有其表述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三、“人民伦理”的叙事样态与矛盾徘徊
在影片叙事上,基耶斯洛夫斯基为了塑造“自由伦理”下迷狂和难以抉择的主人公形象,甚至直接让主人公陷入进“社会伦理”和“自由伦理”双向无果选择中。人的痛苦往往来自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愿望之间的差距,自由主义伦理承认这种人格缺陷带来的人性的苦恼是存在的。[4]《蓝》中的朱莉曾经砸坏了护士办公室的玻璃,甚至想服药自杀,但在故事叙事设定上,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打算让她自杀成功。《白》中的卡洛男性尊严被践踏,深感自身卑微,几欲寻死的他最终却也逃离故地,最后成为地产老板,为影片的第二阶段叙事提供了开篇保证。《红》总是生不逢时,总是在面临重要抉择偶然错过,总是在应然的巧合中戛然而止。这些情节都作为影片的重要叙事策略,使得“三部曲”中的主人公精神陷入进“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的双重矛盾中。“三部曲”的主人公在寻求私人情感自由上的失败,在“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上的矛盾徘徊也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最终想要表达的内容。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到朱莉时,谈到:“没有过去!她决定将之一笔勾销,即使往日又重现,他也只是出现在音乐中。看来你无法从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完全解脱出来。你做不到,因为在某个时刻,一些像是恐惧、寂寞的感觉,或是朱莉经历到被欺骗的感觉,总会不时浮现上心头。”朱莉的受骗让她改变,令她领悟到自己无法过哪些自己不想过的日子,那是属于她个人的思想空间。的确,个人情感在个体的内心深处,那最为属于自己的领域无不昭示着人的愿望有限和欲求无限。这在《红》中也有十分突出的呈现。当影片的老法官偷听和窥视邻居生活,被瓦伦蒂娜斥责却更加怀疑人心无信任可言,停留在“自我意识”中的他尽管曾经作为法官、作为正义的界定者也已经模糊了伦理的边界,进入到了自由伦理的虚空。这也表明被他者违背“人民伦理”伤害过的人,往往在精神空间总是回归于个体的自由想象。“自由伦理”是因为逃避现实而产生的一种个体倾向,其主体思维形式可能存在趋同但个体行为却是因人而异。
“三部曲”的主人公们在“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的夹缝中寻找自身价值,尽管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其作品中都没能给出是否找到的明确答复,或者说本身作为纯粹的艺术探寻就不可能存有答复,但其中被创设和诗化的“崇高”美学表达却也起到了撩拨观众内心“共情”的作用。艺术空间可以将现实生活无限拉伸、压缩甚至颠倒或解构,而双重规约下的矛盾伦理观从现实意义上看已经是无果的探究,但从艺术的理想空间上看却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参与现实比对的方案。在充满生存悖论的叙事下,《蓝》《白》《红》中的色彩都不再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时代隐喻,也不再作为宏大的社群“自由”的象征,而是着重从去寻求和表现个体追随自我理想道路中的艰辛旅程。
如此看来,“三部曲”中的个体都追寻情感自由,都对美好生命满怀希冀,但是,个体无法摆脱生活的创伤,个体也将濒临精神的死亡。基耶斯洛夫斯基对自由价值观的怀疑,并不是从政治和社会基本原则的角度加以思考,而是从个人的在体性缺陷来深入的体察个体脆弱。《蓝》中的朱莉、《白》中的卡洛夫妇、《红》中的瓦伦蒂娜和老法官等都是在没有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的自我追寻中独自徘徊,“三部曲”呈现“自由伦理”,但每一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没有一刻真正的进入到“自由伦理”的时空之中。他们直面选择,却也麻痹自我或不参与选择或被迫选择。
实质上,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热衷于交代影片故事性的完满,其碎片化、情绪化的内容表达总是在影射人物的内心孤独与精神迷茫,不遗余力的诠释着孤独个体的生存悖论和双重道德的艰难抉择。他是想将主体的性情嫁接进艺术的时空,让主人公的经历避开传统叙事,去寻求他作为导演本身的“自由”意志。
四、结语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其三部曲中,《蓝》贴近真实、回归生活,《白》和《红》一度延续、阐发并不断深入的诠释着颂赞生命的主题。作品中所强调的生命道德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带有着人性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观,个体间的残缺、恒在关系的疏离、生命本身的偶在都是其碎片化情感悖论叙事中相互交替、相互作用的内容。“三部曲”的伦理叙事告诉我们人选择生活的能力与生俱来,而也正是探索和运用这种能力的艰辛过程构成了人的本质。处在社会生存空间内的每个个体都终究要直面不同的人生抉择,尽管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意识并不都是明朗的,但意志自由却也是一直隐匿于每个个体的生命之中。
不论是对“人格缺陷”由来的探究还是对“自由伦理”价值趋向的解读,其都无一例外的最终要指向自我意义终极判断。倘若要使得意识回归于行动,就必然要给个体留有一个“寻求情感自由”的实际理由,而这也能够为接下来的“自由伦理”叙事做铺垫。“自由伦理”的叙事衍生的艺术空间多半是虚构的、过度理想化的产物,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叙事的虚构是更高的生活真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伦理观念总是凝结在“人格缺陷”的伤痕叙事中,“自由伦理”的叙事在极端化剥夺了个体信仰后甚至已经沦落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命抉择。“三部曲”的主体叙事善于捕捉真实生活中人类灵魂的羽毛,作品是利用“人格缺陷”塑造了精神个体的形象,援引“自由伦理”架构了艺术时空的文本,回归“诗性自我”诠释了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往往藏匿着不同的隐喻,浓厚的纪实性终归有别于昆德拉幽默式的自由主义伦理思想。
毫无疑问,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人类基于当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创设和约定的一种善恶标准,很大程度上它利用舆论限制着人类的社会意义上的“不当”行为,是一种近似于“社会契约”的存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由社会真实的记录转向艺术叙事的哲思,“三部曲”通过镜头的灵活叙事、光色的完满配合将“个体化的叙事”糅合进了“自由化的伦理”。依托个体的人格缺陷,“三部曲”呈现“生存悖论”、彰显“自我意志”、假定“伦理自由”、诠释“诗性自我”,甚至传达着人类自我选择而不得不进行精神支配的基本理念。“叙事伦理”自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伦理”标准,自由个体在艺术的空间内往往会被赋予进超然物外的合法性。“三部曲”的文本表达,个体主人公贴近自我感受、回归生命本身,普遍追寻自我意志。这种自由叙事的伦理表达尽管在艺术层面上回避了普世通用的现存价值,但究其实质依然是一种抚慰人心,回归特殊样态的伦理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