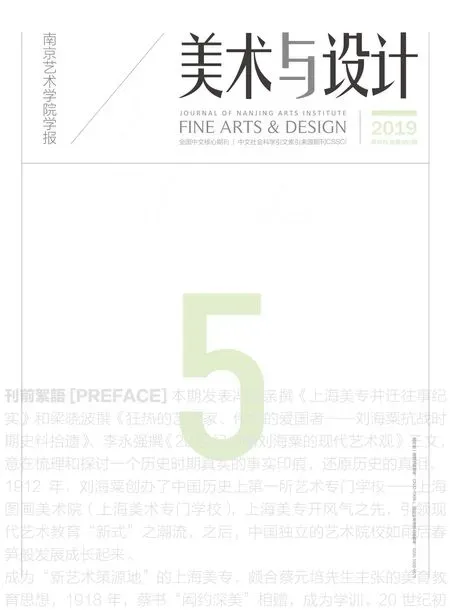从私密文化再到公共象征:美洲非裔艺术“物的生命史”研究①
罗易扉(浙江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物”随着时间其身份随之发生变迁,宗教之物作为神与人的联结,凝结了物与人的互融关系并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因此,宗教私密之物携带着一个地域及一个时期的集体记忆,在时间进程中随着国家话语从而演变成国家公共象征。在当代美洲非裔艺术物质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体现了一种典型方法论,即“物的生命史”方法。此外,学者们纷纷围绕“国家认同”主题讨论物的再非洲化过程。采用此类研究方法及思潮的学者中,以欧美艺术人类学学者戴维·布朗、罗杰·罗卡及玛雅·乔瓦瑟为代表,他们采取人类学方法并选取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以观察所要研究的主题。作为当代美洲非裔艺术研究的代表学者,他们的研究体现出当代欧美艺术人类学一种思潮,呈现了美洲非裔艺术研究的动态以及人类学对于艺术研究的聚焦。布朗围绕宗教中的艺术及仪式展开研究,罗卡关注艺术与文化之间关系,乔瓦瑟关注非洲研究并聚焦卡波耶拉舞研究。在此,通过学者们英文读本研究,呈现了一种美州非裔艺术典型方法与研究思潮。
一、戴维·布朗(David H. Brown):轻盈的内部
戴维·布朗(David H. Brown),美国哈佛大学杜波依斯研究所(W. E. B. Du Bois Institute)研究员。布朗研究方向为人类学与艺术史,其研究注重结合丰富社会史料,采用物质文化与考古学相结合方法论,通过艺术介质而研究宗教。关于非裔艺术研究,布朗著有《萨泰里阿:非裔古巴宗教中艺术、仪式与革新》[1]与《轻盈的内部:阿巴库亚教社会艺术与古巴文化史》[2]。
(一)萨泰里阿教图像历史性研究
古巴萨泰里阿教(Santería),为流行在古巴地区一种神秘宗教,萨泰里阿教派是天主教与非洲宗教混合体。布朗运用多重方法论,结合艺术史、文化人类学及民族志史方法研究。关于萨泰里阿宗教研究,布朗不仅关注非裔文化中的混合化( Creolization,克里奥尔化)、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以及混杂(Mixture)议题,同样十分关注文化变迁与革新问题。他注重历史性研究,细致考证历史过程中图像新形式变迁痕迹,通过形式变迁巧妙进入萨泰里阿教“革新与传统”议题。
关于非裔古巴宗教变迁与革新的话题,往往是一个宗教敏感话题,布朗所选择的言辞往往是谨慎的。布朗对于萨泰里阿教采取历史性研究方法,对于图像形式变迁历史过程都做了细致考证。他仔细考证当今图像形式中可被认同为古巴萨泰里阿教部分,对于萨泰里阿宗教图像进行真伪辨识。他观察到非洲人及他们的先辈在历史时间中不断发展出图像新形式。在殖民时期,图像中反复出现表现王权、牧师会国王与皇后题材。自古巴后殖民时代之始,非裔古巴萨泰里阿教表现出复杂样态。从组织、仪式以及图像方面均呈现出变迁态势,既表现出与传统一脉相承连续性,也表现出连绵不断新样态。在题材方面,王权题材至今仍然在现代萨泰里阿教中反复呈现,传播并显现着贵族化精神领袖话语、权力与威望。这是权威人群之间通过图像所建构的权利关系网,链接着一套极其复杂权利关系。但是这类图像叙事随历史时间进程也发生变迁,譬如萨泰里阿宗教史中,“王”被不断重新定义。因“新”王是依据“古老”甚至“更古老”一级的“王”来重新确定。在萨泰里阿宗教观念中,年代越久远的“王”越被认为传统并具有原真性,因此也被认为更具备王权气息与威望。从此意义上来讲,萨泰里阿教忠实于非洲约鲁巴(Yoruba)宗教仪式话语体系。布朗在此研究中,与安德鲁·阿普特(Andrew Apter)在《黑色的批评者与君王》[3]中所得出结论一致,他们均认同萨泰里阿教的非洲话语源流。
(二)克里奥尔风格:古巴化图像
作为一名美国精英知识分子身份布朗,在寻找萨泰里阿“源头”之旅中,日渐对于混搭与融合风味的克里奥尔风格研究清晰起来。最终他将此种风格确认为一种“纯粹非洲”仪式与物质文化,布朗将当代萨泰里阿中王室图像风格称为“克里奥尔风格”(Creole taste)。
布朗运用变化丰富图案研究,在古巴与美国新泽西州寺庙与南卡罗来纳的奥约图恩吉(Oyotunji)村田野调查,采集丰富革新之后图案。通过图像比较研究,他发现这类图案类似尼日利亚约鲁巴王国图案,从实证中他确认图案的非洲源头。然而,在萨泰里阿教仪式中,因选用精致而华丽服装以及天主教图像,这种外部表面“欧化”,往往误导曲解为削弱了非洲传统意味的原真性。当布朗实地考察萨泰里阿仪式与圣坛之后,他在考证中理解了公众原先对于图像误读,公众往往将萨泰里阿图像误读为“欧洲化”图像。田野调查中,布朗的访谈人听闻此观点时纷纷表示惊讶,他们告知布朗那些被误认为“欧化”图像,实际是“古巴化”图像,被访人一致认为,宗教中图像与物源自于他们过去与历史,源于他们的非洲前辈。他们还举出了图像实例来加以证明,譬如在萨泰里阿仪式中,原本采用非洲葫芦烟斗,今日演变改为萨泰里阿盖碗(Sopera),用以象征奥里萨神(Orishas)神圣力量。萨泰里阿盖碗在此作为一种符号之物,从而被赋予了权利指号意义,故萨泰里阿盖碗成为后殖民古巴一种符号象征。
(三)作为“物”的图像:“可用的过去”文化
关于萨泰里阿教研究,布朗不但从其宗教来源、本真性及传统创新这类传统议题出发。同时他还采用了另一种新颖视角,从庙坛图像出发,将图像视做一种“物”来研究。布朗将视作为“物”的图像置于研究中心,将图像关联萨泰里阿教艺术史研究,并关联发生在此空间里行为研究。他不仅讨论宗教物品与图像之间互动关系,同时讨论从事仪式的人与仪式话语之间关系。因此,在布朗这里,空间图像不仅是一种神话存在,更是萨泰里阿宗教意义转换之后代言物。
布朗观察到自19世纪以来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在意识形态利益竞争中,图像逐渐固化为一种宗教符号、仪式乃至组织系统。在萨泰里阿中,王室王位作为一种潜在暗喻符号之物而存在。在布朗这里,作为权力象征的里萨神神殿与宝座,连同存在于此空间之中图像与物品,均是作为权力指号而存在,这种符号之物体现出权利指号意义。在此空间里所存在的有序之物,譬如陶瓷、精美的刺绣、缎袍、巴洛克家具与图像,这些符号之物作为奥里萨神权利指号而生产意义,图像在变成了权利指号。从此意义上来理解,克里奥尔风格是忠实于萨泰里阿非洲精神。在此空间之中,各类符号有秩序地“诉说”着属于萨泰里阿的宇宙观。无论是“克里奥尔风格”抑或混杂巴洛克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共同影响萨泰里阿中仪式与宇宙观的变化与革新。自始至终布朗保持一种新视角,从非裔散居文化研究来观看萨泰里阿宗教之物,将文化视作一个潜在领域与“可用的过去”(Usable pasts),从而文化引导行动者生产出新形式与文化认同。
二、罗杰·罗卡:神物与纪念之物
罗杰·桑斯·罗卡(Roger Sansi-Roca),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系(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学者。研究方向为人类学与艺术理论、人类学与文化政治、人类学与历史,关注非裔巴西(Afro-Brazilian)宗教、巴西巴伊亚(Bahia)文化政治与艺术、黑大西洋(Black Atlantic)神物观念与巫术、巴塞罗那当代艺术与文化生产政治研究。罗卡研究领域涉及话题广博,不仅涵盖当代艺术、巫术、神物与文化政策,还讨论关于事件、纪念碑、礼品、金钱、身体及神相关话题。罗卡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与巴黎大学,先后学习人类学、历史与艺术专业。博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师从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詹姆斯·费尔南德斯( James Fernandez)及曼努埃拉·卡内罗达库尼亚(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博士期间关注现代非裔巴西人艺术与文化研究。其田野地点多选择在巴西巴伊亚州进行,研究围绕两类议题,其一为关于非裔康东布雷宗教(Afro-Brazilian Candomble)物质文化及宇宙观研究,另一议题为关于葡语大西洋(Lusophone Atlantic)巫术与拜物教历史研究。在金史密斯学院任教时期,他关注当代艺术与博物馆研究,曾特邀担任当代艺术及博物馆专题方面研究顾问,目前罗卡主要关注西班牙巴塞罗那艺术、政治与客体化问题。
(一)葡语黑大西洋文化空间物质研究
黑大西洋(Black Atlantic)空间区域是人类学家关于巫术研究集中地域,多数学者往往将巫术视作为前现代传统残余,但罗卡却在其专著中大胆挑战了此类观点。罗卡专著《黑大西洋巫术》[4]聚焦早期现代欧洲与二十世纪非洲巫术。他采用广阔历史以及地理视野,呈现巫术与大西洋殖民文化话语之间密切关联。此外,在其专著《葡语黑大西洋文化》[5]之中,罗卡选用另类视角观察葡语系大西洋历史。他将葡语系黑大西洋区(Lusophone Black Atlantic)作为一块整体文化空间,将葡萄牙与巴西作为一体空间,并联系非洲历史与文化生产来进行研究。在这个整体文化空间之中,他发现文化不仅是葡萄牙帝国工程实施结果,也是不同殖民文化混杂塑造的一种结果。
关于物的魅惑以及礼物交换,这是人类学家与艺术家们常常津津乐道话题。从莫斯(Mauss)到超现实主义者,再到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与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物成为理解物与人关系的介质。莫斯礼物理论成为20世纪上半叶艺术家实践重要参照,当代艺术开始重新定义关于物的意义。罗卡在《若姆·希弗拉研究》[6]中讨论艺术人类学三个核心问题,即能动性(Agency)、关系美学(Relational esthetics)以及客观可能性(Objective Chance)议题。罗卡没有采取理论演绎而是将问题具体化,通过个案细节来透视问题。通过当代艺术家若姆·希弗拉(Jaume Xifra)作品进行考证彼此关联三个问题,这是一次人类学家与当代艺术家积极对话与碰撞。此外,在《当代艺术中“莫斯与礼物”》[7]之中,他又对于如何开辟艺术理论与实践新可能性打开了新视域。
关于巴西文化艺术研究专题,罗卡通过不同话题切入巴西非裔研究。譬如“金钱”与“宗教”,在巴西传统社科研究中常被视为联系松散的两个术语,罗卡却在其《“Dinheiro Vivo”:巴西的金钱与宗教》[8]中精彩分析了金钱在巴西宗教中渗透作用。他从古典经济话语出发,围绕全球化、现代性介质以及流通多重视角来展开讨论。他清醒批评了将巴西新五旬节教派(Neo-Pentecostal)教堂作为金钱神物膜拜社会现象,不能将巴西新五旬节教派挪用金钱简单理解为经济目的,而是隐在携带着基督教国家政治工程意味。他指出,在现代性话语中,民族国家被日益边缘化,故民族性建构仍然在巴西新五旬节教派工程中占有核心地位。
(二)非裔康东布雷宗教物质文化及宇宙观研究
在上个世纪末期,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Candomblé)之物及巴伊亚非裔宗教,其公共价值经历了剧烈变化。罗卡研究兴趣广泛,宗教很早进入了其宽阔研究视野。罗卡在专著《石头的隐秘生活:巴伊亚康东布雷宗教之物的历史性、物质性与价值》[9]之中,他选取了不同寻常的宗教物质“石头” ( otã )作为研究对象。罗卡选取其中一块“神圣”石头深入追寻神石生活历史痕迹,从而获得“神圣”石头特殊日常生活意义。这块石头具有一部变迁中物的社会生命史,起初作为“神物”存放在一所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房子里,之后作为宗教“巫术”石头被警察追踪。此后又放置在博物馆展览成为“展览之物”,近期又因一次政治家行动,神石又作为“非法之物”撤出博物馆展览。因此, 这块宗教之物“石头”,经历了一部从“神物”——“巫术”——“展览之物”——“非法之物”身份变迁的物的生活史。在这个研究中,罗卡提出一种观念,即物的历史与物质性,为理解物的生活史及能动性之关键所在。《神物与纪念之物:二十世纪非裔巴西艺术与文化》为罗卡另一宗教专著力作。[10]一百年前,巴西康东布雷教仪式曾作为巫术及罪恶象征而遭到压制。而如今作为康东布雷教中神物,则被视为非裔巴西人文化艺术作品,并成为博物馆展览物或者作为公共纪念品。物的身份随时间变迁,罗卡将这种特殊之物置于历史、图像、空间与人多重关系中观察。他叙述了神物的身份变迁过程,他们从被警察洗劫的巫术器具,到秘密隐藏的石头,再到公共艺术作品的身份变迁过程。与此同时,与神物发生关系的人的身份也随之变迁,人的身份从恶魔、巫师而变成艺术家、作家乃至哲学家的过程。
这是一次物的物化与挪用之旅,罗卡用一种新锐而不落俗套研究视角,研究黑大西洋地区混杂主义(Syncretism)及巴西文化张力问题。罗卡通过细节穿插分析对于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符号挪用过程,从一种被政府认定为违法恐惧活动,而在20世纪康东布雷逐渐嵌入巴西文化,并成为巴西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此变迁过程反映出了文化“回到原初”(Return to origins )或者“再非洲化”(Re-Africanization)思潮,罗卡认为这是物的一种另类转型,而这正是一种源自大西洋现代化过程果实。
(三)再非洲化:从私密文化到国家公共象征
罗卡在康东布雷物质文化研究中,通过个案追寻物的意义变迁过程。他通过追寻物的挪用以及物化过程,揭开非裔文化再挪用神秘过程,理解非裔宗教物质从宗教私密文化到国家公共文化象征的身份变迁意义。
罗卡在其《神物与纪念之物》专著中,在“制造神圣:神灵、神殿与康东布雷的融合”部分,他研究了作为地点之物的神庙。神庙虽然是一个具体地点,但是此地点已是神圣化之后物的表征,他们作为“神”(Orixá,Deity)与神域皈依者记忆之间联系之地而存在。从这种变化中,罗卡认为这种物与人的互融实际传递了关于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从康东布雷视角来看则揉进了当地集体记忆历史。罗卡调查了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Ketu”宗派出现过程,无论从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看来,还是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领袖看来,这些均是纯粹非洲源流遗产,理应顺理成章地成为巴西民族文化。罗卡论述了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房屋、物以及神圣空间观念变迁,这种变迁可通过康东布雷原始宗教庙宇博物馆中展览之物可显现出来。正如罗卡所叙述,起初这些物品被描述成‘魔法巫术的神秘武器’。[10]86而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各式各样的符号与物被当做艺术品来展览,并且还被认定为国家文化珍宝。罗卡解释了康东布雷原始宗教房屋转化为非裔巴西文化过程,即宗教房屋从半公共空间变成了冥想空间,再通过“生命力量”(Axé,Power,Vital force)场所转变成民族“文化价值”象征。 在康东布雷原始宗教教义中,这些物是不能被观看与言说,因这是对于神物的不敬。而如今,进入他文化价值中物的意义被再生产,这些私密文化转化为国家公共象征。
罗卡认为,这是在过去一个世纪时间里,知识精英人士与康东布雷原始宗教领袖互动的一种结果。人类学家、作家以及画家,他们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皈依者而参与此进程。伴随着精英分子及皈依者观念变化,还有诸多康东布雷原始宗教“Ketu”派高层领袖,一致主张将康东布雷作为“纯粹非洲”(Pure African)文化而崇拜。罗卡并将此拓展到现代艺术与非裔巴西文化中讨论,他观察到了大众在追求异国情调之中一并携带着政治意味。在瓦尔加斯(Vargas)时期,随之民族主义文化自觉意识上升,国家需要携带“进步”与“原真性”(Authentic)因素的巴西文化代表。在独裁时期,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房屋被作为非裔巴西艺术代表,而其他所谓为旅游者制作“流行”风格手工制品,则不被认可是艺术而视作手工品。通过此时期对于艺术与手工品定义,罗卡在此指出了当代艺术与传统非裔巴西艺术观念之间冲突。近期,五旬节派批评将康东布雷原始宗教神物公开,试图动摇将康东布雷原始宗教作为国家认同观念。此外,罗卡通过“非裔巴西文化的再挪用”过程观察出,非裔巴西文化复兴体现了当代巴西“盛行讨论附着于物上的文化价值新思潮”。[10]188因此,罗卡通过围绕物的价值变迁议题,展开讨论关于物化、挪用、文化混杂以及巴西文化变迁问题。在此,罗卡从政治及社会历史视角观察,清晰地分析了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非洲康东布雷原始宗教的价值与信仰变迁过程。
三、玛雅·乔瓦瑟:卡波耶拉的隐性历史
玛雅·塔尔蒙·乔瓦瑟(Maya Talmon-Chvaicer),加拿大多伦多独立学者。乔瓦瑟在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取得博士学位,乔瓦瑟关注非洲研究并聚焦卡波耶拉舞(Capoeira)研究,代表作为《卡波耶拉的隐性历史》[11]专题研究。
(一)巴西卡波耶拉:一半舞蹈与一半战斗
巴西卡波耶拉为一种糅合武术、杂技与仪式多重元素于一体的战舞,一半融合舞蹈元素,一半融合战斗元素。卡波耶拉具有一套奇特配合舞蹈动作音乐,主要乐器为一种单弦弓状乐器称为比林抱弓弦琴,玄琴配合阿塔巴克落地鼓与潘得鲁手摇铃鼓节奏。刚果学者奇亚·布恩赛奇·伏奇奥(K. Kia Bunseki Fu-Kiau)认为“Capoeira”词语源于刚果语“Kipura/Kipula”,在刚果语中意味“跳跃”与“挣扎”。但巴西学者多认为此词源于巴西本土原住民图皮人(Tupi)语言,意味“林间空地”。但是在葡语中,此词语意味“鸟类居巢”,暗喻囚禁奴隶设施。
卡波耶拉与巴西黑人历史的关联源远流长,16世纪时由巴西非裔移民发展起来。虽然有百年历史,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被合法化,并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卡波耶拉虽源于非洲,但融入了浓郁巴西本土原住民文化气质。卡波耶拉在蓄奴时代体现了奴隶反抗精神,奴隶们在休息时候歌场与跳舞,保留了原始宗教仪式形式。黑人奴隶们将武术与舞蹈相糅合并形成卡波耶拉战舞雏形,奴隶们围成一个圈,在音乐伴奏下,成对演练一种源自非洲大陆格斗技巧。16世纪时,葡萄牙人从西非地区抓捕大量黑人奴隶,并送往南美洲巴西地区。此地区非洲移民多来自莫桑比克、安哥拉与刚果,且多为班图族后裔。自1624年到1630年之间,荷兰入侵巴西,很多巴西农场因此倒闭。1888年,巴西奴隶制度废除,大量奴隶恢复了自由身份。在后奴隶制时代时期,卡波耶拉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卡波耶拉体系从地下转为正式格斗训练。1892年,新成立巴西共和国当局又制定了新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卡波耶拉训练活动,卡波耶拉再次从公开转向地下,但在1930年禁令解除。此后,宾巴(Bimba)发展了卡波耶拉。当今卡波耶拉再次发生价值变迁,演变为巴西国家运动。因其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健身价值,并形成了今日卡波耶拉战舞艺术节。卡波耶拉具有几大流派之分,安哥拉卡波耶拉(Capoeira Angola)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较传统形式卡波耶拉,安哥派较注重舞蹈的宗教性,承袭正统舞步。而耶吉欧纳卡波耶拉(Capoeira Regional),较偏向于武术元素。当代卡波耶拉(Capoeira Contemporânea)则融合这两种气质,融合当代舞蹈与音乐。
(二)卡波耶拉的隐性历史
巴西卡波耶拉近年来在欧洲与北美地区越来越流行,学术研究也因此风尚而增长。从这方面来看,卡波耶拉与非裔巴西另一种传统康东布雷仪式有相似之处,他们均与“非洲”有着千丝万缕的源流关系。在关于西非研究中心文本之中,乔瓦瑟的文本则体现了一种异质性。她采用与众不同的视野与问题研究,她从卡波耶拉的观念、实践、符号以及巫术成分来观察,发现不仅体现了其非洲源流,同时体现了非洲移民殖民遭遇,并体现了欧洲与非洲文化碰撞。乔瓦瑟在关于卡波耶拉历史研究方面,提出了一套新解释与观点。从跌宕起伏的卡波耶拉历史演变进程来看,首先这是一种诞生在作为殖民地巴西街道上现象。卡波耶拉曾被理解为一种自15世纪以来在北美大西洋地区巫术话语系统,在传统巴西观念中也被理解为一种“mulatto”游戏,种种理解体现出卡波耶拉定义其所携带的含混性。卡波耶拉的身份是一种游戏(Jogo),还是武术?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舞蹈?是一种战舞还是一种战斗?抑或涵盖这所有成分的定义?是什么隐形力量造就了这种含混歧义?它是如何从一种定义滑落到另一种定义?它如何从表示勇敢到表示争斗,从表现挑衅到表现反抗?诸如此类的系列神秘面纱,乔瓦瑟在其文本中给出观察与解释。她观察到在这层面纱之背后,事实在各个历史时期,卡波耶拉自始至终均夹带着非稳定性含混定义,种种定义与十九世纪里约热内卢局势亲密关联。在左翼保守党看来,舞蹈的人被视为国家与奴隶动乱中的暴徒。[11]84-85在共和党看来,卡波耶拉群体被视作是敌人。最终在1890年,这种“游戏”在里约热内卢被新共和国一度禁止,故卡波耶拉群体被流放到遥远岛屿之上。[11]74卡波耶拉群体人员身份复杂,不仅包括非裔奴隶,还包括自由黑人、白人以及黑白混血儿,甚至还有来自精英人士,比如伯爵的儿子。[11]74因此,乔瓦瑟认为,对于卡波耶拉研究不能采用简单二分法。正如不能将卡波耶拉群体被简单区分为非洲人或奴隶,或将卡波耶拉性质简单区分为“黑人游戏”或者“弱者的武器”。她透过隐形的表征,观看到了卡波耶拉舞动身影中的隐形历史。
(三)卡波耶拉种族政治中的含混意味
乔瓦瑟对于卡波耶拉的历史性研究,显示出19世纪巴西种族、阶级、奴隶制以及移民复杂政治性。她清晰指出,对于“将卡波耶拉简单认同为一种贫穷黑人反对白人精英反抗形式”[11]74,这个观念我们是需要持以谨慎态度。毫无疑问众多卡波耶拉群体主体为穷人和黑人,但是卡波耶拉在各个历史时期定义不一,并非在所有时期皆是作为一种反抗工具。若用简单二分法来对卡波耶拉做一个绝对划分,则减低了卡波耶拉历史复杂性。如今,卡波耶拉渐渐地成为一种全国性运动,甚至在巴西军队中也练习。此外,巴西巴伊亚(Bahia)混血儿梅斯特雷宾巴( Mestre Bimba)[11]11-15将卡波耶拉发展为一种武术,这种风格被人们称为耶吉欧纳卡波耶拉或区域性卡波椰拉。在同一时期,梅斯特雷宾巴将这种风格又发展为安哥拉卡波耶拉,为了和耶吉欧纳卡波耶拉有所区分,减少了卡波耶拉的身体形式以及攻击性元素并添加舞蹈元素。此后,安哥拉卡波耶拉渐渐在精英人士与艺术家之中流行起来。自此,巴西境外异域国家也逐渐流行这种异域风情舞蹈。因此,在如此复杂话语体系下,将卡波耶拉描述成非洲奴隶为了抵抗奴隶主的运动则需要持十分谨慎态度。因此,乔瓦瑟认为帕斯蒂那(Pastinha)的话语是一种“神话”。[11]152-153她认为需要去发现卡波耶拉背后“隐形的历史”,去发现隐藏在卡波耶拉深厚“非洲象征”。乔瓦瑟正是通过她的文本去寻找一种隐藏的真实,通过敞开卡巴耶拉隐形的历史,来观看巴西迷人而复杂的种族政治。
四、作为“武器”的艺术:从纪念之物、战斗再到国家象征
无论是戴维·布朗笔下的萨泰里阿宗教图像,还是罗杰·罗卡笔下的非洲康东布雷宗教“神石”, 亦或玛雅·乔瓦瑟关于卡波耶拉战舞研究。这些物的原初意义在历史不同时期发生更替变迁,这些物在最原初的宗教意义之上,经历了从“巫术”“纪念之物”“展览之物”“战斗”“舞蹈”多重复杂身份。在国家话语之下,均纷纷经历了从宗教私密之物到国家公共象征的历程。学者们采用了“物的生命史”方法论,围绕“国家认同”的问题意识展开美洲非裔艺术中物质文化研究,体现了欧美学者对于美洲区域再非洲化研究思潮。
(一)物的社会生命史:非裔艺术研究典型方法论
今日非裔艺术典型方法论体现为“物的社会生命史”方法论。布朗、罗卡与乔瓦瑟分别在他们的美洲非裔艺术研究中,通过追踪作为“物”的艺术社会生命过程,去区分同一个“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份及意义,从而去观察作为“物”的艺术所携带的隐性意义所在。
布朗在《萨泰里阿》研究中,运用人类学、史学、物质文化研究以及视觉文化研究方法展开多重论证。布朗对于萨泰里阿宗教图像研究采取图像生命史方法,追踪图像演变的历史过程。从古巴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图像题材及样态做出图像学分析,在图像的社会生命史中观察图像中所蕴含的内部话语,通过图像观察图像叙事中的王权关系。同样,通过图像样态的生命史,追溯萨泰里阿图像风格中非洲源头,并确证萨泰里阿王室图像为克里奥尔风格。他通过严格的图像历史性研究,纠正了原先公众对于萨泰里阿图像的误读,因其表面化符号将之误读为欧化风格。同样,罗卡在其非洲康东布雷宗教研究中,沿着原初作为“神
石”之物的社会生活史痕迹。追踪“神石”从最初的原始宗教房子到最后博物馆空间的流转过程,其身份从宗教的神圣石头到被作为巫术的追踪对象,再到国家纪念物。罗卡通过这一百多年物的流传社会空间,
神石从宗教隐秘冥想空间流转到公共空间展览馆,观看“神石”的意义变迁历程,从而观察康东布雷教的宇宙观变化。作为“物”的“神石”,从巫术到国家象征,体现了非洲艺术从物到艺术身份转变历程。此外,乔瓦瑟对于卡波耶拉战舞研究同样如此。她通过了追踪不同历史时期之中舞蹈形式演变,考察了战舞沧桑历史中的身份变化。考证战舞从地下到合法化的过程,追踪战舞从反抗形式到部队训练内容,从游戏到战舞的舞蹈形式变化过程。她分析巴西奴隶制时期及后奴隶制时期战舞意义内涵变化,从宗教仪式到国家新潮运动的社会身份戏剧性变化过程。乔瓦瑟通过战舞的社会史从而观察战舞社会意义,并通过历史性研究确证卡波耶拉深厚“非洲象征”源头,并论证了卡波耶拉作为一种非裔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混杂相遇。
(二)作为“武器”的艺术:非裔艺术研究典型问题意识
今日非裔艺术研究中亦体现了一种典型问题意识,即将艺术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武器”,成功实现了文化政治上身份认同。体现了今日民族国家独立之后,艺术作为国家认同“武器”,实现意识形态上潜移默化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艺术被视作一种符号与物,视作为国家珍宝与文化。因此,物也演变成民族“文化价值”。
布朗采用奥约图恩吉村图像为个案调查对象,通过图像源流考证并追踪其尼日利亚约鲁巴王国源流,从而论证古巴非裔图案艺术的非洲源流。在田野访谈中,古巴非裔纷纷表示一种认同意识,从图案中认同他们过去的非洲以及非洲前辈。从非裔流散文化来观看,古巴非裔将图案作为一种“可用的过去”文化。从此类型文化中生产出图案新形式,并将图案作为连接“过去非洲”与“今日古巴”的载体,从而生产公众的文化认同意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非裔古巴人图案成为后殖民古巴符号象征。通过萨泰里阿非洲精神内核,完成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在20世纪,康东布雷逐渐嵌入巴西文化,并融入巴西民族文化一部分。罗卡在关于非裔康东布雷物质文化研究中,通过巴西巴伊亚洲及葡语大西洋地区宗教研究,考证宗教与殖民话语之间关系。在此葡语大西洋文化空间中,不同殖民文化混杂并塑造一种后殖民文化。宗教之物也置身于此庞大隐形体系中,潜在于国家文化政治工程中,亦成为文化建构的一种介质。罗卡通过追溯宗教“神石”的社会生命史,完成了神石身份考证过程。观察其作为宗教“石头”,从宗教“神圣意义”,到巫术“罪恶意义”,再到“纯粹非洲艺术”的国家认同过程。当代艺术也同时在过去的民族文化中,在追求异域情怀之中携带着文化政治意味。乔瓦瑟则从巴西种族历史及移民政治的复杂性,追踪巴西卡波耶拉战舞的意义流转。从一种反抗意味的运动演变为国家军队的训练形式,也从地下街道活动摇身一变为国家运动。因此,卡波耶拉的话语体系从非洲奴隶演变为光明的国家话语层面。桥瓦瑟发现了卡波耶拉隐形历史面纱与其非洲象征内核,从卡波耶拉的含混性中剥开了其隐藏的真实内核,从而懂得了巴西迷人的混杂种族政治。
结 语
戴维·布朗对于萨泰里阿宗教图像研究采取图像生命史方法,从古巴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图像题材及样态做出图像学分析。罗杰·罗卡在关于非洲康东布雷宗教研究中,沿着宗教“神石”的社会生活史痕迹,追踪其从原初宗教房子到博物馆空间的流转过程,观察其从宗教的神石到巫术再到国家纪念物身份流转意义。玛雅·乔瓦瑟关于卡波耶拉战舞研究,通过战舞的社会史从而观察战舞社会意义,并通过历史性研究确证卡波耶拉深厚“非洲象征”源头,并论证了卡波耶拉作为一种非裔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混杂相遇。从布朗到乔瓦瑟,今日美洲非裔艺术典型研究体现了一种思潮。学者们采用典型方法论,即物的社会生命史方法,并选取“国家认同”为主题的问题意识,讨论了物质从“纪念之物”到“战斗”再到“国家象征”过程。此变迁过程映射出美洲非裔文化“回到原初”与“再非洲化”过程,正是在此非裔文化的再挪用过程之中,非裔宗教物质从宗教私密文化到国家公共文化象征,从而实现了非裔文化国家认同意义。因此,作为“物”的艺术,以及作为“神圣”的文化空间与地点,成为神圣化之后物的表征。作为“物”的艺术,成为神的空间与人的记忆之间联系之地。物在此成为物与人的互融关系,并融进本土集体记忆,从而成为身份认同的精神内核。私密空间中的宗教之物变迁为博物馆中展览的公开文化。因此,原本在宗教空间中不能言说的私密力量,文化挪用后物的意义被再生产。物从冥想私密空间进入国家公共文化空间,从而实现了从宗教之物到国家认同符号象征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