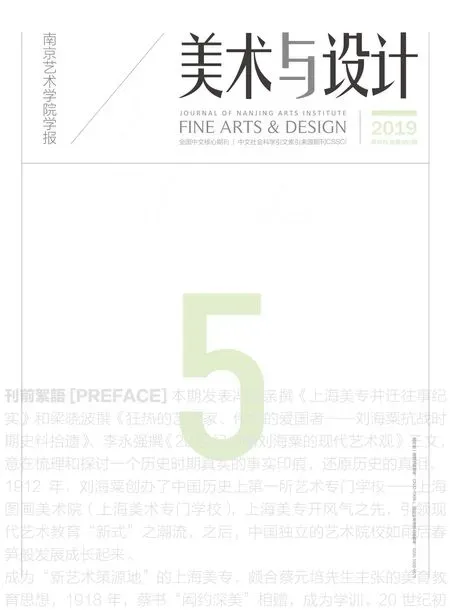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主题类型及解读模式①
曹毕飞(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窦 艳(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引 言
叙事性艺术首饰隶属当代艺术首饰(美国称Contemporary Art Jewelry或 Contemporary Jewelry,欧洲称Contemporary Studio Jewellery),涵盖纯装饰美学、技艺研究、材料探索以及不同观念的集合方向研究,主要 “通过视觉表达来讲述一个具有真实或者想象的故事”[1]。当创作者或艺术家(以下统一采用创作者)想把自己的故事讲述并亲手制作在首饰作品中,叙事性艺术首饰自然产生。叙事性自古以来就隐含在首饰的不同功能中,伴随这些功能显现潜藏的故事。无论是最原本的装饰功能,还是后来赋予的身份、地位、财富、性别以及宗教功能等,首饰永远承载着与佩戴者息息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一个个故事,不断被熔炼在首饰中,代代相传。后人不仅从首饰本身阅读这些潜在信息,也通过文学诗词、民族传说、先人口头传承等方式讲述隐含在首饰中的故事,数不胜数。如流传至今的傣族习俗之一,女子成年后都会得到一条祖辈遗传的或父母攒钱订制的银腰带(见图1),蕴含祖辈或父母寄予的美好寓意。
叙事性艺术首饰在当代艺术首饰领域中占有重要份额,归功于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对叙事学的关注与借鉴。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叙事性与人不可分离;人作为当代社会的主体,艺术和设计必然作为人类情感与心灵寄托,承载人的精神与故事。叙事性在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比如视像装置艺术、新媒体数字交互艺术、情感化设计等,都紧紧围绕以‘人’为核心来开展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叙事探索,叙事性艺术首饰越来越在当代艺术首饰领域中扮演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作用。

图1 傣族女子成年佩戴的银腰带
一、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主题类型
正如文学家撰写叙事文本表达思考,当代首饰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也是各自性格、观点与思考的延伸,通过视觉化艺术造型、结构、工艺和材料来讲述每一件作品蕴含的故事。与古典叙事学认为的“创作手段的调整紧紧吸引阅读对作品的全部注意,其最高境界是让阅读忽略创作这一中间性作用使读者直接进入作品”[2]一致,首饰艺术作品也是鼓励观赏者跨越作品本身的创作手段直接感悟作品叙事表达。艺术首饰创作语言可以截然不同,风格特点可以天壤之别,艺术造型可以具象化或抽象化,作品结构可以复杂或简洁,制作工艺可以传承传统或创新科技,使用材料可以昂贵或廉价、自然物或人工造物等,它们最终都是服务创作者对自己生活的特定环境的典型反映以及对世界独特的态度[3],形成不同的主题类型。
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主题类型必然服务于创作者的意图,即“……可以指从诸如表现人物心态、感情、姿态的行为和言辞或寓意深刻的背景等作品成分的特别建构中出现的观点……”[4]。这些观点在视觉化的叙事性艺术首饰中自然以‘人’为核心,基于自我探索、社会沟通及永恒信仰形成自内向外划分形成个人表达、社会政治映射和宗教信仰三个主要主题类型。这三个主题类型也类似叙事文本中的言情——个人情感、明志——社会志向和载道——永恒信仰,形成‘小家’(人与人)、‘大家’(人与社会)与‘出家’(人与信仰)的扩散,并“娓娓道来”不同创作者阐述的观点。
1.个人表达
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个人表达体现在个人情感、个人观点与个人心理活动等方面的视觉化阐述。创作者追随内心表达,选择相应的材料、工艺与造型,赋予不同层次的个人含义,让视觉化首饰作品来阐述一个个故事。这些视觉化阐述以‘人’为主体,来扩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叙事性艺术首饰成为最恰当表现这两类关系的媒介。例如在凸显个人表达的叙事性艺术首饰中,人与人通过首饰产生的视觉语言、肢体接触以及身体印记来进行互动,让互动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最重要的表达手段之一,首饰作品就在这两者的关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中介。细分视觉化阐述,个人情感主要表现在情感追忆、情感释放、内心世界探索等不同内容;个人观点表现在个人对人文、地域、环境等内容的观点表达;个人心理活动则聚焦在心理性别、身份和种族等个人内心探索。当然,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与科技急速进步,人们在短短的人生中生活经历丰富,内心情感的丰富也自然让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个人表达主题更加深入到身份、文化、背景、生活、关系、性别、性以及种族等内容。这些细分主题也相互联系,让叙事性艺术首饰呈现多样化的状态。
比如,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促进了全球人口频繁迁徙、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个人文化表达、身份认同主题作品剧增。一方面,地域迁徙和文化冲突让创作者在对比中更加思考自身母国文化,深刻认识并进行叙事性艺术首饰创作来诠释这一主题。作品《捉迷藏》(见图2)是笔者旅居美国的个人文化表达主题创作,融入儿时游戏——捉迷藏的追忆,提炼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结合传统珐琅烧制来叙事儿时游戏场景,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个人表达主题胸针作品。另一方面,地域迁徙促使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创作者融合两者或多者地域、文化符号进行文化身份认同表达。韩裔澳大利亚籍创作者都正美(Joungmee Do)感悟异国澳大利亚的文化、自然环境,比如丰富的花卉植物与外来生物灰兔,通过韩国传统文化下的镶金技术、窗花剪纸特点结合异国感受,制作出双重文化身份特征的叙事性胸针作品(见图3)。

图2 《捉迷藏》

图3 都正美(Joungmee Do)首饰作品《胸针(Brooch)》

图4 斯蒂芬·萨拉奇诺(Stephen Saracino)首饰作品《哥伦比亚护佑手镯(Columbine survival bracelet)》
2.社会政治映射
与个人息息相关的是整个社会与政治体系。新媒体网络化的当代社会,人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单位,其主体性日益加强,此主题表达多是指对社会状况的反映与反思,牵涉相关的哲学、现象、问题。二战后,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借助电视、网络、视频等媒体,关注国际社会运动与政治变迁日益增加,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与政治问题也就成为创作者主题对象,不同艺术作品成为他们的视觉化宣言,这也验证了“当代艺术实践之内在的观念维度——政治性”[5]。这一阶段,首饰成为挑战公众或者政治性观点的重要艺术表现方式之一,比如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经常收集胸针并在重要政治见面场合佩戴,潜在表达她的政治观点。

图5 《大鱼》
在社会政治映射主题中,社会方面包括人们休戚与共的社会现象、人文事件、环境资源等;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变迁、国际战争、人权主义、政治运动等。细分主题涉及与人相联系的环境、经济、资源、性欲或性向、女权等等。深究起来,个人表达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某些社会性的体现;但是个人表达主题中,更强调个人的独立与内在的发声,而不是群体与社会大范畴的整体反映,所以两个主题没有归于一类。社会与政治映射主题尽管涉及面广,但在当代艺术首饰范畴里,社会与政治主题很难单独成为一个大类别,其主题呈现的强烈叙事性,使得归纳到叙事性艺术首饰当中。
在此必须提及,创作者所居住国家的法律、公众言论自由程度不同,这一类型的作品表达方式也有所区别。其一,社会政治主题的视觉性阐述非常直接,采用与主题相关的直观图像、符号与造型,如美国金属首饰创作者斯蒂芬·萨拉奇诺(Stephen Saracino)的作品(见图4)直指美国校园枪杀事件,反思不同年龄学生的拥枪行为,彪悍地手工制作手枪、子弹等造型,双枪造型互对,形成非常直接地冲突与千钧一发事态,表达彼此都将是持枪的受害者,讲述他对美国‘持枪’这一政治政策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其二,创作者试图隐含或者隐晦表达各自对社会政治的关心或不满,运用相对不冲突、不对抗的图像、符号等,让观赏者猜测意图。这些作品有可能基于创作者个人的性格有意隐含主要意图,反而给予观赏者更多的空间解读。笔者首饰装置作品《大鱼》(见图5),虽然通过浮漂、留学生肖像、各国国旗等非常直接的现成物组合创作出不同尺寸的戒指,来叙述国际留学生为了学业深造这一‘大鱼’的梦想漂泊欧美国家;这一求学生存的社会现象,结合亲身留学美国的经历进行讲述,赋予这一留学群体的人文关怀,也给观赏者更多的空间猜测。当观赏者接触这一类作品时,就像参与了“用艺术代替文本的社会调查”[6]。
3.宗教信仰
作为人类重要的意识形态,艺术与宗教自古就交织在一起,成为人类不断攀援人生终极意义中形而上的基本形态。宗教信仰通过艺术渲染出视觉形态进行传播,发展至今,也成为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一大主题类型。这也归根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叙述形式,它提供了“人类体验、理解、解释世界的方式”[7]。早期宗教信仰的首饰采用固定的一些宗教信仰符号与标记,基督教的十字架、天使造型与佛教的藏八宝纹样等,偏向记录、忠诚与护佑等隐含诉求。当代叙事性艺术首饰有意延伸这一主题,融入创作者个人的生活情感,创作出更加复杂意义的宗教信仰首饰作品。此类主题细分有故事再叙、图像写实、护身符再造、象征性重构等内容。在具体的叙事表达中,宗教信仰直接影响叙事策略与素材,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提供策略与素材给创作者,比如宗教故事、宗教物品与符号,让创作者在创作中再升华对世界的理解;但是基于当代艺术的个性解放,叙事策略或表达不再禁锢于宗教的神圣、符号和威严,而是用来阐述创作者的观念与想法,显示创作者的能动性,也让作品成为分享理解与感悟世界的叙事方式。美国创作者豪尔赫·罗哈斯(Jorge Rojas)吊坠作品(见图6)采用橙黄色硅胶组成了一个大基督十字架形状,侧面925制成出多个小型十字架型围绕着硅胶主体,明显呼吁上帝创造光热的革命信仰。

图6 豪尔赫·罗哈斯(Jorge Rojas)作品《“帕高”一起走吧(Let's Go “Paco”)》

图7 郭新首饰作品《锐变》
宗教信仰主题“中国化”探索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禅宗精神的领悟或外来宗教的“修炼”。作品掺杂人生的智慧,结合传统绘画、书法、图像等文化元素,从当代语境来反映信男善女对信仰、宗教的教义诠释,引发观赏者思考。中国首饰创作者郭新作品(见图7)糅合个人生活经历和基督信仰,从圣经里的故事入手,运用中国民间传统花丝工艺制作出天使的翅膀,黑软陶捏造出类似孕育的形体,类似挣扎缠绕的蛇型,又如黑色的传统书法空灵的笔触,叙事地展现她个人解读人性、神性、魔性之间的战争。作品虽然来源于对宗教信仰的解读但是在材料的方寸之间叙事出宗教思想与个人情感。

图8 主题分类与交织图示
4.主题交织
三个主题彼此相对独立,但是在细分到不同叙事内容的时候就会出现交织现象,很难将每一件叙事性艺术首饰归结到一类内容,而是可能跨越主题界限归结到两类或更多内容中。在交织图中(见图8),创作者在创作中,其表现语言和观念的不断深入,出现无法把控创作主题所属,基于‘创作者’的发射,三个主题个人表达、社会政治映射和宗教信仰形成一个内环,也呈现边界的模糊性;而在初步细分辐射出去的中环上,展开了艺术表现的多元汇合,边界更显模糊;越到外围的细内容则呈现无边界、交叉性的特点。英国首饰艺术家、学者杰克·康宁翰(Jack Cunningham)在其博士研究调研中阐述,欧洲当代叙事性艺术首饰呈现多元化细分主题,尽管这些细分主题涉及大量的工艺与材料、肌理与造型探索,但是主题表达是叙事性艺术首饰的重中之重[8]。这个观点也适用于整个国际叙事性艺术首饰领域,正因为这些叙事主题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让叙事性三大主题类型不断成为艺术首饰中的常青树。
二、叙事性艺术首饰的主题解读
与绘画、雕塑、摄影、实用艺术等艺术门类如出一辙,叙事性艺术首饰对上述三种主题类型以及辐射的细分主题存在着解读或阅读,这是每一个观赏者所具有的视觉基本功能,也正如加拿大文学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对阅读的阐述“阅读,几乎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情人阅读爱人的身体,精神科医生帮助病人阅读他们自己饱受困扰的梦,农民阅读天空的天气”[9];观赏者对图像、物体、人自身都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阅读。在叙事性艺术首饰中,将阅读换成解读,不仅仅是因为观赏者具有阅读能力,而且创作者也经常通过作品名称、材料、尺寸等部分介绍,给观赏者一些作品的文字解释。比如,图7郭新作品名称《锐变》,就间接性解释了作品表达了一种经过炼狱般的改变,这样让观赏者有了一些基本的文字感知,这是很多艺术门类共有的特点。
1.解读模式一

图9 主题解读模式图示
叙事性艺术首饰,存在“创作者-观赏者”解读模式(见图9解读模式一)。这种模式是所有艺术门类的作品主题解读所共有的,具体指:像所有艺术类别一样,创作者完成作品,寄以叙事性故事;观赏者通过展台、展柜、展区等陈列平台对艺术作品进行观赏与解读。“创作者-观赏者”模式类似叙事文本中的“讲述者-阅读者”模式,除去叙事作品本身自带的工艺、材料、造型等创作语言,创作者与观赏者的文化、身份、背景等主客观因素也左右着艺术作品的主题解读。尤其在叙事信息传达过程中,观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生活经历、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出现片面解读作品,是常说的作品解读障碍问题。这种情况下,鼓励观赏者根据实际情况展现各自的不同解读,形成类似或有所不同的解读空间,是艺术作品“引人入胜”的魅力所在。
在这一种解读模式中,由于叙事性艺术首饰主题类别细分的相互交织,让叙事首饰作品本身再添加神秘性,留下很多空隙给观赏者解读。比如笔者作品《威伦道夫的维纳斯》(见图10)摆放在桌面时,观赏者借助作品名称以及作品的材料、工艺等,来进行“创作者-观赏者”模式解读;观赏者可以全方位的仔细观察作品,没有任何其他媒介的介入。
2.解读模式二
叙事性艺术首饰在主题解读过程中有着两个重要点不容忽视,也就形成另外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即“创作者-佩戴者-观赏者”(见图9解读模式二)。其一,叙事性艺术首饰体积小,容量大,赋予观赏者更多的主题类别上细节解读与空间想象。叙事性艺术首饰宛如紧凑的诗歌,是艺术的极简提炼,将创作者思虑后的故事、想法浓缩到让人佩戴的戒指、胸针与项饰等极小物件中。叙事主题借助作品中每一个微小细节,蕴藏着丰富与多元的故事,向观赏者绘声绘影地讲述每件微型首饰的‘一颗米内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这也正是西班牙首饰创作者、学者拉蒙·普伊格·库亚斯(Ramon PuigCuyas)在展览《创作者-佩戴者-观赏者》研讨会主题发言《小尺寸的维度》陈述:“小物件深藏着大思想……我创作小型首饰物件,但是我感觉内在力量巨大无比”[8]54。

图10 展台摆放的作品《威伦道夫的维纳斯》
其二,正是首饰体积小,具有佩戴功能,很多观赏场合需要服从佩戴者的意图,形成“创作者-佩戴者-观赏者”解读模式,让本身丰富多元的叙事性艺术首饰主题解读更具隐晦。这种独特的解读关系是:创作者完成作品,赋予作品叙事性故事;佩戴者根据之间的故事来佩戴,自然而然增加作品新的故事;当佩戴者不同,其佩戴故事与展示部位变化,导致最后的欣赏者糅合创造者与佩戴者双重的叙事再解读。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佩戴者既是作品的参与者,也成了作品的再次“创作者”。这样一种融合时间、解读、参与、再实践和再解读的综合模式,不自觉地让叙事性艺术首饰作品进行了一场集体创作,恰如笔者作品《威伦道夫的维纳斯》(见图11),通过佩戴者再“创作”,重新赋予了作品新的佩戴方法与内涵,让观赏者得到新的视觉体验与作品解读,验证荷兰首饰理论家伊丽莎白·邓·伯斯特(Liesbeth den Besten)的陈述:“首饰异于其他纯艺术门类,当佩戴者佩戴的时候,佩戴者成为移动的展台……首饰是流动的,是身体上的一个标志”[8]24。无论创作者最初阐述如何,加入了佩戴者对作品的第二层解读与再创作,也给叙事性艺术首饰作品带来另外一层含义,让观赏者添加更层次与丰富的解读,这正是当代艺术首饰承载着概念和功用双重作用的结果。

图11 佩戴者‘再创作'作品《威伦道夫的维纳斯》
结 语
叙事性艺术首饰在当代艺术首饰领域里队伍不断壮大是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叙事性伴随首饰功能延续至今,其强大的讲述、评论和宣泄功能在‘以人文本’的社会凸显出重要表达角色。作为‘可穿戴的艺术’,叙事性艺术首饰以丰富多元的主题类型及不同的解读模式,在表达自我、交流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政治问题、传达人文关怀与信仰上起着重要的传递作用。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个性化、情感化的艺术首饰订制市场,叙事性艺术首饰既融入传统文化审美,又紧扣观赏者与消费者的心理诉求,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引领当代艺术首饰发展,并成为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延续与强化传统首饰叙事功能,形成有鲜明艺术语言的叙事艺术首饰,归纳与分析这一艺术媒介的重要性,让国内从业者与观者更加清晰理解其主题类型与解读模式,从而让叙事性艺术首饰在中国的土壤中能够面向更广的社会人群,在造物与思想之间升华出“新时代”精神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