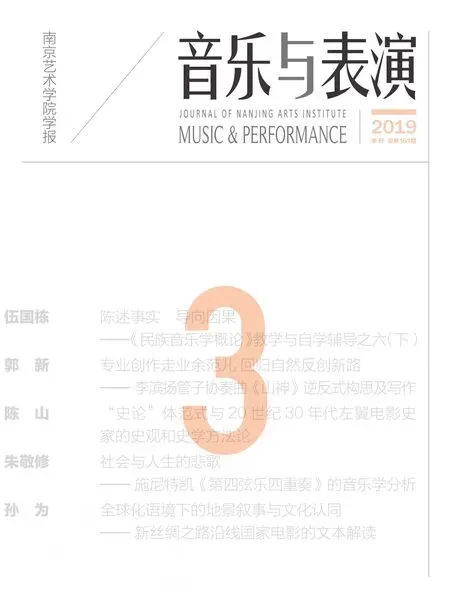论《风雅十二诗谱》并非古乐谱①
刘 义(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孔庆茂(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风雅十二诗谱》(以下简称《诗谱》)首见载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据传为现存最早的《诗经》乐谱,但其可信度历来备受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唐代乃至唐以前的音乐古谱,并据此仿作了诸多“诗经古乐”,如熊朋来的《瑟谱》、清代的《钦定诗经古谱》等;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并不是古代的乐谱,是宋人根据当时音乐曲调编写的,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还有一些学者对其是否为乐谱提出了怀疑,如朱熹、江永等人。诸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诗谱》的作者、创作时代以及性质的定性,关系到古代音乐史的诸多重要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赵彦肃与胡瑗,谁是真正的作者
《诗谱》的作者是谁,向来莫衷一是。而厘清这一问题,对于乐谱最终的定性至关重要。《两浙名贤录》载:“赵彦肃字子钦,建德人,天资孝友,留意圣贤之学,穷理尽性,弗深造自得弗措也,登干道进士第。会光皇遗剑,辍三年不仕,宰臣周必大荐之孝庙甚力,彦肃益以近名为嫌,仕至宁海军节度推官,所着有《易说》及《广学杂辩》《士冠士婚馈食图》行于世,朱文公观其书叹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学者称为复斋先生。”[1]
时人孙应时亦说他中“丙戌(1166年)榜,学行甚高,忧居执礼如古人,但近亦颇好释氏书耳”。[2]赵彦肃作为朱熹的弟子,主要在易礼方面有所研究,且其论《易》与朱子多所不合。[3]②宋朱鉴《朱文公易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卷之二十载:“《易说》用意甚精,然鄙见却有未安处。似是为说太精,取义大密,或伤简易之趣,更俟详玩别奉扣也。”参见:[宋]朱鉴.朱文公易说卷二十[M].元刻本:801.遍阅文献,除载记其传《风雅十二诗谱》外,未有关于赵氏从事音乐研究的其他任何信息。作为南宋的士大夫,他的兴趣只是在“易礼”上,对“礼乐”抑或有研究。但如果从音乐的角度衡量,他对音乐可能并不娴熟。朱熹虽然说《风雅十二诗谱》得自于赵彦肃,但至于作者为谁则语焉不详。
后世学者多从赵彦肃所传之说,也有少数学者据此认定作者是赵彦肃,这当然是对《仪礼经传通解》所载内容的误解。一则赵氏恐不能为。正如吴乔说:“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虽田之硗腴,丝之精粗,为主人之职业,然主人不粗知耕织之事,则无以知硗腴精粗之故。乐当问乐工,虽声之雅俗为儒者之职业,然儒者不习知宫商之音,则无以知雅俗之故也。”[4]士大夫论乐多从“礼”出,音乐水平与实际技能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所成。”[5]胡瑗等人改铸钟磬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二则赵氏恐不愿为。宋人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北宋柳永也因多做曲子词而备受冷落。[6]①宋阮阅《诗话总龟》百家诗话总龟后集卷之三十二载:“耆卿喜作小词,然薄扵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栁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参见:[宋]阮阅.诗话总龟,百家诗话总龟后集卷之三十二[M].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676.虽然南宋时作曲子的文人有所增多,但乐工之技,士大夫仍多不屑为之。[7]134②宋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第十九载:“今时舞者曲折益尽奇妙,非有师授皆不可观,故士大夫不复起舞矣。或有善舞者,又以其似乐工,輙耻为之。”参见:[宋]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M].日本元和七年活字印本:134.赵彦肃这一“执礼如古人”的夫子,不太可能躬亲为作此谱。
关于《诗谱》的作者,遍阅历代文献都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明材料。但《宋史·乐志·诗乐》的一段话,却让人浮想联翩。“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墖,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8]1892
宋人江少虞亦曰:“胡瑗善琴,教人作《采苹》《鹿鸣》等曲,稍曼延其声,傍近郑卫,虽可听,非古法也。……太学诸生承胡先生之教,许鼓琴吹箫,及以方响代编磬,然所奏唯《鹿鸣》《采苹》数章而已。”[7]305-306
胡瑗(993—1085)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1041年创立“湖学”,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影响深远。他曾与阮逸一道参定声律,制作钟磬,1050年又与阮逸进京主持更定雅乐。作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的胡瑗,以他的音乐才能和经历,是有可能为这些《诗经》篇章作谱的。政和七年,典乐裴宗元谏言:“乞按习《虞书》《赓载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关雎》《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之诗。”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宋徽宗的首肯。[8]1710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胡瑗之后,还有许多人从事或参与了这些篇章的“谱唱”,只是,这些所谓的“诗乐”篇章,早在淳化年间就被更改得面目全非,只是套用了原来篇目的标题和歌词形式,歌词也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在目前未有新的史料出现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不能明确《诗谱》的始作俑者,但至少可以认定,胡瑗等人确实曾经参与了《诗谱》的“诵唱”,抑或作了一些“记录”和“改编”。
二、《风雅十二诗谱》并非唐开元乡饮酒礼遗声
《宋史》传云《诗谱》是赵彦肃得自唐开元乡饮酒礼,[8]3934③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第九十五载:“唐开元乡饮酒礼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莫得闻。此谱相传,即开元遗声也。”参见:[元]脱脱.宋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3934.其果真为开元遗声?恐不得如此。
(一)“礼非开元之礼”
考汉郑玄《仪礼疏》、三国王肃《孔子家语》及唐杜佑《通典》,其载饮酒礼乐歌仪礼主要为: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9]104-128,[10]59-60,[11]815-818④其实,乡饮酒礼的仪式程序都是后人根据前人文献记载和当时推行情况推想出来的,其可信度不高,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姑且从之。参见:[汉]郑玄.仪礼疏,卷第九[M].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104-128;[三国]王肃.孔子家语,卷七,观乡射第二十八[M].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59-60;[唐]杜佑.通典[M].清武英殿刻本:815-818.但《诗谱》仅有诗词之谱,而无笙诗之乐,甚为可疑。乡饮酒礼是地方政治教化的重要礼仪活动,主要是诸侯之乡大夫颁法于乡吏、兴贤敬宾;乡党正明养老,正齿位;以及州长春秋习射前所行之仪式。
但自春秋以降,随着秦汉一统,乡饮酒礼见之甚少。东汉永平以后,郡县推行的乡饮酒礼已经搬到了学校,[11]818⑤唐杜佑《通典》卷七十三礼三十三嘉十八载:“后汉永平二年,郡县行乡饮酒于学校,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参见:[唐]杜佑.通典[M].清武英殿刻本:818.加上战乱频繁,基本上是名存实亡。魏晋时期,也只有晋武帝泰始六年、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行过此礼,不仅地点换了,连主角也变成了皇帝。表面上看,好像乡饮酒礼规格得到了提高,连最高统治者都出席了,其实质是地方多不重视,没有推行。[12]①南北朝沈约《宋书》卷十四志第四记载,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参见:[南北朝]沈约.宋书,卷十四,志第四[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67.唐初乡饮酒礼只有在贡举之日才偶一为之,后来由于裴耀卿的力荐和追捧,开元时期又复兴起,但不久又趋于没落。[11]818②唐杜佑《通典》卷七十三礼三十三嘉十八记载:“外州远郡,俗习未知。徒闻礼乐之名,不知礼乐之实。窃见以乡饮酒礼颁于天下,比来唯贡举之日略用其仪,闾里之闲未通其事。……但以州县久绝雅声,不识古乐,伏计太常具有乐器,太乐久备和声,请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简有性识人于太常调,习雅声,仍付笙竽琴瑟之类,各三两事,令比州转次造习,每年各备礼仪,准令式行,稍加劝奖,以示风俗,其仪具开元礼。”参见:[唐]杜佑.通典[M].清武英殿刻本:818页.到了宋朝,乡饮酒礼的仪式被用于宴会科举考试中举的文人学士,后来还曾经颁布地方推行。“乡饮酒,义以天子之立,左圣乡仁,右义背藏,配四时之序,与此异者,彼主乡饮酒之礼言之,非别礼乐而言故也。”[13]但这时的乡饮酒礼,基本上都是乖陋乱造,不合时宜。黎靖德对此就颇有微词:“绍兴初,为乡饮酒礼,朝廷行下一仪制极乖陋,此时乃高抑崇为礼官,看他为慎终丧礼是煞看许多文字,如仪礼一齐都考得仔细,如何定乡饮酒礼乃如此疏缪?……又曰:开元礼煞可看,唯是五礼新仪全然不是当时,做这文字时,不曾用得识礼底人,只是胡乱变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又云:“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于今,如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今强行之,毕竟无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14]宋人李昴英亦言:“吾乡乡饮酒百年几见干道间,龚庄敏尝行之,惜记载脱遗,虽宿辈不可得而闻。”[15]可见,汉唐的乡饮酒礼已经失去古风,更不用说两宋了。南宋的乡饮酒礼也根本不是开元面目了,其内容、形式、场所和参与人员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声非开元之声”
由于乡饮酒礼的湮灭无常,《诗谱》所体现的伦理冲突与矛盾显而易见,学者多有论述。但其音乐的特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却说明它极有可能是宋人的“伪作”。秦灭汉兴,李延年为新声,雅乐遂废而新声用;魏杜䕫犹能传旧雅乐四曲,左延年复改其三;《鹿鸣》一曲尚存,后并失之。沈括《梦溪笔谈》载:“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所谓“与胡部合奏”,指的是外来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结合。《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16]③开元天宝以来的宴乐,实际上乃是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后生发出来的一种新音乐。参阅(日)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所谓的宴乐就是宴飨时所用的音乐,乡饮酒礼作为宴饮嘉宾的重要礼仪,它的音乐也必然有所改变。
朱熹当时存录此谱,已有“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之疑,他在答蔡季通时又云:“昨过詹元善听其歌《二南·七月》,颇可听,但恐吓走孔夫子耳。”[17]明人倪复亦从朱子之说。“乐本于庄正齐肃,故希简而寂寥,若独用其清,不免尖艳,特比俗乐为少耳,岂古乐之本然哉?朱子疑其非古法是也,况其所按声律不类六十四调,而全用管色,其非古音可知矣。”[18]
清人王坦亦言赵彦肃所传《古雅颂十二诗谱》、熊朋来《瑟谱》皆非古乐也。[19]清人胡彦升认为是作伪。“自伪作者出,将使后之人疑古乐之俱不足听,而翻幸其不是古乐,既不幸而尽失于前,又不幸而谬传于后也”。[20]陈沣认为是宋人所托。“十二诗谱不出于开元,而为宋人所依托”。[21]今人杨荫浏认为它是“假古董”,是宋人根据当时的《雅乐》创作的乐谱。“就音乐形式看来,它绝不是周代民歌的音乐,它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说它是在宋代长期复古思想孕育之下,在宫廷《雅乐》传统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作品,还是有较大的可能性。”[22]徐元勇认为它是南宋时的作品。“《关雎》一曲原注‘无射清商,俗呼越调’,实属宋代燕乐音位,乐谱所记录的各曲音域恰合南宋所用黄钟律之音高标准。”[23]其实,“古乐久失,其唐宋诗词及元曲歌法纵令至今尚存,亦不足以存古乐之遗声。”[24]正如李昌集所言:“有声语言与文字语言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任何时代的有声语言都是传给当下人听的,因而任何有声语言都具有当下性。”[25]不管是先秦的雅乐、汉魏六朝的清乐,还是隋唐的宴乐,在其当时都是由前代遗音、民间新调与外来声乐组合而成的。《诗谱》非唐开元之遗音,不辨亦明。
三、《诗谱》是古代《诗经》篇章的“吟诵谱”
《郑风·子衿》毛传本言:“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26]60“诵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早有记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27]孔子特别重视“诵诗”,并主张学以致用。正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哉?”[28]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9],“诵诗”乃诗之“吟诵”,“弦诗”是以诗入乐,“歌诗”乃诗之“徒歌”,“舞诗”是以诗入舞,其意甚明。①关于“诵诗”“徒歌”“乐诗”等概念,可参看:钱志熙.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J].中山大学学报,2011(1)。可今天仍有学者认为“诵诗”是从“歌诗”中分化出来的,[30][31]②公木认为至汉“诵诗已正式从歌诗中分化出来”“特别建安以后……大都是诵诗,不是歌诗”;赵敏俐亦说“中国的诗歌从汉代开始明显的分为歌诗与诵诗两大类别。”参见:公木.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J].文学评论,1980(6);赵敏俐.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问题流变及功能分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吾人不敢苟同。“可诵”是“中国诗之所以为诗的条件”,[32]“诵诗”作为一种学习和审美方式,在中国古代一直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33]“家父作诵,以究王讻”[26]131“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26]229;汉代“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34];甚至“到了魏晋,‘诵’开始取代‘歌’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35];南北朝人“不能谨韫椟玩,耽以为吟颂”[36];与“诵诗”发展轨迹不同的是“诗乐”的日益式微。周朝分崩,礼乐不昌,秦汉一统,“诗乐”凋零。音乐的教化功能越来越淡化,而诗经文字的政治教化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倡和发挥。“诗乐”不兴,就连“歌诗”也逐渐向“诵诗”靠拢。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37]514,“诗言志,歌咏言”[37]218,古代所谓的“诗”与“歌”,其实就是吟诵。心志发为吟诵就是诗,吟诵的声调加以延长就成了歌。[25]③古诗文的吟诵传统见:李昌集.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3。杜甫《解闷》云:“陶冶性灵为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贾岛《题诗后》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朝“南人无不吟诵”[38]。
宋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诗林广记》载:“东坡守钱塘,功甫过之,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击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东坡曰:‘十分来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十分也!’”[39]苏东坡吟诗的故事虽然诙谐,却很能说明当时北宋人重视诗歌吟诵的风气。王灼云:“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40]郑樵亦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41]从中我们可见,“诵诗”在南宋的流行。关于“诵诗”的出现与断代,虽然学界存在诸多争议,但对于其一直存在和学诗的重要作用,意见一直是一致的。
朱熹在录存《诗谱》时即有疑问:“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叹矣。”[42]④其实,诗歌吟诵经久不衰,直到清代都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参见:[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四[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97.朱载堉也说:“以一字一声拟古者,直谓之念曲,叫曲可也。”[24]52“念曲”和“叫曲”,都已经不是真正的乐曲,其实指的就是抑扬顿挫富有情感的“念白”、吟诵而已。徐养原说:“赵彦肃《诗谱》,一字一声是歌而不永也。……然则诵者歌之渐也,欲知歌宜先知诵,诵得其法,其于歌也思过半矣。”[43]江永则认为:“歌以永言,固当延引其声抑扬宛转以其趣,若但一字一声,是谓诵诗,非歌诗也。”[44]103这些古代学者的怀疑可谓切中肯綮,虽然徐养原与江永关于是“歌”还是“诵”的意见相左,那是他们不太了解“吟诵”的传统,不知道“诵诗”及其“徒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吟诵”的原因。[30]⑤公木先生在《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一文中说:“古代,诗即是歌,歌即是诗;后世,歌还是诗,诗不必是歌。所谓歌,包括徒歌与乐歌。凡成歌之诗谓之歌诗,凡不歌之诗谓之诵诗。诵诗从歌诗当中分离出来,又经常补充着歌诗;歌诗在诵诗上面产生出来,又最后演变为诵诗。”其实,一开始出现的所谓“歌诗”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诗,“歌诗”和“诵诗”是后来才出现的并立的两种“学诗”方法。参见:公木.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J].文学评论,1980(6).但他们对《诗谱》并非诗乐的意见是一致的。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有言:“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与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诗皆咏之”,说的便是吟诵,便是徒歌;“以声依咏以成歌”,指的是标记其谱调而转为乐歌。沈约《宋书·乐志》亦载:“吴歌杂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作歌以被之”。这里的“被之弦管”便是标记徒歌谱调,即“以声依咏以成曲”;“因弦管金石作歌以被之”便是再依曲牌按谱填词。清人江永曾经尝试以《诗谱》按声弹之,“只须初弦次弦,其余皆无用,其声全浊不成韵调”,可知《诗谱》并非真正的乐谱。[45]⑥江永又言:“其于《鹿鸣》诸诗,黄钟太簇用清声,犹赖有此两声以济之,稍稍可听。若依蔡氏法,此二律并不得用清声法则密矣,其如声不谐于耳何?”参见:[清]江永.律吕新论,卷下[M].清守山阁丛书本:15.
另外,通过研究2008年5月秦德祥编制的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刘钧若(音译)教授1971年4月录音的赵元任先生吟诵《诗经》等的遗音,其“吟诵调”与《诗谱》还是比较相符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诗谱》极有可能是当时文人根据“吟诵”而标记的谱调。
“吟诵是按照一定的节奏、韵律有感情地吟咏、诵读古典诗文的一种读书方法吟诵,最主要的两个特点就是声音和节奏,声音就是音调的高低,节奏就是根据文字内容和情感做出的长短断句。”[46]也许有人会据此质疑《诗谱》只有音调的高低而没有节奏的“断句”,不是“吟诵”的谱调。其实,对于乐谱来说,没有节奏确实不能成为音乐。[47]①清陈澧曾质疑:“所载诸曲皆无节奏,不知何以云然?”参见:[清]陈澧.声律通考,卷十[M].清咸丰十年殷保康广州刻本:102.但对于这些《诗经》篇章的“吟诵”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诗歌的吟诵一方面是自由的,是即兴的,因声求气,涵咏入境,因人而异,因文而变;但它又是受到诗歌情感、音律等因素的限制。只有准确地掌握住节奏点和平仄四声的变化,诗文的感情及气韵才能得以流畅地展现。一是看“言中之意,诗中之情”。“《书》言歌永言,必先云诗言志。志者,诗人之意也,音节之疾徐,宜视言中之意。”[44]103“歌以永言”,自当延引其声抑扬宛转以尽其趣,因为,“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而表达的有力、细致、正确,都无与伦比。在这方面,声音与诗歌的朗诵相近。”[48]二是看字词关系与章节韵律。在这方面,许多学者早有论述,如赵元任、任半塘、俞平伯、朱自清、叶嘉莹、陈少松、李昌集等。关于如何吟诵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不再赘述。
结 语
宋代的乡饮酒礼,“礼非开元之礼,声非开元之声”;宋人“记录”“改编”和“诵唱”的诗经乐谱只能算是“仿古之作”。《诗谱》其特有的“音乐特性”正是诗经吟诵传统法则和发展规律的自然表现,它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文人“吟诵”标记的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