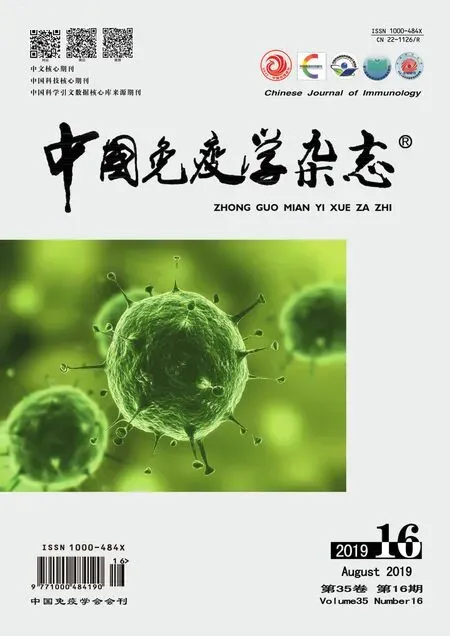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与黏膜免疫研究的前沿进展
俞昊男 刘志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肠道不仅是食物消化与吸收的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肠腔中定居着约1014个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及原生动物等[1]。肠道屏障主要由肠道共生菌、肠道黏液层、肠上皮细胞和固有层内多种免疫细胞共同组成[2]。肠道菌群可促进宿主黏膜免疫系统的发育与应答、增强肠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Tight junction),并对病原具有拮抗作用。肠道黏液层由杯状细胞分泌的黏液蛋白构成,其中富含肠上皮细胞分泌的抗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以及B细胞产生的分泌型IgA(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SIgA),可有效抑制细菌在肠道上皮的黏附和定植。肠上皮细胞通过紧密连接组成了一道物理屏障,有助于肠腔内的细菌和有害抗原与机体内环境分隔。肠道中还存在肠相关淋巴组织(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s,GALTs),其主要包括组织性淋巴样组织和弥散分布的淋巴细胞,前者包括派尔集合淋巴结(Peyer′ s patches)、孤立淋巴滤泡(Isolated lymphoid follicles,ILFs)以及肠系膜淋巴结(Mesenteric lymphoid node,MLN),后者主要指分散于黏膜固有层(Lamina propria)及上皮细胞层内的淋巴细胞,如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T细胞和B细胞等[3]。这些免疫细胞之间的互相作用构成了复杂而精密的调控网络,调节宿主的免疫反应以及帮助抵御病原的入侵。
哺乳动物宿主与微生物经共同进化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宿主为微生物提供营养和生存的环境,微生物则通过参与和调节宿主的一系列生理活动以促进肠道的稳态平衡。人的胃肠道中有1 000多种细菌,其中大部分为专性厌氧菌,包括厚壁菌(Firmicutes)、拟杆菌(Bacteroidetes)、变形菌(Proteobacteria)和放线菌(Actinobacteria)[4]。厚壁菌和拟杆菌是所有哺乳动物胃肠道细菌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胃肠道细菌总数的90%以上[5]。目前认为,在婴幼儿肠道早期定植的是某些好氧菌和兼性厌氧菌,例如肠杆菌(Enterobacteriaceae)与链球菌(Streptococcus)等,这些肠道菌将有助于形成肠道的厌氧环境,进而有利于随后厌氧的益生菌如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与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等定植[6]。乳酸杆菌与双歧杆菌可通过分泌抗菌物质、调节肠道pH等途径抑制某些病原菌的定植[7]。以前的研究发现,宿主可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如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等识别微生物来源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进而引发炎性反应以清除病原[8]。有意思的是,肠道菌可通过PAMPs促进肠上皮细胞分泌黏液,增强屏障功能[9]。肠道微生物除了通过PAMPs对肠黏膜固有免疫反应进行调节外,还与GALTs的发育和成熟以及适应性免疫反应的调节相关[10,11]。比如,分节丝状菌(Seg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SFB)可通过诱导小肠中的辅助性T 细胞17(T helper cell 17,Th17)的增殖与分化发挥抗感染作用,并可能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相关[12,13]。一些梭菌(Clostrid-ium)可诱导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发挥抗炎作用以促进肠道稳态平衡[14,15]。因此,宿主的免疫系统和微生物群之间复杂的互作关系对于维持肠道内稳态十分重要。
有证据表明,肠道菌与黏膜免疫互作的失衡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发生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社会饮食结构与环境的变化,IBD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高,预防和治疗IBD已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许多研究表明IBD的产生和发展与肠道菌群有着紧密的联系,IBD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肠道菌群失调[16,17]。因此,基于调节肠道菌群的研究有望为IBD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近几年来,适应性免疫与肠道菌的互作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因此本文将从肠道微生物对宿主适应性免疫中B细胞、T细胞的免疫应答的影响,以及IBD与肠道微生物的关系和基于肠道菌的治疗策略两部分进行总结。
1 肠道微生物与宿主适应性免疫系统的互作
已有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对宿主适应性免疫的B细胞与T细胞这两大分支都有重要的调控作用。一方面,肠道菌群可通过调节B细胞的应答以促进肠道中IgA的产生;另一方面,肠道菌群也可通过调节T细胞的分化来维持炎症反应与免疫耐受之间的平衡。
1.1 肠道微生物对B细胞应答及IgA分泌的影响 长久以来,大家发现相对于SPF(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小鼠,无菌(Germ-free,GF)小鼠的黏膜免疫系统发育不良,其派尔集合淋巴结发育程度低下,仅有极少的生发中心(Germinal center)且IgA+的浆细胞以及IgA数量也显著减少[18],而给GF小鼠定植肠道菌后可恢复其IgA的产生[19]。这暗示着肠道菌对于肠道内IgA+浆细胞的分化以及IgA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
肠道中的IgA主要由肠道黏膜固有层中的IgA+浆细胞产生和分泌,其通常以二聚体的形式存在,经与肠上皮细胞产生的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pIgR)结合进而被转运和释放到肠腔中以结合肠道微生物和膳食成分等。IgA的黏附和包裹作用可避免肠腔中有害抗原与宿主肠上皮的直接接触,对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IgA也调节着肠道内菌群的组成和平衡[20,21]。肠道菌可通过T细胞依赖和非T细胞依赖的两条途径调控IgA的产生。
T细胞依赖的IgA产生主要发生在派尔集合淋巴结中,DC从肠腔内获取抗原进而刺激CD4+T细胞分化为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Tfh),Tfh细胞主要通过CD40L和IL-21促使B细胞表达胞嘧啶核苷脱氨酶(Activation-induced cytidine deaminase,AID)和促进IgA的抗体类别转换[21,22]。一些可侵入肠道内黏液层并定植于上皮细胞表面的肠道菌可诱导产生高亲和力的IgA,如SFB依附在肠上皮细胞表面进而诱导T细胞依赖的IgA产生,并且这个过程依赖于Th17细胞[23-25]。
非T细胞依赖的IgA产生主要发生在固有层和ILFs中。肠上皮细胞通过TLRs感知肠道菌并产生BAFF (B-cell activating factor)和APRIL (Prolifera-tion inducing ligand),这两种细胞因子可促进B细胞中AID的表达和抗体类别转换进而分化形成IgA+浆细胞[26]。此外,肠上皮细胞也可通过产生胸腺间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TSLP) 来刺激DC分泌BAFF和APRIL,进而促进IgA+浆细胞的产生[26]。然而,这种非T细胞依赖产生的IgA普遍具有低亲和力的特征[21,23,27]。
IgA对肠道菌的调节主要包括改变细菌运动性、调节肠道菌的基因表达以及帮助部分肠道菌定植这三个方面。Boullier等[28]发现,特异性靶向弗氏志贺菌(Shigellaflexneri)LPS的IgA可将弗氏志贺菌限制在肠黏液层中以减少其引起的肠道炎症。IgA还可能通过结合细菌的鞭毛蛋白进而限制肠道菌的运动能力[29,30]。此外,IgA还可调控肠道菌的基因表达。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thetaiotaom-icron)作为肠道共生菌通常不会引起肠道炎症,Peterson等[31]发现在缺乏IgA时,多形拟杆菌会高表达一系列参与一氧化氮代谢的基因并引发炎性信号。Cullender等[32]发现,缺乏TLR5的小鼠体内特异性识别细菌鞭毛蛋白的IgA水平降低,伴随着许多共生菌编码鞭毛蛋白的基因出现异常表达。有趣的是, IgA还能帮助部分共生菌在肠道内的定植。Donaldson等[33]发现,由脆弱拟杆菌(Bacterioidesfragilis)诱导产生的IgA有助于脆弱拟杆菌成群聚集并锚定在肠上皮表面,从而为其提供竞争优势。
IgA靶向的肠道菌对宿主健康的影响目前存在争议。人与小鼠的肠道菌中只有部分细菌能被IgA包裹[34]。IgA-SEQ技术将流式分选与16S rDNA测序结合,能够分离和鉴定肠道菌群中与IgA结合的菌群[35]。Palm等[36]利用IgA-SEQ技术发现,IBD患者肠道中有部分被大量IgA包裹的肠道菌,而将这些肠道菌定植到GF小鼠体内可增加其患结肠炎的风险。Kau等[37]发现给小鼠定植营养不良儿童的肠道菌并喂以营养不良的饲料,小鼠肠道内的肠杆菌科被大量IgA包裹,后续实验结果表明这些肠杆菌科可导致肠炎。然而,被IgA识别和包裹的艾克曼菌(Akkermansiamuciniphila)和梭状芽胞杆菌(Clostridiumscindens)可干预肠炎的发生[3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IgA靶向的肠道菌并非都是致病菌,其中部分肠道菌可通过增强肠道屏障进而有利于维持肠道稳态。因此,被IgA靶向的肠道菌有望为探究肠病的致病原因和治疗方案提供新的思路。
1.2 肠道微生物对Th17细胞与Treg细胞分化的影响 初始CD4+T细胞经抗原刺激后可增殖并分化为不同的亚群,如辅助性T细胞1(T-helper 1,Th1)、Th2、Th17和Treg细胞。其中Th17细胞主要介导炎症反应,参与对抗细胞外的细菌与真菌并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相关。与Th17细胞共存于固有层的Treg细胞则具有抑制炎症和维持免疫耐受的功能。Th17细胞与Treg细胞在功能上相互制约,两者之间的平衡对于肠道稳态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SPF小鼠,GF小鼠CD4+T细胞数目较少,且肠道中ILFs等不成熟[38,39]。Ivanov等[40]发现,GF小鼠的小肠中Th17细胞数目低下,而与SPF小鼠合笼饲养后其Th17细胞数目显著增加。另有研究报道,相较于SPF小鼠,GF小鼠结肠固有层中Treg细胞数目也较少[41-43]。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通过诱导Th17细胞与Treg细胞的分化来维持炎症反应与免疫耐受之间的平衡。
1.2.1 肠道微生物诱导Th17细胞的增殖与分化 Th17细胞是一类辅助性T细胞亚群,主要分布在肠道固有层中[40,44]。Th17细胞可产生和分泌IL-17A、IL-17F和IL-22,在预防致病菌感染与增强肠道黏膜屏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5-48],此外也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49-51]。
Th17细胞的分化受多种环境因素的调控。有研究显示,高盐饮食可导致固有层内Th17细胞数目的上调并增加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52,53]。饮食中的脂质也参与调控Th17细胞的分化。Haghikia等[54]发现,长链脂肪酸如月桂酸促进Th17细胞分化并诱导更严重的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在诸多环境因素中,肠道菌是影响Th17细胞分化的主要因素。最早关于微生物群影响Th17细胞分化的依据来源于Ivanov等[40]发现,直到小鼠成长到3~4周龄时其肠道内才可检测出Th17细胞。并且GF小鼠的肠道固有层内Th17细胞的数目显著降低。
近年的研究发现,SFB对于Th17细胞的增殖与活化至关重要。SFB是一类严格厌氧的革兰氏阳性菌,主要定植于动物体的回肠部分,目前已在啮齿动物、猪等哺乳动物体内发现SFB的定植[55,56]。SFB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指出这类肠道菌是梭菌的一员,其缺乏氨基酸生物合成酶并且依赖宿主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目前尚未在体外成功培养[57,58]。早在2006年,Ivanov等[40]发现Jackson公司的B6小鼠小肠固有层中Th17细胞的数目显著低于Taconic公司的B6小鼠,而将两种小鼠合笼饲养可上调Jackson小鼠小肠中Th17细胞的数目。将Taconic公司的B6小鼠的盲肠内容物灌胃给GF小鼠可诱导其小肠中大量Th17细胞的产生。进一步研究发现,Taconic公司的B6小鼠肠道中存在SFB,而Jackson公司的B6小鼠肠道中则无法检测出该菌。在GF小鼠中单菌定植SFB可诱导Th17细胞,由此发现SFB对于诱导Th17细胞十分重要[59]。
SFB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可以黏附肠上皮细胞,而这也是诱导Th17细胞分化的关键因素。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小鼠肠道中,SFB利用钩状结构黏附于肠上皮细胞并在钩尖处触发内吞囊泡的形成,这个现象被称作微生物黏附触发的内吞作用(Microbial adhesion-triggered endocytosis,MATE)。在此过程中,SFB的细胞壁蛋白经内体-溶酶体网络,从肠上皮细胞顶端被运输至基底侧进而活化Th17细胞[60]。Atarashi等[61]发现,小鼠来源的SFB可诱导小鼠肠道内Th17细胞分化,而大鼠来源的SFB由于无法黏附小鼠肠上皮细胞进而无法介导小鼠肠道内Th17细胞的分化,并且缺乏黏附上皮细胞能力的SFB突变体同样也无法介导肠道中Th17细胞的分化。此外,SFB的黏附作用还可诱导肠上皮细胞中血清淀粉蛋白A(Serum amyloid A,SAA)的两个亚型SAA1和SAA2表达上调[62]。Schnupf等[63]把SFB和上皮细胞系进行体外共培养时,发现上皮细胞中SAA的表达也显著升高,后续实验也表明是SFB与上皮细胞的紧密接触启动了上皮细胞中基因表达的信号传导途径。与此同时,SFB还通过诱导CX3CR1+单核细胞产生IL-23来激活ILC3产生IL-22,IL-22通过引起肠上皮细胞内STAT3的磷酸化进而上调SAA1与SAA2的表达[61,64]。Sano等[64]发现,在SFB介导Th17细胞的产生与分化中,SAA促使RORγt+T细胞中IL-17A表达的上调,对Th17细胞的分化起着重要的作用。SAA是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s,HDL)和视黄醇的载体,因此猜测SAA可将这些免疫调节分子传递给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s,APC)和T细胞进而调节机体免疫反应。由此可见,SFB介导的Th17细胞的分化是通过肠上皮细胞、ILC3和单核细胞等多种细胞之间复杂的互作网络实现的。
由SFB介导的Th17细胞的产生有助于加强宿主对SFB本身以及其他病原体的防御,后者显得尤其重要。有研究表明,SFB诱导的免疫可以保护宿主抵御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rodentium)和鼠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typhimurium)的入侵[12,65]。Edelblum等[66]发现,SFB诱导产生的Th17细胞在刚地弓形虫感染(Toxoplasmagondii)中对于肠道通透性的保护也起着重要作用。Burgess等[67]的研究表明,SFB的定植也可在痢疾变形虫(Entamoebahistolytica)感染中给小鼠提供保护作用。而在GF小鼠中只定植SFB并不能在鼠柠檬酸杆菌感染中为机体提供保护作用,这表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对于协调机体免疫反应十分重要[12]。
除SFB之外,有研究表明鼠柠檬酸杆菌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O157:H7)这两种可黏附肠上皮细胞的致病菌也可以引起Th17细胞的分化[61]。同时,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另一类可黏附肠上皮的致病菌——白色念珠菌(Candidaalbicans)是诱导人体产生抗真菌Th17细胞的主要致病共生真菌,且其他种类的真菌引起的Th17免疫反应依赖于白色念珠菌诱导的交叉反应性Th17[68]。以上研究结果提示肠道菌对肠上皮细胞的黏附作用可能通过传递某种信号进而对Th17细胞的产生和分化起调节作用,而其中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1.2.2 肠道微生物对Treg细胞分化的影响 Treg细胞是一群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调节性T细胞,其在调节自身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功能。相对于全身其他部位的Treg细胞,肠道中的Treg细胞可维持机体对膳食中的抗原和肠道菌群的免疫耐受[69],并且在抑制机体针对鼠柠檬酸杆菌等致病菌产生的免疫应答造成的组织损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0]。
肠道中Treg细胞依据来源可分为两类:来源于胸腺的tTreg细胞(thymus-derived Treg)和来源于外周的pTreg细胞(peripherally differentiated Treg)。前者在胸腺发育并分化成熟为Foxp3+CD4+Treg细胞,后者首先在胸腺发育为初始CD4+T细胞,随后在外周组织中表达Foxp3,成为Foxp3+CD4+Treg细胞。
pTreg细胞大部分表达RORγt,而在GF小鼠体内缺失RORγt+pTreg细胞,说明这类Treg细胞是由微生物诱导的。有研究表明,RORγt+Treg细胞可产生和分泌IL-10,IL-10可抑制骨髓细胞和Th17细胞的异常活化,对维持肠道内的稳态有重要作用。另有研究表明,RORγt+Treg细胞也高表达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在肠炎模型中相对于RORγt-Treg细胞具有更强的抑制肠炎的作用。
相对于SPF小鼠,GF小鼠肠道中pTreg细胞数目显著减少,提示肠道微生物参与Treg细胞的增殖与成熟[41-43]。目前研究发现,厚壁菌门梭菌属中的一些菌在诱导肠道Treg细胞中发挥重要作用。Atarashi等[15]利用氯仿处理正常小鼠的粪便得到46种梭菌并将其定植到GF小鼠体内,可诱导GF小鼠结肠中Treg细胞数目的上调。随后,Atarashi等[14]将从健康人体中分离得到的17种梭菌定植到GF小鼠和大鼠体内,发现也可诱导肠道pTreg细胞的增殖,而且这几种梭菌还可促进Treg细胞表达CTLA-4与IL-10,帮助小鼠抵御实验性结肠炎。Stefka等[71]发现,梭菌属还可刺激ILC3细胞产生IL-22,这有助于加强肠上皮屏障并降低肠道对膳食中蛋白质的渗透性,进而减少食物过敏反应。有研究发现,梭菌属还可诱导肠上皮细胞产生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TGF-β)为Treg细胞的形成提供有利环境[72,73]。此外,给小鼠给予高纤维饮食可进一步上调Treg细胞的丰度[74]。
梭菌属诱导肠道Treg细胞产生的机制正逐渐被研究人员所揭示,其中可能的途径是通过梭菌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的SCFAs进而发挥作用。SCFAs是一类由五个或以下的碳原子组成的饱和脂肪酸,主要由肠道菌发酵膳食纤维产生,包括醋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等。SCFAs主要通过两方面诱导Treg细胞。首先,SCFAs可通过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GPRs)介导的信号通路调节Treg细胞的分化。GPR43是多种SCFAs的受体。Smith等[75]研究发现,肠道Treg细胞表达GPR43,且醋酸盐与丁酸盐等SCFAs可通过激活GPR43促进小鼠结肠中Treg细胞的增殖。GPR109a是一种丁酸盐受体,其主要在肠上皮细胞与部分固有免疫细胞中表达[76]。De Rosa等[77]发现丁酸盐与GPR109a的结合可促进巨噬细胞与DC产生IL-10与视黄酸脱氢酶(Retinal dehydrogenases,RALDHs),进而诱导Treg的产生。另外,SCFAs还通过改变表观遗传修饰来调节Treg的分化。Furusawa等[75]发现,丁酸盐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的抑制可导致Foxp3基因中非编码保守序列1(Conserved non-coding sequence 1,CNS1)上组蛋白H3的乙酰化,进而促进Foxp3的表达使初始CD4+T细胞向Treg细胞分化。
Treg细胞也可被除梭菌属外的其他肠道菌所诱导。有研究表明,罗伊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reuteri)和鼠乳杆菌(Lactobacillusmurinus)的定植可上调小鼠肠道中Treg细胞的数量[78-80]。Round等[81]发现,脆弱拟杆菌荚膜中的多糖A(Polysaccharide A,PSA)可被结肠中Treg细胞的TLR2所识别并介导IL-10的产生。另外,脆弱拟杆菌来源的PSA还可被肠道中DC细胞识别并产生IL-10,这些DC细胞产生的IL-10会促进Treg细胞IL-10的产生[82]。Kullberg等[83]发现,肝螺杆菌(Helicobacterhepaticus)的感染可诱导肠道中的Treg细胞产生IL-10进而缓解结肠炎的发生。
2 肠道微生物与IBD
IBD是一种具有复发性的慢性肠道炎症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IBD的主要临床症状是腹痛、腹泻和便血[84,85]。虽然CD和UC的临床症状有部分重叠,但它们也有各自的临床特征,比如CD的发病可位于消化道内的一个或多个位置,而UC的病变主要发生在结肠和直肠,且会造成血便[85,86]。IBD是一种全球性疾病,其中西方国家患病人数居多,美国拥有约160万IBD患者,而欧洲则超过200万[87]。虽然IBD在西方国家发病率最高,但其在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国家中的发病率也在迅速上升[88]。
2.1 IBD的致病因素 目前IB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IBD是一种复杂疾病,遗传与环境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作用,肠道菌群作为环境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的研究发现,人基因组含有超过200个IBD易感位点[89-91]。核苷酸结合寡聚化域蛋白2(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2,NOD2)是重要的IBD易感基因,其编码的胞内模式识别受体特异识别特定细菌细胞壁成分肽聚糖进而激活NF-κB和MAPK通路介导的免疫反应[92]。有研究表明,NOD2还参与调控位于小肠隐窝的潘氏细胞中溶菌酶的分拣[93,94]。拥有NOD2突变的IBD患者肠道菌群发生改变,梭菌属的ⅩⅣa和Ⅳ簇数目减少,放线菌和变形菌的数目增多,患者对肠道炎症的易感性的增加[95,96]。另有研究发现,Nod2缺陷型小鼠的肠上皮屏障受损,上皮内淋巴细胞数目降低,在实验性结肠炎模型中更加易感[97-99]。 ATG16L1是一种自噬相关蛋白,其在潘氏细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tg16l1缺陷型小鼠的潘氏细胞功能受损,形成的抗菌肽减少,对实验性结肠炎更易感[100]。除了Nod2和Atg16l1,还有例如Xbp1、Fut2和Card9等基因均被报道与IBD相关[101-103]。通常认为,遗传因素通过与肠道菌群的互作影响了IBD的产生和发展。
IBD的产生和发展也与许多环境因素相关,如饮食习惯、年龄和压力等。西方国家的饮食结构与IBD高发病率息息相关[104]。西方饮食的特点有高脂、高糖和低纤维,这种饮食可能导致IBD发病的机制部分依赖于肠道菌群。David等[105]发现,连续5 d食用动物性食物会导致人肠道中胆汁耐受的肠道菌,如另枝菌属(Alistipes)、嗜胆菌属(Bilophila)和拟杆菌属的丰度增加,而与植物多糖代谢相关的厚壁菌门的比例则下降,这将增加患IBD的风险。Schroeder等[106]发现,将具有西方饮食特点的食物喂给小鼠导致其结肠黏液层变薄且通透性增加,这与IBD的临床表现相似。西方饮食中包含高度加工的食品,这些食品中通常含有乳化剂,一系列体内和体外实验表明乳化剂可改变肠道菌群,增加其促炎性,导致结肠炎病情加重[107,108]。除了饮食因素外,压力、年龄等其他环境因素也可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进而影响IBD的发生和发展[109,110]。
2.2 基于调节肠道菌的IBD治疗策略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都表明IBD与肠道菌密切相关,肠道菌在IBD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11-113]。许多研究指出,IBD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肠道菌群失调,其主要表现为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减少和厚壁菌门丰度降低[16,114]。Furusawa等[75]的研究发现,隶属于厚壁菌门梭菌纲的柔嫩梭菌属(Clostridiumleptum)通过产生丁酸盐促进结肠中Treg细胞的分化进而减少炎症的发生,而这类肠道菌在IBD患者体内的丰度是降低的[115,116]。相比之下,另一类促炎的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Adhesion-invasiveE.coli,AIEC)被报道在成年CD患者肠道内的丰度有显著的增加[117,118]。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来缓解和治疗IBD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抗生素、益生菌和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
2.2.1 抗生素 抗生素治疗主要通过减少消化道中有害细菌的丰度进而利于益生菌定植和生长来缓解炎症和减轻症状。甲硝唑、环丙沙星和利福昔明均被报道能够缓解IBD病症[119-121]。然而,抗生素治疗IBD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局限性。Ungaro等[122]通过Meta分析发现长期使用抗生素甚至会增加患CD的风险。另外,抗生素的使用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而停用抗生素后可能导致炎症的复发[123]。
2.2.2 益生菌 益生菌是指一类定植于宿主体内并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微生态平衡进而有利于宿主健康的活性微生物。益生菌可表达PAMPs进而激活肠上皮的模式识别受体并调节宿主免疫应答相关基因的表达[9]。此外,Nami等[124]发现,益生菌有利于调节肠道杯状细胞的功能和促进肠上皮释放IgA和防御素等。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是两种常见的益生菌,有研究表明,二者有助于改善免疫系统应答、抑制病原菌的定植以及增强肠道上皮屏障[9,125]。鼠李糖乳杆菌(LactobacillusrhamnosusGG,LGG)是从健康人肠道分离出的1株乳杆菌,Gosselink等[126]发现,口服LGG可有效缓解UC的病症。一种包含4种乳酸杆菌、3种双歧杆菌和1种链球菌的益生菌复合物可以缓解轻度到中度UC患者的肠道炎症,并减少炎症的复发[127-129]。益生菌治疗同样存在局限性。虽然益生菌能够缓解UC的病症,但益生菌对于CD的治疗效果尚不明确。其次,益生菌治疗的具体机制以及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待探究。
2.2.3 FMT FMT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性菌群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重建其肠道菌群的治疗方式[130]。FMT在艰难梭菌感染治疗中有着突破性进展[131],这使研究人员开始探究利用FMT开启IBD治疗的新领域。两项随机对照研究均发现,FMT可诱导成年UC患者的临床缓解和内镜下病症的改善[132,133]。其中,Paramsothy等[132]在研究中发现,FMT组临床缓解人数的比例达到27%。然而,FMT治疗可能存在IBD恶化的风险[134]。目前研究者们对FMT的认识仍然有限,FMT不只是供体来源的细菌本身,还有很多非细菌成分,如脱落的肠上皮细胞、真菌、病毒以及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等,这些成分在被移植到受体体内会引起一系列复杂的反应。因此,目前对于FMT的临床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肠道菌引起的肠道适应性免疫反应也调节着肠道菌的组成,维持肠道微生物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对维持肠道稳态与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无菌动物的广泛应用推动了肠道微生物对宿主适应性免疫调控的细胞与分子机制研究,研究人员通常将特定且已知的微生物定植于无菌动物体内,以探究这类微生物在宿主生理与病理反应中的影响。其优势在于可排除各种未知微生物对实验结果的干扰、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微生物群所受调控非常复杂,遗传和环境因素均影响着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肠道菌的研究还需放在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系统中进行。
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对宿主生理活动的调节也是近年的热门研究方向。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表明,肠道菌通过SCFAs等代谢产物调节宿主适应性免疫反应。因此,未来对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研究将有望为新药和疫苗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肠道噬菌体作为肠道微生物中的一部分,与肠道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作。宏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健康人与IBD患者的肠道噬菌体组结构组成显著不同[135]。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Ma等[136]发现Ⅱ型糖尿病患者肠道中噬菌体的数目明显高于健康人。这也说明噬菌体与细菌的互作可能影响着人体健康,解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为肠道菌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利用噬菌体干预肠道菌以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深入理解微生物与宿主的关系,探究肠道微生物影响黏膜免疫系统的机制,对预防和治疗肠内外疾病及改善人类健康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