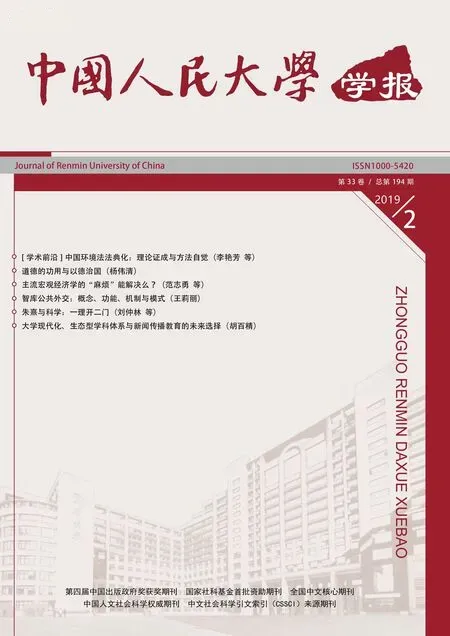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功能、机制与模式
王莉丽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非常重视智库建设和公共外交。智库和公共外交作为构建国家“第二外交渠道”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形象、全球治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最近20余年,智库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智库研究已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显学。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来自政治学、传播学和公共管理学等。“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是指影响公众对外交政策形成和实施态度的做法。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理论图谱主要建立在传播学和国际关系两大学科基础之上。根据传统的公共外交理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外国公众为目标受众的一种外交行为。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舆论的不断多元化和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传统公共外交模式已无法适应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已进入多元化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向政府、智库、媒体、企业、公众等多元化主体转化。智库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因其相对独立性和智囊专家地位,在多元公共外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对智库建设和公共外交的高度重视,“智库公共外交”一词迅速进入中国精英和公众的视野。有关智库公共外交方面的文章和评论也经常见诸学术期刊和媒体。本文对“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做出界定,分析其功能作用、发挥作用的机制与传播模式,冀望进行深入学术探讨和理论分析。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界明确将“智库公共外交”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探讨的还非常少。从国际学界来看,对智库的舆论影响和政策制定作用都有提及,但是至今还未有学者提出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公共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角色,不少研究成果有所涉及,但观点存在一定分歧。大部分学者对智库的权力给予充分肯定,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持有肯定和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致力于在国家精英集团、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和政治领导者之间寻找契合点。[注]托马斯·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詹姆斯·史密斯指出,智库与其专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是思想的掮客,是信息传播者和政策倡导者。[注]James Smith.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1; Donald 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Toronto: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保尔·迪克森认为,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注]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Athenaeum,1971.霍华德认为美国的智库通过与政党、利益集团相结合,成为新政策理念的来源和政治议程的设计师。[注]Howard Wiarda.“Think Tanks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ew Ideas, New Tanks, New Direc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5,70(4):517-525.库必来 ·阿林认为,在政策议程的形成中,智库发挥的是软实力,对决策者的思想产生影响。[注]⑨ 库必来 ·阿林:《新保守主义智库与美国外交政策》,3、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持有质疑态度的学者指出,尽管智库是积极的政策参与者,但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比较微弱。[注]Fraussen Bert, and Halpin Darren.“Think Tanks and Strategic Policy-mak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nk Tanks to Policy Advisory Systems”.Policy Sciences, 2017, 50(1): 105-124.龙吉尼认为意大利外交政策智库依托于政治体系,同时也严重受其限制,政府决策人员对智库的研究成果接受度很低。[注]Anna Longhini.“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in the Italian Political Context: Evolutions and Perspectives”.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5,70(4): 573-592.还有一部分学者从批判的视角对智库的作用进行分析,唐纳德·阿贝尔森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和欧洲外交智库的演变与转型,认为这些智库表面上从事政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却已经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注]Donalde Abelson.“Old World, New World: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Foreign Affairs Think-tanks”.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4,90(1): 125-142.戴安·斯通认为,像美国传统基金会这样的一些智库的研究结论是可预测的,这种可预测性是源于一套保守主义原则和固有的意识形态。⑨
在中国学界,虽然整体上关于智库公共外交的研究文献很少,但是已有学者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业界和学界普遍高度认可智库在全球治理和外交中的影响力。2012年,《现代国际关系》杂志发表《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一文,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探讨了智库的功能与角色,指出美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开展“二轨”外交、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持以及构建政策理念与价值观传播网络的巨大作用。[注]王莉丽:《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1)。2013年,《公共外交季刊》就“智库与公共外交”专题组织了6篇文章,分析了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功能角色以及智库外交的案例,等等。在公共外交的“多轨”体系中,智库开展的第二轨外交活动,不仅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而且是整个公共外交体系的智力和信息中心,是公共外交的“舆论领袖”。中国应重点支持一些公共外交智库。[注]王莉丽:《中国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拓展》,载《公共外交季刊》,2013(3)。智库在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调解和解决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智库帮助政府对复杂的国际问题做出决策。[注]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50-51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有学者认为,智库可成为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可以通过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对公共外交发挥作用。[注]王义桅:《公共外交需要智库支撑》,载《公共外交季刊》,2013(3)。还有学者以南海争端为切入点分析智库在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国家形象等方面起到说服作用。[注]聂书江:《南海争端视角下我国智库公共外交的创新发展》,载《对外传播》,2016(11)。2014年至今,智库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和智库业界在外交实践领域推进的重要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专业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或着重分析民间智库如何参与公共外交[注]赵新利、于凡:《民间智库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以察哈尔学会的实践为例》, 载《对外传播》,2016(5)。,或着重分析媒体智库的公共外交效应[注]黄超:《中央媒体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现状与愿景》,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2)。。还有学者认为高校智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是人才精英的聚集地、政治舞台的展示地,具有舆论场域的吸附力和决策角色的权威力等独特优势。[注]刘峰:《我国高校智库公共外交功能的建设路径思考》,载《高校教育管理》,2017(5)。
总体而言,智库公共外交理论的滞后从某种程度上限制并影响了智库在公共外交实践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因而,需要大力拓展智库公共外交理论研究。
二、智库公共外交:概念与功能作用
对智库公共外交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这一概念和领域进行学术界定。但因“智库”与“公共外交”作为两个专业词汇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学界对其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在界定“智库公共外交”之前,首先需要分析“智库”与“公共外交”。
(一)“智库”与“公共外交”的概念理解
智库也称思想库,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注]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4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关于智库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论述[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和马克斯·韦伯关于“学术志业”与“政治志业”的思想之中。[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欧美。近年来,随着智库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智库研究也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国学界,其中中国学界的智库研究已经具有重要话语权。
对于“智库”这一概念,因其发展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各国学者对其界定的分歧主要在于,智库在机构属性上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是非党派还是与党派有一定关联。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智库必须是非政府、非党派组织,欧洲、亚洲学者对此的理解和界定比较宽泛。安德鲁·瑞奇认为,所谓智库就是指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提供专业知识和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和影响决策过程。[注]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肯特·威佛指出,智库是指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注]Kent Weaver.“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89 ,22(3):563.詹姆斯·史密斯认为,智库是指运作于正式的政治进程边缘的、非营利的私立研究机构。[注]James Smith.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唐纳德·阿贝尔森界定智库是非营利、非党派的研究机构。[注]Donald Abelson.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Foreign Polic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中国学界对智库的定义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其一是延续国外学者关于智库概念的界定,强调智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其二是侧重于智库的现实属性与社会职能,强调智库的核心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注]任恒:《国内智库研究的知识图谱:现状、热点及趋势》,载《情报科学》,2018(9)。薛澜指出,智库主要指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宗旨的政策研究机构,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或其他与政策制定者有效沟通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注]薛澜:《思想库的中国实践》,载《瞭望》,2009(4)。孙哲认为,智库特指针对各种内政外交政策问题,由学有专精的学者组成的决策服务团体和咨询机构。[注]孙哲:《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基于已有的研究,根据智库国际比较研究的需要,笔者对智库的定义是: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注]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公共外交研究的重镇也在欧美,尤以美国学者为主。美国国务院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的、意在引导或影响其他国家公众舆论的项目,其目的是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注]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汉斯·塔奇提出,公共外交是政府与外国公众沟通的一种努力。[注]Hans Tuch.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0.英国学者通常将公共外交称为文化外交,认为政府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是公共外交,其目的是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以获得国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日本学界对公共外交定义为在国际社会提升国家的存在感,加深理解。[注]赵启正:《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新媒体与社会》,载《新媒体与社会》,2014(5)。印度学界认为,公共外交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既要赢得支持,又要说服他人。[注]Kishan Rana.Bilateral Diplomacy.New Delhi:Manas Publications,2002,p.24.中国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和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来说服他国受众。[注]唐小松:《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体系构建》,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6(2)。上述公共外交概念的界定,基本上遵循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理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众舆论影响力重要性的不断增强,公共外交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新公共外交应运而生。
在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共外交概念界定为: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下,通过以智库、媒体、企业等为主的多元化的行动主体,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传播内容,通过人际交流、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刊、书籍等全方位的传播媒介,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注]王莉丽:《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二)“智库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功能作用
结合对“智库”以及“公共外交”的概念分析,我们认为,公共外交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其中,智库是思想源泉和具有较强公信力的行为主体,这使得其所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对于舆论的形成、传播和受众说服都有特殊的作用。[注]王莉丽:《“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2)。笔者对“智库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如下:智库作为一种积极的公共外交行动主体、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的三位一体的角色,以高水平的政策专家和其创新的思想成果为基础,以国外智库和各界公众为目标受众,运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模式,以融合传播的方式,全媒介、多网络传播思想成果,开展对话与交流,影响他国公共政策和舆论。智库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思想的双向对称交流和舆论传播,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加深理解、增进互信、促进和平。智库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在国际舆论空间构建和提升本国意识形态权力。
具体而言,智库公共外交的功能可以分为以下两大层面:
第一, 影响舆论,在国际舆论空间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竞争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更重要的是以思想创新为核心的软实力之争,进一步而言,就是意识形态权力之争。一个国家是否受到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取决于它所传达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采取的沟通策略。智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政策研究、非营利、客观、中立的身份更容易被各国受众所信任,智库公共外交影响力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力量的充分结合影响他国舆论。智库公共外交对舆论的影响,具体可分为设置舆论的议程与引导舆论走向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都建立在智库具有优秀的政策专家和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就设定舆论议程而言,智库可以把创新观点、思想介绍给国际受众,或者把一些原本受到忽视的问题提出来。智库公共外交要实现这一影响力,可以通过在国外智库发表演讲、组织会议交流,在国外媒体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或者直接通过自媒体平台和社交媒体等多元化的融媒体传播方式来实现。就引导舆论走向而言,智库公共外交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传播媒介和模式,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进行舆论引导。
第二,加强理解,增进互信,提出思想建议,助推政府外交。在智库公共外交中,智库通过组织有关敏感问题的对话,作为对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或在政府外交陷入僵局时作为政府外交的替代品,为双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承担一种积极的助推政府外交的角色,从而有效加深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以中美关系为例:自2018年7月中美爆发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美政府外交一度处于紧张状态。2018年8月至9月中旬,中国多家智库与美国智库开展了思想交流与对话。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组织了专家代表团到访美国,与美国智库联合主办了一系列中美智库贸易对话。两国智库专家和原政府官员就中美经贸摩擦和中美关系等一系列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些系列智库对话中,参加者除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资深智库专家外,很多前任政府官员也参加对话,中方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美方有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约翰·艾伦、美国国防部原部长威廉·科恩等。这种智库公共外交的方式相比政府外交,氛围更为宽松,双方不受特定谈判指标限制,对话人员可以就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两国政府外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智库对话的专业性、灵活性、深度和广度为双方政府进一步寻找合作与对话的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使两国智库间的对话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有效防止双方的误解进一步加深,缓和冲突的紧张气氛,为官方外交提供问题解决的思路,为政府外交做好铺垫。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智库外交的作用,尤其是在政府外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公共外交毕竟只是政府外交有益的补充,并不能替代政府外交。
三、智库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机制与传播模式
智库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制定中不具有行政权力。智库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思想,其形式是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不同,智库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运用舆论的力量发挥其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舆论是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问题进行抽象思维,形成关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不同强度和类型的舆论。智库正是通过各种传播模式和媒介,影响一国舆论,塑造公众的认知框架,影响其态度和行为。
(一)智库公共外交影响力实现机制
智库公共外交发挥舆论影响力的机制可以从两方面来阐释:一是以美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迈克尔·曼的国家权力理论为分析框架,明确智库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二是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公信力理论、公共政策舆论场为理论框架,分析智库作为一种舆论力量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第一,智库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实践行为,通过思想的创新与信息传播,播散到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之中,从而在国家权力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模型。他认为,国家权力由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组成,这四种权力构成了重叠的社会互动网络,其中,每一种权力都贯穿于弥散的意识形态权力之中。[注]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1-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马克斯·韦伯指出,虽然直接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兴趣,但是,由观念所构建的对世界的认知往往像一个先锋一样,在决定行动方向方面起着确定性作用。[注]朱迪斯·戈尔斯坦等:《观念与外交政策》,49-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结构中,产生于社会机构所从事的实践行为中。[注]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24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世界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观念化的建构,对于世界的认知,取决于观念的创造、信息的传播和框架建构。智库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组织,其核心角色就是知识的储备、思想的创新和传播,因此,智库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国意识形态权力的创新源泉和发动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智库公共外交所能产生的作用,实际上是对一国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直接影响,而意识形态权力又是弥散性的。
对于智库的意识形态权力,西方学者也毫不隐晦。哈特维希·波伊茨指出,智库是根植于公民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机器。[注]唐磊主编:《当代智库的知识生产》,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乔治娜·穆雷和道格拉斯·帕切科认为,智库在维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转上发挥了看门人的作用,这部分归因于其能够在文化、道德、伦理和知识领域使其话语合法化。[注]R.C.Blank.From Thatcher to the Third Way.Think-tanks, Intellectuals and the Blair Project.Stuttgart: Ibidem,2003; R.Desai.“Second Hand Dealers in Ideas: Think-tanks and Thatcherism Hegemony”.New Left Review,1994, 3(1):27-64.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智库帮助建立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注]库必来 ·阿林:《新保守主义智库与美国外交政策》,4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以中美关系为例,自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美国对华关系每一次大的战略调整,其背后都是以美国智库为首的战略界进行思想大讨论和舆论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定的舆论声势,影响了舆论的空气,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和具体政策。对此,美国智库界著名的中国通杰弗里·贝德曾坦言,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是符合美国利益。[注]Jeffrey Bader.“U.S.-China Relations: Is it Time to End the Engagement?”.September 2018, Brookings Institution.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china-relations-is-it-time-to-end-the-engagement/.这是智库意识形态权力的直接体现。
第二,智库作为具有较高公信力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对目标受众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其在一国“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普遍居于舆论领袖、舆论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是思想形成、辐射、传播、交互的中心。
从理论支撑上来看,智库公共外交能够发挥作用的理论认知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和精英理论基础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观念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公共外交是建构主义理论在外交领域的体现。精英理论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和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精英而不是普通大众。包括约瑟夫·佩谢克、托马斯·戴伊、威廉·多姆霍夫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智库是整个国家权力机构的一部分。[注]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69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智库作为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商业精英汇聚的组织,在一国舆论场中,处于舆论领袖的地位。对此,“公共政策舆论场”理论给予了清晰的阐释。“公共政策舆论场”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政府舆论、智库舆论、利益集团舆论、大众传媒舆论和普通公众舆论。公共政策的形成是政府、智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公众通过各种媒体的互动达成的共识。智库影响力的实现是在这个多中心、网状互动的舆论场中与不同舆论因素的互动中得以形成并传播。[注]王莉丽:《论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形成机制》,载《国外社会科学》,2014(3)。在这个舆论场中,智库发挥着 “舆论聚散核心”的功能:智库一方面是各种舆论创新、融合、碰撞的磁场,另一方面是舆论传播的平台与交互中心。基于智库在一国公共政策舆论场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通过开展智库公共外交,可以与世界各国公共政策舆论界进行对话和交流,从而影响其国家舆论,最终加深理解、构建互信、促进和平。
从传播学视角分析,智库公共外交影响力的实现实际上是“一套政策理念构建与传播的互动过程”[注]V.A.Schmidt.“How, Where and When Does Discourse Matter in Small States’ Welfare State Adjustment?”.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3,8(1):127.。如果把智库公共外交视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传播主体是智库,传播内容是思想,传播媒介既包括智库自身创办的媒介也包括大众传播媒介,目标受众是智库及各界公众。对于目标受众而言,传播主体公信力如何是影响其信息接受度和态度、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卡尔·霍夫兰认为,公信力高的传播者更能改变受众的态度,而公信力主要与专业知识的掌握、公正度等有密切联系。[注]陈丽玫、吴国庆:《态度改变:说服策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社会心理科学》,2008(6)。按照罗伯特·加斯和约翰·赛特提出的公信力理论框架,智库在专业能力、可信度和友好善意这三大公信力理论维度上都具有优势,也因此使得智库创造和传播的舆论相较其他舆论传播主体更具可信度,对于受众而言也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智库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组织,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高度专业性。从友好善意的维度看,智库是非营利组织,其从事的研究关乎国家发展、社会民生,提出独立性、专业性的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这应该属于“善意”的最高层次,易于为公众信任和接受。[注]王莉丽:《“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2)。在智库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智库可以直接面向广泛的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另一方面,智库可以通过影响“一级受众”进而影响“二级受众”或者“多级受众”。信息的二级传播和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信息经常首先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注]Herbert Menze,and Elihu Katz.“Social Relations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Epidemiology of a New Drug”.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5,19(4): 337-352.
(二)智库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
智库公共外交实现影响力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舆论,使其意识形态发挥权力的作用。因此,智库公共外交具体传播模式和媒介的使用又是实现其影响力的具体路径和关键。关于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杰弗里·考恩和阿米莉亚·阿瑟诺提出的独白、对话、合作模式理论框架。[注]Geoffrey Cowan,and Amelia Arsenault.Moving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to Collaboration: The Three Layers of Public Diplomacy.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p.10-30.
独白式公共外交主要是指使用单向传播模式,向外国公众传播本国的政策。这种模式很难改变目标受众的刻板印象。对话式公共外交是一种双向对称的信息交流,有利于消除刻板印象,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话,分享意义,相互理解。兼具独白与对话优势的合作式公共外交,指在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合资企业或者项目中实现跨国参与,这种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影响目标受众。如果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智库公共外交,独白式模式显然不完全适用,对话与合作两种模式具有一定适用性。但仅仅强调对话,不足以解释智库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特性。合作模式在智库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中操作难度很大,各国的智库虽有其独立性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毕竟智库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国家的智库在本质上服务于国家利益。
智库公共外交追求的理想效果是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加强理解、增加互信,这与格鲁尼格的卓越公共关系理论诉求是一致的。卓越公关理论认为,双向对等是卓越公关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公关的理想模式。双向对等的公关模式强调对话,注重坦诚、完整、准确的双向交流,目的是促进相互理解,这种公关模式不以功利动机为出发点,以增进双方了解为目的。[注]黄懿慧、吕琛:《卓越公共关系理论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载《国际新闻界》,2017(5)。智库公共外交因其主体是智库,作为政策研究组织,其公信力建立在专业性和一定的研究独立性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智库公共外交在信息传播时不能过于注重说服性的技巧和宣传,而是要坚持客观研究基础上的双向对等的沟通与对话,以免影响其公信力。另外,智库公共外交还有一种通常采用的方式,就是智库以自媒体为中心,把各种有关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的研究成果,通过融媒体传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扩散其舆论影响力,构建全球舆论传播网络,注重加强社交媒体的交互式对话。
结合考恩和阿瑟诺的独白、对话、合作理论框架及格鲁尼格的卓越公关理论,我们认为,智库公共外交理想的传播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双向对等传播模式。主要是指围绕具体议题和内容开展智库对话、思想交流,以及可能的合作研究空间,目的是通过思想的交流与对话,加强理解,增进互信。第二,以我为主的融合传播模式。这里的融合传播,一方面是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模式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指智库以自媒体为中心平台,把智库的思想成果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进行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交互式对话,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智库思想的全球舆论传播范围,影响媒体议程、政策议程和受众议程与认知框架。
在智库公共外交的舆论传播中,除了以上两种主要的传播模式发挥作用外,在传播的层次上又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1)最直接的日常传播,通过融合传播的模式传播智库思想;(2)战略传播,在特定的国际关系背景和政府外交需求下,在一定时间段内,有针对性地围绕特定议题策划会议交流、研究合作、舆论传播活动;(3)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长时间段内,通过各种智库活动培育与目标受众国智库及各个层面公众舆论的友好关系。
四、结语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真正的大国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有创新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权力。在近现代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以思想的崛起为前提和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智库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全球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国家层面的智库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智库自身的机制建设和思想创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中国智库公共外交与欧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注]王莉丽:《从“智库公共外交”看智库多元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11。另外,智库公共外交普遍停留在浅层次的调研和会议交流上,还远远达不到双向沟通对话以及在国际舆论场设置舆论议程、引导舆论走向的目标,在为政府外交提供创新思想和有益补充方面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智库公共外交要取得良好成效,还有待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人才为核心提升智库思想的创新能力,通过智库公共外交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不断提升传播效果。关键在于:
第一,构建智库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当前中国智库公共外交实践缺乏理论的框架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智库公共外交的泛化和低水平传播。
第二,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智库要为人才的发展和知识创新提供培育土壤和有效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为智库人才提供制度化的上升空间,全面开启智库旋转门。这不仅有利于智库研究的创新与智库公共外交的实践,还有利于架起连接知识与权力的桥梁,长远来看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稳定。
第三,在明确智库公共外交功能、机制和传播模式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层次地安排智库交流活动,选择和设计战略传播模式,从而有效塑造与引导舆论。具体而言,通过举办品牌化的国际会议、专家互访、内部座谈、课题合作研究等活动搭建智库公共外交的平台;构建不同语言、不同媒介的新媒体传播网,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加强受众研究和新媒体时代舆情动态研究,不断有针对性地进行议程设置和舆论引领;加强智库学者与受众的互动和对话;借鉴欧美智库运营模式,探索建立中国智库海外分支机构。
第四,智库公共外交是一种双向的思想交流与对话,不是宣传和单向度的传播。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活动中,要明确自身智库的定位,不可把智库公共外交混同于媒体传播和政府宣传,坚持智库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避免被西方国家贴上“锐实力”标签。
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推进对这一重要而又被学界所忽视的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相信智库公共外交所产生的创新活力和构建的意识形态权力,必将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