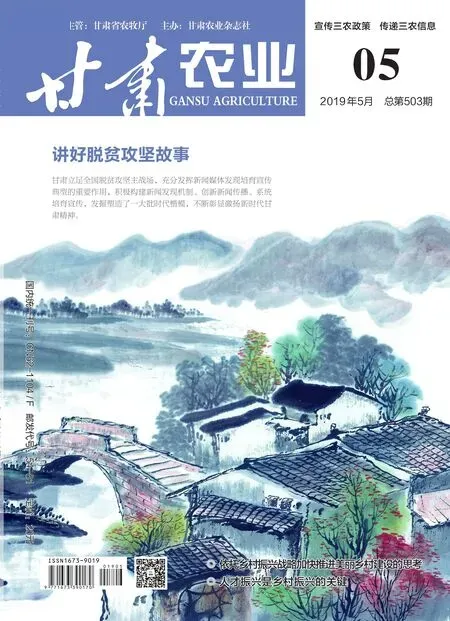加强和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
季存华
中共菏泽市牡丹区委党校,山东 菏泽 274000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其实质就是对乡村自然资源及报括乡村习俗、政治、经济制度、公共社会财富和服务的分配和处置。其目标是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经济运转高效、社会和谐、生态良性发展的目标。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关键、最基层,也是最难的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好坏,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如何在新时代推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施全面振兴乡村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一、建国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历史演变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由夺取全国政权过渡到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的上来。其中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前进。
第一阶段(1958-90年代中期)实行村级“政社合一”。我国在1958年开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即公社将生产与社会管理统一掌握到政府组织手中。无论耕地荒地、农具农机、种子肥料,还是瓜果、蔬菜、粮食等一切归于集体所有。既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对乡村社会成员统一集中劳动和管理。.
1964年之后,这种村级“政社合一”的管理权限逐步下放到生产队。从此以后一直长时间延续和执行这管理体制,只是具体形式在各地有所差别。
1980年代中国农村率先拉开改革的序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土地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土地等生产资料及财物进行重新配置,但在各地又有所不同,农户对土地等财产的权、责、利的权限划分比较模糊。
村级“政社合一”的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覆盖广,基本上包括绝大部分甚至全体社会成员;二是三级相连(政府、村委、村民)连接;三是村委包揽责任,即俗称“谁家的孩子谁管”,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事务都有所在的行政村村委负责处理;四是对资源再分配处置权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级,等级越高对资源分配处置权就越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效用,是乡村社会治理得到维系的原因。这一管理体制化解和抵消了组织外的社会冲突和干扰,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正常运转,正是得益于这种体制得存在。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90年代中叶以后,我国乡村发生了两个社会现象的变化。一是农村人口的流动出现,离家进城的人数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10年间,全国自然村由363万个减至271万个,有90多万个自然村销声匿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荒芜村、无人村。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下降、经济意识增强、社会治理环境发生变化。现在的乡村基层治理不再是对封闭的固定人群的治理,而是对不断变化的、流动的、差异的社会治理。村民对个人事务的处理不再单一的依靠村委解决,对法院、妇联、仲裁机构等社会组织有更多的选择性。同时社会资源的配置大多进入市场,由市场分配调节。因此乡村社会成员对基层政府的依赖性降低,社会治理职能退化。
二、困扰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
近年来,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不好,甚至有的地方问题频发,表现为:基层社会政治情绪化,群体事件不断,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对社会舆情把控不准,黑恶势力有所蔓延抬头。
(一)基层治理主体虚置,人民群众缺位
社会治理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谁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人民不能也不应缺席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广大村民应该在社会治理中唱主角,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基层治理中政府往往被治理主体的位置上,承担了过多工作。把民众当作治理的客体和“物”化的对象。替民做主,造成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在场”,甚至成为“看客”的尴尬场面。在治理过程中导致个别基层政府过度关心政绩和形象工程。有的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指出和强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二)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出现一定偏差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上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部分基层政府认为社会治理就是“治理社会”,“治理社会”就是力求社会稳定。维护稳定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有的基层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严防死守。有些基层制定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三不”操作原则,导致许多问题与矛盾被强制性地压缩在村镇而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当一些问题和矛盾长时间得不到妥善解决,民众得情绪得不到释放。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因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与矛盾积累到临界点而爆发的。这种治理理念是典型得传统管理理念和价值取向。不仅不能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反而会破坏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出现南辕北辙得治理效果。
(三)部分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弱化”
“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把党建设好,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广泛的影响,也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照样会毁于一旦。”从总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都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有所“弱化”,具体表现为:某些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被靠边站,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治理得主心骨,失去核心地位和领导权。某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组织力不强,对人民群众没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某些党员干部自身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在群众需要党组织解决问题得时候优柔寡断,不具有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和服务于人民的意识,导致基层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和核心地位下降。不断树立基层党组织应有的政治权威,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
(四)社会基层黑恶势力有所抬头
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村黑恶势力滋长蔓延有所抬头。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社会的治理环境发生了变化加;国家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缺失,管理松散和缺位;真正的农村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离家进城,留守人员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从而导致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治能力长期得不到有效培养”“党在基层力量的退化或退场必然有其他力量补场或进场”。一些所谓的乡村“能人”趁虚而入,渗透和介入基层社会治理。而留守在农村的老少妇儿显然处于弱势群体的处境,为乡村黑恶势力的蔓延抬头提供了发展环境。同时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党性不强、滥用职权、贪污腐败,成为农村黑恶势力滋长蔓延的保护伞。
(五)不能很好的把握社会舆情
众所周知,我国已迈向全面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农村网络的普及成为群众表达看法、排泄不满情绪,反映社会问题的主渠道。虽然社会网络舆情表面上是反映和传播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但往往一些关于政治、经济、民生、治安和腐败问题都有可能成为舆情的导火索并能够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如果对社会舆情不能够及时疏导处理和把控,就有可能演变成群体突发事件,产生一些方面效应甚至引起社会混乱。
三、加强和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举措
社会治理主要指基层社会治理。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基层治理实践由地方性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层面得认同。
(一)以创造美好生活为治理目标
现代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留的住“乡愁”的理念,振兴乡村,把乡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这就意味着现代乡村的治理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身边的困难问题着眼,从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做起,以群众得实惠、增进民生幸福为出发点,把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满足居民群众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旨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二)以党建引领为治理前提
坚持和完善党对乡村基层治理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工作的具体贯彻。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领导权,加强党引领做为乡村善治的一条红线。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培训,增强服务群众、清正廉洁、敢于担当,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意识和政治自觉。使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成为群众的领头羊和主心骨,对群众形成感召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其领导和核心作用。
(三)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自治法治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自治增活力、法制强保障、德治扬正气,自治以其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而凝聚共识,实施共治;法治以其规则刚性、程序透明、准则有效而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德治以其核心价值、公序良俗、社会贤达而弘扬正气、引领风尚”[1]。自治是法治与德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与德治的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德治以自治与法治为基石,并对自治与法治形成有力补充。
自治、法治、德治都是乡村社会治理基本关键路径。“三治融合”不是三条路径的平行也不是简单相加。关键在一个“融”字。“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产生的效果不是“和数结果”而应具有“乘数效应”,是倍数的增加。
“三治”有优先次序,但更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才能发挥“三治”结合的“乘数效应”。这要求在“三治”建设中要统筹兼顾,通盘设计。同时,社会力量成长是“三治”结合的“点睛之笔”,要充分吸纳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使整个基层社会治理迸发活力。如此,才能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甚至走向它的高级阶段“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四)坚持人民群众参与为关键
加强基层治理主体多元化建设同时,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的无穷的创造精神和活力。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才能使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走向良治和善治。没有群众的参与,自治形同虚设;没有群众的遵从,法治举步维艰;没有群众的自觉,德治难有成效。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