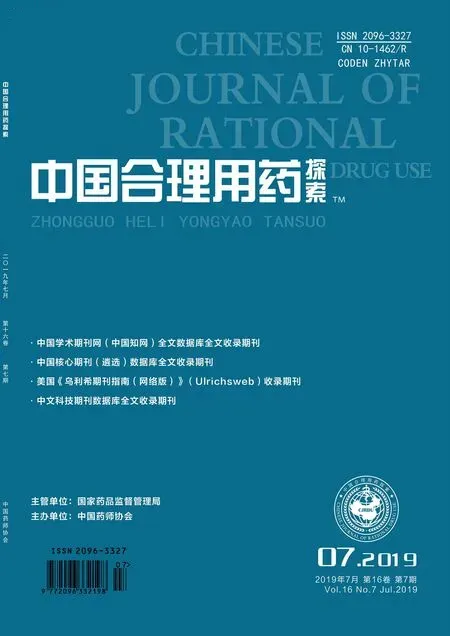“中医将毁于中药”的深层次原因探讨
罗超应,罗磐真,王贵波,李锦宇,潘虎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50;2. 西安市鄠邑区中医医院,陕西 西安 710300)
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曾不止一次指出[1-2]: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这不是危言耸听!社会各界对“中药材质量下降,行业无序竞争”的关注也是前所未有,并随着2016年12月6日《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与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此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莫大的希望。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今天中医药学所面临的危机绝不仅仅是中药材质量的下降,还有中医西化、人才流失、名家越来越少、后继乏人、临床阵地萎缩等;尤其是这种情况是在各方重视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似乎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遏制。笔者以为,学术异化所导致的“重药轻医”思想日益蔓延,也许才是其根本原因所在。在此不揣浅陋,愿就有关问题做一探讨,不妥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1 中药材规范化管理的不规范结果
1982年,我国首次将“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就陆续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与中医药医疗、教育与科研机构。1988年开始实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AP(药材生产管理规范)、GLP(药品非临床安全性试验规范或药品试验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规范)与GPP(药店管理规范)等规范化管理措施。截止2016年,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200余所高等西医药院校或非医药院校设置中医药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达75.2万人[3]。2016年12月6日发布了《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2017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4]。然而,据食药总局抽检数据显示,2017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19日,全国共计932批次药品被披露不合格,431家药企被点名通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619批次为中药饮片,占66.41%,成为行业质量问题的重灾区。痛定思痛,众多中医药企业均把矛头指向那些“乱像频出”的中药材种植源头;而除少部分因灰分、杂质、水分、掺假等其它原因造成不合格外,很多被查获的“曝光点”占比最大的症结还是种植、采收、初加工方面不规范。如不分地域南北的胡乱种植,以及种植期间无所节制的使用高毒农药、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是直接导致中药材道地性缺失、品质低下、农残与重金属超标,甚至性状变异的原因。为了赶上“好行情”,不分季节、时令提前或延后采收,以及初加工方面的不规范更是造成中药材成分含量流失、不足,最终成为不合格药材[5]。
这其中的原因并非“不重视”,而是长期以来西医药学观念主导所形成的中医药学学术异化,导致“重药轻医”甚或“废医存药”思想日益普及,对中医药认识与处理出现偏差。其一,在中药材所出问题中,最常见与最主要的是对“中医对中药要求”的忽视与丢失,而把中药逐渐沦落为某种植物或动物等的产品,非中医所要求的“中药”。其二,自“龙胆泻肝丸”及“鱼腥草注射剂”等中药注射剂事件以来,人们对中药安全性评价愈来愈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开展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然而,纵观中药安全评价方法与研究,多局限在动物实验的“唯成分”上,不仅脱离了中医药学最根本特色与优势——辨证施治;而且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看,更有待完善[6]。其三,现代研究表明,0.2 mg乌头碱就可引起中毒,2~6 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医辨证施治心衰时,在针对不同证候采用不同炮制、煎煮与处方配伍中,附子用量从0.3 g到600 g,其间相差2 000倍,却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而无毒副反应[7]。对此用现代毒理学的“唯成分论”研究是无法理解的。其四,临床中,许多人不敢使用“有毒”中药,或者是减少用量,结果虽无毒了,但也降低了临床疗效,一方面使中医沦为“慢郎中”,急症阵地逐渐丧失[8];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显著疗效”,有意无意地在中药制剂中添加西药等物质,给中医药带来很坏的影响。如香港麦永礼在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amacology上发文指出:从2005年至2015年,共有404人在服用了有问题的中成药保健品后入院治疗;而在检测病人提交的487种制品中,发现有1234种隐藏成分,其中包括多种经批准或被禁用的西药、药物类似物和动物甲状腺组织[9]。
2 转变科学观念,正确认识中药的特色与优势
中药之所以为中药,是因为它是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应用的,其特色与优势是与中医药学理论指导密不可分的。其一,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是通过化学物质发挥作用的。中药使用不仅要辨证施治与复方配伍,而且讲究一定的炮制与煎煮方法,以达到减毒增效的效果,并非天然的无毒不良反应。西药最初也是来源于天然的植物或微生物等,只是为了使结构更加稳定、毒性更小、疗效更好更持久、成本更少或使用更加方便等,进行提纯、结构改造或人工合成,其实在物质本性上与中药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10]。其二,西医处方中也常有2种以上的药物联用,但多是针对不同病因而各自为战的一个药物大拼盘;而中医药处方是根据中医药学君臣佐使理论将所有药物组成一个整体,针对一个证候而设,与西医药处方有着本质区别[11]。其三,中医药学辨证施治不仅在理论上强调要“因人、因时与因地制宜”,中药与针灸等不仅因为证候状态的不同,对机体机能活动具有广泛的良性双向调节作用;而且针对不同的证候状态,不仅药味不同,而且每味药的用量、炮制甚或煎法也有很大的区别,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科学“非线性作用特点”;而不像西医药辨病治疗,除过体液疗法等以外,大都是根据患者的体质量来计算药物的用量,一般变化都比较小。
中医药学辨证施治的实质是“状态分析与处理”。由于证候状态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不可能与某一种或几种因素或物质发生固定不变的联系,使中医药学辨证施治千百年来也没有筛选与开发出像抗菌药与疫苗等特异性高、作用强的防治药物,而对单一因素或物质的认识、把握与处理存在着不足,作用大多是非特异性与比较弱的,往往不被传统科学所重视。然而,根据复杂性科学,生物等复杂系统的物质或因素作用,不仅取决于物质或因素本身,而且也与作用的“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从而使物质或因素的作用具有了“非线性特点”,即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物质或因素的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所谓的“蝴蝶效应”、生物钟现象、药物的过敏与耐受现象,以及中药针灸等对机体功能的双向调节作用等等,说明生物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作用特点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在传统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的理念主导下,现代医药学愈来愈重视对物质或因素本身作用的认识、把握与处理。为了消除所谓的干扰因素,人们愈来愈重视对实验条件的严格控制,愈来愈讲究对临床数据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处理,而忽视了临床实际中各种干扰因素的真实存在与变化,随着慢性复杂性疾病的日益增多而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尽管从临床认识与处理的角度来说,有更充裕的时间与更多的机会,但临床疗效却往往不佳,或者是临床毒副反应更加多见与严重。如据JAMA(美国医学会杂志)2014年报道,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同时患有2种以上的慢性病症,其中14%的人患有6种以上的常见病症,超过三分之二的医疗费都是用于多种慢性并发病症的防治。然而,已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因为费用高而疗效差,在多种慢性并发病症的防治上面临着挑战[12]。2016年又发文指出:从美国内战到20世纪后叶,由于食物供应、卫生和医疗保健的改善与进步,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巨大胜利,美国人寿命迅速增加。1850年白人的预期寿命估计男性为38岁,女性为40岁;到1980年,估计值几乎翻了一番,男性为71岁,女性为78岁。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肥胖开始流行,预测美国人预期寿命在21世纪中叶将下降,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初步数据已为这一预测提供了新的证据[13]。2015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约为3.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与德国的国民经济总值,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2015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支出不到6000亿美元。到2020年,美国的医疗支出预计超过德国的国民经济总值,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的国民经济总值[14]。
不仅在临床应用上,而且在基础研究与药物开发上,西医药学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完成15年后,人们把基因组变异与疾病风险相关联,公开的结果数以千计,有关信息被期望作为精准医疗的基础,期望通过它对未来筛查、预防与量身定做的治疗提供建议,以达到对个体及其家庭的最佳管理。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因组的致病性变异信息往往是不可靠的,一般不能提供一个定量的疾病风险度量。文献报道常常是互相矛盾,不同实验室对基因组变异的致病性分类各不相同。由于缺乏共识,使基因组变异的临床重要性产生了分歧与混乱,或表现为意义不明[15-18]。对此Science指出:基因组生物学的教训很清楚,基因及其产品几乎从不单独起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基因、蛋白质及环境背景相互作用的网络中发挥作用的[19]。据统计,FDA1990年前每年批准新药不少于50个,到2002年逐渐减少到20个左右;而这种情况是在产业不断地合并与获得巨额支持,年度研究与开发花费约300亿美元的条件下发生的,且依旧在持续。据分析,是由于分子生物学体外实验与其要模拟的体内系统缺乏一致性,使药物研究由于缺少整体动物实验研究而广受危害,致使基因治疗(gene therapy)、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组合化学(combinatorial chemistry)、基因组学(genomics)、蛋白组学(proteomics)与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等,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20]。从2001年到2010年,FDA共批准了222种新药(183种化药和39种生物制剂),在平均11.7年的随访期内(IQR,8.7~13.8年),发生了123起上市新药安全性事件(3起撤销药物,61起警告与59起安全通报),共涉及71个新药,占新药总数32%[21]。
中医药学辨证施治虽然对单一因素的认识、把握与处理存在不足,但其“状态分析与处理”却是一种“多因素非线性分析与处理“的综合认识方法,不仅对现代科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在认识方法上具有很强的补充作用,而且从“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的认识过程来看,其也比“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更高级[22]。如中药针灸的抗病原体作用大多是非特异性的与比较弱甚或完全没有作用,但中西医药学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结合不仅可以克服中医无证可辨与西医无病可识之不足,而且还能非常显著地提高抗菌药等中西医药的临床疗效;尤其是在慢性复杂性疾病的防治中的优势更是明显与突出。然而,在传统科学理念的主导下,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最常见模式是将一病分成若干固定证型,列举症状、标明治法、规定方剂,把疾病分割成若干个固定的片断,既不能完整地把握疾病的本质,又把动态的疾病发展过程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无法体现“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辨证施治原则[23]。结果,该方法在初期虽是尽显优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的概念不断被强化,而证的理念是愈来愈弱化;前者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而后者则是逐渐枯竭乃至消亡,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了见什么病用什么方药的“对号入座”,不仅影响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而且严重干扰与影响了中西医药学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24]。因此,转变科学观念,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正确认识与处理中西医药学的优势、特点与关系,也许才是解决“中医有可能毁于中药”等诸多问题的当务之急。
3 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走出“重药轻医”的误区
3.1 走出“重药轻医”的误区
根据复杂性科学的认识来看,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医药学的最大特色与优势,而且也是西医药学辨病治疗的不可或缺补充,甚或是其认识的更高级形式。因此,应该走出以往“重药轻医”,以西医药学衡量与解释中医药学的误区,重视对有关辨证施治的知识与经验的继承与开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药的舍本求末;尤其是不能忽视中医对中药之要求,而将中药沦为没有中医属性的所谓天然物。后者不仅不利于中医药学的发展,也不利于西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3.2 坚持继承与借鉴并重
无论是中医还是中药,都面临着继承与发展问题。继承是发展的前提,而发展是最好的继承。发展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也可以通过借鉴来发展,且可能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历代的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中药就不乏吸收与借鉴外来药物;尤其是清末民初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与1949年后我国广泛开展的中西医药学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与改善了中医药的临床诊疗效果。只是由于在传统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主导下,走入了“重药轻医”的误区,给中医药学乃至中西医药学结合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转变科学观念,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促进中医药学继承与借鉴的并重发展。
3.3 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给中医药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由于中药复方成分众多,作用复杂,尤其是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尚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技艺,给中医药的现代科学技术认识、把握与应用等,带来了不少难题。如有企业就被质疑“以苹果皮代替原料”制作板蓝根以蒙骗质检[25]。那么,在今天日益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检测的情况下,应该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非简单地替代,以更科学、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与应用中药。
3.4 从中西药相互转化到中西医药相结合
在我国的中药现代化研究中,既有中药西药化研究,也不乏西药中药化的探讨。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中西医药学在对疾病认识与处理上,互有优势与不足,无法互相取代。而中西药物由于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在当今西医药学理论愈来愈强势,中医药学理论愈来愈弱化的条件下,不仅难免发生用药理论和方法上的牵强附会与偏差,而且还常常影响临床疗效,甚或导致严重的毒副反应[10]。因此,转变科学观念,充分认识中医药学辨证施治与西医药学辨病治疗在认识方法上的优势互补性与不可替代性,真正做到对二者并重发展,以相互借鉴与相互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