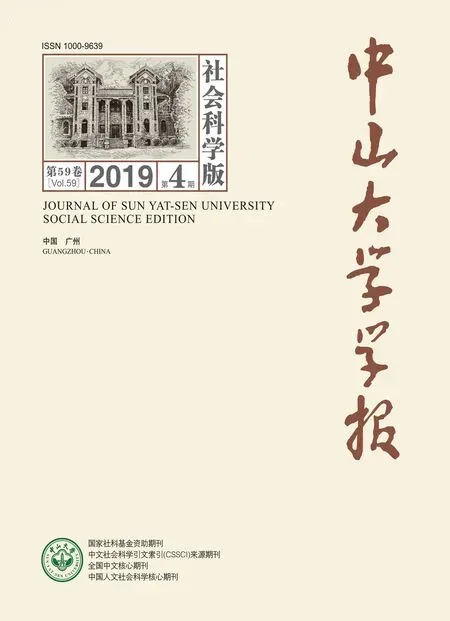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赵 德 波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辞赋大家,刘勰《文心雕龙》以“扬班张蔡”并称。费振刚《全汉赋》辑录蔡邕赋作17首,其中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述行赋》《释诲》《青衣赋》三篇,其他诸篇皆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其中《述行赋》为汉代纪行赋之殿军,学界讨论较多,《释诲》主要展现了蔡邕青年时代的思想和处世态度,学者在探讨蔡邕思想时也多会论及。《青衣赋》内容以叙写男女恋情为主,而且女主角为身份低微之婢女。该赋面世之后,即遭到张超《诮青衣赋》的严厉批评,但也有文学史家认为《青衣赋》为蔡邕的戏谑之作。受到以上因素的制约,《青衣赋》长期遭遇冷落。本世纪以来,伴随着学术思想与研究思路的转变以及学界对蔡邕文学史地位的重评,《青衣赋》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①参见俞纪东《蔡邕〈青衣赋〉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黄萍《蔡邕赋作的文学性审美阐释——以〈述行赋〉〈协初赋〉〈青衣赋〉为例》(《名作欣赏》2010年第17期)、《蔡邕〈青衣赋〉的诗学解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陈海燕《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恋情赋——论蔡邕〈青衣赋〉》(《名作欣赏》2011年第14期)。。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虽多有发明,但是对于《青衣赋》的写作时间及创作背景这一关键问题还没有考证清楚,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的遮蔽。因此,写作时间考察也就成为探讨《青衣赋》主题内容及文学价值的前提。
一、蔡邕《青衣赋》的写作时间与创作背景
蔡邕《青衣赋》的写作时间史无确载,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灵帝建宁四年说。邓安生认为,本篇写寒冬经过杨国,与主人女婢嬿娩情好,而迫于程限,不得不匆匆离去,追述别后相思之苦不可排遣。据赋中所述时地,当是建宁四年赴吊郭林宗,途经山西杨国情事②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99页。。第二,灵帝建宁三年说。俞纪东认为,此赋应该写于灵帝建宁三年(170)作者进入司徒桥玄幕府后,或者可能就在“出补和平长”之时。然而结合赋作内容及人情常理加以判断,以上说法均难以成立。首先,邓说之作于蔡邕吊郭林宗返程途中,很不合情理。郭林宗是当时的名士,被士人誉为“八顾”之一,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声望。郭林宗英年早逝,“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注]范晔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27页。。蔡邕还为郭泰撰写了《郭有道林宗碑》。丧礼是古之重礼,吊唁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吊唁之人及丧家主人的言行有着严格要求。吊唁尊者之后即沉湎于美色,对于逝者而言是不敬,而将此等风花雪月之事行诸笔端,更会招致谩骂和批评。蔡邕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其专长正在于礼学,况且素以孝著称。因此,《青衣赋》不可能作于此时。另外,据邓安生先生考证,《后汉书·蔡邕列传》所载“出补河平长”之事不载在何年。“按邕以建宁三年辟乔玄府,三年四年皆在京师,有事迹可按,则其出为河平长,或当在胡广卒后……又:《续汉书·郡国志》无河平县,本传亦未出注,其地未详。”[注]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第600,534页。至于俞纪东灵帝建宁三年说则不知其所据。
《青衣赋》所言故事发生在杨国。据《后汉书·蔡邕本传》所载蔡邕行迹,除了邓安生所指出的汉灵帝建宁四年,蔡邕因吊唁郭泰经过此地之外,还有一次发生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该年灾异频仍,蔡邕、杨赐等人应灵帝召答灾异,蔡邕因此先后上《答诏问灾异疏》和《答特诏问》,将灾异出现归咎于宦官专权。后诏书外泄,蔡邕被宦官谄害收治狱中,经中常侍吕强等营救,减死罪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居五原郡安阳县。蔡邕《月令问答》载:“光和元年,予被于章,离重罪,徙朔方……故遂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③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第600,534页。晋国故地是蔡邕从洛阳到五原郡的必经之地。《青衣赋》很可能作于蔡邕从洛阳流放五原途中,这可从《青衣赋》本身找到内证。
纪行赋作为汉赋之一种,通过记述行旅中所见所闻抒发自己感慨,作者借所经之地历史典故抒发自己感慨成为其写作的重要范式,这在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和蔡邕《述行赋》中都有体现。因此,通过纪行赋中出现的历史典故可以大致还原作者的行旅轨迹。《青衣赋》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行赋,但肯定是蔡邕对行旅之事的记载。通过其中出现的地名及历史典故,亦可还原蔡邕的流放轨迹。赋中写道“故因杨国,历尓邦畿”[注]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第147页。后文蔡邕赋作原文均据该书称引,不再一一出注。,其中“杨国”是邂逅青衣的地点。杨国为周初所封姬姓诸侯国,“晋灭之为杨邑,汉为杨县也”[注]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29页。。两汉时期杨县属于河东郡,《汉书·地理志》载:“河东郡,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濩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讘,骐。”关于杨,应劭注曰:“杨侯国。”[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0—1551页。《后汉书·郡国志》载,河东郡二十城,杨为其中一城。杨县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五十里左右。另外,赋中还写道“代无樊姬,楚庄晋妃。感昔郑季,平阳是私”。樊姬是楚庄王的妃子。樊,又称樊阳。《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对此,杨伯峻注曰:“阳樊即隐十一年《传》苏忿生田之樊,亦曰阳,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2页。郑季是西汉大将军卫青之父,河东平阳人,为县吏,给事平阳侯曹寿家,与其婢卫氏私通,生卫青。又《史记·卫青列传》载:“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张守节《正义》曰:“《汉书》云:‘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之家’也。”[注]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21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此外,该赋的结尾之处写道:“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其中“河上逍遥”出于《郑风·清人》有“河上乎逍遥”。《毛传》:“清,邑也。”《郑笺》:“清者,高克所帅众之邑也。”《水经注·潧水注》:“渠水又东,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阳亭西南平地,东北流经清阳亭南,东流即清人城也,《诗》所谓‘清人在彭’,故杜预《春秋释地》:‘中牟县西有清阳亭。是也’。”[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42—343页。后文《诗经》原文及注解,如不加注释均据该书称引,不再一一出注。因此,《清人》中出现的地名,彭地、消地、轴地均是黄河临岸之地。蔡邕被流放五原,其地在今内蒙包头,离开临汾一带后沿黄河东岸北行到达那里。由《青衣赋》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断蔡邕流放途中进行路线如下:洛阳—济源(樊)—临汾(平阳)—杨县—黄河沿岸。
蔡邕的流放轨迹可以在刘歆《遂初赋》得到印证。汉哀帝时刘歆争列《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论其义,诸博士不肯置对。刘歆乃移书让太常博士,因“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注]严可均:《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8页。《遂初赋》作为刘歆被贬到五原的文献,其中出现了诸多的晋地名称。如其中写道:“过下虒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关于虒,《左传·昭公八年》杨伯峻注写道:“《水经》汾水注云:‘汾水西经虒祁宫北,横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径五尺,裁与水平,盖晋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败也。’又浍水注:‘又西南过虒祁宫南,其宫也背汾面浍,西则两川之交会也。’则当在今侯马市附近。”[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00—1301页。赋中又写道“唁靖公于铜鞮”,其中铜鞮在今山西省沁县南,而“历雁门而入云中”的雁门,在今山西朔县,从那里越过长城进入云中郡,然后向西到达五原。据此可知,刘歆的行程路线为:洛阳——侯马——铜鞮——雁门。进入三晋故地之后,他也是沿着黄河东岸北行,与《青衣赋》所涉地域大体一致。
蔡邕作为戴罪之身,有没有与青衣邂逅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蔡邕在流放途中得到保护,没有性命之虞。《后汉书·蔡邕列传》载,流放途中“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其次,在中常侍吕强的营救下,蔡质、蔡邕“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蔡邕、蔡质叔侄同时入狱,亦当同时流放五原,否则,对蔡质下落应当另作交待。另外,蔡邕被程璜陷害后上书自陈所言:“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注]范晔等:《后汉书》,第2002页。可知,流放途中蔡邕没有家属可以携带,而携带家属的应是蔡质。从洛阳流放至五原,费时既久,加之没有家眷在侧,与青衣之邂逅亦属情理之中。基于以上推断,《青衣赋》应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流放五原途中。
二、《青衣赋》的隐性主题及内容的时代超越性
《青衣赋》全篇共计264字,全用四言,注重押韵,格式较为整饬,是汉代唯一通篇用四言写成的赋作。从“金生沙砾”至“在此贱微”为第一个层次,作者从容貌和品行两方面表现青衣之美,并对青衣的身世寄寓了深势的同情。从“代无樊姬”到“尔思来追”为第二个层次,描述二人邂逅及离别的过程,并叙写了别后对青衣的相思。从文本显性层面来看,《青衣赋》确实是以纪实的手法,叙写了蔡邕与婢女的交往及别后相思。然而,结合《青衣赋》的创作背景不难看出还有一个隐性主题,而且这一主题作者主要通过《诗经》典故加以展示,在形式上比较隐蔽。
该赋的结尾之处写道:“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此处叙写作者别后相思之情,不仅出现了“河上”“庭阶”“井柳”“斗机”“牛女”等表达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情的经典意象,还有一系列《诗经》典故的称引或诗句的化用。其中“河上逍遥”出于《郑风·清人》“河上乎逍遥”。关于《郑风·清人》诗旨,《齐说》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遥不归,思我慈母。又曰:慈母望子,遥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毛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毛序》更得该诗之本旨,该诗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表面上讽刺对象是高克,深层次斥责的对象则为郑文公,造成高克奔陈的根源在于郑文公昏庸。朱熹《诗集传》中有如下评论:“胡氏曰,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惟我所制尔。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坐视其离散而莫之卹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注]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0页。“非彼牛女,隔于河维”,化用了《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关于《小雅·大东》诗旨,《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笺:“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大东》产生于西周后期厉幽之世,此时赋役严重,民怨深重,其根源亦在于君主的昏庸。此外,“思尔念尔,惄焉且饥”,化用《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关于《汝坟》诗旨,《鲁说》曰:“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来,妻恐其懈于王事,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国家多难,惟勉强之,无有谴怨,遗父母忧。”《毛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郑笺谓“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与《列女传》“生于乱世,迫于暴虐”合。可见,该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商纣王之时。近人多认为该诗为妻子挽留久役归来的征夫而唱的诗歌,而造成夫妇别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商纣王倒行逆施和沉重的劳役。此处密集使用《诗经》典故,且所取诗篇之诗旨具有相似的政治指向。因此,所化用的《诗》句,抒发的就不仅仅是对婢女青衣的相思怀念,更多的是对当朝君王昏庸所导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及自己惨遭流放现实处境的愤慨。《文心雕龙》称:“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9页。蔡邕之精雅,由此可见一斑。
美女祸国理念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汉代刘向《列女传》进一步确立了比较明确的丑女兴邦,红颜祸国的观念,且这一观念在后来逐步强化。到了东汉中后期,伴随着外戚干权现象的反复出现,红颜祸国的观念也就成为抨击这一政治事象的理论基础和当时士人群体话语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美色成为汉代学者敬畏的话题,对女性的赞美往往注重于对内在德行的赞美,而非外在的美色。即使在汉代美女赋中,虽然不乏对女性形貌的描写,但是落脚点仍在对其品行的赞美上。这一点在《青衣赋》也有体现,赋中不但称赞青衣外貌之姣好,还对其品行极力称赞。然而,与汉代美女赋的不同之处在于,美色当前蔡邕没有守住道德底线,而且还将欢会的场景写入赋作:“寒雪翩翩,充庭盈阶,兼裳累镇,展转倒颓。”诚然,对于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也存在于蔡邕其他作品之中。如《协初婚赋》:“其在近也,若神龙采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立若碧山亭亭竖,动若翡翠奋其羽。众色燎照,视之无主。面若明月,辉似朝日,色若莲葩,肌如凝蜜……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茵褥调良……粉黛弛落,发乱钗脱。”《检逸赋》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然而,就描写的目的而言,《青衣赋》与以上两部作品存在着明显不同。《协初婚赋》描写的对象为新婚夫妇,女性体态及相关男女好合场景的描写是为了实现对女性的教育。其作品性质与张衡的《同声歌》、荀爽的《女诫》、程晓的《女典篇》、曹植《感婚赋》、秦嘉《述婚诗》一样,“都是以文学的形式来讨论妇顺的内容,重申女子事夫的原则的”[注]许云和:《张衡〈同声歌〉:一部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女诫》,《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至于《检逸赋》的主题,陶渊明《闲情赋序》中写道:“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注]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3页。因此,《青衣赋》中的女性描写不仅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于雅正的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
三、“青衣”形象的确立及其文学史意义
《周礼·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5页。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色彩理论的最早记载。“按周代奴隶主贵族的传统,色彩也有尊卑的区别,青、赤、黄、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贵,正色是礼服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流黄(駵liú音留)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色。”[注]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54页。由此可知,先秦时期,青色作为纯色属于尊贵的颜色。《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注]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0页。春天举行春祭,天子着装、配饰、车驾的颜色均为青色,这与战国至汉代逐渐形成的五行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在五行系统中青色与东方相配,与生命初生的事象相配。如《郑风·子衿》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起兴,《毛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郑笺》曰:“礼,父母在,衣纯以青。”《楚辞·九歌·东君》在描写太阳神形貌时写道:“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王逸注曰:“青云为上衣,白蜺为下裳也。日出东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为饰也。”[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页。汉代经学系统中进一步用五行观念来解释服饰制度,《春秋繁露·服制像》称:“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韨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注]董仲舒撰,苏舆义证,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1—152页。《说文解字》曰:“青,东方色也。”[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释名·释采帛》中也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注]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校:《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7页。高诱为汉末建安人,其在注解《淮南子》“黼黻之美,在于杼轴”时写道:“白与黑为黼,青与赤为黻,皆文衣也。”[注]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16页。可见直到东汉末年青色在服色系统中地位并未降低,青衣并未成为身份微贱之人的代称。另外,据《魏书·礼志》载:“《续汉·礼仪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帻,秋夏悉如其色。’”[注]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7页。又《晋书·礼志》载:“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注]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0页。可见,东汉春祭仪式继承并发展的周代春祭服仪,时至魏晋仍在袭用。
蔡邕《青衣赋》中的“青衣”究竟是婢女的名字,还是指婢女的着装,已经无法确知。然而,蔡邕《青衣赋》之后,青衣逐渐成为婢女、童仆等代称,青色也成为古代下等人着装的底色。蔡邕《青衣赋》将婢女与青衣相关联,使得后世文学中往往以青衣指称婢女。建安二十四年(219)杨修死后,曹操写给杨彪的《与太尉杨彪书》中写道:“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注]严可均:《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32页。《徙东莱王蕤诏》中写道:“收舆之日,蕤与青衣共载,微服奔走,经宿乃还。”[注]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0页。此外,青色在民间服色和官方冕服制度中地位也逐渐下降。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青色,成为低级官吏着装的服色。据《晋书》记载,永嘉七年,晋怀帝为刘聪所俘。刘聪“使帝著青衣行酒”。所谓“青衣行酒”就是穿着仆役穿的衣服在宴会上给人们斟酒。这一侮辱之举,令“侍中庾珉号哭”[注]房玄龄等:《晋书》,第125页。。中国古代服装中以颜色标示着装者身份地位还表现在“品色衣”制度上。“品色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北朝时期,《周书·宣帝纪》载,大象二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注]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23页。。这种按服色标示官品等级的制度在唐代官服定制中正式确定以来,“唐代的官服服色制度就有一品红色、二品以上紫色、五品以上朱、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青等”[注]李当岐:《服装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伴随着青衣指称婢女内涵的确定化,从南北朝开始,“青衣”作为男女相思爱恋的主角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徐陵《玉台新咏》卷六所收录的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中写道:“芳树发春辉,蔡子望青衣。水逐桃花去,春随杨柳归。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独知离心者,坐惜春光违。洛阳远如日,何由见宓妃?”[注]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唐代诗歌中青衣意象更多,如王建《早春病中》写道:“师教绛服禳衰月,妻许青衣侍病夫。”[注]彭定求:《全唐诗》(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409页。后文出现唐诗均据该书称引,不再一一出注。在白居易诗歌中“青衣”更成为常客,《和春深二十首》(其十八):“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斜。”《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其一:“青衣报平旦,呼我起盥栉。”《残春晚起,伴客笑谈》:“披衣岸帻日高起,两角青衣扶老身。”《三年除夜》:“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作为晚唐诗歌中的名篇李商隐《锦瑟》,其主题一直争议颇多,胡应麟在《诗薮》中写道:“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谓义山有感作者。观此诗结句及晓梦、春心、蓝田、珠泪等,大概‘无题’中语,但首句略用锦瑟引起耳。宋人认作詠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胡应麟认为锦瑟应为婢女的名字,其身份也是青衣之属。
然而,蔡邕《青衣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止于此,该赋中以蔡邕自身经历而创造的才子佳人遇合情节模式,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的先河。从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芳树发春辉,蔡子望青衣”一句不难看出,《青衣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男女恋情的憧憬与渴望,在费昶看来已经俨然成为一种美学范式。直至清代袁枚《亲种》(其二)中还写道:“凉月香灯梦未消,青衣作赋诮张超。凤凰飞去箫声远,不管梧桐叶尚摇。”[注]袁枚:《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4页。此处,袁枚将蔡邕与青衣的故事作为才子佳人遇合的典型写进诗作,体现了《青衣赋》在主题上的永久魅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蔡邕本人在后世文学中的形象也屡经沉浮。正如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其四)所写:“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注]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93页。其中描写的正是村民围听盲翁演说“赵贞女蔡二郎”故事的场面。《赵贞女蔡二郎》为民间南戏“戏文之首”,其中塑造的蔡二郎形象与蔡邕历史形象出现重大反差。“我们不禁想到文学史上的一件悬案:蔡邕明明是‘博学多才’、‘行义达道’、‘忠孝素著’(《后汉书》本传)的一代名士,为什么在南戏‘宋元旧篇’《赵贞女蔡二郎》中被写成‘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徐渭《南词叙录》)的反面形象?”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俞纪东指出:“《青衣赋》没有写到爱情故事的结局,但‘始乱终弃’则是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人们往往喜欢站在弱者的一边,对于《青衣赋》来说,同情当然就落在了‘青衣’身上。”[注]俞纪东:《蔡邕〈青衣赋〉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俞氏所言可谓慧识,指出了后世戏文中蔡邕负面形象出现的原因与《青衣赋》的内在联系。需要补充的是,蔡邕在世之时及被杀之后,常被时人当作偶像对待。然而,“人一旦从历史舞台上淡出,换言之,物故了,就真是变成了物,不仅完全失去了支配自己的能力,而且,还会落得被后人随心所欲歧解曲解的下场”。“蔡邕的神话,固然使得他成为同时代人的偶像,使得他成为《后汉书》中的英雄,成为《三国演义》中的义士,成为一些文人的同情对象。(温庭筠的名诗《蔡中郎坟》颇具代表性。诗云:‘古文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注]朱国华:《蔡邕的悲剧》,《读书》1998年第4期。及至明代,高明不满《赵贞女蔡二郎》中对于蔡邕形象的塑造,又做了翻案之作《琵琶记》。从这个角度而言,蔡邕成为蔡二郎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于蔡邕与青衣结局的悲观预测,“蔡二郎”更不是指的蔡邕本人。唐代以来的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中,悲剧多喜剧少,负心汉多痴情汉少。由于蔡邕在《青衣赋》中最早将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写入文学,其本事也成为后世才子佳人故事的典范。因此,正如青衣是婢女的代称一样,《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二郎”已非历史上的蔡邕,而成为负心汉群体的指称。“蔡二郎”也就为唐代以来的负心才子背负了骂名。明代高明创作《琵琶记》为“蔡二郎”正名,也源于他没有真正理解《赵贞女蔡二郎》中运用的正是《青衣赋》中才子佳人遇合之情节,而不是着眼于历史上蔡邕本人的文行出处。
综上所论,蔡邕《青衣赋》不仅叙写了与婢女青衣的恋情,更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在中国文学史上,《青衣赋》不仅是第一篇大胆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更是将婢女形象纳入了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本事也就开创了后世没落才子佳人遇合之先河。后世以青衣指代婢女或平民,乃至戏剧中将“旦”作为女性角色之一,并将青衣作为戏剧中年轻女子角色的代称,都是受到了《青衣赋》的影响。以上正是《青衣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以《青衣》为书名写了一部小说的作家毕飞宇,认为‘青衣从来就不是女性、角色或某个具体的人,她是东方大地上瑰丽的、独具魅力的魂。’”[注]于平:《舞剧〈青衣〉的奔月情怀》,《艺术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