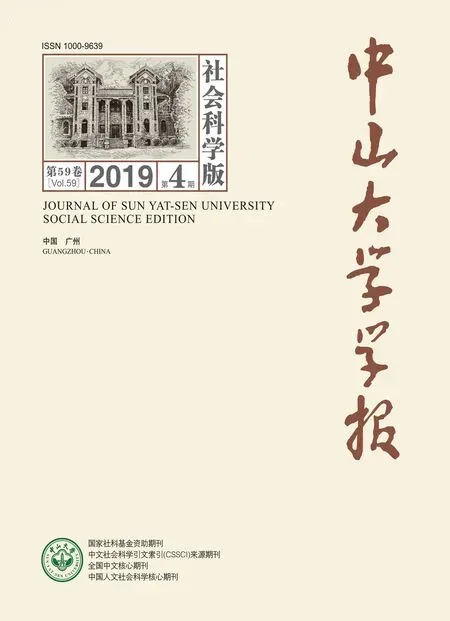文化自信的对话性建构*
金 惠 敏
中国和平崛起,进而参与全球治理,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解决世界乃至人类普遍性问题,远不再是从前那种国际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言壮语,而是切切实实地正在发生着的伟大历史事件。与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上大国地位日益凸显的过程相呼应,从1980—1990年代在民间开始酝酿,到中央层面上2011年胡锦涛首开关注①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2版。,2016年习近平两次隆重阐述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 年5月19日,第2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接着2017年在十九大开幕会上庄严昭告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19、23、41,41页。,文化自信逐渐演变为现今政治宣传、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最活跃的话题之一。四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它荣居其一,而且与其他自信相比,被渥眄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攀升至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19、23、41,41页。。
文化自信“信”什么?当然是信“自”了,是对自身的信心与骄傲。但“自”“自身”又是什么呢?对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有最新、最权威的表述。他指出,文化自信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种文化首先由两大成分构成: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绝不停留于一种观念或话语的形态,相反,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7、19、23、41,41页。。由于其实践性品格,由于其从而被宣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以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而非“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基本原则,这样的文化当然也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包括外来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是本来文化的当代化,是外来文化的在地化,是作为话语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具身化和现实化[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25、59、41页。。对此,以习近平为首席作者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讲得异常清晰,不存在歧义和歧解的空间:“创造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更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凡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文化,既渗透着历史基因又浸润着时代精神,既延续着本土文化的血脉又吸纳着外来文明的精华。”[注]刘奇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36页。这即是说,如果就其来源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一定是“我中有他”“我中有异”的,当然此时的我中之他、我中之异已非先前之他、之异,它们因脱离其原先的语境而不再是其自身。它们获得了新的归属,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
按理说,有十九大报告之权威表述以及近年来数以千计万计的阐释类文章,对于什么是“文化自信”这样基础性的问题不应该再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了。但事实是,我们发现,文化自信并非不言而喻,而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甚或言之即非。这其中,对文化自信的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偏执理解尤为刿目怵心[注]参见金惠敏:《人类文化共同体与中国文化复兴论》,《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似乎早已氤氲成一种公共阐释,乃至社会情绪。例如,每逢中外某种摩擦或冲突之发生,文化自信便经常火爆为网络口水大战,甚至有时还被倾泻为一场场街头闹剧或悲剧,以至于官方总是不得不出面提醒“理性爱国”云云。
文化自信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强盛,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换言之,文化自信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甚或是全人类的问题。文化自信是显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标志,或简言之,文化自信即文化软实力。如所周知,“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④刘奇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36页。。一个被扭曲了的文化自信如文化民族主义,不是文化软实力,而是文化破坏力,必将误国误民,并殃及世界。职是之故,如何正确把握、熔铸和传扬我们的文化自信便是一项亟待研究的政治课题和学术课题了。
正确理解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一个“自”字,即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自我和文化特殊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针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文化特殊论,从能动自我、结构自我两个新创概念,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重新界定自我和特殊性,将其作为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和建构,提出自我即对话、特殊性即对话的理论命题。文化自信由此而得以成为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生活的而非教条的、当代的而非复古的概念,即是说一个对话性的或曰间性的概念。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自信!
一、能动自我、结构自我与文化“自”信
谈论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当是其首要的所指。毫无疑问,重振文化自信就是恢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凝聚自我文化身份。尽管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自我是各种话语和体制的想象性建构,但这仅仅是就其构件而言的;一旦这些构件得以形成一个有机体,发挥其功能,那么它便不再是构件而成结构了。结构主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在自我中只看见构件,而不见结—构,不见构件之结合而成一新的功能体,更不见此结构实乃一生命。作为结构(structure)的自我也是生命的自我,是能动(agency)的自我[注]在当代社会学中,结构指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而能动则是个体行动和改变社会的自由。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叫“能动”;但说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必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则指的是“结构”(See Anthony Giddens & Philip W. Sutton, 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2014, p.23-26)。笔者的“能动”概念要宽泛一些,不仅指个体的行动(表面上),更指个体的生命及其能量(深层里),因为有生命,而后才有行动,行动的本质是生命的冲动和运动。此外,笔者还特别强调结构的能动性,即结构而成生命,与能动的结构性(起源上或构成上)和结构化(对外在资源的整合),于是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被彻底打破。不过在具体使用中,笔者有时也保留了能动的积极性与结构的消极性,二者仍是各有其意义侧重点的术语。。凡结构必有生命隐含于其间,反过来说,无生命则不成结构。试想,假使不存在能动的言说者,那究竟是谁在推动德里达所谓的能指的“延异”?能指无能,能指自身无能于“延异”,能指的“延异”根本上是言说者为了实现其最终意指的“延异”。
与结构主义将主体风干于虚无缥缈的符号世界不同,吉登斯夫子自道:“就社会理论而言,最重要的进展并非与一个语言转向多么相关,而是更系乎这样一种被修正过来的观点,即主张言说(或意指)与行动相交接,这一修正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实践(praxis)概念。”[注]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1986 [1984], p.22,25.其“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若就字面上看似乎不过是符号自身的游戏性展开,仍然闭锁在结构主义的深宅大院,但实际上由于他将结构置于鲜活的实践之中,让言说与行动相交接,结构因其不只是对行动者的限制,而且也是行动者借以行事的规则和资源,那么,了无生命迹象的结构便进入了生命的过程:“结构并不‘外在’于个体:作为记忆的雪泥鸿爪,作为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显现,它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内在’于,而非如涂尔干所假定的,是外在于个体的活动。结构绝不等同于限制,它永远是限制与使动(enabling)兼而有之。”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1986 [1984], p.22,25.吉登斯虽非完全否认结构,例如在涂尔干那里(“社会事实”[注]涂尔干以“社会事实”(socialfacts)指称符号系统、意识形态、经济制度、道德义务、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它们对于个体的构成和行动具有“外在性”(exteriority)和“制约性”(constraint)。此外,涂尔干还提出“将社会事实视作物”(consider social facts as things),其意在突出社会“事实”具有坚硬如自然之“物”即轻易不为直觉所透视、不为个人意志所塑造的特性(See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86-91)。在否定的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也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来源之一。)对于行动者的制约作用,但他更愿意做的显然是,赋予结构以生命,让结构具有“使动”因而具有生命的功能。不过,在此需要明确一下,结构之“使动”并非意味着结构本身自动地给予行动者以行动的能力,而是行动者将死的结构(规则和资源)使用为活的生命,使其在为生命活动的服务中转化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吉登斯未作严格而清晰的界分,其解说即“结构与能动相互包含。结构是使动,而非只是限制,它使创造性行动得以可能”[注]Anthony Giddens & Philip W. Sutton, 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p.25.,歧义丛生,读者极易陷进结构本身在行动这样的错误观念之中。准确地说,作为规则和资源的结构只是有助于行动者达到其目的,其本身无能行动,“使动”的是行动者。但无论如何,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与能动不再是两个对立的范畴,不再是结构取消能动,或者能动无视于结构,它们在实践中合二为一:接合,并融合。吉登斯之引结构入能动或者说化结构为能动的这种理论努力,在结构主义深入人心的1980年代里,实属难能而可贵!
对于我们的命题,结构即生命,即能动,吉登斯道出了它的第一重意义,即结构融入能动而获得能动,换言之,是能动赋予结构以生命或生命的力量;但更根本的则是其另一重的含义,即结构化(让我们继续使用吉登斯这一未尽其用的术语吧)在起源上即产生能动。在这里,我们不必谈论生命在其原初出现时便是各种元素的阴阳化育,每一种文化——其身份,其特殊性——的形成较之自然生命的诞生都更显其在来源上、构造上的复合性。没有哪种文化不是结构而成的。结构化,更准确地说,趋向于结构,乃生命之形成过程,结聚、构造而成生命。我们不是生命的先在论者,即坚持先有生命而后再有生命对结构的使用这样庸常思维中的论点,而是认为自然的生命是自然的结构化,文化的生命是文化的结构化。此乃其一。但是,其二,一旦结构而成生命,那么生命便以其能动而对自然进行积极的回应和改造。在人的生命这个层次上,文化以人作用于自然的方式,但更以在人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与其他人建立互动关系即主体间性的方式被创造出来。是人的生命创造了人的文化,这一创造物为文化生命;而既然作为生命体,它便一定要继续外突、外显、抢占和入侵,这仍是一个结构化过程,即是说,它仍需不断地结构进其身外的自然和社会语境以及与其相遇的其他文化,如同滚雪球一般把一切能够吸附的东西都碾压进来。这样的文化就更显其结构化之本质特征了!可以认为,文化从来就是结构性的,无论其在始源上抑或在表现形态上。
然而,揭示和坐实文化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必然导向对其作为生命的否定。叔本华以剥洋葱为喻,说寻找人生的意义如同剥洋葱,剥到最后一无所有。罗兰·巴特也使用过这一比喻,认为根本不存在作品或作品的内核,而只有一层层叠加的文本或文本间性,文本之内无一物。延展这一比喻,也许结构主义者会说,寻求文化的生命,或者,界定文化的特殊性,就像剥洋葱一样,但见一层层的结构,而不见生命本身。其错误显而易见,即如前所谓,结构主义者不了解结构与构件的不同:结构是有机的,而构件则是无机的。例如在个体的结构中,若是删除其文化、其肢体等构件,那么个体及其生命亦将不复存在。这也就是说,生命是整个的洋葱,而非某一层面的洋葱。同理,文化是结构的,但也是结构整体的或结构有机体的。
既然结构即生命,结构即能动,那么结构自我与能动自我的关系,在二者作为生命、自主和独立个体的意义上也就没有必要划江而治了,它们本就是一家。自我可以还原为结构,而结构亦可组构为自我。结构自我同时即是能动自我,反之不谬。据此命题,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断言,中华文化既是结构性的,但也是生命性的。无论其构成多么混杂,其来源如何多样,如历史学家所证明的,中华文化都仍然具有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身份,都是一个有机能、有意志的生命存在。就像将主体风干为语言符号,以结构来解构中华文化特殊性的尝试,也注定是劳而无功的。作为生命,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基因般的存在。不要不相信文化的生命性存在,即便在吉登斯之结构化的意义上。
中华文化产生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能够满足中华民族的文化需求,包括日常伦理需求和形上之精神需求以至信仰需求,生生不息而成所谓之“传统”,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传统是活着的历史,而遗产则是有待复活的历史。至于人们让哪些遗产复活,或者,让哪些遗产继续冷藏,则取决于其不停躁动着的生命欲望及其所外化的社会实践。我们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并非表明我们多么地恋旧、念旧,而是我们所置身其中的文化体即我们的生命与其形式建构了比较牢固的粘合。因而必须指出,人不是文化的形式主义者,其所秉承的总是文化现实主义。现实流变,文化亦相应地跟着变化。就其决定性作用而言,文化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和实践。这本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推及文化内部而言,即视文化由生命与其外化(而为所谓的“文化”)两部分构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仍然有效。人们常常是错把文化的话语维度当成了其生命维度。其实,文化的话语以及话语实践维度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附着于生命,是生命的表征;然而滑稽的是,它有时竟俨然代表着生命,以生命本尊自居!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而是要立足于当代文化之现实需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复古主义者忘记了其脚下的大地,其实质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强调中华文化的自我性、自我能动性,或者,作为能动自我的中华文化,绝不意味着一个自我封闭的单子世界,相反,它是一个自我敞开的“大同”世界,因为生命在于能动,在于运动,而运动则必须是离开自身而向外伸张,伸张到身外的世界,异在的世界。生命有赖于异在和他者!趁便指出,古人所谓的“大同世界”并非同一性的世界,而是美好的“相与”世界,是我“与”你而非我“驭”你的世界,进一步,也是我“与/予”你的世界,相互赠与/予,彼此得益;用英语说,是GreatWith-ness的世界,是“GreatWith-Win”的世界。
结构主义的自我观也并非全无道理。自我首先是生命的自我,身体的自我,物理的自我,人生功名利禄无不托于此身,故老子有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13章)诚哉斯言也!身体是自我之根柢,它们一体不二,是以习谓“身体自我”亦为不谬。但另一方面,自我也是,或许应该更是,象征秩序的自我,认识论的自我,话语的自我,社会的自我,等等。前者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是盲目和盲动的存在;后者则是对自我的认识,即是说,自我认识到了他的自我存在。当自我成为自我意识的对象时,自我遂开始成型。自我是一种意识现象,自我是自我意识。然而处于意识中的自我不是孤立的自我,浑噩的质料,而是关系中的自我,进入象征秩序的自我。我是谁?我自身是无法定位我自身的,自我的出显必须借助于他物、他人,在他者所构成的关系网中确定自身的位置。拉康说,这个他者在人之初是镜像,婴儿在镜子里发现其自我;及其长也,镜像被替换为语言,是语言符号构造了其之为自我。
德国语言分析哲学家图根德哈特反对经典近代传统将自我意识与客体意识对立起来的做法,他从第一人称“我”的出现及其意谓角度揭示了呈现在意识中的自我与世界(其他客体)之间一存俱存、一亡俱亡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述谓语言,对其他客体的意识和将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客体的意识统一起来,两者都处于对一个客观世界的意识关联之中,我和其他人在这个世界中都有各自的位置。”[注][德]恩斯特·图根德哈特著,郑辟瑞译:《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引文根据该书德文版(Ernst Tugendhat,Egozentrizitãt und Mystik: Eine anthropologische Studi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 Auflage 2004, S. 28-29)有所改动,下同。这就是说,自我同时意识到其自身和不属于其自身的其他客体,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图根德哈特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命题言说者没有对一切事物即对一个客观世界的意识,他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同样,如果他不能够指称自己的话,他就不可能有对客观世界的意识。”[注][德]恩斯特·图根德哈特著,郑辟瑞译:《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第22,22页(Ebd., S. 29)。自我与世界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浅近言之,以“我”所标志的自我是区别性的,而所谓区别也就是同时假定了两个事物的存在,在此即自我和世界的存在。“我”在世界之中,“我”从世界中走出即与世界相揖别而后出显为自我。在命题语言中,“我根本不是用‘我’来确认我自己”[注][德]恩斯特·图根德哈特著,郑辟瑞译:《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第21页(Ebd., S. 28)。“确认我自己”(mich … identifiziere)可以理解为“建构自我的身份”。,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经由对“我”的述谓即作为主语“我”的谓词部分将“我”表述出来。那谓词部分表述的固然是“我”之性状,但此表述所借用的种种元素则不属于“我”,即“我”是被“我”之外的事物(作为能指)所确认和建构的。
这就回到了拉康和海德格尔多次说过的“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的那一著名论断。自我的确立及其意义需要通过外于它的符号体系来完成。在此意义上,一旦说到“自我”,也就先已说到了他者;同理,一旦说到“主体”,也就先已说到了“交互主体”。依据图根德哈特的表述,一旦有人说“我”,他也就是说到了与其相同的多个说“我”者:
没有人会单单为了自己而说“我”,理解这个词,意味着理解了,每个人说出“我”时,他指涉他自己……而一旦我会对自己说“我”,那么,对我来说,诸多其他的说“我”者就是实际存在的了。这样,不仅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宇宙为我而构造起来,我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宇宙中的一部分也由彼此独立的感知着的说“我”者构造起来,每一个言说者都具有自己的感受、愿望、意见等等。④[德]恩斯特·图根德哈特著,郑辟瑞译:《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第22,22页(Ebd., S. 29)。
由此而言,自我的确立也同时带有了伦理的意义。萨特是错的,他人不是地狱。兰波是对的,兰波说,我就是一个他人(Je est autre)[注]Arthur Rimbaud, Oeuvres complètes, éd. Antoine Adam, Paris: Gallimard, 1972, p.250.。他人是自我的成就者!自我需要依赖他人而成就自身。自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我,打开看,它就是社会的构造物。在其现实性上,即当其实现和展开之时,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自我也不会在这种总和中丧失自己,泯然众人,而且如图根德哈特所警示,“如果他不能够指称自己的话,他就不可能有对客观世界的意识”。这种说法并不导向唯心主义,它指示的是,恰恰是因为有了主观之“我”,整个世界才可能被划分为自我的世界与自我之外的世界,后者无论是自然抑或社会都具有不轻易服从于我的主观意志的外在性。自我是重要的,自我带出了世界。当然,它同时也被世界所带出。二者相携而出!
在图根德哈特所演示的语言哲学和拉康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视野中,如果从复古主义和教条主义角度来要求和期待文化自信,那么其中的自我就像自言自语地说“我”是谁、“我”怎样一样显得不可思议。因为,如图根德哈特所发现,“没有人会单单为了自己而说‘我’”,即便是疯人的自说自话,然一经使用语言,其表达便不再属于自我而进入世界了,尽管疯言疯语中的世界是被扭曲了的世界。不存在私人语言,如维特根斯坦所坚持,这个我们好理解,任何语言都是公共的,语言的世界是公共的世界;不过遗憾的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即使语言被私人化地使用,使私人言说具有特定的内容和风格。但这样的言说也仍然是公共的,其公共性在于言说总是言说给他人,言说根本上是交往性的,言说者听众的多寡无法撼动语言的公共性。个人日记也不是私人言说。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一份日记除却其作者本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读者,但记日记的过程则是一个与理性的对话过程,是整理、清理、梳理个人化的活动和感受、感想。通过付诸言说这样的行为,私密的空间先已为理性所探视、检阅和规制,即原则上已成为公共的空间,而后只要作者本人同意,其他人是可以阅读和分享的,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障碍。海德格尔讲得好:“依其意义而论,每一言说都是向他人且与他人之言说。至于在此是否实际地存在着面向某一具体之他人的一种特定的致辞,对于言说的本质结构是无关紧要的。”[注]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esamtausgabe, B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S.362, S.362, S.361.由此而论,“作为此在即共在的存在方式,言说在本质上就是共享(Mitteilung)”②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esamtausgabe, B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S.362, S.362, S.361.,换言之,“言说即造成公共”③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esamtausgabe, Band 2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S.362, S.362, S.361.,无待乎言说什么以及以什么方式言说!同样道理,一种文化,无论其如何宣称、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只要其特殊性一经言说,也无论是自己言说还是由他人言说,就已经进入话语、翻译、交往和他者了,因而也就一定是公共的、共享的和世界性的。
文化复古主义和教条主义总是在念叨,中华文化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转译的,具有不可与外人道哉的微妙。例如,有中国学人就放言,汉学者,西学也,即其以西方的话语和方法得出此话语和方法所预定的结论,与真实的中国及其文化毫不相干。面对来自中国同行的轻视,作为外人的法国汉学家朱利安表现出有节制的抱怨,似乎深得“怨而不怒”的中国古训:“对于并未成长在其文化氛围中的外国人能否进入其中,他们表现得有所保留。”[注][法]朱利安著,高枫枫译:《美,这奇特的理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在此朱利安说的是,能否深入中国传统“美学”渊源。再者,这些国学原教旨主义者还坚持,在一个对话主义时代,若是没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凝聚自我的身份,中国文明也将失去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的资本与前提。
这些听起来都很在理,文化确乎是特殊的,是在一定的地域中生活的人们所建构起来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一生活方式的价值、精神、信仰和制度。但是,让我们再次从能动自我及其结构化属性的角度来驳难吧,如所周知,文化特殊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身份并非一开始就是特殊的,任何一种文化从其起源处便是混杂、融合的结果,西方文化如此,中华文化亦非例外;而且文化也是流动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它总是不断地为我所用地汲取外来文化营养。文化不挑食,它是杂食者,故能成其葳蕤。据《国语》之记言,中国古人早就明白杂合之于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注]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70页。杂合是万物生长的规律,是人丁兴旺的规律[注]认识到“同则不继”这一规律,“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2页)。,进而也是诸如调口、卫体、聪耳、役心、成人、立纯德、训百体(百官之体)[注]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0—471,472页。的规律,而这一切(它已经是全部的人类生活)不也说的是文化吗?!即是说,杂合同样是文化生长的规律。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夫如是,和之至也。”②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70—471,472页。
秦相李斯更是直击杂合之于文化发展的意义。在其《谏逐客书》中,他以音乐为例:“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禹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禹,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倘使只是固守一种本地音乐,如秦乐,“真”则“真”矣,纯则纯矣,然如此便不能“快意”“适观”即满足视听等感官的“当前”需求了!在传统和需求之间,需求总是被优先考虑。在此文中,李斯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云云[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6页。,也同样是暗示说,一切风俗即文化形式都必须让道于民富国强这个坚硬的指标,以此为鹄的,则没有什么文化是不可移易的,即便是“真秦”之文化。显然,李斯看到了文化以杂合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泰山之不让土壤,河海之不择细流,而且他也透彻地体悟到文化的存废兴替悉以人之需要为转移,并不株守某一传统而不放。如果说《谏逐客书》之“客”乃文化之他者或一切异质的因素,那么李斯所呼吁的便是一种容异、用异、融异的文化理念。如《国语》所示,这也是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我们承认文化的特殊性,而且还坚持文化特殊性是文化对话的前提或必要条件——例如说,越是特殊的,便越是普遍的。在这两点上,我们的立场与文化复古主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与复古主义者的分歧在于:复古主义者逡巡于特殊性,将特殊性绝对化、先验化、单子化、神秘化、神圣化、禁忌化,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不知道“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这一屈骚之问,于是其特殊性成了独断论的、僵尸般的特殊性。而我们,如前所示,则以特殊性为起点,将特殊性移置在能动自我和结构自我这一双重变奏的理论框架之内,从而使特殊性变身为流变不居、开放性、互文性和对话性的概念了。前文有所提及,能动自我不偏嗜任何一种指意形式,它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做出指意的抉择。任何符指、话语均在其身外,并作为其可能的营养物。甚至,能动自我之特殊性一旦成型,它便成为外在,成为传统,成为话语了,故而在永不消歇的能动自我面前,没有什么比自我之当前的、应身的需求更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了。能动自我在不断地寻找能够满足自体需求之新的表意符号,并形成新的表意系统,即形成新的文化或者新的身份、新的特殊性。但能动自我就其作为能动自我而言,其对新的表意符号的寻求和对接,进而形成新的文化,此一过程具有无意识的特点,是之谓“文化无意识”。然而它仍可称为一种对话,即于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话,作为特殊性的文化在不言不语中汲取他者而丰富和强健自身。
能动自我一旦能够自我反思、自我界定,那它便即刻成为结构自我、意识自我、话语自我、述谓自我、互文自我等等称谓的那种自我了。与能动自我不同,结构自我是自由自觉地与身外的世界进行对话,通过此对话建构自我的身份和特殊性。无论对于能动自我抑或结构自我,在本质上,自我即他者,自我即对话。其区别仅在于:在前者,自我是无意识生成的;在后者,自我则是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在我们看来,结构主义对自我之建构性的揭示并不必然意味着自我的组合和拼贴,因而是被动的、惰性的。与多数结构主义理论家不同,我们把结构理解为“机”构(institution),即功能性构成,这种功能性也是结构主义所矢口否认的自主性。
从能动自我和结构自我出发,我们将自我和自我的特殊性视作对话,即是说,自我既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性,也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话性。离开了他者和异质,自我亦不复存在。自我与他者相异相成!依据以对话性为其本质属性的能动自我和结构自我,文化“自”信既然以自我的文化或者其文化的自我性和特殊性为根本,那么毫无疑问,它也必然将是对话性的,生成于对话,显露于对话,璀璨于对话!
以能动自我和结构自我界定对话,并以被如此界定的对话理解文化自信,就其基本原则而言,这一理论并非晚近社会学、人类学、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独门秘籍,其实前苏联文论家和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早在1920年代写作的《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等著作中就已提出了成体系的对话主义学说,且其一生都在深化之、拓展之,终成20世纪西方对话理论的集大成者。完全可以期待,检视、捡拾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遗产,将强化和更新我们对于文化自信之对话性的认识。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已然是硕果累累的巴赫金研究界,这份珍贵的资源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开掘和使用。那么我们就勉力为之吧!我们不拟研究巴赫金全部的对话理论,而是仅仅聚焦在自我、差异、特殊性这些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的要素上。我们将追随巴赫金将其悉数植入对话,并以如此被充实的对话校正那种对文化自信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理解偏差。
二、巴赫金:外位性作为对话
特殊性或者说文化的特殊性在巴赫金那里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特殊性之根的自我的唯一性。特殊性虽然是在比较中显出,是观念性的,但决定这一显出有别于其他物之显出的基质则是其本身的特殊存在。如果说前者是文化这棵大树的枝叶或花朵,那么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文化本身,即是说仿佛作为有机体的文化,其唯一性,则是它不在我们视野之内的根须。其二是由这种唯一性所给定的自我对于其认识对象的外位性,而反过来说,被认识的对象也同样具有唯一性,因而也具有其对于自我的外位性。
巴赫金在其《论行为哲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存在着”,“我的的确确存在着(整个地)”,“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人无法进入……的位置。现在我身处的这一唯一之点,是任何他人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时间和唯一空间里所没有置身过的。围绕这个唯一之点,以唯一时间和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唯一的存在。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实有存在的唯一性质是绝对无法排除的。”总之,“任何人都处在唯一而不可重复的位置上,任何的存在都是唯一性的”[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0—41,17页。。
关于自我的性质,巴赫金语意清晰而连贯:我存在,我唯一,我积极,我外位,且我之外的任何人均此性质。然则,依据巴赫金的理论,这种密不透风、坚如磐石、独往独来、标新立异的自我并不妨碍其与他我即另一个自我之间的相互理解、认识和交流;相反,自我的唯一性及其外位性倒是实现、达成在原本彼此有其特殊存在的个体之间对话性“表接”(articulation)的必要条件。所谓“表接”,就是对话语与生命的表述性链接。
在其《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是在考察“审美移情”现象时带出个体的唯一性及其外位性的,不过需要指出,这在逻辑上绝对是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即巴赫金是从审美个体的唯一性和外位性来看待和要求于“移情”的。巴赫金知道,“审美观照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方面,就是对观赏的个体对象进行移情,即从对象的内部,置身其间进行观察”②(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0—41,17页。。不错,所谓“移情”当然就是移入、进入对象内部的情感和认识游历了,这一直以来便是移情的基本语义。但是且慢,巴赫金从中区分出两种情况,或者说,存在着两种性质的移情:一是积极的移情,一是消极的移情。积极的移情是观赏主体在其中永远活跃地存在着的行为,而消极的移情则是在观赏过程中主体的放弃自我而与对象合二为一。关于积极的移情,巴赫金有生动的描述:“我积极地移情于个体(即作为个体的对象——引注),因而也就一刻都不完全忘掉我自己和我在个体身外所处的唯一位置。不是对象突然控制了消极的我,而是我积极地移情于他。移情是我的行为。”[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页。与此相反,消极的移情,他也称之为“单纯地移情”②(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页。,其特点是“与他者重合、失掉自己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位置”③(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页。。但他又认为“单纯的移情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假如我真的淹没在他人之中(两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是存在的贫乏化),即不再是唯一的,那么我不存在这一点就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意识的一部分,不存在不可能成为意识存在中的一个因素,对我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存在,换言之,存在此刻不能通过我得以实现。消极的移情,沉迷、淹没自我——这些与摆脱自己或自我摆脱的负责行为毫无共同之处;在自我摆脱中,我是以最大的主动性充分地实现自己在存在中的唯一地位”④(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页。。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当我意识(移情)到作为对象的某物时,我之不存在也蕴涵在这一意识(移情)之中,因为我虽然不会意识(移情)到“不存在”,如胡塞尔所发现,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这“不存在”由于依附于“存在”即某物,于是便也显示出其存在来,就像在中国山水画中,空白(留白)是靠有物而存在的。在移情中,不存在是我的一种状况,因而意识到我之不存在也就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在我意识到我不存在而意识中只有对象时,并不是我意识到了绝对的不存在,而是意识到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即以一种不存在的方式而出显的存在。相反,如果我与对象完全化为一体,那么我和我的意识将即消失,对象亦随之烟消云散。要之,移情尽管看起来是“我不存在”,但实际上则是我自始至终意识到我之“不存在”。与此相关,第二,在移情中的放弃自我、拥入对象是表面上消极而实则积极的作为。移情的积极性在于:我是主动地投奔对象的(a);我始终意识到我的自我放弃即“我不存在”的(b);在我意向于对象时,对象也以我或我的意识而生成,即对象被揽入我的意识,成为我的意识的填充物(c)。顺便指出,如果所有的移情都是主体之积极的移情,那么准确言之,便不再有两种移情现象,而只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移情观了。进一步,那大约也便不再有王国维之借鉴叔本华而得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了[注]王国维之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与“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页)本身即已透露,纵使客观性较强的“以物观物”也是有一“观”之主体的。。是的,没有绝对的无我之境,若此,那是谁在意识?谁在想象?谁在体验呢?!
人们通常把移情理解为“入乎其内”,巴赫金提醒,移情还是“出乎其外”,而无论入乎其内或者出乎其外,他坚持,始终都是我之入、我之出,是主体之我的积极作为,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存在才不再是僵死之物,而是人与物的相互作用,存在于是成为所谓的“事件”。也是在此意义上,巴赫金称移情中若真是出现主客体的合二为一则是“存在的贫乏化”。这涉及移情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结构,本文随后再论。
我们习惯于将“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作为移情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巴赫金认为,这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并非实际的移情过程。他称前者为“移情”,后者为“客观化”:“诚然,不应以为先有纯粹的移情因素,之后依序出现客观化、成形化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是不可分的,纯粹的移情只是审美活动的统一行为中一个抽象的因素,不应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时段;移情与客观化两个因素是相互渗透的。”⑥(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8,18,18,18—19,17—18页。面对千差万别的移情现象,区分移情和客观化似乎没有多少意义,它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也可能是交替出现的,可能是以移情为主、客观化为辅,或者相反,等等。然而对于巴赫金的理论建构来说,这种区分却是至关紧要的:它使巴赫金得以将客观化作为较移情更加重要的审美元素,然后借此以引出其外位性理论:“在移情之后接踵而来的,总是客观化,即观赏者把通过移情所理解的个体置于自己身外,使个体与自己分开,复归于自我。只有观赏者复归于自我的这个意识,才能从自己所处位置出发,对通过移情捕捉到的个体赋以审美的形态,使之成为统一的、完整的、具有特质的个体。而所有这些审美因素:统一、完整、自足、独特——都是外在于所观察个体(指被观察的审美对象——引注)自身的;在他的自身内部,对他和他的生活来说,这些因素并不存在……现实生活的审美反射,从原则上说并不是生活的自我反射,不是生活过程、生活的真实生命力的自我反射。审美反射的前提,是要有另一个外在的移情主体。”[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7,18页。客观化即观赏者的外位性,其重要性在于:它创造了审美对象,即对象呈现出具有审美性质的形象;审美对象不属于此对象本身,对象本身没有审美性可言,是一个外在于审美对象的“移情主体”赋予其审美的效果,即看起来是一个审美的对象。这种美学观有唯心主义的嫌疑,但巴赫金这里不关心美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抑或客观的传统论争,而是强调审美效果的发生有赖于一个外在的观赏者或者观赏者的一个外位性。
如果有人一定要将巴赫金划归主观派或客观派的营垒,那么我们毋宁视其为第三派——主—客观派,他超越了这种旧式的美学,而将移情作为使主客体相互作用并使双方都有所增益的活动:“通过移情可以实现某种东西,这既是移情对象所没有的,也是我在移情行为之前所没有的;这种东西丰富着存在即事件,存在已不再是原样了。”②(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17,18页。移情丰富了存在,使存在发生新的变化,成为充满意义的事件。但万勿忘记,这一切都是观赏者的外位性所带来的!如果说外位性在主客体之间创造了审美的效果,那么这也就是意味着它不仅没有阻隔,反倒是确保了主客体之间的往来交通,进而说这也意味着外位性还具有促成主客体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织对话或主体间性的功能。移情是必然通向主体间性的,就像胡塞尔的“意向”之必然通向主体间性那样。就外物之充盈于、内化于主体或意识而论,移情与意向无异。
有学者称,巴赫金的文化外位性观点源自其关于审美活动的外位性观点即审美移情说,是审美移情说的延伸和运用,二者之间乃源与流的关系[注]参见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173页。。我们不拟在事实上做此求证,因为如前指出,审美移情说的逻辑前提是自我的唯一性,且其同样为文化外位观的逻辑前提,这即意味着,文化外位观未必要绕道审美移情说才能取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我们只想坚持:自我的唯一性同时统领着以外位性为其枢机的审美移情说与文化外位观,而后两者之间却并无统属关系,它们位处同一层级,于是就文化外位观而言,它亦可直承自我的唯一性。但是,必须承认,熟悉审美移情及其为巴赫金所突出的外位性特征,确乎能够为进入文化外位性的讨论提供便利。在技术层面上说,它提供了一个转入文化分析的工具箱,其中有积极移情、消极移情、客观化、存在即事件,等等。
为丰富和砥砺这些工具,现再次引入王国维的观点。前文未及时说明,“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是王国维词话的关键词,流布甚广:
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注]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第304,313页。
这里说的不是接受,而是创作方面;不是面对艺术创作,而是社会人生。显然,在王国维,出和入的对象是没有限定的,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合理地包括进来,此其一也。其二,对象之或出或入在价值上并无高下之分,仅是所带来的效果不同而已:入则可写,体物状物,纤毫毕现,栩栩如生,是所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者也。而“出乎其外”,其优点是可以“观之”。所谓“观”,乃居于对象之外而观之,故“观”便假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前引巴赫金谓移情之“客观化”,即是让对象保持为对象,即客体,而这同时也是让观者保持在一个主体的位置。观的本质是外位性的。
关于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特别是观之外位性,王国维还说过:“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⑤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第304,313页。轻视外物是出于外物、居于外位,从而统观外物,故可能卓有高致;而重视外物则是入于外物,与外物一体,随物赋形,神与物游,是故俗趣盎然。前者迹近“有我之境”,后者则为“无我之境”。但无论轻视或重视,都始终不能是无“视”,其所指向的也始终都是“外”物。
这种被置于审美关系中的人物之论,简明言之,审美移情说,如前申明,虽然不是我们转向巴赫金文化外位观的逻辑前提,即是说,有无这个审美移情说,我们都可以从自我的唯一性顺顺当当地过渡到文化外位观;然而有了它,对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一过渡,是不无助益的,因为自我的唯一性已经在审美移情说这里演练过一番,而对于文化外位观,不过是重复演练一遍而已。现在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来谈论巴赫金的文化外位观了。
下引是巴赫金谈论其文化外位观最集中、最完整的一次。作为引文,它是长了一些,但作为对一个重大论题的阐述,它则又是言简意赅的,值得一气读完。若是采取边引边论的方法,自是中规中矩矣,然则于巴氏之语意,殆支支吾吾、支离破碎耳!我们且先试读之,论析随后:
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于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念,如我所说是片面的。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照世界——这些都是理解这一文化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如果理解仅限于这一个因素的话,那么理解也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
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意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这当然应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410—411页。
这多像从自我的唯一性出发对于审美移情论的阐说啊!巴赫金坚决反对纯粹移情式的即入乎其内的对于他者文化的理解。他提出的理由是:融入他者文化,观其所观,言其所言,行其所行,入乎其内,与他者浑然一体,即完全地成为他者,虽为理解行为之必需,但这在获得一种视角(他者视角)的同时丢失了另一种视角(自我视角),也就是仅剩单一的视角,而使用任何单一视角的理解不过是对此视角之所见、之所习见的跟随和复制。
巴赫金的理想是“创造性的理解”,而要实现此创造性理解,则必得有另一视角的存在,在此就是自我视角。保持而不放弃自我视角,就是在入乎其内的理解中同时能够出乎其外,保持一个外位性的位置。这一位置为自我所有,因而出乎其外也就是返回自我或自我的位置。外位性即自我的外位性,即自我面对其对象时所由以立其身的外位性。显然,对于巴赫金来说,理解的外位性意味着多重视角或多重视界。
这是外位性在理解活动中的第一项价值。其第二项价值是,外位性能够使主体对客体“整体地加以思考”,即对客体做整体的观照,将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观,乃统观,统而观之。更精准地说,凡观皆为统观。那么,这种统观的性质是什么呢?或者说,统观能够使我们看到什么呢?巴赫金的回答是:“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对象——引注)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显然,统观之所观即内容乃对象之“真正的外表”。此观为外观,在外位之观以及由此所得到的外观、外表。这尤其贴合于西洋油画的观赏情况:近看是涂料,是死的物质,远观是图像,是活的艺术形象。也许读者早已看出,在巴赫金,这作为外表的外观并非与内蕴、本质相对立,它不是皮相、浅表。它是客体事物本身所呈现出来的表象,出自客体,未与客体断裂,虽经由主体的反映和建构,但在根本上仍归属于客体。一句话,所谓的“真正的外表”就是对象本身的整体形象。没有外位之眼,便没有客体的整体形象。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外位性的整体形象、“整体地加以思考”或出乎其外的“观之”只是指向对象一方的。苏轼告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我们一直奉之为至理名言,但实际上即便跳出庐山的局限,人们亦未必就能获得庐山的“真面目”,那只是一种从外观得到的庐山形象。因此,指向客体的所谓“整体地加以思考”仅仅是指向该客体一方之整体(多么悖论的措辞啊),而非包括主客体以及超越此两者的全能视角之下的整体。这样的统观、整体思考不过仍是一己之视角和一隅之所见。改借杜诗说,何以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认识上没有绝顶!认识永远是被限定的认识。巴赫金对此早有认识:“审美移情(不是指失掉自我的单纯的移情,而是引出客观化的移情)不可能提供关于唯一存在(在丰富的事件性方面)的情形,而只能提供对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的审美观察(也包括观察主体本人,但却是外在于自己主动性的主体,是消极性的主体)。对事件参加者的审美移情,还并不就是对事件的把握。”[注]②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论行为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一卷,第20页。这就是说,审美移情即使有积极主体之主导而非消极主体之完全化入客体,即使能够始终坚持外位性的客观化、统观化,那至多也不过是触及了客体一方极其有限的内容。审美移情达不成一个“丰富的事件”,它无法做到对“事件”的整体把握。由此而言,外位性的根本价值仍在于其对自我本位及其视角乃至多重视角的保证和坚持,在于其反对纯粹移情论或“无我之境”的文化交流观。被限定的视角涵盖了对多视角和全视界的吁求,进一步说,也是包涵了对交互透视、主体间性和对话主义的期盼。在对话主义者巴赫金看来,单独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把握我们共在于其间的作为事件的世界:“即使我看透了我面前的这个人,我也了解自己,可我还应该掌握我们两人相互关系的实质,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统一而又唯一事件的实质;在这个唯一事件中,我们两个当事者,即我和我的审美观察的客体,都应当在存在的统一体中得到评定。”②所谓的“统一体”便是由对话而建立起来的共在场。用巴赫金本人的定义说:“统一体不是指天然生成的一个唯一的单体,而是指互不溶合的两个或数个单体之间的对话性协调。”[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1页。在此,外位性自身已经无足轻重,其轻重将取决于能否导向进一步的对话。
因此,言及文化间之理解,重要的不是“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也不是“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的确是有此情况: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重要的是,“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同样道理,重要的不是“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意义”,也不是“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而是“我们”和我们“自己的问题”与他人和他人的问题构成了一种对话性关系。
显然,巴赫金之所以坚持外位性的奥秘在于对话,在于创造事件性的对话。不是为了安然于自我不受外物、外界干扰的存在状态,不是为了坚守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当然更不是为了自得于其“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恰恰相反,坚持外位性最终是为了创造一种文化间的对话,在此对话中实现他所推崇的“创造性的理解”和彼此间均会发生的改变和增值。对话需要自我,需要自我的外位性,不过,说到底,对话需要的实则是其所必然意谓的多重视角。无多重视角,便无对话之可能。
复归本文之初心,巴赫金的自我的唯一性和外位性,或可谓“外位自我”,说的就是文化的自身存在,其地方性,其历史性,其差异性,其特殊性,而尤为可贵的是,巴赫金没有将这些硬化,石化,固化,无意识化,而是软化,气化,语言化,动态化,将个体之不可移易的身体性存在转变为一种视角。其方式就是将其牵引到对话的场域,一旦开始对话,他们就不再是自身存在,而成了一种关系性存在,既是其自身,又非其自身,是对话个体,是赫尔曼斯所称扬的“对话自我”[注]See Hubert J. M. Herman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Dialogical Self”,https://doi.org/10.1080/10720530390117902, published online,10 Nov 2010, and originallyin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vol. 16, 2003-issue 2, pp.89-130.。对话并不消灭个体,但也不保全个体,于是“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因为个体仍然坚执地存在着,故而总是能够“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但由于进入了对话,故而它又是开放的,处于无限的开放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指出:“特定的文化的统一体,乃是开放的统一体。”[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409页。这种开放既是历时性开放,也是共时性开放。
如果单从其对永不消逝的和坚硬的个体的坚持和张扬方面观之,抑或,单从其对个体之间话语性连结的渴望和要求方面而言,即是说,单从以上任何一方面考量,巴赫金在西方思想史上都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此一家,但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要求个体进入话语性的对话,而在此对话中同时还应葆有个体的存在,这样的智者在20世纪的西方并不多见。
三、巴赫金的对话不是主体间性或文本间性,而是个体间性或言语间性
这里需要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的一种结构主义如在托多罗夫那里的解读略做澄清或修正。在托多罗夫看来,巴赫金对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是互文性:“为了表示每一述说(énoncé)与其他述说的这种关系,他使用的术语是对话主义。”[注]Tzvetan Todorov,Mikhaï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Seuil, 1981, p.95.需要辨别:“énoncé”指述说的结果或内容,“énonciation”指述说行为。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两种述说之间的一切(tout)关系都是互文性的”[注]Tzvetan Todorov,Mikhaï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Seuil, 1981, p.95, p.95-96.。托多罗夫引巴赫金原话为证:“被并置的两种语言作品,两种述说,进入了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称其为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是在语言交际深处所有述说之间的(语义)关系。”⑤Tzvetan Todorov,Mikhaïl Bakhtine: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Seuil, 1981, p.95, p.95-96.显而易见,在巴赫金,互文关系即对话关系,或者,互文性即对话性,反之亦然。而这进一步也似乎是,对话仅仅漂浮在文本、述说的表层,而非发生在其存在具有唯一性的自我或个体之间,简言之,似乎对话仅仅是话语性的。
对于这种可能的误导,结构主义的传译也许负有主要责任,但巴赫金本人恐亦难辞其咎。在其对话理论中,话语不时地蹿跃到最突出的位置,例如成为一种对人进行本质界定的视角:“人的存在本身(外部的和内部的存在)就是最深刻的交际”,“存在就意味着交际”[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78页。,“人的行为是潜在的文本”[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13页。,“人的身体行动应该当作行为来理解”——“而要理解行为,离开行为可能有的(我们再现的)符号表现(如动因、目的、促发因素、自觉程度等等),是不可能的”[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13页。,“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87,387,387页。。巴赫金这种从“文本”或“文本间性”来界定对话,从而界定人的存在的理论,无论怎么辩解都难逃其遮蔽人之物质性存在的嫌疑。这也许是巴赫金必须为其对话理论所付出的代价。
再例如,当其对人文科学(或曰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或曰精密科学)进行区分时,巴赫金同样表现出浓重的文本中心主义而非物质主义的音色:
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无声之物和自然现象的科学。人带着他做人的特性,总是在表现自己(在说话),亦即创造文本(哪怕是潜在的文本)。如果在文本之外,不依赖文本而研究人,那么这已不是人文科学(如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等等)。[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页。
说人文科学研究人文,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这表面上看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若是将人文仅仅等同于人所借以表达自己的语言、人所创造的文本,进而说,研究人文而不考虑其物质属性,那么这样的研究不啻与尸骸对话:无言说者的话语一如没有生命的尸骸。然而,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话语。一切话语都是人的话语,一切文本都是人的文本;而人不仅是话语的、文本的存在,也是现实的、生命的存在;总之,是欲求—言说的存在。人文科学固然以话语、文本为其对象,但它不是将其作为空洞的能指,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符号表现。所有符号都是指示性的!有所指,有所透漏,或者有所藏匿,总之不是自我指涉的。德里达的“延异”是意指的延异,不是无所指的延异。我们不反对巴赫金斩钉截铁的断言,“文本不是物”③(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页。;不反对他将人文科学定性为文本研究;同样,我们也不反对他关于精神科学所说的:“精神(无论自己的精神还是他人的精神)不能作为物(物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出现,无论对自己和他人来说都只能表现为符号,体现于文本中。”④(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页。但是必须坚持,人文科学不是纯书斋式的学问,不是能指的游戏,而是探究文本对现实世界的种种意指。
巴赫金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多次表示过“作为话语的文本即表述”⑤(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页。(而表述总是意味着有所表述)、文本“是意识的表现,是反映某种事物的意识之表现”⑥(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四卷,第301,300,299,297,312页。(而根据胡塞尔,意识总是意向性的,即有对某物的意识)之类的意思。但毋庸为尊者避讳,其对话理论未能将话语和作为生命的话语对谈者之从属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并使之勾连为一个严密的体系。不过这并不关紧;关紧的是,对于我们试图予以澄清、重构、发展的对话理论,巴赫金都已或东或西、或明或暗地触及和指示过了,借着他的指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迈向我们自己的结论。例如,如下的说法就足以使我们不再认为巴赫金的对话仅仅发生在文本或话语的层次:“语言与表述的对立,就如同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所以,表述完全是个人的。”[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二卷,第399页。“一般来讲,要摆脱外位因素的实体存在恐怕是个无法实现的任务。”[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巴赫金的讲座》,《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七卷,第338页。“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87,387,387页。“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精神、整个躯体、行为。”[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87,387,387页。对巴赫金而言,显而易见,个体的不可言说的方面也是包含于对话之中的。是个体在言说,而非语言在言说。个体的表述(parole,通译“言语”)内蕴着言语(langage,通译“言语活动”)与语言(langue)之间的张力。语言之所以不言说,是因为语言不具备言说的意志和动力。索绪尔讲得清楚,“语言不是说话者个人的活动……语言从来不允许有意图”[注]引文见(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二卷,第398页。索绪尔的法文原文是:“La langue n’est pas une fonction du sujet parlant, ...elle ne suppose jamais de préméditation”, “La parole est au contraire un acte individuel de volonté et d’intelligence.”(Ferdinand deSaus 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echehay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Albert Riedlinger, quatriéme édition, Paris: Payot., 1949 [1916], p.30) 注意:《巴赫金全集》中文版将“parole”翻译为“表述”而非“言语”,将“fonction”翻译为“活动”而非“功能”,原则上并不错,但与通用译法不同,需要读者鉴别。,“表述是一种意志和思维的个人行为”[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七卷本)第二卷,第398页。。这些话,巴赫金都抄引其法语原文;此中之深意,他该是多么地心领神会啊!纯粹语言学可以不研究具体的言说,但对话哲学则必须将个体考虑进来,且许以一个始源的位置。
在谈到作者与其作品中的人物的关系时,巴赫金区别了前者的两种主动性:
作者具有积极的主动性,但这个主动性带有特殊的对话性质。针对死物、不会说话的材料,是一种主动性,这种材料可以随心所欲地塑制和编织。而针对活生生的、有充分权利的他人意识,则是另一种主动性。这是提问、激发、应答、赞同、反对等等的主动性,即对话的主动性。[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全集》(六卷本)第五卷,第375页。
在此,与巴赫金的着意点不同,我们并不担忧作者是否以己之意而强加于其笔下的人物,即以主客体关系的方式错待作为主体间性的对象;我们关心的是在巴赫金所倡导的作者与人物之间对话性关系的范型中已悄然透露出:其一,作为个体的作者具有对话的积极主动性,他是一场对话的发动者。我们知道,唯其作为个体,作者才有所谓的“主动性”。话语从不主动。其二,人物作为作者对话的对象不是未经形式化的质料,而是活生生的另一存在,是他人或他人意识。于是,这也就决定了,对话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活动,而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活动,且主体又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对话以个体存在为基础,而后寻找一种主体间性。在巴赫金,对话原则上就是主体间性。但如果说主体是话语的建构,如结构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我们毋宁说创制一个更贴合巴赫金意谓的术语:个体间性。个体之间彼此寻找沟通,而他们能够沟通的则一定是话语。当然如果把主体理解为个体在言说中的符号延伸,那么说对话即主体间性亦无不可。但麻烦在于,现在的主体概念已经被结构主义风化为一具没有血肉的木乃伊。严格说来,巴赫金的对话是个体间性,而非仅仅作为“文本间性”的主体间性;其个体间性的对话已经涵括了结构主义的主体间性。在此我们不由得感叹,那些声称是索绪尔子孙的法国结构主义者,其实对于索绪尔的遗产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他们丢弃了他的言语学,而单单拿走了其语言学[注]索绪尔将语言学分作“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Ferdinand deSaus 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37)两个部类。。这当然不是学科对象意义上的,而是哲学上的,他们这样做造成了严重的哲学后果,即他们的哲学只能是荒无人烟的哲学,他们在能指的盛宴中饥毙。而巴赫金(此处是沃洛希诺夫)虽然难说对索绪尔多么满意,但无论如何,结果是他兼取其语言学和言语学,并进而做了哲学上的混融,其对话既有话语、又有个体,是个体间的对话。
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哲学的沃洛希诺夫不完全等同于信奉个体间性对话的巴赫金;其二,沃洛希诺夫并未完整把握索绪尔的思想,而巴赫金却不动声色地抓住了索绪尔语言学的枢机:在“言语活动”中语言和言语的互动关系。“言语活动”是索绪尔语言学的直接对象或第一对象,而后他才从中抽象出“语言”和“言语”两个部分,并始终坚持其相互依存、浑然一体的实存状态。对于语言学来说,语言或言语,无论索绪尔委何者占据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但对他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言语是对语言的个体性使用。因而言语活动或言语既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注]索绪尔警示:“言语活动有个体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我们无法离开这一方面而去设想另一面。”(Ferdinand deSaus 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24)合而言之,“言说主体利用语言符码以表达其个人的思想”(Ibid.,p.31)。。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索绪尔的“言语活动”即是巴赫金的“对话”。如上证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有时有偏向话语一维的嫌疑,但从其整个学术生涯观之,基本上是结合着个体性的。其对话是个体间性,在个体之间寻求话语的沟通。
结 语
本文在引进能动自我、结构自我、外位自我等概念,界定文化自信之“自”即“自性”“自我”“特殊性”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文化自信的理论认知和图绘。以下所谓的结语不过是对前文已经达到的结论做更简明的表述罢了:
第一,能动自我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总是以其当前的、现实的需要和状况为出发点,它原则上并不特别拣选自己的历史和遗产,也不特别排斥外来的文化和文明,一切都以其是否有用、有益为取舍。在此意义上,能动自我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
第二,从结构自我可以得知,文化自性、文化特殊性、文化身份在缘起上便是复合的、构成的、杂融的(a),在认识论上都先已/同时假定了一个文化他者(客体)的存在(b),即是说,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客体)被自我意识一道建构出来,它们相携而生,舍此则无彼。
第三,能动和结构并非两个相对立的概念。文化因结构而成其自身,因结构而获得其能动,并以结构化的方式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身,而所谓结构化乃是一个将身外文化(包括异质文化)引入自身系统并予以粉碎和整合的过程。文化因而在本质上即是对话性的。文化即文化间性。
第四,外位自我实乃对话自我,它要求文化自信必须成为一种间性自信,一种对话自信,即一种文化对话主义,其中既有自我的存在,也有他者的进入,二者共同创造了一个事件性的空间,文化从而得以更新和发展。依据巴赫金外位性理论,文化自我或文化特殊性是要通向对话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为对话而存在的。此乃打开流行格言“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正确方式。
不言而喻,在能动自我、结构自我、外位自我或者对话自我面前,文化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据以抵抗从当代文化需要出发对传统文化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堡垒(即文化特殊论)将灰飞烟灭。如果说从前的文化自信是后殖民的文化自信,是抵抗性的和二元对立性的文化自信,具有情感的合理性和历史的真实性,那么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则应理性地、包容性地成为间性文化自信,其中的对话原则同时将文化特殊性作为本体论的存在和认识论的存在。一句话,文化自信是自我开放的对话性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