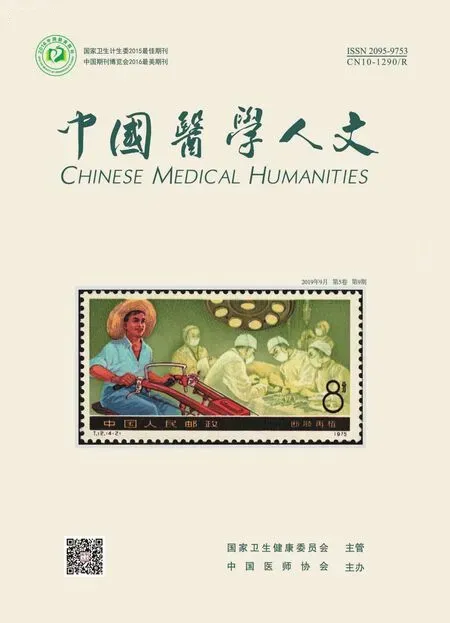向上
文/范志伟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夜色中一只知了正在急诊抢救室门前的梧桐树上艰难爬行着,虽然从没有人注意到它,但它依旧要向树枝的最上方前行,因为它知道在那里能够看见其它知了都看不见的星空。
一阵刺耳的报警声慢慢响起,又带着蓝绿相间的灯光疾驰而过。
知了停止了向上爬行的脚步,只是缓慢的看着这人世间常常发生的一幕,在它凝视的那一刻,这时间或许便是静止的。
“快,病人没有了自主呼吸!”打开120救护车的车门之后跳下来的急救医生慌忙的说着。
“有心跳吗?”我赶紧上前查看病人。
只见这位被插着气管插管的年轻患者已经处于深昏迷状态,全身散发着浓烈的酒精味。
“到现场已经没有了心跳呼吸,大概按压了二十多分钟……”
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身边满头大汗的急救医生,因为连续的心肺复苏,汗水已经浸透了他的上衣。
“现场是什么情况?”
“这个人醉酒后呕吐窒息,倒在了卫生间,现场有很多呕吐物,插管时可见大量的分泌物。我们赶到现场时依旧没有了心跳呼吸,到现在为止刚好28分钟!”他看了看挂在抢救室正中央的电子钟给出了准确的时间。
对于年轻醉酒者来说,呕吐窒息往往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之一。
我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何时醉酒的?呕吐后窒息有多久?在120急救医生赶到现场之前意外情况已经存在多久?是否只是普通醉酒那么简单?
“家属呢?”为患者接上呼吸机后首要的便是向家属了解情况。
大约五六个男性拥挤在门前,却没有人回应我。
“谁是病人的家属?”我大声的重复道,因为患者的病情不准许我浪费哪怕一秒钟的时间。
这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了看,却还是没有人回答我。
“你说什么?”一个中年男子说着我听不明白的方言站了出来。
重复几次之后,我才明白男子的意思:“已经通知了患者的妻子!”
“那你们了解情况吗?什么时候喝的酒?喝了多少酒?除了喝酒有没有其它特殊情况?”这些问题对于患者的治疗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我能够得到的消息却只是:从患者自行离开酒桌到被送进急诊抢救室,最少已经过去了40分钟,没有人知道具体喝了多少酒。
这些同乡原本便说着一些我听不明白的方言,更何况是在都已经被酒精麻醉后状态下。
“开绿色通道,先检查处理,等他老婆来了再说。”我向领导汇报后第一时间开通了先抢救后付费的绿色通道。
对于心肺复苏后的患者来说,在我们手中流失掉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事关病人的生死存亡。更何况,我需要明确的是:患者是单纯的醉酒呕吐窒息后心跳呼吸骤停,还是饮酒后诱发了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
“不等他家属了?”
“不等了,要是等太久岂不是浪费了时间!”
在将患者转运往CT室时,我才再次注意这位昏迷之中转运呼吸器辅助通气之下的年轻患者:几根沾着呕吐物的头发覆盖在眼角、鼻部外伤后还没有愈合的伤口、被脱光衣物后全身黝黑的肌肤、身材较矮且瘦弱的躯体、裸露在被子之外的右脚上穿着破漏的黑色袜子……
CT室之中,我呼喊患者的几个同乡前来帮忙。
除了那位首先回答我问题的男子之外,其它人依旧没有回答我,依旧只是漠然的看着我和眼前的患者。
因为是急诊抢救室的抢救病人,一切检查都遵循优先原则,所以患者的CT很快便完成了。
同预想之中肺部大量的呕吐物相比,患者颅内的情况却要更加让人揪心,因为已经有着十分明显的颅内水肿,有着严重缺血缺氧性脑病了!
以患者的病情来判断:如果放弃积极抢救治疗,必定是死路一条;如果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治疗,最大的可能便是植物人或者脑死亡。
“家属呢,来了没有?”带着外科无菌口罩的我站在抢救室门口大声的呼喊着。
还是那名同样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男子用极难明白的话回答了我:“来了!”
既然患者的妻子来了,那么一切就好办了,只需要患者妻子给出一个治或不治的答案。
然而,让我意外的是这男子却给了一个我从没有听过的答案:“她婆娘来了,她不敢进来,她害怕。”
这个答案让我非常错愕,自己丈夫病危、九死一生,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以往遇见这种情况,都是妻子们哭天抢地双手紧紧拉着抢救病床不愿离开,都是妻子们不顾众人反对要求继续抢救。
现在,这位已经被死神夺走一大半的患者正躺在抢救病床上仅有心跳而没有自主呼吸,他的妻子却徘徊在医院的大门外不敢进入。
凌晨一点钟,我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对眼前这位有些尴尬笑着的男子大声说:“对他老婆说,再不进来看看,就永远看不到了!”
“会不会在醉酒的背后另有隐情?”患者妻子的反常表现让我不得不思考。
很快,患者的妻子被我带进了抢救室。这同样是一位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的年轻女子,她穿着一件蓝色外套、梳着两根齐腰的辫子。
她开口说了几句话,除了喝酒两个字之外,剩下的我完全听不明白。
好在那位始终同我沟通的老乡能够从中翻译,否则我真不知道该要如何去向患者的妻子解释了。
患者妻子的意思是:患者常常喝酒,每天都要喝酒,当天上午起床后自己便已经喝了将近一瓶白酒,晚上又继续喝酒,自己知道丈夫早晚要出事。
“下一步要怎么办?治还是不治?”决定这个问题的既不是患者本人,也不是医者,而是患者的妻子。
“要多少钱?”患者同乡翻译着。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要取决于患者的治疗情况。如果患者很快死亡或许不需要很多费用,如果患者生命体征能够稳定需要进一步治疗则可能需要很多,如果出现脑死亡或者植物人状态则更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当然,以患者的状态来看,脑死亡的可能极大。
如果患者是一名老人,或许可以明言应该放弃。但,眼前的患者只是一名既往没有任何疾病的27岁年轻人。
他是一个丈夫,是一个儿子,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家庭的顶料柱,在没有百分百宣判死刑前,又有谁能够轻言放弃呢?
“家属人呢?去缴费取药!”
家属未赶到医院时,因为患者病情危重,可以通过先抢救付费的绿色通道制度,这是所有医院都有着的制度。但是,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属赶到之后,便应该尽可能自己付费。毕竟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毕竟绿色通道是留给那些真正需要的危重需要的患者。
然而,家属却没有了踪影。
只有那名能够为我翻译的男子前去缴费取药。
“家属人呢?进来帮忙!”
患者很快大便失禁,夜间值班护士原本人手不足,为患者清理大小便必须要有家属的协助。
然而,家属却迟迟不到。
只有这位同样皮肤黝黑的男子可以忍住酒精同大便一起发酵后的恶臭,耐心协助护士为患者清理大便擦净身体。
“家属人呢?做好决定了没有?”
虽然患者病情危重,生命在一点点消失掉,虽然我郑重其事的大声告诉了她,甚至当她的面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但是,她却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慌张、没有哭泣。
或许,只是我看不见她镇定表面背后的失措吧?
答应我只是考虑商量一下的患者妻子,几度从凌晨的抢救室门外消失不见。
患者的同乡向我解释:“她在打电话。”
然后又向我解释:“她还要考虑考虑。”
一会又向我说道:“她害怕,不敢进来。”
凌晨三点,那几个始终不愿说话的同乡已经躺在抢救室门外的板凳上熟睡了。
仿佛整个世界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在拼命的奔跑。
抢救室之中,我问这位可以勉强沟通的男子:“你们都是一个村子的吗?”
“我们不是一个村子的,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在一起的。”
“他老婆为什么不敢进来?病人随时都是没有命,现在不看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他却没有回答我,不知是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还是不愿回答。
“你们这里怎么这么臭?”一位会诊医生捂着鼻子抱怨道。
这种恶臭的味道正是来自患者失禁的大便和被发酵后的酒精掺杂在一起的结果,它是这个人世间最真实的味道。
我站在患者的床头看着他睁开着的却透露着冰冷的双眼,盯着他瘦弱的随着呼吸机而起伏的胸膛,闻着他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丝让人恶心欲吐的味道。
因为刚被又一次清理过失禁的大便,插着管子的患者裸露着身躯任人摆布着:他的双手被搁置在胸膛之上、他的双腿被弯曲着向外搁置在床沿之上,在心跳的波动之间看不见一丝生的迹象,在呼吸的间隙之中感受不到一毫活着的温度。
凌晨三点半,梧桐树上的那只向上的知了也暂停了脚步。它太疲惫了,它需要停下来再次仰望树叶之中的那星空。
患者的妻子给出了最终的答复:“放弃抢救,但要等他的父母赶到!”
“你知道放弃抢救就是死吗?”我深怕患者的妻子做出了自己并不知情的决定。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患者沉默不语。
“我不能保证可以等待他的父母赶到,他随时都会死亡!”等待父母的这个决定我可以理解,但我却不能答应。因为患者远在千里之外打工的父母最少需要十个小时才能赶到。
凌晨六点钟,抢救室门前树上的那只知了准备开始新一天的鸣叫了。
然而,我的病人却即将走到了生命的最终时刻。
他的生命体征逐渐消失,她的妻子要求拔下呼吸机、停止一切药物等治疗手段。
我戴着外壳无菌口罩,套着手套准备拔下我亲手插进患者器官之中的气管,我一低头便又在患者散大的瞳孔之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都说昏迷之后的人再也没有了自主意识,然而又有谁能够知道在拔下患者气管插管的那一刻,我手下的27岁年轻患者是否在心底发出过不要的呐喊?
拔出了气管插管、停用了呼吸机,患者没有任何反应,心电监护上的数字却剧烈的变化着。
代表着心率的数字从60开始慢慢下降到0,代表心律的Ⅱ导联也从曲曲折折慢慢化作了一条直线。
做完最后一份心电图之后,阳光刚好透过抢救室巨大的落地窗照射在患者右脚上。
他的妻子因为害怕,还在抢救室门外徘徊着。
他的同乡们,开始分工去操办了后事。
他的父母,此刻已经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他的医生,只能坐在角落里默默的看着别人为他穿上最后的新衣。
“喝酒把自己喝死了,值吗?”同乡亲来穿衣的老大爷一边整理着寿衣一边感叹着。
他已经为患者穿上了明显宽大的西装,甚至已经要覆盖了患者的双膝。
“这衣服好像大了一些!”我忍不住问起了大爷。
没想到大爷却给了我一个哑口无言的答案:“寿衣本来就要大一点,临时又哪里来正好的衣服呢?没有人关心这个的,反正送到火葬场也是要一把火烧掉的。”
我想反驳些什么,却又一个字说不出来:“患者生前没有得到尊重,难道死后不应该得到一些尊重吗?有尊严的不仅是活人,还有那些没有心跳呼吸的尸体。”
或许,患者生前便也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只知了蝼蚁一般的小人物。没有人会关心他如何生存,也没有人去关心他如何生活。
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在意,死后同样得不到一点尊重。
交完班后,我顶着烈日走出了医院,庆幸自己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又听见了知了的鸣叫。
我想虽然大家都同知了一般渺小无人在意,但我们总应该认真过好每一天,不应轻易放弃自己,更要时刻记住向上的方向。
因为,向上便会有另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