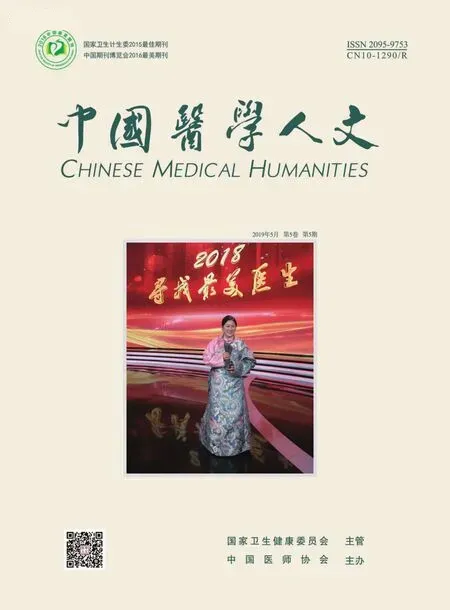孝的普适性与宗教性
文/谭明冉
(根据谭明冉教授在第四届儒学文化与医学人文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报告整理)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孝。
孝是什么
孝是以子女对父母依恋和爱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道德意识。它不仅加强了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这种自然情感,而且还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和帮助父母实现其志愿。这种对反哺和承志的强调使人类超越于动物对父母的本能性依恋和成年后对父母的遗弃,奠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
最早的孝行记载:《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颍考叔到郑庄公处汇报政事,用餐时,不忘记家中母亲没有肉吃,就留下一些肉带走。这个举动感动了郑庄公,使郑庄公与其母恢复了母子关系。左丘明为此盛赞孝的威力,认为孝子的德行力量无穷,将永远感动他人。后来石蜡谏卫庄公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将孝列为人的好品德之一。
《左传文公二年》有“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左传定公四年》说“灭宗废祀,非孝也”。综合《左传》中的记载,孝的含义当包括:赡养父母、祭祀祖先、传宗接代。这些含义基本上为《论语》《孟子》等书所继承。
孔子论孝
孔子主张赡养父母之时要内心庄敬,反对像养牲畜那样,让他们吃饱就行;埋葬时,要做得得体;祭祀时,要虔诚恭敬。这就是他所要求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循礼是行孝的规范和表现。孔子更以实现和完成父亲的意愿为孝。父亲死后,至少三年不要改变父亲的规划。这一点司马迁做得很好,宁可接受宫刑,也要完成父亲司马谈修史的遗愿。孔子的要求虽然有导致父亲家长制的危险,但是如果父子都能以礼相待,这种专制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礼还规定了父亲和儿子各自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不鼓励那种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偏颇关系,这就是“父慈子孝、兄悌弟恭”的对等关系。
孟子论孝
孟子同样要求以恭敬之心赡养父母,且要将父母的生命传递下去,这就是他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孝乃人之无法超越的自然情感。他说古时人曾经不埋葬父母,弃其尸体于沟壑,过了一些时候,经过那里,狐狸吃着他父母的尸体,苍蝇蚊子咀吮着他父母的尸体,那个人不禁额头上流着悔恨的汗,斜着眼睛望望,不敢正视。这一种流汗,不是流给别人看的,实是由于内心的悔恨而在面貌上表达出来的,于是,他回家取了锄头畚箕,再把尸体埋葬了。
庄子论孝
孝的发生当起源于人类因对父母之依赖和亲近而产生的爱慕和关怀。庄子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人间世》)。
庄子似乎将“子之爱亲”与孝视为一体,没有严格区分。在庄子看来,孝是自然的,是“命”。只要你是人,是父母所生,就无法逃脱孝的义务或使命。但是,庄子认为最高的孝是:自己忘记自己在孝敬父母,而且父母也忘记子女在孝敬自己。孝完全出于一种自然而然。
荀子论孝
荀子直接将孝当做一种理性的回报。他说:“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荀子·法行》)恕就是推己及人之道。可以说,孝是孔子基于人类理性对子女之爱的提升。它使人类高于动物,使人有了为人之根本。
荀子反对无原则的愚忠愚孝,他认为大孝乃是通过遵循礼义来实现的。这里加入了人的理性判断,而不认为孝乃人生之良知良能,也不是对父命之愚昧服从。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
孝的评价
所以,先秦时忠孝的含义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看父亲和君主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父子、君臣之关系是对等或平等的,他们共同向一个公共的目标奋斗,这个公共目标就是国家或家族的整体利益和名誉。以这个公利为目的,以道义为准则,君和父的专制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其实,直到现在,家长虽然享受权威,但是其作为往往是以家庭整体利益为目的。其作为如果从家族的发展上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种以家庭利益至上必然限制或伤害个体的利益。这也是五四以来反传统反家长制的主要原因。
孝的普适性
孝的普适性首先是因为它产生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和爱慕之情。只要人类继续生存繁衍,就需要父母,就会产生孝的情感。当然,儒家的孝并不止于这种自然而生的情感,更强调对父母有意识的赡养、实现父母的意愿和传宗接代。通过孝,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父母的指导下,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冒险和少走许多弯路。当然,孝并不仅仅是对年迈父母的照顾,还是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取生活经验的重要方式。儒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孝不但维持了家庭的温情,而且增强了家庭成员的社会生存能力。因此,孝是对自己所出的追寻,是对本根的爱护。自然界的生物都是成长后遗弃本根和父母。儒家的孝正是从爱护本根的角度,达到根芽共茂的和谐关系。
其次,孝是仁爱他人的开端和基础。只要我们崇尚友爱和谐的社会关系,我们就必须从爱父母兄弟的地方开始。陈荣捷解释说:“儒家从父母开始,是因为与父母的关系是人生的第一个关系,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关系。人们可能缺乏其
它关系,但不可缺乏它。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最近的关系。作为一般的实践之事,虽说人有对着所有人而发的良好心意,但是人最先尊敬的是其中离自己最近的人”。
孝的宗教性
孝之所以具有普适性还因为它完成了人对生死的超越。通过对祖先的缅怀和繁衍子孙,个人的生命被深远的植根于过去,并通向未来,使个人通过血缘和基因的延续达到永生。可以说,孝架起了神和人、宗教与伦理之间的桥梁,达到了生与死的统一,完成了佛教的轮回和基督教的天堂的功能。它具有养生送死,且使人乐生安死的功能,这可以说就是儒家孝道的宗教性。
孝的普适性实际上也是与孝所具有的特殊宗教功能相关的。虽然传统的观点不认为儒家是宗教,因为一般来说,宗教应当具有最高的人格神或精神诉求,有圣经、仪式、教职人员和教堂等,而人们常常认为儒家没有这些设施。但是,谢幼伟通过仔细考察,认为儒家也有仪式、神龛、圣经和精神诉求,从而得出:“儒者虽不谈宗教,而实有一宗教的代替品。这宗教的代替品就是孝。儒家的宗教,可说就是孝的宗教。”李湘云也说:“儒家通过一个孝字,抹掉了道德和宗教两者间的界线,使宗教的隐性功能和道德的显性功能得到高度统一”。
孝的宗教性首先体现在它对终极关怀做出的解答。这个终极关怀就是人如何完成对生的解释和对死的超越。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他关注的是自三代以来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和延续祖先之生命和意志的使命,而这二者正是生命的来源和延续的问题。
对生命之源的探索必然与生命的延续联系在一起,孔子虽然对鬼神的存在持模糊态度,但是从殷周延续下来的祖先崇拜无疑证明儒家的孝道承认一个不言的前提:灵魂是存在的。既然灵魂是存在的,它必然与其子孙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它需要子孙的祭祀和怀念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避免被人遗忘,这样“有后无后”就成了祖先神灵和父母最关心的问题。同时,它也需要保佑子孙以证明其被祭祀和怀念的价值,这就给子孙带来“得救的希望”。
由于祖先存在的意义在于被人发现和认可,于是,儒家的“终极关怀”就从灵魂不死过渡到了“有后无后”。没有子孙,一个普通的灵魂即使永存,也会被人彻底遗忘,其意义等同于没有存在。据此,王邦雄评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给出了‘生之前,我从哪里来?死之后,我往何处去?'的最后解答。在生之前,我从祖宗来;死之后,我往子孙去。”
如果说普通人通过生儿育女来获得小我生命的延续和永恒,士大夫或君子关心的则是通过让世人铭记而达到精神不死、生命不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曾述说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三个“不朽”,是着眼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与对后世的影响,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把个体小生命融入了社会群体的大生命,在大生命的延续中求不朽。个体的生命总是有限的,短则数十年,长亦不过百年;而其体现在德、功、言中的精神,其对社会、历史的贡献,却可以在人类群体大生命的延续中永存而不朽。这种追求可以说是对“天地”尽孝,对人类全体尽孝,而其实质仍不外乎将孝悌之情推广到天下,以成就仁道,因为只有真正仁爱人类的人才会立德、立功和立言。
其次,孝的宗教性表现在“得救的希望”。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既是祈求他们的保佑,也是对自己生命之来源的敬重。殷墟卜辞中多有殷之先王在于帝所,因而可以保佑其子孙的记载。如,“咸不宾于帝,下乙宾于[帝]”(乙7179)“下乙不宾于帝,大甲宾 于 [帝 ]”( 乙 7434)、“大甲不宾于帝,宾于帝”(乙7549)。“宾于帝”当有殷之先王在天帝左右服侍帝,传达帝的旨意的意思。正因为“殷多先哲王在天”(《尚书·召诰》),侍奉上帝各有其序,故殷人有哪一位先王此时“宾于帝”之问。或许,若龟卜告知哪位先王“值勤”帝所,殷人则祈祷这位先王,让他影响帝,以给予殷人更多的恩惠和保佑。
最后,孝的践行体现在对父母的晨昏定省,婚丧和祭祀等仪式上。这些仪式所体现的精神主要是对生命之源的敬重和怀念。这个生命之源近者是父母和祖先,远者则是天地阴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婚礼上首拜天地,次拜父母,其含义与基督教首先感谢上帝的恩赐实有相似之处。
这种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表面上是崇拜超自然之势力,但实际上其归宿仍在于现世,因为正是通过对这些仪式和礼节的一丝不苟的践行,孝子的德行得以积累,最后可以获得祖先的保佑。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虽然没有教堂中的祈祷和寺庙中的唱经,其礼节仪式的践行就是变相的祈祷;虽然没有上帝的恩宠,其祖先的保佑就是变相的恩宠;虽然没有至上的上帝,其对生死的超越,对茫茫宇宙的敬畏就是变相的上帝。儒家的孝道具有为中国人养生送死,且使人乐生安死的功能,这可以说就是儒家孝道的宗教性。
但等到这种传统让位于重视修德、重视当世的周文化之后,人们则更重视遵守周礼的孝行,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发肤,光耀父母而不给父母蒙羞。从庄子的“阴阳之于人,不啻于父母”(《庄子·大宗师》),到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的天地境界,将对父母之孝与对天地的孝统一起来,完成了孝行的宇宙性超越。对此,王夫之说:“尽敬以事父,则可以事天者在是;尽爱以事母,则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亲,则所以存心养性而事天者在是。……人之与天,理气一也;而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气之中,而气为父母之所自分,则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于天地也,无有间矣。”
儒家既然坚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坚持一生按周礼积德,自然会得到皇天和鬼神的保佑,那么儒家自然不会把生命的意义放在对鬼神和天帝的机械崇拜上,而更重视个人的修为,这就的是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立宗论的根本所在。而且,在孔子看来,只要一个人认真循礼以修德,就自然会得到上天和鬼神的保佑。《论语》中孔子病,而子路祈祷于上下神祗,遭到孔子的反对。孔子如何反对的呢?孔子说:“丘祷之久矣”。孔子的祈祷不是跪在神祗前的祈祷,而是自己时时刻刻的德行。这样,孝行虽然要求对祖先的祭祀,但是却更重要的落实在通过修德明礼以光耀门庭、传宗接代和留名青史。这就把孝的宗教性与伦理性结合为一。
结 论
孝是儒家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方法,是人之异于动物之所在。孝虽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爱,但是如果不加以人为的培养,很容易被子女对其自身子女的种族繁衍之爱所冲淡。于是,孔子以“反哺”作为孝的理论支持。孝虽然本意在于逆父母对子女之本能之爱而起,但是其目的又在于子女的福利。为了孝,父母尽心尽力养育子女,以求得自己生命和精神的延续;通过孝,子女得到祖先和父母的保佑而“得救”;通过孝,子女将自己的生命与人类集体的利益融合,以光宗耀祖,求得精神的不朽。可以说,孝架起了神和人、宗教与伦理之间的桥梁,达到了生与死的统一,完成了佛教的轮回和基督教的天堂的功能。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