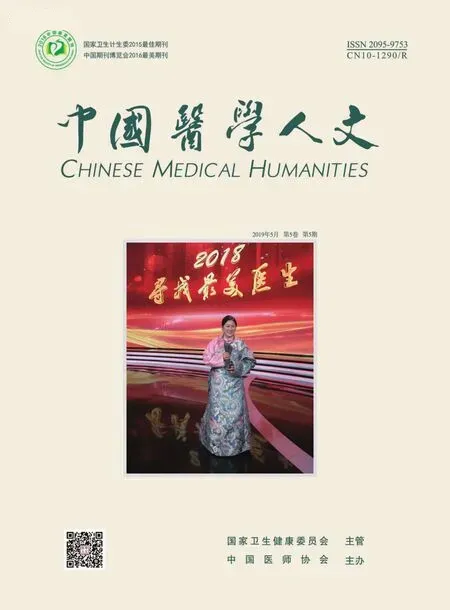电影《杀生》与中国医学人文教育
文/郭莉萍
“文学与医学”和“医学与文学”
1972年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医学院设立文学教授教席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与医学研究领域的开端,当然最初的理想是要把文学与医学建立为一个学科(Discipline),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学者们认为还应该将其定位为一个“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这个领域的发起人是在医学院任职的文学教授们,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文学放在医学的前面,这个研究领域被命名为“文学与医学”1。此后,论述文学对医学益处的文章大量涌现,其作者既有文学教授,也有医生和医学教育者。他们的基本的观点是:文学对培养医学生有百利而无一害,可以培养医学生的共情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临床想象力、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巧、反思能力;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让身体健康、没有经历过疾病和死亡的医学生经历疾病体验;从医生作家的视角看待疾病、病人和世界,会发现与生物医学视角的不同侧面,阅读疗法有利于心理疾病病人的康复,等等。
在医学院教授文学有两种路径,一个是由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医学院任职的文学教授班克斯(Joanne Trautman Banks)提出的,她认为“一个好医生最基本的特点是能够容忍模糊性,能够在数据不完整,或者有多种解释的情况下做出最恰适的结论,而这些正是文学的训练可以提供的;教会医学生在最完全的程度上阅读文学作品,就是在医学上培养他们……”2另一个是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科尔斯(Robert Coles)提出, 他认为“医学院的文学课程提供了伦理反思的机会,医学生因此可以知道,伦理选择不仅仅关乎治疗(做还是不做)和插头(拔还是不拔),而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关乎每日生活的重大决定。”3前者被称为文学与医学教学的“审美路径”,后者则称为“伦理路径”4。审美路径旨在教会学生阅读复杂文本,教给他们细读的能力,并且认为从阅读复杂文本得到的关注细节的能力可以迁移到疾病诊断和病人照护当中。
在我国,也有不少关于文学与医学亲和性的论述,以及为什么医学需要文学的论述5-6,其观点与英语论文的观点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文献当中,几乎总是习惯以“医学与文学”命名这一研究领域。从郎景和院士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医学与文学”应该指具有文学风采的古代医学典籍,如《皇帝内经》《汤头歌》《药性赋》等;而“文学与医学”多指记述了医学实践、疾病和治疗的文学著作,如《红楼梦》等7。
经过对比可以发现,“医学与文学”和“文学与医学”的倡导主体不同:前者为医学界,后者为文学界;前者为医学实践者,后者则多为医学教育者,特别是文学学者;前者为我国提法,后者为英语世界提法。但提倡文学与医学结缘的中西学者对二者性质的认识,以及对文学之于医学实践和医学教育的意义的论述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二者可以相互等同。
运用中国文学作品/电影进行医学人文教育
文学的作用得到了医学教育界的一致认可,但迫于时间的压力,医生或医学生似乎总是没有时间去完整地阅读文学作品;电影因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借助电影艺术的种种表现形式,能够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或“案例”,就被作为“压缩的文学作品”而受到青睐,甚至出现了一个医学人文教育的新名词“Cinemeducation”, 即“ 影视医学教育”。其倡导者提出,电影有助于提高学习热情、突出讨论主题、强化讨论和反思,有助于阐释临床实践、卫生政策、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具体主题8。但在过去20年当中,我国医学人文课堂上使用的多是英语电影和影视剧,如《弗兰肯斯坦》《心灵病房》《姐姐的守护者》《周一清晨》等。但正如胡克和努南(Claire Hooker and Estelle Noonan)所发现的那样,亚洲的医学人文教育多使用西方“经典医学人文作品”,她们认为,发端于美国的医学人文表达的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的精英文化,这些作品有可能不适应于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亚洲文化9。英语里的一些词汇,如Patienthood, Personhood,Doctoring等,强行译成中文是可以的,但总是感到与我们的文化和认知方式脱节。在世界医学人文发展的潮流当中,中国的贡献在哪里?为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前身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医学人文评论2013》10,向国外介绍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建立明确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医学人文”?在当前“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将通过细读中国电影《杀生》来探讨如何在我国运用中国电影和文学作品进行医学人文教育,以更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
电影《杀生》
电影的英文名为Design of Death, 是第六代导演管虎2012年的作品,改编自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儿戏杀人》,讲的是一群人合谋设计杀死一个不合规矩的人。影片的时代设定是民国时期,位于西南边陲的长寿镇。镇子自清朝以来,已经产生了18位110岁以上的老人和无数90岁以上的老人。长寿镇的居民在“祖训72条”的训诫下规规矩矩地生活。牛结实虽然生长在长寿镇,但在本镇人看来,他是地道的异类。牛结实吃肉不付钱,长期偷窥油漆匠的性生活,捞起被殉葬给老祖的寡妇,与寡妇私通,破坏取圣水仪式,掘开坟墓拿出陪葬品在村民婚礼上当礼物送人。最让居民不能忍受的是,他把催情药倒入镇子的饮用水系统,让全镇人斯文扫地。在规训牛结实的种种努力失败后,镇长最终请回了牛医生“设计死亡”,全镇人共同参与,用心理战摧垮了牛结实,为了保住寡妇肚里的孩子,牛结实选择自己赴死。一个外部医生被派来调查长寿镇所谓的瘟疫,他在悬崖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牛结实,通过抽丝剥茧,发现了牛结实的死因。
细读《杀生》
细读是叙事医学的两大工具之一,卡伦甚至称其为“叙事医学的特色工具”;她认为细读可以培养医生和医学生认识到病人疾病叙事当中的隐喻,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病人,并有助于帮助他们做出更加正确的诊断11;细读是一项广泛适用的技能;受过细读训练的人会将这种技能应用于各式文本,从而发现他们原本忽视的事情。如果细读可以帮助人们“发现他们原本忽视的事情”,那么它也可以帮助临床工作者注意到病人试图传递的信息;细读教会学生专注而熟练地阅读复杂的文学文本,也能教会医生带着细微而深刻的理解力来阅读或倾听病人的疾病叙述12。
在这个电影中,导演运用了大量的闪回和非线性叙事,使得理解情节就很“烧脑”。为了找到牛结实的死因,外来医生提出假设、找证据、做访谈,然后通过逻辑整合,把这些线索拼接在一起做出了结论——这个过程就像诊断疾病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外来医生实际上就是导演的化身,带领观众一起做“侦探”的工作。
此外,这个电影运用了大量的隐喻——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是“过度”使用了隐喻13。读懂隐喻才能看懂电影:为什么牛结实的住所是镇上的祠堂?为什么他的“随从”是镇上的孩子和傻子?为什么他脖子上总带着三把钥匙?为什么他是电影里唯一有名字的人(其他人都是用其职业来称呼,如油漆匠、接生婆、铁匠等)?为什么马寡妇是哑巴?为什么牛医生总带着黑皮手套、说普通话(其他人都说四川话)?为什么铁匠光膀子戴皮草?山顶上的巨石、葬礼上的黑袍、风筝和八音盒(八音盒放的生日快乐歌)、片尾的卡通蓝色海洋和鱼、影片颜色的变化……这些都有什么意义?以及影片的终极问题:到底是谁设计了谁的死亡?
正如影片的海报所说,“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带领学生细读这个电影,会让他们关注细节,认识到事件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多重解释的可能性;也会意识到不同的叙事视角会对阅读者/观众产生不同作用、影响他们对整个故事的理解和对人物的情感。经过细读训练的医生和医学生能学会容忍临床工作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也会知道面对病人和家属等不同的叙事者,听到的故事可能会不一样。
《杀生》中其他的医学人文主题
仔细分析《杀生》可以发现,它属于裴开瑞(Chris Berry)所说的“中国家庭伦理片”:个人不仅与家庭(此处为家族)有矛盾,而且家庭(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危机之中14。牛结实与家族的矛盾源于家族要规训他,而他拒绝被规训。作为一个外来者,他的行为和人们对他行为的反制导致了村子的灭亡;作为一个赎罪者,他不是一个品行高尚的英雄,而是一个小混混;他是个毁灭者而非受害者——在村民合谋除掉他之前,他们才是他恶作剧的受害者;他的自我牺牲也是为了让未出生的孩子活下来,而不是为了保持家庭(家族)的运行和价值观。但笔者认为,正因为牛结实这些与“正宗”家庭伦理片主人公的不同,《杀生》才可以作为讨论家庭伦理或家族伦理的绝好材料——在这里,家族伦理的意义是:在“家族”这样封闭的建制当中,什么才是真正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而封闭的家族建制和封闭的医院建制之间的类比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出发点,来类比讨论医学当中被忽略的一些“阴暗面”。
等级制度和服从
《杀生》拍摄于四川省一个传统的羌寨。寨子群山环抱,建筑依山层层而上,站在上层看,下层的房子就一览无遗,像极了福柯所谓的“嵌套的等级式监控结构”15,这也是村子权力结构的象征。村民在“祖训72条”的训诫下规规矩矩地生活:何时起床、何时入寝、何时吃饭、何时戒食、相互之间如何讲话、婚礼葬礼如何行事、如何服从族长的管制等都有规定。牛结实,这一强留于此并死于癌症的过路小贩之子,带着孩子气般的恶作剧破坏了每一项规定。但祖训是不能糟蹋的,牛结实因此一定会受到惩罚。
等级制度是医学这一建制中重要的体制建设方式,实习生、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等级需要一步步攀爬;但在以往,这一点被作为不言而喻的医院文化而没有被讨论过;医院的各种职业之间、各个科室之间有不成文的“鄙视链”。在从医学生到医生的转变当中,并非所有的转变都是积极的。医学生们逐渐“从头脑开放变得头脑封闭,从共情变得情感疏离,从理想主义变得愤世嫉俗”16。 在这个过程当中,医学生要对医院中的等级制度有心理准备,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处于等级性的监管之下,对此会习以为常,也会主动攀爬这个等级阶梯。在东亚文化中,从众的压力、集体主义、对权威和年资的尊敬使医院里的等级制度比西方更甚。日本、台湾和韩国都拍摄过名为《白色巨塔》的医疗剧揭示这一问题。在讨论中,我们要让学生知晓医院里的等级制度,并让他们知道,在医院这个“白色巨塔”当中,照护者和来此寻求帮助的病人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规训”:医生要有权威性,对病人显示出“有距离的关心”,而病人则要尊重医生的权威,“依从”医生的建议。医学生也许会觉得在这样的文化和建制下自己无能为力,为了生存,他们也需要“依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盲从。日益发展的叙事医学鼓励医生和医学生书写并反思自己的实践,自己与病人、同事和社会的交流。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医学生正在学习认真倾听病人的故事,表现出真正对病人的关心,并愿意为病人的痛苦承担见证。通过这样“审美性”地分析电影,并利用叙事医学的工具,医院中的权力关系会有所改变,与病人和同事的归属关系有望建立。
避谈死亡,追求“长寿”
“长寿镇”因长寿得名,“长寿”也成了村民的执念。老祖已经活了119岁零3天,卧床不起,靠静脉注射维生。他从年轻时就好喝一口,镇长“抓到”偷着喝酒的老祖,训诫到:“祖训说人到76不喝酒。你可不要坏了规矩啊。”他以个人成就的形式诱导老祖自我规训:“如果你再多活几天,就破了长寿镇的长寿记录了。”但牛结实悄悄给老祖嘴里滴了几滴酒:“乌龟倒是活得长,但整天缩在壳里,有什么意思嘛!喝!”老祖满意地点点头,喜笑颜开。
清代有复杂的优老制度:活到100岁以上的男性(只有男性)被称为“人瑞”,皇帝会命建牌坊,并赏赐给丝绸和银元宝;活到120岁的则赏赐加倍17。虽然到民国时期没有了物质的奖励,但追求长寿的执念并没有消退。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追求长寿,或曰推迟或避免死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医学的目标。当代的中国人也加入到了“青春崇拜”的行列,越来越不能容忍衰老,更不愿意去讨论死亡。虽然衰老、死亡和延长死亡过程不是这部电影关注的主要内容,但仍为我们讨论这些话题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的文化忌讳谈死,人们把它归为孔夫子的教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此为知也;这些教导让人们只管今生,莫问来世。我们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抓住此生不放手。因为我们不谈论,濒死的人在家人的忙乱中孤独地死去。一项研究显示,57.7%的癌症病人家属不会告诉病人他们得了癌症18;有70.0%的癌症患者希望医生和家人“尽一切所能挽救他们,虽然他们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但76.5%的病人希望能跟家人或临床工作者讨论死亡19。这些研究显示了癌症患者的希望和病人家属做法之间的落差,也显示了癌症患者对死亡的接受和求生愿望之间的落差。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生物医学思想一致的时候。年轻健康的医学生面对衰老濒死的患者时也许没有做好准备,死亡会让他们对现代医学技术及医学本身产生怀疑,或者认为技术还不够多、不够好而陷入更多技术的泥沼。如果他们从上面第二个研究得到的结论只是“为病人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以挽救他们的生命”这样的“峻猛医学”的信息是可悲的。我们要通过讨论,让学生意识到衰老不是病,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他们要不怕跟病人和家属谈论死亡,也要学会有技巧地谈论这些话题。当恢复健康已经不可能时,医生的责任是帮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不适和失能完成他们个人的愿望。”20
医生形象
北大医学部的学生在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对影片中两个医生的形象非常敏感。在电影展映后与导演管虎的对话中,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要把中医(外来医生)设定为“好医生”,而把西医(牛医生)设定为“邪恶的医生”?管虎回答说,直到学生问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学生们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
前面已经说过,外来医生发现真相的过程就像是导演带领观众所做的“侦探”工作,也像是诊断过程。但他确如学生所认为的那样,从开始时就是一个仁慈的、富有同情心的医生吗?虽然他从始至终都面带微笑,但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他是冷静的、不掺杂情感的,他甚至解剖了还没有“死透”的牛结实。
美国医学院协会把共情当作医学教育的目标之一21,简言之,共情就是把自己投射到他人的境遇,想象自己在他人的立场如何看待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医生和他的笑容在探究真相过程中经历了转变,他开始慢慢理解牛结实,欣赏他对自由的向往;到影片最后,他甚至模仿牛结实骑着自行车在镇子里逡巡、剪了他的发型、跟镇长探讨如果用牛结实的视角看待整个事件,另一种解释会是什么样——村民的生活不那么僵化,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温暖……到影片最后,他的脸上带着平和满足的笑容,看着马寡妇和婴儿在温暖的光线中离开长寿镇,做到了与他的研究对象完全共情。
相反,牛医生是冷血的“死亡设计者”,他为了报私仇而答应回来帮忙除掉牛结实。在他们小时候,牛结实用钩子从牛医生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偷腊肉,牛医生为保护腊肉,堵住了房子的通气孔,爷爷奶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但他认为是牛结实而不是他自己害死了爷爷奶奶。他在国外接受了医学教育,是电影里唯一讲普通话的人——只有一次例外,当外来医生发现他是“死亡主谋”时,他苦笑着用四川方言说 “我爷爷奶奶不能白死”(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笑)。他坚持要把马寡妇的孩子打下来,要“斩草除根”,但村民们很犹豫,镇长的意见是“剜疮不割肉”。
跟医生“济生”的职责相反,牛医生是杀人医生。村民们请他想个办法除掉牛结实,他问道:“你们是否都想杀了他?”村民们对他要“杀”了牛结实感到震惊。电影中牛医生代表的西医形象让医学生感到尴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今媒体曝光的医学丑闻和医患纠纷的主体都是西医。当然媒体有歪曲报道的现象,但不可否认西医是当今中国医学实践的主体,公众一般也会认为中医更以人为本因此更人道,西医以技术为主因而更冷漠。这个电影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医患关系的出发点:媒体和影视作品对医生的刻画是否影响了公众心中的医生形象?是否影响了高中生的学医意愿?如何改善医生形象?不可否认,医生形象的改善与医患关系的改善直接相关。
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或“隐匿课程”的英文是“Hidden curriculum”,在英文中,其意义是“作用于组织和文化层面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正式课程之外的、未经阐明的、未经讨论的一些过程、压力和约束。本质上说,隐性课程是一个机构没有意识到它正在教授的一些东西”22。在西方的医学教育中,隐性课程一般体现在“未表达出来的等级制度、分层、羞辱式教学、不合职业精神的行为、将病人去人性化,以及负面榜样等”23-25。但在我国,“隐性课程”或“隐匿课程”指的是以间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的正向道德教育,如责任、利他、尊敬、关心和美,其手段是课外活动和校园环境建设,包括看电影、演讲比赛、戏剧比赛、辩论赛、白袍仪式,也包括雕塑、书法作品、绘画作品等其他美化环境的艺术作品。电影是中国隐性课程的绝好载体,可以用来讨论西方的 “Hidden curriculum”所涉及的负面内容,从而引导医学生能够认识到这些负面因素,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