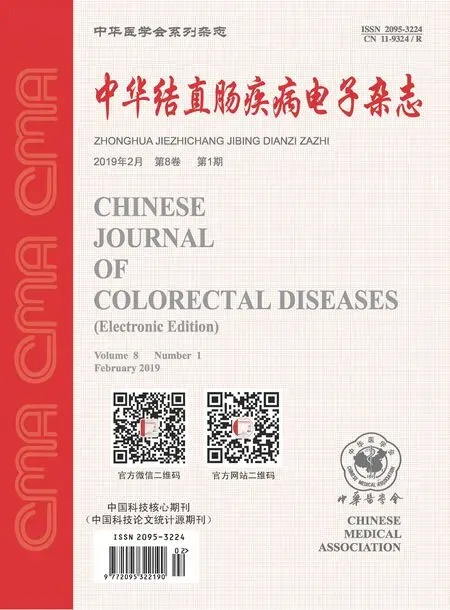春花秋实
——中国人向死而生的“百媚千红”
靳珍珍 尹梅 张持晨,3
作者单位:030001 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1;150081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310058 浙江大学医学院3
靳珍珍, 尹梅, 张持晨. 春花秋实——中国人向死而生的“百媚千红”[J/CD].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 2019, 8(1):103-105.
春花其发,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爱登其质。人生如草木一秋,春种发芽,秋收得果,有朝终将落叶归根,而在这个向死而生的过程中,生命之花“百媚千红”,生活之道春花秋实。
一、向死而生——认知死亡的前提
于世人而言,生是个体人生剧的片头曲,死则是“片尾曲”,比较震撼的是这个剧本因人而异,向来没有彩排,故事有始有终,且生死边线主角独一无二。正如“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乎人乎!”[1]先人由自然界变化的信息中透视出人类死亡的现实,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大多数情况下,死亡是个体生命由盛及衰的自然转化状态,向死而生则是我们必经的人生轨迹。
无知催生恐惧。尽管向死而生是活着的必然状态,但由于死亡的神秘和不可验证,人们对死亡总是充满恐惧感。这种恐惧可能直观感受于亲友临死前的痛苦神态或死后的可怕面目,可能间接体悟于宗教理论描述的死后恐怖世界,还可能深深潜伏在对生命死期的无可预知上。就其恐惧实质,正如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干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许死亡原本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真正令人们惶恐的是人们对死亡的无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纵观古今,“天花”“鼠疫”“SARS”等一度给国人带来恐慌,这其实就是对疾病与死亡的恐惧。后来,随着医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相关疾病的防控知识和技术,便不再那么恐慌了[2]。可见,人们对未知的事物总是饱含恐惧,恐惧冲散了个体的理智,也影响了个体的判断,而科学知识可以武装头脑,安定心智,协助个体做出理性的预判。
死亡认知的前提是“死亡是什么”,而在“死亡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人们因无知而平等,没有人堪称绝对权威。但我们须明白:我们不可能逃避它,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迎向它。但是对于死亡,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并非毫无选择。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死,但我们却能选择如何看待死亡。我们选择如何看待死亡,便决定了死亡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排斥它、恐惧它,它就越发阴魂不散、令人毛骨悚然;当我们直面它、理解它、发自内心的包容它、接纳它,它就像四季更替、日月升降、潮起潮落,成了再自然不过的过程。叔本华曾言“死亡之于种族,犹如睡眠之于个人”[3]。他认为,原始的个体或快或慢地趋于衰弱,同时新的生命继之而起,死亡与再生交替,宛如种族脉搏的律动,死生对于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而言,是不可分割的连贯,正如“流年周而复始,终古循环不已”。《歌德谈话录》中也曾提及,“我们的精神是‘绝对不灭之自然’的存在,死亡之于个体,不是在宇宙中彻底消失,而是以一种能量存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存在形式,某种程度上,是其从肉体束缚中解脱,得以弥漫于无限时空——一种更自由的存在状态和更无处不在的存在感”[4]。此外,墨子“明鬼”的死亡观,使人们相信人死后变为鬼神的观点,虽有一定的落后性和局限性,但通过信鬼神来实现治国利万民的做法在当时发挥了相应的社会作用。就“明鬼”实质而言,其影射的是死亡只是旅途中转站的死亡观,对当代人的死亡意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早已摒弃了鬼神说,但我们可以通过提倡理性的信仰让人们树立“旅途中转站”的死亡意识。或许以这些意念认知死亡的存在状态,我们更能体悟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感恩与豁然。
二、尚力非命——认知死亡的关键
直面向死而生的现实,具备淡定豁然的死亡意识是认知死亡的基础,而坚定“尚力非命”的生命观信念则是认知死亡的关键。
死亡虽是人类个体无法逃脱的宿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束以待毙。先秦墨子主张“尚力非命”的生死观,他认识到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支配和改造自然,从而获得生存。而动物往往只能依靠其自然属性以消极适应自然得以生存。在《非命下》中,墨子提到“强必富,强必饱,强必暖,强必治,强必宁,强必贵,强必荣;不强则贫,不强则饥,不强则寒,不强则乱,不强则危,不强则贱,不强则辱。”他极力推崇“强力有为”的人生观,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自身勤劳的程度,人只有强力有为,方可实现“无忧、便宁、饱食、暖衣”。墨子尚力非命的观点,强调的是人们通过劳动和进取获得生存的信仰,故他非常反对“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生命观[5]。
墨家“尚力非命”的生命观启示我们,生命是身体和思维的统一,生命的价值在于人能思维和劳动,并不在于“天命”之规定。在当代中国,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墨家生命观的意义,积极推崇生命的价值,鼓励以思考致胜,以劳动创造生命的价值。因此,必须通过生命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认识生命,珍重生命,加强人文关怀,让人们自觉感受到生命的无限温暖,进而获得生命生存与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生命教育应立足于生命存在的本质,以及生命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促使人们了解“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价值”,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灌溉生命之花,体悟人生真谛,并潜移默化地提升其精神境界,激发其欣赏生命,善待他人,构建和谐美好世界的热情和信念。生命教育,不但要引导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客观存在,同时也认识到生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生命之花“百媚千红”,而人们唯有在生活实践中辛勤培育生命之花,生命的价值才能在拼搏奋斗中逐渐实现。
三、生命有限——认知死亡的目的
坚定“尚力非命”的生命观是死亡认知的关键,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越趋近死亡,越发可以体会“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正因死亡作为生命的尾音,生命的有限性才如此真切,而有限的生命才弥足珍贵。那么,与其计较生命的长短,不如让有限的生命充实丰满。
复旦大学陈果老师曾言:多数人看来,死亡意味着“自我”彻底消散,不难想象,自我“随风而逝”,自此,“云淡风轻,抑或热闹非凡,我将不复感知,与我毫无干系”,人们害怕“空虚”,而对死亡的害怕是不是正因为人们觉得那将是永恒的“空虚”[6]。若真如此,那消除“空虚”比超越“死亡”更为关键。或者说,与其煞费苦心却徒劳无功地计较生命的长短,不如思考如何使用我们有限的生命,使之绝不空虚,这样的意义则更为重要。的确,我们应觉悟到死亡的真谛。弗兰克尔认为死亡的逼近提醒我们生命的限制性,提醒我们它留给我们可供利用的时间是非常之少的。这一启示并非不幸而是希望,因为有限性本身必定建立起某种能赋予人类生存意义的东西,而不是某种剥离其意义的东西。正如余华《活着》[7]里的福贵,年少时,祖传家业殷实,他却好逸恶劳,挥霍无度,嗜赌成性,在倾尽万贯家财后,实在落魄不堪,一度想自寻短见,但家庭的牵绊又使他不忍割舍,只能勉励为生,而后不幸被抓了壮丁去拉大炮,却有幸在战场捡回一条命;曾不幸把家底抵给龙二,侥幸的是,龙二作为恶霸地主,在土改中成了他的替死鬼。几度与死亡交臂后,福贵深感生命的珍贵和活着的意义,郑重地告诉自己:“这下可要好好活了。”生命正如这般脆弱,生活就像这般柔韧,人们游历于不同的时空,演绎着各自生活的悲喜,九曲回肠后总有些荡气回肠,山重水复后总迎来柳暗花明,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切还来得及,一切皆有可能。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定论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句箴言:“未经自我反省的人生是白活了。”正因如此,浪子回头金不换,人们应把握机会,让有限生命在未尽之前做出积极改变。李敖坦言: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当百花凋零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8]!总之,生命的有限性促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命,进而努力抓住构成生命整体的一次次机遇。正如尼采所讲“参透为何,定能接受任何”。
死亡相对于生命的目的:让有限的生命柔韧坚定,让甘苦的生活生机勃勃,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9]中的保尔,《我与地坛》[10]中的史铁生、《滚蛋吧!肿瘤君》[11]中的熊顿、《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12]中的李开复、《皮囊》[13]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的蔡崇达等,都可以深切感悟生命的韧性和奇迹。对那些精神世界充实丰富的人而言,他们尽力创造着并享用着生活中的每一刻收获和欢乐,使之了无遗憾、心满意足。当然,他们并不期待死亡,也不热爱死亡,但他们不惧怕死亡,坦然面对死亡,甚至他们对死亡心怀感恩,因为死亡并没有切断他们这幸福的时刻,死亡无法阻挡他们当下胸膛里流淌的深情款款,即使死亡意外到来,要将他们带走,他们也无怨无悔,因为生命业已如此精彩,最终他们在爱中离开,也因爱而永生,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更好的社会价值其意义则不言而喻。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逐渐成为指导国人参与社会实践,实现个人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义无反顾地选择把个体生命融入人民群众的整体和历史的运动中,循历史潮流而进、为人民利益而死。他们虽死犹生,五星红旗上浸染他们的殷殷鲜血,历史画卷中铭刻着他们的不朽身躯,中国人民心中传颂着他们的民族精魂。正如保尔的生命箴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创造出生命的奇迹,彰显更大的人生价值。
直面向死而生的生命过程是中国人理性认知死亡的基础,它强调处之泰然的死亡态度,人们应将死亡看作自然界万事万物运行变化的有序组成部分,科学树立“旅途中转站”的死亡意识,生命的存在是身体和思维的统一,生命的价值在于人的思维和劳动,以劳动创造价值,感知生命的可贵,以激发欣赏生命,感知生命的美好。
生命过程于个体而言相当有限,死亡的趋近提醒人们生命的限制性,而死亡的真谛则是传递人们生命旅程弥足珍贵,我们与其计较生命的长短,不如把握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人们应在盖棺定论之前认真思考人生并尝试做出积极改变。同时,应不断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祖国的发展、人民的福祉联系在一起,在服务社会、奉献他人中获取幸福感和满足感。光阴荏苒,弹指之间,懵懂却已不再少年,生活还在风雨羁绊中继续,生命仍在向死而生中延展,生命之花“百媚千红”,生活之道“春花秋实”,当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