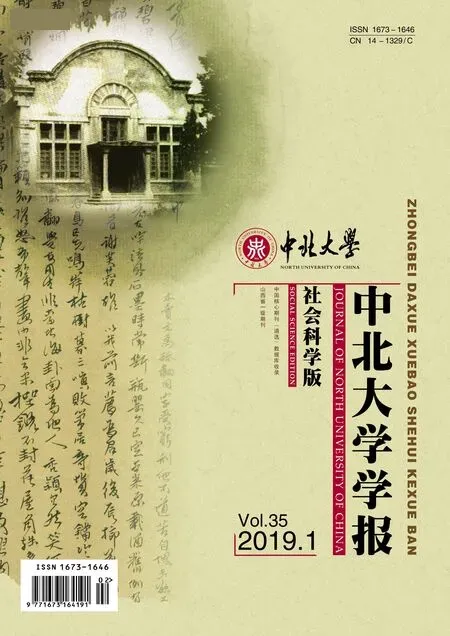《幸福过了头》叙述中无声的权威
刘冰洁
(吕梁学院 外语系,山西 吕梁 033000)
爱丽丝·门罗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在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形形色色,遭遇到的现实生活却是一样的残酷。小说集《幸福过了头》写于门罗罹患癌症之时,她欲将患病以来对人生新的感悟和对世界的深刻思索诉诸世人,以此作为她人生的绝唱。十篇饱含深情的故事,太多不能承受、无法诉说的幸福与伤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背负着各自的创伤,穿行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平静,清醒,睿智。她们的生命从不喧哗,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坚强印像。
《幸福过了头》是小说集题名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索菲亚来自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是一名极具天赋的数学家。她渴望实现自我,向往幸福生活,却因时局动荡、世俗偏见而举步维艰。为了出国留学,她经历了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并以丈夫自杀告终。她因马克西姆燃起生活希望,却因他的虚伪独断、毫无担待而只能生活在自我欺骗的“幸福生活”中。她虽然在数学研究领域大放光彩,却始终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工作机会。索菲亚极具代表性,通过了解她的经历,读者对当时知识女性的遭遇便可见一斑。她仿佛在无声却清晰地诉说她人生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建构显然与之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方式是不可分割的。
1 隐藏的作者型声音模式
女性主义叙事学“处于语境叙事学的前沿”[1]26。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首次根据作者、叙述人、故事讲述者、故事主人公在文本中的位置及其关系为依据,将叙事声音分为了集体型声音、个人型声音和《幸福过了头》中用到的作者型声音这三种女性独特的叙事模式。作者型声音在此指称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且在潜意识中可以自我表述的叙事状态。而所谓“异故事”,通常指“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2]18,因而讲述不遵循故事本身的进程或者线索。作者型声音模式同时也是“故事外的”,即叙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种叙述有两种优势:一是文本对(隐含)作者和主述者之间没有做标记性引入,读者在直观上感知不到叙述声音,叙述更加客观真实,更易承载社会权威。苏珊·S·兰瑟指出:“这样的声音产生或再生了作者权威的结构或功能性场景”[2]18。亦即,文本在处理(隐含)作者和主述者之间关系之时,没有作显性的区分或明白的标识,读者即被引入,同时由于主述者的异故事和集体性,叙述者便等同于作者,受述者相应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如此,赋予作者声音优先权和权威性。二是作者型叙述者并不存在于文本之中,可以称之为隐藏的叙述者,无声的叙述者,仿佛全知全能的上帝,因而拥有了某种规约性的权威。正如苏珊·S·兰瑟所说:“比起那种赋予小说人物的、甚至是正在叙述的小说人物的权威来,这种作者型叙述者的权威更加优越。”[2]18在《幸福过了头》的叙述过程中,正是由于爱丽丝·门罗采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这一叙述模式,叙述者仿佛消失,作品更加客观,更加真实,因而载负了更多的社会权威,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建构起来了一种无声的权威,传达了女性的声音和主张。
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存在于故事之外,似乎并不干涉故事的发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甚至都意识不到叙述者的存在,叙述声音被抹去。事实上,任何一个故事的结构都是叙事者精心安排的,叙事者通过行为或者话语来干涉故事的发展走势,而所谓故事之外的叙事则是指叙事者放弃了利用话语和行为来参与故事,任其发展。例如,《幸福过了头》的叙事者并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小说的叙述视角仿佛总是在变化。以索菲亚的视角开篇,“那时候,也正是她日以继夜工作的时候,她要准备提交勃丁奖的文章。……索菲亚这么想。开始是勃丁奖转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当她正沐浴在温暖之中时,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3]290。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又进入了马克西姆的视角,“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他从博利厄写来了冰冷愠怒的道歉信,拒绝了她一旦忙完了就来看他的提议”[3]291。文中索菲亚第一次走进魏尔斯特拉斯教授家中时,是以教授的两个妹妹为叙述者,“克拉克和伊利斯吓着了。……姐妹两人不知道她的年龄,不过让她进书房之后,她们猜测她应该是哪个学生的妈妈,是来请求减免学费或者讨价还价的。克拉拉的猜测更生动,‘我的天哪,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家的这个人是不是个夏洛特·科黛?’”[3]295文中叙述视角的多变赋予了叙述声音如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权威。同时,由于叙述者在故事中的缺席,使得它无法干涉小说情节的发展,因而放弃了它对小说行为的干涉。除此以外,作者通过对故事人物和情节的客观叙述,不加评价,放弃了对故事发展的话语的干涉。
2 客观叙述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作者为了便于表达作品内容所选择的叙述主体和叙述的立足点,是作品的整体架构方式,可以分为全知叙述、限制叙述和客观叙述。在客观叙述中,叙述者总是冷静客观地叙述故事的走向,描写人物的外部肢体动作,不添加任何个人情感,不做任何主观分析和评价,也不分析任何小说内角色的心理活动,或者以读者毫不察觉的方式巧妙地在叙述中插入自己的主观思想,把想要表达的内容交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思考。这种客观叙述力求将客观真实不经雕琢、直接呈现给读者,因此比全知叙述和限制叙述更具真实可信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客观叙述只能是相对而言,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意愿的表达,因此它或多或少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打上作者的主观思想的烙印。
例如,死亡,一个严肃的话题,总是伴随着沉重、痛苦、纠缠,这种煎熬的过程让人不寒而栗又难以自拔,发人深省又难以描述。因此,很多作者对于死亡的书写总是不惜笔墨,唯恐表达不清,让读者无法感知。但是门罗在描写索菲亚的丈夫弗拉迪米尔的死亡经过时却只用了三言两语,就交代了一个事实上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耽搁了一段时间。四月的时候,他用一个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了氯仿。”[3]312而对于索菲亚的感受作者也一样简明扼要,“在巴黎,索菲亚绝食,闭门不出。她全身全心集中在绝食之中,这样她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了。最终,她还是被强迫进了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强烈的羞愧。她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开始继续工作”[3]330。《幸福过了头》中关于死亡的书写主要有两处,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特蕾莎和艾伦被从睡梦中惊醒,她们叫醒了馥馥,让孩子最后见见还活着的妈妈”[3]347。“大约四点钟,索菲亚去世。……她去世前,马克西姆接到了米塔·列夫勒的电报,从博利厄赶来,他抵达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在她的葬礼上发言。……他提起索菲亚,更像是提起一位他相熟的教授”[3]348。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死亡的过程只是冷静记录,好像科学实验室里的数据记录员,丝毫不掺杂个人情感。这与读者关于死亡的联想——声嘶力竭、痛不欲生、留恋挣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而也给读者留下了客观叙述的深刻印象。作者正是通过这样冷静客观的叙述放弃了对小说的评价,放弃了对读者了解人物的任何干涉,由此放弃了对故事发展的话语的干涉。读者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虽然感受不到叙事声音,却被一股不可名状的力量牵引,去感知作者赋予作品的话语,感受到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叙述的权威。
3 影子情节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学术界出现了女性“在结尾之外写作”[4]95的认知。南希·凯·米勒称“女性作家的情节由否定的动力所驱动”[5]。苏珊·S·兰瑟认为,如果女性写作一再被认为是无情节的,那么“现行的情节概念就可能出现了问题”[6]。因而近期,在“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她提出了一个重要新观点,丰富了女性叙事情节理论,国内学者通常将其称为“影子情节”,是将情节模式投影于金伯勒·克伦肖所说的“交叉路口性”[7]女性主义的叙事技巧。影子情节指的是作者在情节描写中,反传统叙事方式而行之,常常依赖“非叙事”[8],将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覆盖于事件的对立面的描述之中的一种情节叙述手法,这种情节与所叙述的事件如影随形,即“事件的重要意义来自于它们在文本引发的(但不一定是直接表达出来的)的对立面”[9]4,而不是事件本身。简而言之,一些在文本中没有被叙述出来的情节可以在文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影子,这两种情节同时运行,没有发生的情节由于暗含在文中真实发生的情节中,或者通过读者的叙事认知被真实虚构而具有了一种无声的权威。[5]由此可见,这种影子情节往往比真实情节更加发人深思,意义深远,甚至成为了一些文中发生情节的真正目的和叙事意义所在。
“根据‘影子情节’是在文本内部召唤出来的还是依赖读者的外部知识而存在”[9]4,影子情节被分为“内在影子情节”和“外在影子情节”。外在影子情节依赖于读者的阅读体验、知识建构和叙事认知。《幸福过了头》在描述索菲亚的数学家身份时,极力渲染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新贵,一个数学天才,相当地迷人,受到了无穷无尽的赞叹和吻手。甚至在垂死之际,索菲亚都呢喃说着“幸福过了头”。但是,读者建构索亚菲的幸福生活,其实是对当时女性所受到的歧视与压迫、不公正对待的真实情况的一个隐含的反情节,而这种认知之所以成立,有赖于读者外在的历史知识。19世纪后半叶沙皇专制下的俄国,封建农奴制残余。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工业革命对女性影响甚微,女性地位依旧低下,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未婚女子没有父母许可不准出国。文中索菲亚就是为了出国学习宁愿嫁给一个思想激进但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收场。一个新贵尚且如此难以实现自我,普通社会阶层女性的境遇又会如何呢?不言而喻,自是命途多舛了。
内在影子情节是在文本内部可以得到明示的情节。在《幸福过了头》的叙事线索中,一直有一条备受期待的主线引导全文,那就是索菲亚和马克西姆的婚礼。“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3]290但是,小说却以悲剧结尾,索菲亚死于肺炎,“痛失”与马克西姆完婚、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良机。如果说索菲亚与马克西姆的天人永隔是小说的交叉点,那么二人的婚礼则是文中错失的影子情节。读者不禁会为索菲亚感到惋惜,认为她曾经离幸福如此之近。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索菲亚爱的小心,总是担心马克西姆离开自己,努力迎合马克西姆的喜好。“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和她一起坐到戛纳,……她如此地感激他。”[3]295在得知索菲亚的死讯后,马克西姆仿佛没有丝毫悲伤,反而把参加她的葬礼当做曝光的好机会。从文中不难推断出,二者在爱情中的地位是极其不对等的,即使索菲亚嫁给了马克西姆,也得不到她想要的幸福。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另设了一种情节——索菲亚与马克西姆顺利完婚,它与文本情节相互对立,同时运作,却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索菲亚无法实现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这种影子情节和文本情节的碰撞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女性在社会上家庭中得到承认的艰难,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女性不幸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文化原因,进一步强化读者的叙事体验。
4 结 语
爱丽丝·门罗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叙事是她认知世界和表达自我的特有方法,而近期提出的交叉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她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这是对文学实践交叉性的新的尝试,也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的丰富,而分析门罗作品中独特的叙事声音和叙事情节本身也为诠释和挖掘其作品的深意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打开了另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