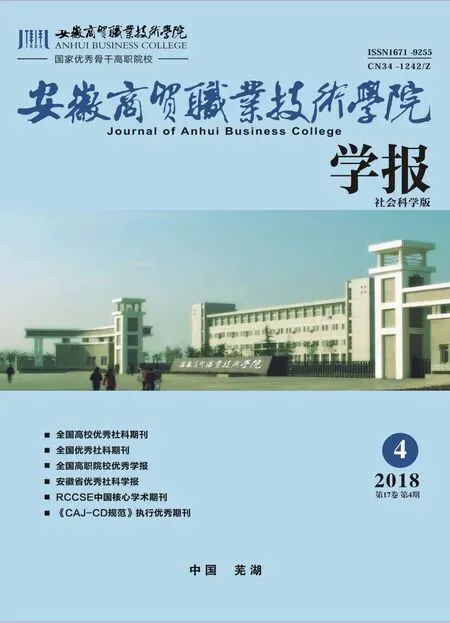演化博弈视角下PPP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彭金道
演化博弈视角下PPP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彭金道
(铜陵学院 监察审计处,安徽 铜陵 244000)
演化博弈理论是博弈论和动态演化过程的结合,参与人均为有限理性。构建不完全信息下PPP项目参与方地位不对称的风险分担博弈模型,建立合理有效的PPP风险分担机制,通过“机制找回效率”,提升债务资金配置效率,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应优化PPP合约及规制体系设计,构建PPP风险管控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升公共投资效率,同时要改善政治环境。
PPP项目;债务风险;演化博弈;风险管控机制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最早应用于英国并逐渐向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推广。我国自2014年以来关于PPP的政策密集出台。PPP是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既创新了投融资机制,又创新了管理模式。“十三五”期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融资缺口更加明显。中央政府将PPP模式作为化解地方债和推动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机制。PPP模式具有三大效应: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相关利益主体契约意识,转变政府职能。PPP项目推介规模大,但存在的问题亟须解决:地方政府异化PPP变相融资,项目落地难,运作不规范,甚至“伪PPP”呈现加快出现态势。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结构调整带来的宏观紧缩和房地产调控致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急剧上升。规范使用PPP模式化解债务风险并实现地方政府债务运行“新常态”,是当前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PPP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逻辑机理分析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多数是基于财政视角,关注的是地方政府不能按期履约偿还债务及其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其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包括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即债务资金运行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不能够补偿社会成本。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资金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债务行为是追求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追求GDP、政绩寻租、在职消费等非社会利益目标干扰,在缺乏严格行为约束条件下,盲目扩张债务引起财政冗余下的低效率资金配置,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中体现在债务资金的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债务成因复杂。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预算内软约束”以及“预算外基本无约束”的不合理体制,追求政绩的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现“异质性”。
地方债务的盲目扩张导致效率偏离最优。债务风险的本质是非社会理性条件下政府“行为牺牲效率”,防范债务风险的关键是提升债务资金配置效率。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聚焦于应用PPP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公共领域PPP的有效利用,引入市场机制,社会资本的加入,考虑到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抑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提升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
当前必须考虑制度背景因素,通过“机制找回效率”,构建有效的PPP风险管控机制,防范债务危机的发生。PPP能优化风险分配,提高效率,增加供给,从而减轻债务压力,缓解财政风险。
(一)提升债务资金“责任分担效率”
准公共产品如教育、公路、市政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如果全部由政府负责提供,势必因过度提供加重财政负担,最终无法经济、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根据公共物品理论,鉴于公共产品的不同属性和特征,应安排多元供给制度满足社会公众需求。[1]政府应保障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纯公共物品的供给,通过有效的配置市场资源提供准公共产品。因此,教育、文化、邮政、供电、公共交通等准公益性项目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承担。运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改善财政资金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2]根据责任分担原则,政府和私人部门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按照各自所占份额承担供给责任,避免了政府通过举债完全承担准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的“公共地悲剧”。通过PPP机制的引入,政府把准公共产品的运营权交给私人部门。为了弥补成本,私人部门对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进行收费。私人享受公共产品服务的意愿以及私人部门的承担成本影响准公共产品的收费价格。政府和私人部门对于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进行明确而合理的责任划分,弥补了因政府举债全部承担准公共产品带来的责任分担低效率。[3]在PPP项目中,根据公益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分别确定政府与私人部门的承担责任以及由谁收费效率更高。
(二)提升债务资金“投入产出效率”
“政府失灵”是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由于非理性行为的干扰,举债过程中出现的投入产出效率异象。公共服务的供给中PPP机制的引入,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和维护权力将由私人部门负责,避免了完全由政府供给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举债供给的非社会理性行为干扰。[4]PPP模式下,政府和私人部门在实现社会利益目标的前提下,按照相应的份额分享收益。私人部门因融资的高风险而获取较高的报酬。同时,因利益与公共服务产品的项目效益密切相关,私人部门密切关注项目的资源配置模式,时刻防范政府官员个人利益侵蚀公共项目利益。因此,合理划分公、私部门的管理责任,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防止个人利益、市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可以提升投入产出效率。
二、模型构建
PPP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合理有效的PPP风险分担机制,通过“机制找回效率”,提升债务资金配置效率,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置身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在PPP项目实际运营中,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地位是不对称的。政府部门也许会利用其强势地位威慑私人部门,私人部门运用其自身优势进行讨价还价。其谈判过程是多回合的动态的博弈过程。
文章借鉴相关文献,构建基于不完全信息下PPP项目参与方地位不对称的风险分担博弈模型。
(一)提出假设
假设一:PPP合作方均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但是皆期望双方能够合作;假设二:公、私合作方投入性质具有不同性,政府部门是公益性投入,私人部门是自利性投入,但是追求自身利益同时实现社会利益;假设三:代表政府的公共合作方先出价且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双方承担的风险比例之和为1。
(二)模型设定
在初始合作阶段,项目风险完全由单方即掌握控制权的合作方承担。PPP项目风险与控制权成正向关系。构建合作方静态博弈模型如下:
表1 公共部门(G)和私人部门(P)的静态博弈模型

表1中,私人部门(P)的风险偏好系数为M,公共部门(G)的风险偏好系数为N。当M>0 N>0,或者M<0 N<0时,没有唯一的纳什均衡,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担风险;当M>0 N<0 时,公共部门(G)承担项目风险;当M<0 N>0时,私人部门(P)承担项目风险。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不完全信息下不能够了解对方的策略,但双方期望合作成功。公、私部门进行讨价还价谈判,双方每多一轮博弈,消耗的成本提高。
第一轮谈判中,公共部门强势威慑私人部门,明确以q1的概率承担N1风险比例,转移k1风险比例给私人部门,此时构建的模型如下:
G11=q1(N1- k1)
S11=q1(1- N1+ k1)
当公共部门不威慑私人部门,以q2概率承担风险,此时构建的模型如下:
G12=q2N1
S12=q2(1- N1)
因此,第一轮谈判公共部门G1和私人部门S1的风险期望为:
G1= G11+G12=q1(N1-k1)+q2N1
S1=S11+S12=q1(1- N1+ k1)+q2(1- N1)
G21=gq1(N2-k2)
S21=fq1(1- N2+ k2)
当公共部门不利用其强势地位威慑私人部门,以q2概率承担风险,构建模型如下:
G22=gq2N2
S22=fq2(1- N2)
因此,第二轮谈判公共部门G2和私人部门S2的风险期望为:
G2=G21+G22=gq1(N2-k2)+gq2N2
S2=S21+S22=fq1(1- N2+ k2)+fq2(1- N2)
同理,可得第三轮谈判公共部门G3和私人部门S3承担的风险期望为:
G3=G31+G32=g2q1(N3-k3)+g2q2N3
S3=S31+S32=f2q1(1-N3+K3)+ f2q2(1-N3)
依次类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进行多轮讨价还价谈判,直至双方接受风险分担比例,此时动态博弈结束。
三、PPP模式下债务风险控制对策
作为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PPP,具有伙伴关系、责任整合、风险转移以及不完全契约等特征。PPP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有效地整合了政府的政策优势、私人部门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及金融资源,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管理技能和创新激励。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关键在于PPP项目参与方合理的风险分担。因此,应规范运用PPP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高PPP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5]
(一)优化PPP合约及规制体系设计
PPP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以及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如运营期间可能经历政府官员交替,因此PPP合约是不完全的。涉及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祉的PPP,必须进行系统的法律规制设计。一方面增强民间资本的安全感及信任度,保障民间资本权益;另一方面监督政府权力,协调PPP参与主体利益。PPP模式的顺利实施以及提升PPP服务供给效率应该以适当的合约及规制体系的构建为基础。[6]通过缔约高效的规制机构能够防止政治机会主义及利益集团的阻碍,确保PPP合约高质量地运行。同时促使政府部门尊重契约理念,认同契约约束力,培育契约精神。
现行的PPP实践主要是政策驱动。政策目标的不一致及政策自身的不稳定使得PPP亟须立法规范。PPP规制涉及诸多复杂关系、专业技术等。单纯的法律无法解决现实众多问题,需综合利用系列规制工具包括法律、政策、指南和合同,设计一个从宏观到微观、层层递进、相互联系的立体PPP规制体系。
(二)构建PPP风险管控机制
缘于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备、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政府和企业之间权责不清等,在运用PPP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时会面临政府决策风险、市场变化风险、政策变更风险等。因此,政府要构建PPP风险管控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PPP的可持续性极其必要。识别PPP风险因素,通过熵值法确定PPP风险指标的权重系数,运用TOPSIS 法确定 PPP项目参与方的最优风险贴近度,构建基于随机合作博弈理论的风险共担模型。另外,也要完善PPP合作伙伴遴选机制,设计项目流程监管机制。
(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升公共投资效率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大量融资,需要引入社会资本,改变过去的公共基础建设的投融资来源的集中化、以及投融资主体的单一化局面,在PPP项目中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主体。PPP项目中,相关利益主体要在价值观和行为理念等方面降低差异,发挥非契约机制的优点,减轻公共财政压力,提升公共投资效率。同时实施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增强地方债务的偿还本息能力,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四)改善政治环境
基于实践人们开始反思:PPP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灵丹妙药”还是“美丽谎言”?随着PPP扩展到公共服务领域,其创新了公共服务产品的融资模式,提升了经济效率,但是PPP项目由于交易成本高昂、参与主体的利益冲突、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等复杂因素而失败的事实不容忽视。制度质量影响PPP,良好的政治制度对于降低PPP的政治风险和交易成本是有利的。制度是不易量化的,体现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政府效率及对私人部门的管制程度等。“全球治理指数”(WGI)和“国家风险指数”是目前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反映制度质量的数据库。社会资本面临PPP项目的抉择时,会考虑来自政府的政策变更风险、契约失灵风险等,以及项目合同执行手段及时间的合理性。PPP项目中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与所在国家制度质量是正相关的关系。
政府需要考量PPP机制的设计,优化权力清单,保障相关利益主体和谐共生共赢。[7]致力于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明确政府干预项目的条件、权限、责任等,确保政策与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监管PPP运营状况,设计契约与非契约约束机制。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机制就风险问题达成共识,依靠非契约约束机制弥补契约无法覆盖之处,有效控制异化,为项目合作方定纷止争,寻找利益关系的平衡点。
政府应提高自身能力建设,开展网络治理,实现善治。[8]PPP连接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系统如教育系统、法律系统、环境系统等众多利益主体,形成比市场交易和科层制更加重要的契约关系,不再适合传统的项目行政审批方式。为顺应时代的发展,多方主体应互动参与网络治理过程。政府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治理能力如领导能力、PPP合同设计和管理能力、建设法律制度和规制的能力,实现善治。
[1]Li et al., A Unifi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harmacokinetic Theory: Intravasular and Extracellular Contrast Reagents[J]. 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2005,54(6):1351–1359.
[2]李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视角下的 PPP 项目风险分担研究——基于参与方不同的出价顺序[J].财政研究,2015(10):50-57.
[3]王桂花,彭建宇.制度供给视角下PPP 模式风险分担博弈研究[J].经济问题,2017(10):39-43.
[4]PPP 风险分担合同的地方善治效应:理论构建与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2017(9):79-87.
[5]刘尚希.以共治理念推进PPP 立法[J].经济研究参考,2016(15):3-9.
[6]马恩涛.公私伙伴关系与政府或有债务研究[J].财政研究,2014(12):38-43.
[7]陈婉玲,曹书.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利益协调机制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4):100-112.
[8]温来成,刘洪芳,彭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财政风险监管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5(12):3-8.
Research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via PP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PENG Jin-dao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is the one that combinesgame theory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process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all theparticipantshave bounded rationality. In this paper, a risk sharing game model is built based on the status inequality of PPP project participants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thusa reasonable as well as effective risk sharing mechanism of PPP is established. By doing this, the efficiency of debt funds allocation can be improved,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can beprevented.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optimize the PPP contract and design of regulation system, construct the risk control mechanism via PPP project, encourage social capital inpu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as well as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roject; debt risk; evolutionary game; risk control mechanism
2018-09-29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334)
彭金道(1969- ),男,安徽合肥人,铜陵学院监察审计处研究人员,会计师。
10.13685/j.cnki.abc. 000374
2018-12-06 11:05:0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81206.0845.004.html
F812.5
A
1671-9255(2018)04-0036-04
(责任编辑 胡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