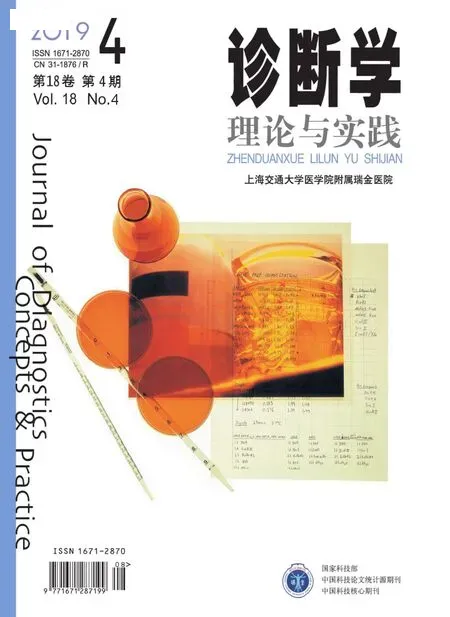肿瘤免疫治疗策略的转变及相关标志物研究现状
罗清琼, 陈福祥,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检验科,上海 200011;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检验系,上海 200025)
机体免疫系统具有识别和清除突变细胞的机制,可通过激活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应答来防止肿瘤进展,但多种因素可使免疫细胞失去对肿瘤细胞的控制,从而导致肿瘤的持续生长。这些因素包括:①肿瘤细胞抗原性和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分子的改变;②肿瘤细胞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前列腺素等炎症介质和外泌体;③肿瘤细胞代谢方式改变,导致对T细胞的免疫抑制;④肿瘤细胞表面抑制性配体的表达;⑤肿瘤细胞及微环境中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免疫抑制因子的分泌;⑥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性细胞的浸润等[1-2]。此外,机体基础免疫功能的状态和肠道菌群的构成也可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3-4]。
作为一种尚未被攻克的疾病,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有外科手术、放疗和化疗。通过手术能够直接切除某些实体肿瘤的原发及转移灶,但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肿瘤细胞的转移和肿瘤的复发。放疗和化疗分别是利用放射线和化学药物来杀灭肿瘤细胞的治疗方法,其疗效取决于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和化疗药物敏感性。尽管放疗和化疗能够直接杀灭对治疗敏感的肿瘤细胞,但在治疗过程中常伴随对机体正常组织细胞的严重损伤,从而影响了整体的疗效。总的来说,以上方法着重于借助“外力”来移除或清除肿瘤细胞,而忽视了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潜在杀伤作用。肿瘤免疫治疗方法的出现为人类解决“肿瘤”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不同于手术、放疗和化疗,肿瘤免疫治疗是基于对肿瘤微环境、肿瘤细胞和免疫系统之间关联性的深刻认识而发展起来的肿瘤治疗方法,其着力于调动和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能力,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疗法[2]。随着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方法的出现,及其给某些肿瘤患者带来的生存受益[5],“免疫正常化”治疗策略迅速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此同时,对相关标志物的探索也备受关注。
肿瘤免疫治疗策略的转变
肿瘤免疫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1年,美国的 “免疫疗法之父”William Coley意外发现术后化脓性链球菌感染可使肉瘤患者的肿瘤消退,从而揭开了肿瘤免疫治疗的序幕[6]。一百多年来,肿瘤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不断发展、交叉渗透,随着人们对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肿瘤免疫逃逸机制和肿瘤微环境的深入认识,肿瘤免疫治疗的策略和思路不断拓展,其焦点也由传统的“免疫增强”疗法逐渐转变为当前热门的“免疫正常化”疗法[7]。
一、“免疫增强”疗法
机体在对肿瘤的清除过程中,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活化和发挥效应作用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①肿瘤抗原的释放和抗原递呈细胞对肿瘤抗原的摄取及处理;②抗原递呈细胞向特异性初始T细胞呈递抗原,使其活化成为效应T细胞;③抗原特异性效应T细胞从淋巴器官向肿瘤组织迁移;④效应T细胞对肿瘤细胞进行识别和杀伤[8]。基于对这一过程的理解,目前已开发了众多类型的肿瘤免疫疗法,通过对这些步骤的常规调节和(或)激发“免疫激活”机制,在程度和(或)质量上提高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这种总体思路旨在激活和提高机体免疫反应的免疫疗法被称为“免疫增强”疗法[7]。
“免疫增强”疗法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使用免疫系统的效应细胞和(或)分子直接攻击肿瘤细胞,即“被动性”免疫疗法,其通常包括以下2种。
1.抗体及其衍生物靶向治疗:典型的例子是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能通过抑制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与其配体结合,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并可通过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及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等,进一步杀伤肿瘤细胞[9]。放射性核素、药物和毒素通过与抗体偶联,可借助抗体靶向到达肿瘤组织,从而提升其肿瘤杀伤能力。如维汀-布仑妥昔单抗(Brentuximab Vedotin)(SGN-35)利用靶向CD30的嵌合抗体偶联强效抗微管药物——甲基澳瑞他汀E(monomethylauristatin E),在治疗复发性霍奇金氏淋巴瘤、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中表现出良好的临床效果[10]。
2.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其是通过从肿瘤患者体内分离免疫活性细胞,在体外进行扩增及修饰,然后回输至患者体内,发挥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或激发机体的免疫杀伤能力。过继的免疫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自然杀伤细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 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 细胞及 T 细胞受体-T细胞等[11-14]。其中,CD19-CAR-T对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表现出较为稳定且有效的治疗效果[15]。
第二类方法是通过调节内源性调控和 (或)免疫激活机制来增强免疫系统的活化,即“主动性”免疫疗法。这类方法包括:①肿瘤疫苗治疗,包括肿瘤细胞疫苗、抗原疫苗、以树突状细胞为基础的疫苗、亚细胞结构疫苗及核酸疫苗等,用以增强抗原递呈细胞向T细胞的递呈,从而诱导特异性T细胞应答。2010年,美国FDA批准了首个用于治疗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树突状细胞疫苗Sipuleucel-T。该疫苗可以降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的死亡风险,使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延长超过4个月[16]。②细胞因子和小分子制剂治疗,其中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肿瘤坏死因子 α、干扰素α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小分子制剂包括Toll样受体和干扰素刺激因子激动剂等[17]。
总体来说,“免疫增强”疗法主要侧重于常规激活免疫系统的应答能力,因此其在增加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能力的同时,也会将机体的整体免疫应答推向超生理水平,从而引发免疫相关副反应(immune related adverse effects,IRAEs),不佳的疗效和伴随的治疗副反应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17]。另外,部分“免疫增强”疗法虽对某一种肿瘤具有一定的客观反应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但缺乏广泛的适应证[15]。且在肿瘤疫苗治疗中,肿瘤疫苗接种虽然能够诱导外周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增加,然而这些细胞却没有表现出客观的抗肿瘤活性,未能有效抑制或清除肿瘤[18],提示特异性抗肿瘤免疫应答的启动环节并非是影响抗肿瘤免疫应答效应的决定因素。
二、“免疫正常化”疗法
某些特定分子的表达可以抑制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导致肿瘤免疫逃逸[1]。不同于肿瘤“免疫增强”疗法提高机体对肿瘤免疫应答能力的方式,“免疫正常化”治疗强调在肿瘤进展过程中抗肿瘤免疫应答存在的特定缺陷或功能障碍的重要性,并据此开发对策以纠正这些缺陷,从而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能力[7]。“正常化”的结果也能导致免疫反应增强,但这种增强不同于“增强”治疗所致的“超生理”水平,理论上其应该在有限的范围内短暂波动,且不会对正常器官或组织造成永久性损伤。这种“免疫正常化”治疗期间的免疫反应“可控”性升高,可能是正常反馈调节性的免疫反应造成的。为更好地说明“正常化”这一概念,可以把免疫反应的过程看作是一根大水管,在正常免疫反应的情况下,水管具有通畅的排放;然而,如果管道被堵塞,水流将受到影响,管道无法正常排水。“免疫增强”疗法可以被理解为增加管道前段的压力,以克服排水不畅的问题,但这种方法会伴有加压过度后管道破裂的风险;而“免疫正常化”疗法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通过识别并移除阻塞以恢复正常水流,且不会危及管壁的策略[7]。
T细胞的激活、发挥效应需要表面共刺激分子如CD28等提供活化信号。相反,表面共抑制分子可抑制T细胞过度活化而维持稳态,这些分子也被称为免疫检测点。肿瘤特异性T细胞或肿瘤细胞表面可高表达共抑制分子(或其配体),造成抗肿瘤免疫应答受挫。基于这一原理,可采用针对共抑制分子(或配体)的单克隆抗体来阻断其信号,使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正常化”。抗免疫检查点分子——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 1 (programmed deathligand1,PD-L1)和细胞毒 T 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4,CTLA-4)治疗是“免疫正常化”疗法中的范例。
1.抗PD-L1/PD-1治疗:免疫抑制分子PD-L1/PD-1在肿瘤微环境的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上过表达,负向调控肿瘤特异性效应T细胞应答,从而产生局部免疫反应缺陷,使肿瘤细胞无法被清除。阻断PD-L1/PD-1通路则可以选择性地修复这一缺陷,从而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能力[5]。有研究对287例经铂类化疗药物治疗后病情进展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其中144例接受阿特朱单抗(atezolizumab,抗 PD-L1)治疗,另外 143 例进行多西紫杉醇化疗。结果显示,阿特朱单抗治疗组患者的总体生存率为12.6个月,显著长于多西紫杉醇化疗组患者的9.7个月;且阿特朱单抗治疗发生严重IRAEs的患者百分比(11%)远小于多西紫杉醇化疗组(39%)[19]。另外,对复发性头颈鳞癌的研究表明,患者对纳武单抗(nivolmab,抗PD-1)治疗的ORR及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均显著高于标准治疗(甲氨蝶呤、多西紫杉醇或西妥昔单抗)组(分别为13.3%比5.8%,19.7%比9.9%),且纳武单抗可明显延长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20]。目前,FDA已经批准抗PD-1用于治疗转移性黑素瘤、肺癌、头颈癌、肾细胞癌、尿路上皮癌、肝癌、胃癌、霍奇金淋巴瘤、梅克尔细胞癌、大B细胞淋巴瘤和宫颈癌等[5]。
2.抗CTLA-4治疗:CTLA-4是T细胞活化后诱导表达的表面受体,其与B7分子的结合后向T细胞传递抑制信号,从而抑制T细胞的活化[5]。研究显示,前期未经任何治疗的转移性黑素瘤患者,在接受 10 mg/kg伊匹单抗(ipilimumab,抗 CTLA-4)治疗后,其4年生存率可达37.7%~49.5%[21];对于前期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的晚期黑素瘤患者,伊匹单抗再治疗可使55%的患者受益,并使患者的2年存活率提高到42%[22]。替西利姆单抗(tremelimumab,抗CTLA-4)治疗可使52%对化疗耐受的恶性间皮瘤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且持续10.9个月中发生严重IRAEs的概率仅7%[23]。另外,替西利姆单抗注射联合射频消融治疗能使26.3%的晚期肝癌患者病情得到缓解,6个月和12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提高到57.1%和33.1%,总体生存期的均值延长至12.3个月[24]。此外,多项研究显示,联合抗PDL1/PD-1和抗CTLA-4治疗可使肿瘤患者的总体生存率进一步提高[25-26]。
不断涌现的临床结果表明,这种“免疫正常化”策略可以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诱导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总体约30%的ORR),且严重的IRAEs发生率较低(7%~12%)[5]。 相较于“免疫增强”疗法,“免疫正常化”疗法中较佳的反应/毒性比给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引发了对肿瘤免疫治疗的新思考。
除PD-1/PD-L1和CTLA-4外,基于其他免疫检查点如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含粘蛋白结构域的蛋白3、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唾液酸结合性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15等的肿瘤免疫疗法也在不断深入探索中[27-29]。
相关标志物研究
“免疫正常化”疗法目前主要是以抗PD-1/PDL1治疗为主。抗PD-1/PD-L1治疗为晚期黑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的生存获益,使得人们对免疫治疗的关注度和期望值愈来愈高。但实际上,接受抗PD-1/PD-L1治疗患者的总体ORR仍较低,且伴随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5]。因此,临床上迫切需要寻找相关的标志物,来筛选对该类免疫治疗有效、低毒的人群,以预测疗效、预后及不良反应,从而更好地为患者带来长期、安全的生存获益。根据不同标本来源,抗PD-1/PD-L1治疗相关标志物可分类如下。
一、肿瘤组织标本
1.PD-L1:通过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表面PD-L1的表达情况,并以此作为抗PD-1/PD-L1治疗疗效预测的潜在标志物,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在一项针对晚期黑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及结肠直肠癌患者使用纳武单抗的临床研究中,PD-L1表达阳性患者对治疗的总体响应率要高于PD-L1表达阴性的患者[30-31]。然而也有研究显示,低表达或不表达PD-L1的患者也能够从抗PD-L1治疗中获益[32-33]。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PD-L1的表达时,所使用的检测方法和抗体缺乏统一标准,PD-L1评估阈值和评分标准也不一。标准的缺失使得从多个单独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得到一个统一的共识,变得异常艰难。另外,肿瘤的异质性、细胞类型、原发部位与转移灶、干预治疗影响等都影响着PD-L1的检测结果[34-36]。因此,需要不断地优化和细化使用PD-L1表达状态作为免疫疗法生物标志物的标准。
2.肿瘤突变负荷和肿瘤新生抗原:发生在肿瘤细胞中的突变可导致肿瘤新生抗原的产生,这些新生抗原被免疫系统识别为“非己”,从而增强T细胞对肿瘤的反应性,并促进ICIs的疗效。另外,DNA修复机制的缺陷可导致肿瘤中的高突变负荷,从而增加患者对ICIs治疗的反应[37-38]。研究显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肿瘤组织中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和肿瘤新生抗原表达越高,其接受抗PD-1治疗的疗效就越好,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更长[39]。另外,在一项予局部晚期转移性尿道上皮细胞癌患者使用阿特朱单抗治疗的临床试验中,治疗后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患者的TMB要高于疾病稳定或进展的患者[40]。这些研究为使用TMB作为生物标志物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TMB作为标志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也有一些研究报道了TMB高而ICIs治疗没有反应的患者,以及对治疗有良好反应但TMB非常低的患者[41]。
3.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instability,MSI):DNA 复制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概率在1/10 000~1/100 000,并且这些错误由细胞内的DNA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MMR)机制进行纠正。因此,MMR基因的突变会导致大量突变,并影响微卫星DNA序列的稳定性。在一项针对接受抗PD-1治疗的晚期癌症患者的Ⅱ期临床研究中发现,MMR缺陷肿瘤患者的总体反应率及无进展生存期均高于MMR正常的患者[42]。MSI的结肠直肠癌患者的ORR接近60%,而微卫星稳定的患者均对治疗无反应;同时,在非结肠直肠癌的其他MSI肿瘤患者中也存在与MSI结直肠癌患者相近的治疗反应率[42-43]。这些结果表明,MMR和MSI可用于预测泛肿瘤患者接受抗PD-1/L1治疗的疗效。
4.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肿瘤组织中TILs数量的增加及空间分布情况与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相关。研究显示,与对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抗PD-1)治疗无响应的黑素瘤患者相比,治疗响应患者治疗前的肿瘤组织边缘及内部可检测到大量CD8+PD-1+或PD-L1+的细胞。同时,通过对患者治疗过程中的连续取样分析发现,患者肿瘤组织中浸润的CD8+细胞数量增加越多,患者的疗效越显著[44]。另一项研究通过对转移性黑素瘤患者治疗前的组织样本进行流式细胞术分析发现,肿瘤中浸润的PD-1hi/CTLAhi-CD8+T细胞比例增加与其对派姆单抗或纳武单抗治疗的响应情况高度相关。进一步对PD-1hi/CTLAhi-CTLs的功能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细胞可以表达干扰素γ,但不表达肿瘤坏死因子α和IL-2[45]。此外,根据肿瘤微环境中PD-L1与TILs的浸润情况,微环境可分为不同的模式,而具备不同模式肿瘤微环境的患者对ICIs的反应性也不同。微环境中PD-L1高表达及TILs浸润数量较多的肿瘤患者对治疗的响应率较佳[7]。
二、外周血液标本
1.免疫细胞:外周血免疫细胞的比例和表型分析可反映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性,并可预测不良反应。一项对Ⅳ期黑素瘤患者的研究显示,对抗PD-1治疗响应的患者,其外周血中CD4+T、CD8+T和γδT细胞比例无论是在基线水平,还是在治疗后12周,均显著低于对抗PD-1治疗不响应的患者(相应的,治疗响应者肿瘤组织中CD4+T和CD8+T细胞浸润增加);而CD19-HLA-DR+髓系细胞的比例无论是在基线水平,还是在治疗后12周,均显著高于对治疗不响应的患者。细胞表型分析显示,对抗PD-1治疗响应的患者其CD4+T细胞表面CTLA-4、HLA-DR、CD69和BTLA的表达水平在治疗前后均高于治疗不响应的患者;类似的,对治疗响应的患者其外周血 CD8+T表面 CD45RO、CTLA-4、CD62L、CD69、CD11a及CCR4的表达均明显较高。另外,抗PD-1治疗响应的患者治疗前外周血中表达IL-4、颗粒酶-B、干扰素(或 GM-CSF的CD4+T细胞比例高于治疗不响应者,表达CTLA-4、颗粒酶-B或IL-13的CD8+T细胞的比例也高于治疗不响应者。此外,患者外周血CD14+CD16-CD33+HLA-DRhi单核细胞的比例变化可作为抗PD-1治疗反应性的预测指标,治疗后其比例的升高与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期呈正相关[46]。研究发现,治疗前Ⅳ期黑素瘤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5的患者,在接受了纳武单抗治疗后,其总体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期均明显差于比值<5的患者[47],提示免疫细胞亚群的比值也可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此外,ICIs治疗后患者外周血中CD21low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增加,可提示严重IRAEs的发生[48]。这些结果表明,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各亚群的占比、比值和表型等可作为判断ICIs治疗效果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但尚需更多的数据验证。
2.细胞因子和可溶性蛋白:迄今为止,临床尚无单一、有效的生物标志物来区分哪些患者在接受ICIs治疗后将出现IRAEs,或者在IRAEs临床症状出现前给予警示。最近有研究发现,抗PD-1和抗CTLA-4联合治疗的黑素瘤患者血清中11种细胞因子(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不规则趋化因子、成纤维生长因子-2、干扰 素 α2、IL-1α、IL-1β、IL-1RA、IL-2、IL-12p70、IL-13)的基线水平及早期治疗后的表达升高均与IRAEs的发生有关[49]。这些细胞因子具有很强的促炎症作用,在免疫细胞的招募、增殖、分化和效应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这11种细胞因子组合的细胞因子毒性评分能够预测严重IRAEs的发生[49]。在抗PD-1治疗反应性方面,患者血清中IL-2水平越高,提示其对治疗的反应性越好[46]。某些可溶性蛋白也可反映ICIs治疗的效果。一项对接受伊匹单抗治疗的肿瘤患者的研究显示,患者的血清乳酸脱氢酶和S100B如果在基线、治疗后3周及6周均维持低水平,则提示其对治疗的反应性和预后均较好;另外,患者的基线可溶性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链相关蛋白A水平越高,则其IRAEs发生率越低[50]。此外,肿瘤患者血清可溶性PD-L1水平的升高与其预后呈负相关[51]。另有研究显示,肿瘤细胞会分泌出表面带PD-L1蛋白的外泌体,在抗PD-1治疗高获益人群中,其治疗前外泌体PD-L1表达水平低,而治疗3~6周后表达急剧升高,提示追踪抗PD-1治疗前后患者血清中外泌体PD-L1表达的变化能够区分获益与否[52]。可见,某些细胞因子和蛋白也可作为ICIs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3.循环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和微小RNA:ctDNA作为液体活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为肿瘤患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有力帮助。研究发现,伊匹单抗、纳武单抗或派姆单抗治疗前ctDNA基线水平低 (<10拷贝/mL)的患者,其治疗反应性是高基线水平患者的5倍,且这些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也长于高基线水平患者(风险比=3.7,95%置信区间 1.2~12.5,P=0.034)[53]。在高ctDNA基线水平患者中,治疗后ctDNA水平的降低程度与其治疗效果呈正相关。一项针对抗PD-1治疗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治疗响应患者的KRAS和Q61R突变ctDNA急剧降低,而治疗不响应患者的PI3K3CA和E542K突变ctDNA随肿瘤进展持续升高[54]。此外,微小RNA表达在ICIs治疗评价中也受到关注。基于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浆中24种免疫相关微小RNA的检测分析显示,微小RNA特征分类风险越高,患者抗PD-L1治疗的ORR、总体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期越低[55]。目前尚未见报道患者血清中其他非编码RNA,如长链非编码RNA和环状RNA等作为ICIs治疗评估的标志物。
三、其他标本
此外,肠道微生物组的构成影响了机体的免疫功能,对患者粪便菌群的分析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患者对ICIs治疗的反应性[56]。对于唾液、泪液或其他标本中特定指标的检测也可能为ICIs的治疗评估提供帮助,但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小 结
随着对免疫系统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作用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型肿瘤免疫治疗策略应运而生,给患者带来希望。尽管“免疫正常化”疗法在某些肿瘤中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但仍面临总体有效人群偏低及副反应等问题,因此需要借助生物标志物以更精准地筛选治疗有效人群,或通过综合评估进行个性化诊疗。目前研究报道的多个相关生物标志物,都只是从某个层面进行的表征,无法准确提示用药响应程度。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免疫治疗的效果,成为未来解决临床问题的一个趋势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