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文学的几点断想
⊙ 文 / 晓 航
这几年有关城市文学的话题逐渐升温,其实这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在我个人的印象中,当代城市文学涵盖的内容非常驳杂,有“进城文学”“打工文学”,也有“市民文学”(包括世俗摹写、城市民俗和部分底层写作)。如此分类都是纯个人化的,并非专业界定,不必太当真。
我的小说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城市文学的一种样式,早些年被人称为“智性写作”。确实,它们跟以上列举的小说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同样属于城市文学范畴。本篇文章我想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谈一谈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由于个人视野与能力的原因,只能勉强以小见大,难免会有种种错漏,希望读者诸君指教。
一、我和城市的关系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没有任何农村经历,城市是我唯一的具有可靠经验的地方。如同很多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我的青春时光都“浪费”在读书考试上,我念过物理化学和国际贸易两个学科,毕业后,从事过很多职业,搞过科研,当过电台主持人,后来一直做国际贸易,也接触过企业管理。
无疑,我和城市的关系是紧密的,我生活在这里,所有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都在这里,我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看着它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也看着它越来越脏,越来越庞杂。北京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存在之一,我爱它、怨它,却永远无法离开它。我没有什么归隐情结,从未想去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开始新的生活,那种诱人的清静和背后贫苦的日子我根本受不了。——当然,这是我想象的一种情况。
事实上,我只喜欢北京,喜欢它的闹腾,喜欢它的生生不息。我也不想出国,虽然我接受的是西化教育,一是我学不好外语,二是我吃不惯西餐。我只想在这个城市终老,即使它有雾霾,有不健康食品,水很硬很难喝,但是我还会长久地待下去,直到和我的爱人垂垂老去。
二、我和文学的关系
我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业余写作,到二〇一七年已经超过二十年。时间算起来长得可怕,但是度过时又快得不知不觉。我为什么写作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困惑,无法直面现实的无奈、虚伪与打击,因此想自我拯救。
记得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常常问自己,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每次产生几乎都是在夜晚,当所有的喧嚣都散去,我直视自己的内心时,这往往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问题。我问过很多人,答案因人而异。我向宗教、哲学求援,它们时而滔滔不绝,时而沉默不语。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的回答能够让我信服。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意义的寻找以及对于被拯救的渴望,我从二十年前拿起笔,开始了孤独的文学之旅。
三、当代城市文学的样式
如上所述,我个人把当代城市文学分为这么几类,“进城文学”“打工文学”“市民文学”,城市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具有很好的投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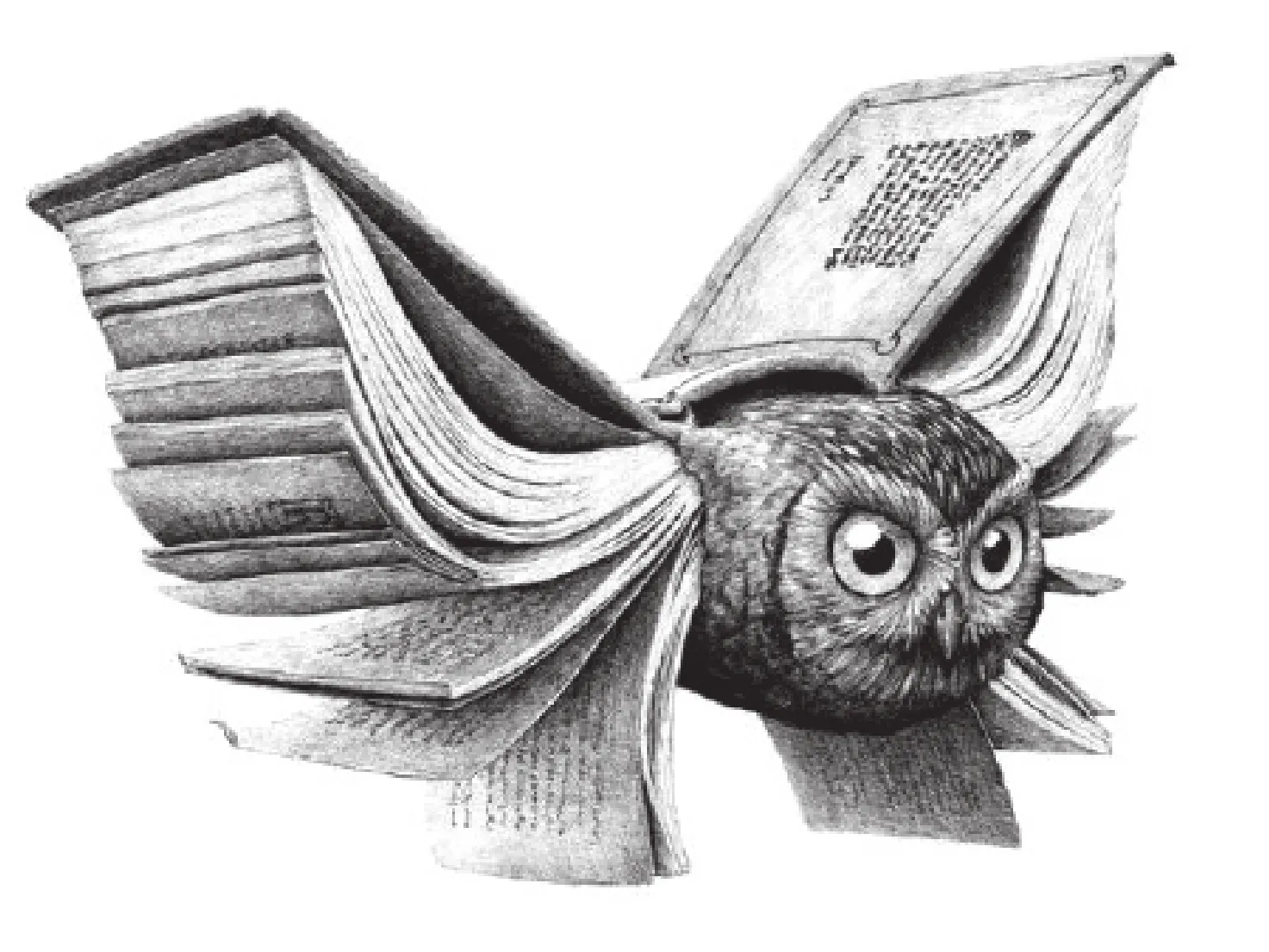
⊙ 书本· 猫头鹰
建国之初,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到了二〇一六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腾飞,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与城市并存,向大规模城市化大幅度迈进。这就使大量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一句话,他们进城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当人们离开土地,到达城市之后,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物质形态以及精神冲击,都会使他们产生一定的心理不适,因此人们势必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心理调适。这一过程,据我观察,在当代城市文学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
当代中国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这些“进城”人群的,他们本身具有广泛的乡村以及小城镇生活经历;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进城之后遇到的种种困难,各种改变命运的可贵的努力,作品充分表达了那种自强不息的人类精神以及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而当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他们的笔触开始转向城市中的世俗生活时,这样,“市民文学”就会随之大量产生。
“进城文学”“打工文学”“市民文学”,这三种类型的城市文学并不具有简单的时间顺序,或者说它们三者不是顺序向后推演的,而是复杂叠加的,有时A在前,有时B在前,有时AB又混搭在一起。我记得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阵子“新写实”流派很火,在我看来,那就是一段“市民文学”的辉煌,它反而产生在进城、打工、底层之类的写作前面。
虽然有这么多类型的城市文学风起云涌,但是很可惜,据我观察,真正具有长期的、高质量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经验的作家并不太多;即使有,他们大多也沉浸在“市民文学”的通俗中难以自拔,有的甚至还自说自话地进行“底层想象”。因此,在城市文学创作中那些穿过城市表象能够深入城市内心的作品并不多。
四、我的城市文学创作实践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的小说注定是关于城市的。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写作,直到二〇〇二至二〇〇七年,我的作品才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的小说逐渐受到了重视,一些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创作方法提出了一个“智性写作”的概念。之后,到二〇一二年,在这个阶段我尝试着使作品向两头靠近,一个方向是现实,我打算更深入地理解和表达现实;另一个则是向思维的深处,探索一些更抽象的哲学与宗教问题。再后来,我从二〇一二年起开始长篇创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历程,我又成了文学新人。
对于“智性写作”这个概念,我自己的阐释如下:我以为,“智性写作”就是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以不断扩展的想象力,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个超越现实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关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于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
这些年由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扩展,使我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看待世界的框架,即理性的批判主义框架;同时由于对哲学与宗教的涉猎,使我深深了解了上帝或者说佛陀植根于人类心中的那些基本善念,以及人们永远无法解决的种种困境。科学、哲学、宗教这些不同框架的相互参研与对抗都让我受益匪浅,给我提供了很多不可多得的思想体验。
因此,正是依据上述框架的建立,并且借用各种学科的工具,我逐渐完善了自己的“智性写作”模式。我认为小说需要本质,其目标是崇高的。文学最终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一个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重新观察事实,重新建构世界,或者说给世界一个新的解释;就好比音乐、绘画、政治、科学,都有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一样,文学也必须得有它独特的方式。基于这样的观念,我写每一篇小说都打算努力摆脱对世界的庸俗化阐释,这种努力逐渐发展下来,就形成了我自己独特的“智性写作”风格。
五、我不喜欢什么样的写作
从我个人的偏好来说,我很愿意把写作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愿意在思维的探索中得到具有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的东西,我认为这才是小说的乐趣所在。因此我特别不爱看当下的某些具有“庸俗”气质的小说。
第一种是“伪底层”写作。其实作者的现实生活经验相当枯竭,每天除了开会,就是书房或者办公室,他们天天想象底层的现实生活,然后加上点道听途说就开始表达,一边表达一边觉得自己悲天悯人,觉得自己有大爱,这种创作方式在我看来相当可笑。我自己由于机缘巧合,干过不少行业,见多识广不敢说,但是比起一般作家,对于现实的接触要广泛得多。从我的社会经验看,他们写的底层完全不是真实的底层,他们不太了解现实是怎么样的。我曾接触过贫困县投资企业的管理者和大型企业的维稳工作,那些经历都让我刻骨铭心,使我有机会看到当代各阶层真实的生活状态。可是安于书斋、会议中生活的作家们能写出什么样的底层呢?他们写出来的既不是真实的事实,也不是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很多人只是功利主义使然,为了获得利益跟风而已。
第二种,我不喜欢那种无聊的、世俗化的“市民小说”。这类小说现在期刊上比比皆是,一翻开全是鸡毛蒜皮,一点小事无限扩大化,从书房到客厅接个电话能写好几千字,一直在那里絮叨。开头是什么样,结尾还是什么样,完全没故事没结构,想象力和思想能力匮乏,只有无意义的呓语,这种小说不写也罢,它几乎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种是有些恶俗的农村题材,写得那个脏乱差,那个假丑恶,那个血腥暴力,还动辄就“乱搞”。我觉得,文学根本上是审美的而不是审丑的,看到人类的恶并不独特也没有多了不起,谁也不是盲人谁也不傻,真正有价值的是在我们的作品中如何让人类最终的善战胜人类广阔的恶,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希望。作为作家,我们除了要揭示人类的恶,更重要的是给人类以希望!
第四种是那种新闻化写作,就是把公共新闻事件转化为个人小说中的叙述元素,处处都是新闻点。这么干的作家很多,横跨老中青三代。问题是,写小说跟写新闻能等同起来吗?那要记者干吗?要新闻干吗?人家网络上的种种深度分析、评说再加上后续报道,比你想象到的、揭示的要深刻得多。拿新闻写小说,这是写作能力衰退的表现,这是现实生活匮乏的表现。
文学圈的这些怪现象长期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觉得这些怪现象的产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有作家生活面狭窄、信息匮乏的原因,有作家受功利主义驱使的原因,也有作家世界观单一而原始,方法论笨拙而故步自封的原因。正是因为对上述写作的不敢苟同,我在写作时才会保持着特别的警惕,对庸常经验毫不犹豫地拒斥,努力求新求变。
六、未来,我的城市文学创作方向
与“进城文学”“打工文学”“市民文学”有所不同,未来,我自己的城市文学创作道路应该是这样;它一定会跟上述庸常写作所对立,超越简单朴素的生存经验范畴,要尽量书写个体在巨型城市中的存在与文化经验,展现出个体身上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冲突。
城市文学应该具有现代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具有开放、多元、动态、复杂的视野。在城市文学中,个体不仅关注自身,也关注社会,并把哲学批判当作最终的批判。城市文学应该从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看到人类的基本欲望、基本窘境,体悟人类的基本情感。在城市文学中,对于终极关怀的追求是自始至终的,写作者要力求从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中,上升到对神性的思考。
一个好的写作者需要经久不息的理想主义精神,持之以恒的思考能力,以及自我牺牲的勇气。经过多年的写作,我虽然依然无法摆脱自身的怯懦、卑微、功利,但是我已经从只关注自我的生存状况变成一个关注群体、大众、民族的思考者。我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希望我们的民族获得更高的腾飞。这些年没有改变的是,我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思考是我终生的痛苦的任务,也是我面对客观世界时唯一有力的武器。
七、城市化进程将推动城市文学高歌猛进
从二〇一二年起,我开始长篇创作,题材依然是关于城市的,五年之内写了两个长篇,一个叫作《被声音打扰的时光》,另一个叫作《游戏是不能忘记的》。我认为,未来中国一百年以内的道路都将是城市化的道路,城市文学会大行其道。历史会把它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城市的深处,我们这些忠实于城市题材的写作者将会接受历史的考验,会努力表达出城市的开放性、多元性、矛盾性,还有它极为深刻的“变形记”。
作为一个骨子里的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人类的孤独与哀伤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它归因于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理智的有限性。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我们对于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无所知,这些本质上的绝望,这些人类最终的窘境深深困扰着我,因此这是我永恒的城市文学的创作动力。我力图在我的小说中,在我“建造”的城市中揭示这些困境,展现出人类在与这些困境进行斗争时所激发的伟大情感与基本理念,比如爱、怜悯、宽恕、正义、自由,等等。
城市化进程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向前,城市文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蓬勃发展。作为城市的表达者之一,我会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讴歌它批判它,为之痛苦为之欢乐,为之汗颜也为之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