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建成环境保护
—— 一段在实践中往复的历史
Written by Seán O'Reilly
江孟繁 陈曦 译 Translated by Jiang Mengfan & Chen Xi
潘一婷 校 Proofread by Pan Yiting
引言
英国的“Built and Historic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我们称之为“历史建成环境保护”,它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由两项相互影响的指导性原则塑造而成。第一项原则侧重于建设目前已经被认可、但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保护专业人员”培养学科。由于保护实践的演变与保护史的形成关系密切,实践中的变化是塑造这一历史的基石。
第二项原则立足当下,通过回溯探究保护史,印证了英国的保护有一段特别复杂的过去。这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在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至今这仍然是保护演变的一个关键动因,但同时也让人容易忽略那些真正的发展脉络。通过追溯历史的演变——从今天的从业者和政策,到塑造他们的人、事件和动机——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发现最重要的时刻和问题。这彰显了一个具有反复性的历史,因为当下和趋势同时与过去和未来密不可分。
我们还会发现英国各地区的保护情况也在随之变化。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作为英国的分权政府或“构成国”,往往在这段历史上留下标记(图1、图2)。这一标记尤其重要,因为将遗产管理和控制权力下放给最具活力的地方权力机构——无论是分权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既是英国保护管理的一项关键原则,也是贯穿历史、启发城市规划进步的法律遗产。
一、英国目前的保护实践:21世纪的“跨学科”专业

图1:约克历史城市鸟瞰

图2:考文垂的登录历史建筑
目前公认的英国“保护专业人员”(Conservation Professional),是一些熟练的、有能力和道德约束的从业者。他们帮助确保传统历史建筑和场所的未来安全。由于保护实践者的关注重点是一个历史场所的未来,那么该实践者的定位就有可能延伸到形成该历史建筑和场所的所有学科,包括对它的理解、维护和变化的管理。这些保护技能跨越了不同的传统实践或学科领域:
·历史,等同于理解和评估;
·规划,管理和维护;
·建筑设计,对形式和设计进行适当的干预。[1]
作为专家型的“保护专业人员”必须掌握跨越不同历史学科的技能,因此他们被定义为“跨学科”从业人员,而他们的实践则被定义为“跨学科”的活动。事实上,培养“保护专业人员”这一学科已被正式定义为“年轻、独特和具有环境意识的教育活动,具有独特的地位,参照国家,国际保护标准和模式建立的‘跨学科’专业。”[2]
在英国,研究国内、国际政策和建议,以及包括保护实践和可持续发展在内的示范实践标准,整合各种成功的保护实践(以及确保历史建筑和场所的未来)的重要性已得到了认可。
从根本上来说,保护实践是一项“跨学科的专业活动”,其基础是保护界全球公认的保护技能指导准则——1993年ICOMOS发布的《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保护教育和培训指南》,又称为《ICOMOS指南》。[3]该指南全面地描述了保护实践本质上的“跨学科”特征:
“有必要对我们的遗产制定整体的方法……(因为)许多专业的工艺、技能都被包括在这项跨学科活动中。”[4]
《ICOMOS指南》是由英国著名的保护建筑师伯纳德·费尔登爵士(Sir Bernard Feilden)在1990年代初起草的,它的正文和附属指南中没有将“跨学科”的保护实践充分阐述为一门独立的、个人实践的学科[5],相反它把保护描绘成“多学科团队”合作的成果。然而,它确实描述了这一职业的基本原则,概述了可用于区分这门学科的三项原则术语: 技术、能力和道德:[6]
·它确定了承担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所需的技能、知识和理解;[7]
·它规定了在实践中达到胜任水平的标准,从而对工程能够进行评估和质量保证;[8]
·它认识到需要一个总体全面的道德规范和纪律框架,尤其侧重于被称为“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的保护成果。[9]
在英国独一无二的是,这三项现代专业的实践原则已被历史建筑保护学会(IHBC)纳入了这个跨学科专业团体,以及“保护专业人员”的“跨学科专业”发展和管理中。由此,IHBC将贯穿英国保护史的线索联系在了一起。
英国保护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及其技术规范、能力鉴定和道德规范,意味着IHBC所运作的“跨学科专业”面临着独特而艰巨的挑战,但同时也是这段历史合乎逻辑的延伸。
二、综合保护:当今英国的跨学科实践——具有更广阔图景的现代产业
跨学科专业的概念完全符合21世纪的英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认识,即发展综合技能,以更好地管理复杂的、新旧场所的维护和改变。对于未来的保护而言,必须认识到在个人领域内,这种新型的、交叉跨学科技能是必要的,它能融于更广泛的建设和发展政策、实践过程,而不仅仅局限在相对狭窄的保护实践领域。
约翰 · 伊根爵士(Sir John Egan)的《可持续社区的发展能力》(Skill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10]是英国第一份、关于确保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开创性公开声明。伊根强调了他提出的“通用技能”的必要性。这是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专业人员——“那些几乎将全部专业时间用于规划、提供和维护可持续社区的活动的人” 的交叉能力。[11]他详细描述了一个拥有这种通用、跨学科能力的从业者是如何跨越历史上传统学科的界限,并胜任工作的。
伊根还设想了“这些跨学科的职业所需要的新管理机制”,[12]并强调了跨部门工作中认证的重要性,呼吁专业机构建立“认证……跨学科工作”的制度。[13]伊根没有建议授权任何现有系统进行这种认证,也没有就如何评估、操作或监管这一系统提供任何答案。事实上,他也没有意识到,保护工作得益于其长期的综合实践,已经为现代“跨学科”专业提供了一个典范。[14]
然而,伊根的确将保护专业人员置于“可持续社区的核心职业”中,即使他们被归类为“环境官员”而不是建成环境专业人员。不过关键的是,在这里他们被明确认定为具有跨学科能力及符合标准的历史角色,即地方政府的“保护官员”(Conservation Officers)——这是英国保护史上最关键的角色,本文将在其后进一步讨论。
同样重要的是对跨学科能力的更广泛认识,在与伊根的声明同时代的——21世纪的建设和发展中,跨学科能力和标准的原则从《ICOMOS指南》被介绍到了主流语境中。
2013年,另一家全球公认的、从根本上跨领域的英国机构——英国标准学会(BSI),用自己的权威和品牌为定义跨学科能力添砖加瓦。与伊根不同的是,这种支持是针对保护的,并直接受到《ICOMOS指南》的启发。它采用了修订的、但基本是全新的英国标准(BS)的形式,制定了《传统建筑保护指南》(BS 7913)。[15]
通过《传统建筑保护指南》,BSI强调:成功的保护成果需要跨学科实践来塑造,也应采用“多学科方法来评估所有相关价值”。[16]在第5节“历史环境管理”中,它概括了可由有能力的从业人员监督的、广泛的跨学科范围。在此范围内,BS 7913阐述了主流(BSI出版物的主要用户群之一)发展实践,这一发展过程完全符合费尔登和ICOMOS编写的“权威”历史文件。
无论伊根还是BSI都还没有充分显示现代保护专业人员所承担的跨学科角色。因此,在2017年,IHBC与有代表性的社区和规划合作伙伴一道,[17]就客户和权益相关者应从遗产保护工作者那里得到什么,提供了独特的、易理解的公众指导,即《保护专业实践原则》(简称“实践原则”)[18](图3)。新文件采用了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术语——“遗产专业人员”(Heritage Professional),来作为与“保护专业人员”对等的非技术人员。但它的描述总结了保护实践的跨学科属性,这是《ICOMOS指南》、伊根和BS 7913都强调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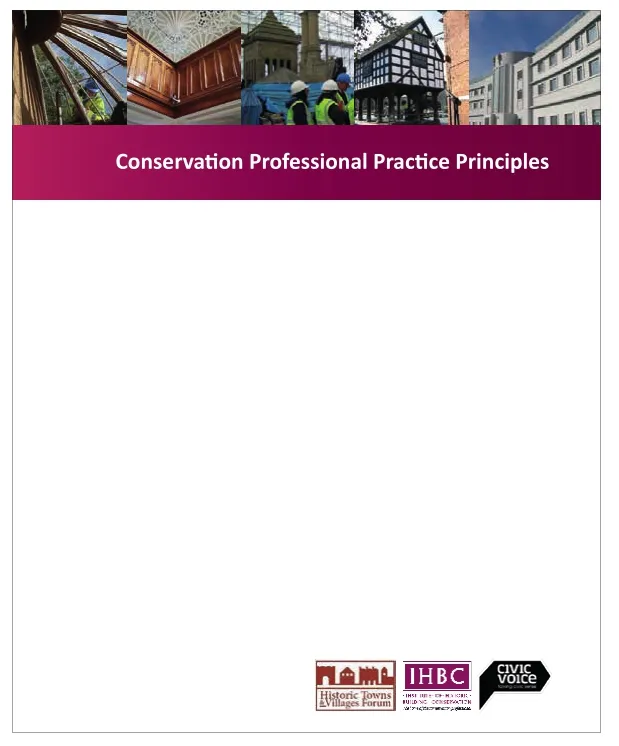
图3:IHBC 学会保护专业实践原则出版物封面
《实践原则》重申,跨学科遗产保护是现代可持续规划和地方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如我们所见,这是从一个多世纪保护史得出的必然结论:
“保护实践包括管理维护场所和建筑物,以及规划它们的未来。遗产具有与过去相关的文化价值,但它也是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支撑其可持续未来的根本资源。因此,遗产是现今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价值的资源。”[19]
它接着阐述了对从业者的要求:
“遗产专业人士面临的挑战是,保存文化价值的同时,允许地方和建筑在适当或必要的地方进行调整,使其适合现有功能,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20]
2017年的《实践原则》成功地总结了不同的思路,这些思路塑造了现代保护实践的根本整体观念,它不仅形成了地方遗产的概念、也创立了塑造这些场所的学科遗产:
“保护专业实践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不仅需要知识的深度,而且由于决策范围广泛,因此也需要知识的广度。良好的保护实践不是孤立地看待遗产和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视为规划、地方发展、帮助场所和建筑物适应现代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21]
《实践原则》总结了目前的研究现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在保护中看到的)综合方法是专业实践的核心。”[22]
三、 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保护立法与服务: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
《实践原则》所描述的保护概念:“综合的方法是专家工作、专业实践的核心”,也一直是现代英国“保护专业人员”的中心理念。这一演变的运作中心和(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熔炉,是当地政府在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保护措施。这反而又是伴随着1990年代现代保护立法所影响的遗产规划实践而发展起来的 ——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990年颁布,苏格兰在1997年颁布的法律。[23]
自首次整合以来,整个遗产部门,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方面,近30年发生了彻底的变革。整个英国,遗产立法、管理和实践的广泛原则能够基本保持一致,其根源在于1990年法案合并后的立法中演变出来的相同保护原则。
在这30年中,英国各地区的立法机构各不相同,随着权力下放和授给在实践中拓展的新维度,这种变化也越来越明显。继1990年涵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案确立之后,苏格兰因其更加独立的立法,于1997年制定了自己的补充法案。而出于政治原因,北爱尔兰直到最近才开始通过地方政府发展自己的服务,但仍然依赖于1990年法案中的做法来具体操作。
1990年法案的标题表明了它的地位,它是一项“巩固某些法规的法案,涉及对建筑物和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价值的地区等的特殊控制”。因此,它巩固了现有的保护立法,依赖并同时反映了立法机构、进程和原则,这三者已经因为早期立法的影响而改变,稍后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管理和咨询的主要责任落在地方政府的保护顾问和管理者身上。因此,现代立法重新肯定了地方政府“保护官员”的定位,即保护专业人员的前身。
为了应对二战期间,尤其在1944~1947年发生在英国的轰炸造成的破坏,现代立法出于监管控制和许可随后的发展目的而设立,遗产受到自身破损而非社会发展的威胁。这种广泛的破坏产生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即确定哪些建筑应该且可以被保存下来,因为它们具有文化价值;哪些建筑可以失去和替换。这就需要根据受损结构被挽救的可能性,对其文化“价值”进行评估,即对特殊建筑和场所进行“分类”。
虽然这种遗产“分类”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但围绕这些遗产问题进行规划和开发的管理过程主要属于地方政府的规划职责。最后,由于在发展过程中,结构性保留问题带来了对遗产保护的担忧,管理过程变得十分本地化和复杂,需要当地合适、熟练和知情的专家提供保护建议。在地方政府中,这一咨询角色通常属于规划部门,通常由内部保护专家、地方政府的“保护官员”承担。
保护官员的作用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者: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虽然他们主要在规划部门的范围内工作,但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优先事项是文化。1990年立法的条款明确了他们的作用,因为他们被要求就下列事项提供咨询意见:
“希望保护建筑物或它的环境,或它所拥有的、任何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价值的特征。”[24]
因此,任何保护服务都必须强调其主要责任:以文化为优先,同时在由发展主导的、规划优先的职权监督下运行。[25]在文化保护和规划发展的对立驱动力下,一门跨越传统服务界限的学科——“跨学科专业”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保护官员宽泛的能力范围也在主要立法中得到正式和具体的论述。
1990年的立法帮助巩固了地方政府机构的跨学科实践,但直到1994年《ICOMOS指南》的出版之后,对这些能力更精确的定义才被公布,以强化这些服务角色,甚至提高能力。英格兰和威尔士中央政府发表了 《规划政策引导15:规划和历史环境》( PPG 15 ),实际承认了实地保护工作者经常从事的一系列行动和起到的作用。[26]
通常被称为“PPG 15 ”的文件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开发管理是“第一部分”的主题,它反映了遗产立法的规划背景,涉及“与规划系统最直接互动的保护政策方面”。相比之下,第二部分涵盖了“与规划系统不太直接相关的保护政策方面”,实际为更具体的文化方面。[27]这一分法进一步注明了,规划还是文化优先在当地保护服务中的特殊结构划分,以及它们不同的部门、行政的职责。
“PPG 15”的细节强调了地方政府遗产管理的根本分歧。明确了从业者作为“遗产”的守护者,有责任平衡和整合遗产实践在文化上的优先权,正如围绕着非物质文化优先权建立的传统“遗产”概念。他们还强调了这一职责的迫切性,例如规划、土地使用、地方政府财政等决策往往不仅会挑战遗产果实,而且经常会与之发生冲突。[28]
受立法条款的影响,保护角色的“二元对立”在中央政府的监督疏忽下对比更加鲜明。文化和遗产优先事项通常由国家遗产主导机构——最常见的是英国的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苏格兰的苏格兰文物局和威尔士的威尔士议会历史环境部。然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里又有另外的规划部门专门与地方政府对接来监督优先发展事项。[29]
由于监督疏忽,中央政府部门始终未能理解实地保护实践中固有的、相互冲突的责任。的确,在整个英国遗产保护史,尤其是保护官员的角色的演变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基层当地政府人员每天都在持续地管理、解决着中央政府没有意识到的不同压力。
保护官员的能力跨越了监管和政策的驱动,从最细小的遗产价值——如表面的纹理或最脆弱的细节,到更典型直接的发展重点——如房地产投资的商业回报,最终导致了多种跨学科技能的系列整合,这与《ICOMOS指南》和其后、最新标准的要求都对应起来。
这些“保护官员”逐渐演变为一代又一代的“保护专业人员”,最显著的标志是他们最初的关系团体——保护官员协会(ACO),演变成后来的正式专业机构——IHBC。[30]这种转变依赖于一种新的技能规范——一种可以直接从那些“保护官员”的操作中获得的规范——首次形成对个人的跨学科保护技能,即IHBC所说的“能力”和“能力范围”的全面界定。所有这些都被概括在IHBC的上述“保护周期”模型中,本文将在其后进一步讨论。[31]
四、20世纪中叶专业标准的空缺:焦点下的保护能力
作为监管者,专注于具体案例审查的地方当局专家可以依靠他们一手和一流的保护实践经验,对保护建成历史环境的实践中宽泛而多样的技术做一个概括。然而,他们不是教育家,即便他们能很轻易地发现,但却很难客观地定义或描述保护技术的实际标准——这是保护专业人员的内在能力。
纵观英国保护史,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对“拥有特定保护实践技能水平的从业者”这一概念也经常有原则性的质疑。其特殊原因是,保护实践必然涉及文化和发展部门二者共同的跨学科实践,并由相应的多种学科进一步加固它们的基础。
在大约两百多年的相关实践中,保护实践的失败、灾难和亏损只是一个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最终它们汇成了对正式的能力评估需求的共识,这在英国的保护认证体系中得以实现。这些保护的讨论在20世纪中叶达到最高点,当时战后发展、现代建筑和公民压力围绕着一些最有争议和最引人注目的遗产不断地辩论和调整。
公众反对声音的日益增强是英国保护史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在反对政府专权主义坚持执行这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现代运动”议程时,这种声音尤为响亮。这种公民倡议根植于西方民主国家中——不只是英国,在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以非专家的身份阐述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显而易见的关注焦点。
雅各布斯的许多优点也反映在英国早期的女性保护倡导者身上,(她们)也常常像她那样并不具备在相关领域的正式资格。这些知情但非专业人士群体的发声扩大了职业和专业“专家”的规模,尤其是对那些历史上与建造和发展相关的建筑,专家们不得不承担他们保护的核心责任——那些写在他们最高宪章里但常被忽略的义务。
在有争议的保护案例中,“专门知识”的判断一如既往地至关重要,因为社团和政府,以及支持者、反对者,都需要专业顾问来证明遗产价值,或证明其存在缺陷。然而,在保护中,这些顾问的身份和地位尤其令人费解。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都可以轻易地在他们自己的学科中宣告权威,并且宣称自己的学科与保护考量相关,因为它没有更宽泛的定义、测试甚至对保护能力自身的认证。
大约在20世纪中叶,建筑史这门学科在很多保护案例中,扮演了基本不受管制的重要角色。建筑历史学家采用了一种相对较新的“专业主义”,在为建筑物的遗产价值提供建议时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符合立法对“特殊建筑或历史价值”,同时也是对最有争议的保护案例的首要关注。在缺乏更广泛的专业规范的情况下,举例来说,不管对保护规划或美学的更广泛原则有什么专业的理解,(任何专家)都可以对建筑的“特殊权益”进行评论。
没有一个标准来定义他们在保护问题上的“能力”意味着,无一例外,任何争议总能在分歧的另一边找到专家权威。这类从业人员的地位仅受自身声誉、感情和责任感的约束,通常建立在最学术的经验基础之上。他们甚至比建筑师还自由,建筑师至少坚守一方、受到一个独立的职业机构、已被认可的职业标准管理,而这类从业人员除了他们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标准之外没有其他准则。
这里给出两位建筑历史学家的案例,清楚地展现了在没有更广泛的保护实践的情况下,特定学科的专业性会对遗产做出缺乏可靠性的评价——约翰·萨默森爵士(Sir John Summerson)和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 Nikolaus Pevsner)。[32]约翰·萨默森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之一,与1933年在英国定居的德国纳粹政权下的犹太难民佩夫斯纳不同,他扎根于英国社会。他们都是建筑史学科发展史中独树一帜的权威。与此同时,几乎没有被意识到的是,他们反映了:当与保护有关的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占主导地位,而更广泛的保护能力缺失时,就会产生的无法解决和不可调和的冲突。
例如,萨默森对后来的乔治亚时期的伦敦,典型的、单调乏味的联排住宅特色进行了最严厉的建筑批评,而当他参与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发展标准评定中,他再次给出的这种感性评价,导致了这个国家巨大的保护灾难之一。
萨默森出版于1946年的经典著作《乔治时期的伦敦》时,就显露出了十分明显的个人审美倾向:
“想象一下,一个城市的每条街道都是高尔街……景观的压迫性令人难以忍受,圆滑的威尔金斯先生(Mr Wilkins)、傻傻的斯米尔克先生(Mr Smirke)或者滑稽的纳什先生(Mr Nash)设计的充满情感的屋顶……”[33]
在评估都柏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乔治晚期的街景时,他的偏见说明了任何将标准纯粹地、死板地运用在保护领域所带来的问题。该街景位于连接梅里恩广场和里森街的菲茨威廉庄园街上。萨默森在国家权力机构——爱尔兰电力局( ESB )的要求和高额报酬的驱动下提出建议,认为都柏林联排别墅的遗产价值很小,甚至更糟,称它们是“一个草率的不均衡序列”“就是一栋又一栋该死的房子!”他总结说,“按照乔治亚时期的标准,这些房子都是垃圾”。[34]
然而萨默森的判断存在根本缺陷。他仅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建筑价值,他的结论没有认识到一个历史街区联排住宅设计上的创新性和连贯性,这些建筑的价值超出了他的认知能力。这些价值包括:建筑和场所营造方面更广泛的传统,这些价值根植于城市文脉,以及它们在爱尔兰遗产的地位中。最初的方案中独特的、壮观的联排城市街道设计以及其建筑形式——当时爱尔兰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在1952年首次发表的《都柏林,1660 - 1860 :城市的塑造》中已经将之描述为一种“类型”——都没有对萨默森产生影响。相反,他把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标准强加于后殖民时代的爱尔兰首都,他的建议导致了16栋19世纪早期的联排住宅的拆除,这些房屋曾构成都柏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乔治晚期街景,但是现在被现代写字楼取代了。
由于对萨默森所持观点缺乏保护能力方面的评价标准,因此他的观点不会受到质疑,也无法被客观地被认定是否合格或有效。
20世纪中期建筑史与保护产生交集的另一方面,可以从尼古拉斯 · 佩夫斯纳的作品中看到。 他里程碑似的《英格兰建筑》系列——“佩夫斯纳”的名字今天已成为这部系列的代名词——在1951年到1974年之间出版了约46卷书籍原稿。“佩夫斯纳”成为对一个国家建筑史最深刻的批判性评价。无论是何种具体灵感促使佩夫斯纳,承担了在最详细、最广泛的背景下——包含经济、地质、地理、历史等方面,描述“英格兰建筑”这一庞大的非官方任务——“佩夫斯纳”成了评估遗产和非遗产利益的重要工具,包括让保护官员了解对遗产价值的自我评估方法。
虽然作为一个项目,它非常有意义,但对于保护史来说特别讽刺的是,在 “佩夫斯纳”的地方卷没有被提到的建筑,至少原则上,更容易被忽视而倾向于被拆除,特别是被能力较差的政府官员,以及不太严谨的开发商和顾问所拆除。尽管地方保护官员可以容易地认识到、并阐明佩夫斯纳倡导的遗产的“舒适性”价值(Amenity Value),但由于在建筑史上“专家”较少,如果遗产存在致命缺陷,就会注定要爆发一场推翻“舒适性”的战斗,同时由于 “佩夫斯纳”地方卷的遗漏又产生了鼓励性拆除。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一门无法衡量能力的保护学科来说,早期保护史中一直存在着困扰着遗产争议的那些不协调之处。缺乏能力衡量的标准意味着,保护者和开发者在任何时候都会要求旗鼓相当的专业权威参与进来为他们辩护。
一直以来,从19世纪及以前,到21世纪直到今天,都缺乏一种更公认的能力规范来对与保护有关的问题作出判断,无论结果如何,这都使得保护的过程变得复杂。
围绕伦敦两大火车站——尤斯顿(Euston)火车站和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火车站,二者沿着伦敦的尤斯顿路相隔几个街区——20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清楚地凸显了对保护能力的困惑有多大。这两个车站都面临着威胁,因为汽车的崛起导致列车运输的倒退,新的、尤其是对运营效率的需求,在尤斯顿通常是通过拆除和重建来满足,在圣潘克拉斯则是用裁员和替换来解决。
尤斯顿是世界上第一个位于首都的主线总站,特别有价值的是其设计核心,即1838年建造的70英尺高、44英尺深的、新古典主义的“尤斯顿拱门”(图4),实际上更准确的称呼是希腊复兴多立克式的“入口”或大门,由菲利普 · 哈德威克(Philip Hardwick)设计,来彰显火车站的(宏伟)入口。1960年代,该车站计划将其替换,尽管存在巨大的争议和公众的强烈抗议,拱门还是被拆除了。
尽管这个传奇故事的详细历史太过复杂,无法在这里进行探讨,但这个故事具有保护争议的典型特征,包括呼吁反对的专家,以及政府的不当处理——例如撤销迁移和重建拱门的高层协议——尤其加剧了公众的抗议。[35]但拆除行动前后的参与者和人物的两极分化揭示了当时英国保护的普遍情况。[36]
后来成立的维多利亚协会(Victorian Society)是反对拆迁的主要保护机构,它成立的故事也众所周知。它起源于由安妮 · 梅塞尔(罗斯伯爵夫人)发起的个人倡议,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保护和欣赏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和艺术的协会”。[37]1957年,她邀请了一批维多利亚时代遗产的爱好者——包括公认的专家和高调的非专业人士——来争取支持,于是次年“维多利亚协会”宣告成立。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协会主要致力于保护19世纪的建筑,其最重要和最适时的成就可能是,它戏剧性地改变了公众对维多利亚建筑的看法。它改变了公众对它“丑陋”表面的普遍厌恶,尤其是对它过度装饰和精巧癖性的厌恶。尽管当时这个团体相对年轻,但它在拯救尤斯顿拱门的尝试中特别活跃,提高了社区和政府对历史价值的认识,同时试图扫除影响萨默森在都柏林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维多利亚协会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并向政治家施压——1961年10月24日,保守党首相哈罗德 · 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举行会议,讨论了拱门的保护问题及其重建的可能性——并敦促公众和专业人士重新评估他们得到的想法。尽管尤斯顿拱门的(拯救)事业最终失败了,但其中的宣传倡导经验帮助该团体完善了它的保护运动手段,使它在另一个受到威胁的重要的伦敦车站——圣潘克拉斯车站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这次它成了火车站的救星。
圣潘克拉斯建于1876年,是为米德兰铁路公司( MRC )建造的,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建筑师乔治 · 吉尔伯特 · 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了酒店和车站的住宿,这些设施位于火车棚工程项目前方,这是此类复杂的工业建筑的通常设计。[38]酒店面向公共的正立面——像尤斯顿拱门一样——是公众所知的最著名的特征,也同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图5)。但与尤斯顿不同的是,圣潘克拉斯躲过了20世纪中叶的威胁,在21世纪作为一个国际交通枢纽重生,除此之外,它还是欧洲之星火车通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到达巴黎的终点站。[39]显然,圣潘克拉斯与尤斯顿有着不同的保护结果,但其保护历史的演变非常相似。
斯科特设计的火车站在街景中高耸入云,采用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粗犷的、明亮的红砖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甚至在建造一个世纪后仍被大众嘲笑。在1960年代,斯科特的设计明显与英国20世纪中叶的大众品味不一致,因为它的风格更符合现代运动风格。但维多利亚协会毫不气馁,凭借通过尤斯顿车站和其他地方建立的势头,和汲取的经验教训,与其支持者们一起为反对拆迁而斗争。公众、媒体和政客,当然还有保护部门,都被要求保护这一遗产。此外,正如协会今天在其网站上简要地总结的那样:“1966年,当英国国家铁路想要拆毁圣潘克拉斯车站时,该车站却被列为I级(最高级)登录建筑,这是国家对其遗产价值的最高评价“。[40]
这两个故事的统一特征是不同的单学科专家和热情的非专家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性。尼古拉斯 · 佩夫斯纳是维多利亚协会的创始成员,对其有着开创性的影响, 该团体也是建筑史领域中最重要的支持者。秘书,也是更具有号召力的招牌人物是广受欢迎的民粹主义桂冠诗人约翰 ·贝杰曼(John Betjeman),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活力和个人热情——虽然在他的诗歌中反映得不太成功——使得他被公认为那个时代建筑领域的权威之一。外行人和公众的反对是由罗斯伯爵夫人的基金会领导的,她是一位富有手段的独立女士,她也表现出巨大的个人热情。[41]约翰 · 萨默森在他的著作中积极地重新评价了维多利亚时代,随着他也加入到尤斯顿的示威活动中,参与保护活动的积极分子圈终于完整了。
尽管尤斯顿车站和圣潘克拉斯车站在遗产管理、经营不善和保护方面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但最终,除了输了一场、赢了另一场的偶然事件之外,它们都没有给已知的保护实践带来更多的经验。如果这两次事件中,最惊人的是个体参与者的多样性——包括外行、学者、专业人士等,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专长,同等的权威或者明确的领导,使得他们能提供自己领域的专业知识。
20世纪中期的争论为一个世纪及今后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保护概念息息相关,继而又是一个类似的争论,但仍然对保护能力的概念视而不见。

图4:尤斯顿拱门历史图像
19世纪对于重要标志性建筑——例如英国的大教堂的强力“修复”,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乔治 · 埃德蒙 · 斯特里特 (George Edmund Street),和斯科特一样,是另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建筑师。他实际上是将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座堂(Christchurch Cathedral)拆毁,作为他所谓的“修复”的一部分。他甚至声称基于想象的重建是有权威准确性,因为后来发现的一个原始造型轮廓与他的设计有相似之处。[42]如果(像)他(一样)显然把自我置于现实之上,那么即使在今天,保护规划领域备受关注的案例中,也充斥着一些与斯特里特和萨默森在都柏林一样的、不受监管的作为。[43]
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的争议,当前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公认的方式来定义保护“能力”的情况下,保护争议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提供无可置疑的“专家”建议,因此需要另一种“控制”。这种控制将集中在建立专门针对保护成果的职业道德标准上。
五、 公共利益中的保护:“舒适性”(Amenity) [44]与保护伦理的根源
在英国,直到20世纪末还没有公认的保护能力水平衡量标准,因此保护建议中最关键的质量控制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水准。[45]
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技术和能力水平,传统的观点认为保护相关学科——例如建筑学和考古学,并不与可以支撑保护的跨学科的技术和能力完全一致。那些被伊根、ICOMOS、BS 7913和其他标准所认可的唯一可行的控制仅是一个伦理标准。即便如此,评估也不容易。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保护行为是为了支持公众利益,但保护通常被认为与其他传统学科关系更大。需要一个更易识别的框架来描述保护的伦理基础,并在“舒适性”的概念和通过规划的管理实践中建立这一框架。
遗产与发展之间的两极分化在上文提到的伦敦火车站的案例中得到集中体现,这种分化在英国,就像许多现代欧洲国家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哥特复兴运动,在1836年由奥古斯塔斯 · 普金(A.W.N. Pugin)和他的《对比》一书引发,是一种早期的、对于重要事务的公共关注,因为它清楚地显示了一场未受控制的工业革命导致的破坏。[46]尽管普金的作品是在风格的伦理基础上进行的,但在场所管理方面,他的声音却被忽视了。相反,保护运动在建筑修复的争议中获得了最高的地位,其中最令人熟悉的是遗产爱好者们的故事,他们关注的是在历史建筑的修复过程中,发展和保护间的冲突,通常是关于标志性的、深受喜爱的和被广泛使用的历史建筑。
这些戏剧性的修复在19世纪晚期的大教堂修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斯特里特主导的基督教会座堂修复,以及在那个世纪的修复与保护之间引人注目的对抗中最突出的案例。这些争议引发了“古建筑保护协会”(SPAB)的诞生,该协会于1877年随着“SPAB宣言”而成立,写下宣言的领导者和杰出人物是“反修复主义者”威廉 · 莫里斯 (William Morris)。[47]
莫里斯对一系列或高调或低调的项目都很愤怒,这些项目越来越令关注老地方的特性和气质的人感到失望。莫里斯谴责了当时的实用主义方法——所谓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的“修复”。随着“修复”这一流行的委婉说法(以后可能会被更好地描述为“重建”,或者更准确地称为“重新开发”),将这种做法贴上“保护”的标签,就像乔治 · 埃德蒙 · 斯特里特在都柏林所做的那样,只会引起最早的倡导者和保护历史古迹的活动人士的反对。针对这种激进的干预措施,人们的反应可能不是保护(Conservation),而是在莫里斯和SPAB的领导下的“保卫”(Protection)。
威廉 · 莫里斯在他的“SPAB宣言”中呼吁“抵制对建筑物现有结构或装饰的任何篡改”,为后来的保护运动人士树立了底线、灵感和榜样。然而,就像那些后继者一样,采取单一原则的立场也有严重的局限性。这样的绝对主义中潜在的风险和威胁,从莫里斯提供的“恢复”的唯一选择中体现得清清楚楚,因为他呼吁在恢复之前就毁掉建筑:“……如果(老建筑)不适用于现在的功能,应该使用另一个建筑而不是改变或扩大老建筑。”[48]就像斯特里特的修复和尤斯顿的重建一样,这一极端观点无法与后来的保护标准相一致 。”
虽然莫里斯的立场有很强的道德基础,就像他之前的普金一样,同样可能会具有极端的唯物主义美学倾向。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索也在演变、并形成保护史,它依赖于更微妙的社会目标和实践标准。[49]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保护伦理的起源始于地方管理的新过程和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城镇和乡村规划”,甚至简写为“城镇规划”或“规划”。[50]“ 城镇规划”起源于1909年与《住房与城镇规划法》相关的立法,该法案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部城镇规划法”[51],它与现代保护运动实践的原则与道德准则既有交集,也有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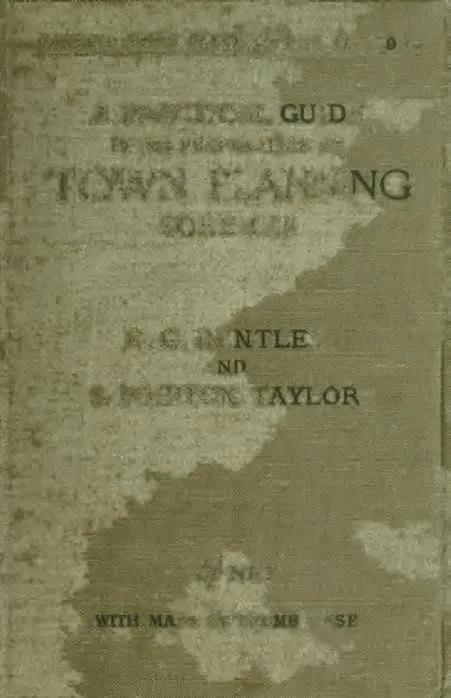
图6:1909年颁布的《住房与城镇规划法》
规划的实践逐步发展,与莫里斯和他的反对者建立的、更为成熟的遗产历史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平行关系。它根植于与公共服务相关的、通常是在地方政府的实践,它提供了一条通往现代保护实践标准的路线,因为它不太关注特定修复——保护主义之间争议的原则,而更多地依靠对个人品味或抽象哲学之外的、承认遗产价值的伦理概念。
城镇规划起源于19世纪后期,与保护运动的发展密切并行,因为两者都面临着工业的强大进步,这些进步导致了数十年的、文化和自然的破坏和丧失,以及就像普金当时认清和预言的那样,还导致不合人性的新地方不断增多。这种早期的工业发展越来越与传统价值观念和更强的社会意识发生冲突。不可避免的是,公众和公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对新的发展进行管理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普遍。从大约1900年起,在场所变化的过程中,对社区利益的认可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后工业时代的英国重新定义了发展,它不再是一个由土地所有者或实业家决定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通过规划、集体管理变化的过程。
“城镇规划”提供了一种新工具,通过这样的管理过程来提供更人性化的场所。它就应该以及如何改变场所达成共识:计划必须在社区和发展利益之间的公开讨论中达成一致,并首先由地方政府的民主政体监督。这一过程的重点是一个商定的“计划”,以实现一个地方的未来发展。
1909年颁布的《住房与城镇规划法》(图6)是作为指导立法制定的,以支持这些规划过程,并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整个英国工业区的公共卫生和住房。在这一模式中,“公共利益”的目标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公共福利、健康和住房问题。针对这些期望,该法案提出了一个总体规划目标,并一直延续到现代实践中:维护一个对公众有益的、地方的内在品质。这些品质在当地建筑遗产及其保护等价值中得到记录,在“舒适性”的概念下得到承认、描述和管理。
尊重 “舒适性”意味着:该法案的更广泛的公共目标中,存在为了维护、保护建筑物和场所的规划考虑。这说明,在法定规划发展过程中,那些关心当地遗产的“舒适性”受到威胁的人士,包括那些“代表建筑或考古协会的人士,或对计划的舒适性感兴趣的人士”,他们应有一个选择权,应该可以直接,或由专业人士代表他们,来表达他们的顾虑。[52]
在没有更加专业人士参与的情况下,该法案还是明确了建筑学和考古学相关的顾问作用,但通过这种做法,它阐明了社会、发展和经济的优先性是相同的,这些优先事项将被囊括在英国随后所有的主流规划进程中。于是,通过这些独立的顾问角色,该法规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培养了第一批专家保护顾问,从而为未来的地方政府的保护官员,甚至后来的保护专业人员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在伦理的实践方面,该法案的首要主旨是强调“舒适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赋予了当局确保公众利益的必要性,例如“健康的环境……充足的光线和空气,合理的娱乐设施,以及……环境中的愉悦和舒适”,从而确认了健康和娱乐与遗产和场所的基本联系,这是未来所有遗产和保护规划的基础。[53]
1909年法案早期出版的指南受到公众关注的启发,既面向专业读者,也面向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其中第一本(指南)——由雷蒙德 · 安温(Raymond Unwin)所编纂,他是塑造该法案的“花园城市”运动的主要建筑倡导者。(他)在前言中用大众熟悉的语言介绍了立法背景,并反过来聚焦在英国各地的运动和 “舒适性”立法机构,并促进公众理解和接触上,同时也谦虚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下文摘录了一段完整的引文,其中的精神将为后继的保护工作者所熟知:
“这项法案标志着两个重要进步,不仅土地所有者与拥有城镇规划权的各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确保公众有健康的环境、充足的光线和空气、合理的娱乐设施,以及对全民福利至关重要的舒适性环境而开展的运动,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项法案也不像有时被误解的那样,是一项适应性的法案。这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普遍适用的公共通用法规,地方政府委员会保留全部权力,以便在适当情况下付诸实施。
当该法案的优点能被读者们充分理解时,作者就会感到放心,觉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行使这些权力,但鉴于该法案以及更大程度上地方政府委员会的程序规定必然最为复杂,似乎应以全面和易懂的形式向公众提出这一问题。
作者在本卷中努力做到这一点,无论有多么精辟的批评家,作者比他们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份先锋作品的许多缺陷,以及目前仍未解决的许多疑问和困难。”[54]
在1909年的立法及其后继法案中,“场所质量”与“舒适性”两个概念紧密相连,成为新规划学科的一项基本原则。随后,在更专业的遗产团体手中,“舒适性”要求下的公共利益与遗产场所之间的联系将继续同时响应民众以及遗产倡导团体和慈善机构的呼声。从1968年起,维多利亚协会和SPAB等领导机构依法正式成立为“国家舒适性协会”,作为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机构和遗产事务的“法定顾问”。[55]
通过规划中的场所管理和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目标之间的联系,与 “舒适性”相关的道德标准在主流规划过程和服务中仍在继续发展。在场所规划的道德基础问题上,苏格兰博学的学者帕特里克 · 格迪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不仅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规划者,而且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在世界尚未认识到这门学科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杰出的跨学科保护专业人士。[56]通过他具有启发性的“调查、分析、规划”来关注场所管理和复兴的过程,让“舒适性”相关的道德标准不再是抽象的规则,而是建立在对个人和社区需求的详细观察之上的技术过程。[57]正因如此,他的做法——就像许多规划者的做法一样——可能被认为本质合乎道德,因为它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58]
这种公共和“舒适性”的道德标准通过与规划部门的结构联系,继续扮演着地方政府“保护官员”的角色。通过对遗产场所进行知情的管理,保护官员提供公共福利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因为在1967年的《城市文化设施法案》中引入了一项新的、以场所为基础的社区遗产焦点。[59]像英国1909年的法案一样,1967年的法案是长期的运动和游说的产物。具体而言,19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案,和后来的1997年苏格兰的法案,它们名义上“合并”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将1967年法案的理想与列出的建筑法规放在一起,正式置于保护官员或服务部门的管理下。
受新发起的公民信托运动的启发,1967年的法案在国会得到了其创始人邓肯 · 桑蒂斯(Duncan Sandys)的推动,成为英国议会的一项私人法案。该法案将公众和公民社区利益置于其目标的中心,桑蒂斯在以下背景下取得了这次运动的成功:
“在这个钢结构和玻璃幕墙建筑的时代,新建筑比它们所取代的建筑大得多,而且性质也大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建筑和早期建筑不协调。但这意味着今天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更有责任尊重和理解前人的工作……《法案》要求地方当局在批准可能对保护区特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新开发项目之前,先发出通知。这将使公众,特别是遗产保护团体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感受 。”[60]
1909年以来,遗产维护和保护就已经植根于一个以场所为中心的规划过程中,1967年的法案——和后来在1990年的合并及再之后的法案——在保护实践本身方面几乎没有改变。1909年法案中的场所管理原则和标准——基于公众利益的知情审查、评估、审视和妥协——于1967年正式纳入地方政府保护官员和相关服务部门的实践中。早期法案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关注——通过舒适性和规划——帮助制定了1940年代和以后颁布的法律。
这些过程如何演变成1990年及其后续法案,太过复杂而无法详细展开,苏格兰则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小案例来解释。那里的历史被前苏格兰文物局的历史遗产清单负责人,黛博拉 · 梅斯博士(Dr.Deborah Mays)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简洁地概括了:
“英国政府寻求的是……提供一种工具,(让人能)在给‘具有特殊建筑学或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设置法定名称的规划系统内工作。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932年的《苏格兰城乡规划法》中……
立法的关键是1947年的《苏格兰城乡规划法》,该法通过保护名单、保存令和收购等方式处理保护问题。我们目前法案的核心就在这里,目前对建筑物的定义演变为‘建筑物的任何结构或竖向支撑,以及符合定义的建筑物的任何部分,但不包括建筑物中的任何植物或机器……’
然而1947年法案为保护带来的唯一麻烦是,如何制定保护命令……保护命令允许,如果建筑物的状况显得很危急,就可以转移为公共资产(通过强制收购)。1947年法案出台后,中央政府官员开始监督法案的实施……
1967年《城市文化设施法案》的出台进一步保护了建成环境,为‘保护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意义的地区。该立法建议,应注意通过挂牌保护的个别建筑物的更广泛背景……
1969年,另一项《苏格兰城乡规划法》的出台产生了重要的新权力,以改善冗长的保护名单出台程序。为此,它取消了对指定范围的法律记录的需要……将保护名单通知的责任转移到地方规划部门……
1969年的法案还带来了另一个有益的转变,那就是‘对保护名单上的建筑物的拆除和其他工程的限制’,引入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LBC系统的框架。它授权内阁大臣在官方调查员和地方当局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聆听和决定申请。“[61]
1967年的法案通过关注专业顾问的建议和道德方面的原则,为1990年的法案预先做了准备,它代表了一个更完善的保护过程,比高调的、两极化的运动更具实质意义,也更经济有效。然而,道德标准的实施仍然是个人决定和决心的问题,没有更广泛的规定,至少在保护专业人员出现之前是如此。
六、英国保护史的回顾与展望
1909年的法案奠定了现代保护专业的伦理基础,并与和善性立法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它还引申出一种更微妙的方法,采纳了更广泛的“舒适性”道德原则,并承认现代保护过程是指导原则,而不是像莫里斯被迫做的那样,将保护视为“不管怎样都保留”或“防御性拆除”的两极化二选一方案。
关于保护能力的定义,它本身就是道德判断的出发点,它进步的主要动力是现实中大量的不称职现象,这种不称职往往通过实践标准的操作,造成对历史场所的破坏,而这些实践标准被主流传统学科中被完全认可。
ICOMOS指南的条款概述了实际技能,该指南是由一名非常了解英国保护史,并在地方政府保护服务中操作标准的建筑师撰写的。
只有在能够达成一致并确定这些要素的情况下,才能将道德标准与技术能力纳入进更广泛的监管。这些措施和控制是规范保护实践的必要前提。甚至,在为保护实践建立一个清晰的专业构架之前,(保护实践)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此,到了20世纪末,在英国的“第一部”规划法颁布和现代保护开始近100年后,任何与保护有关学科的专家——确实有许多——都可以站出来,在保护实践的某些方面声称他们的意见是权威的。不管他们的建议如何,监管当局都无法客观评估他们的个人保护能力或技能水平。
早在1990年代,缺乏保护实践标准就变得至关重要并且众所周知,因为对保护工作的公共投资没有适当的保护实践标准来指导。ICOMOS指南是对这些担忧的部分回应,但另一项同样与伯纳德 · 费尔登爵士的工作有关的倡议,在推动这一议程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它激励了一个专业团体联系中心的建立,以确立实践领域的保护标准: COTAC——“建筑保护培训委员会”。[62]
COTAC成立于1959年,在英国多种多样的建成环境专业中,作为专业的保护实践标准的领导机构,形成了保护的成果。[63]后来,特别是在英瓦尔 · 麦克斯韦(Ingval Maxwell)的领导下,COTAC首先代表苏格兰国家遗产机构——苏格兰文物局,领导了保护认证标准的推广工作,以作为在传统主流建成环境的体制中,衡量同行评审能力(的标准)。这些都是基于ICOMOS指南中定义的技能,并通过由COTAC支持的、非正式的集体——“爱丁堡协会”进行协调。[64]
COTAC对主流建成环境专业保护标准的积极关注,与另一个机构——国家遗产培训中心(NHTG)的工作相互补充,该中心更强调行业和工艺领域的保护实践标准。[65]2005年,NHTG发表了《英格兰建筑遗产部门的技能需求分析》,这是一系列遗产部门研究中的第一项,旨在直接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帮助,尤其关注对历史建成环境培训的支持和维护。[66]前IHBC教育部长约翰 · 普雷斯顿 (John Preston)对NHTG关于行业中优先事项的研究要点进行了如下描述:

图7:IHBC学会《文脉》杂志创刊号的卡通画
“一份重要报告显示了该行业的经济意义。在调查前的12个月,所列出建筑的全年总开支估计为17.2亿英镑,12个月后则增至18.5亿英镑。对1919年以前的建筑,预算从35.4亿英镑增至了36.8亿英镑。”[67]
本文开头所引用的文件——关于可持续发展、发展和建设标准等,只是为了说明保护实践的基本原则与当代主流建设和发展的专业需求关系紧密。NHTG和COTAC等机构的工作重申了遗产部门的具体需求,以及更广泛的历史环境如何为工业和社会的主流同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从就业、碳减排,到社会和环境效益。
七、 总结: 英国今天的专业保护实践与IHBC
《ICOMOS指南》确定了保护技能的基本范围,而COTAC则肯定了至少在传统学科中保护能力的重要性,并计划为遗产管理中的实践伦理建立通用语境。然而,这是地方政府保护官员的遗产,将技能、能力和道德整合为一套连贯的保护专业人员专业管理标准,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跨学科专业来运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分布在英国各地的保护官员和相关同行,主要在英格兰的,开始聚集在一起,共同考虑他们的实践和服务标准。他们采用了保护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Conservation Officers ,ACO)的名称,专注于个人在保护方面的技能,并于1983年出版了第一期会员刊物《文脉》(图7)。[68]
20世纪90年代,ACO继续巩固关于保护专业技能、能力和道德的原则。直到1997年,它将这个非正式组织“协会”转变为正式的专业及慈善机构IHBC。虽然转型发生在1997年,但正式的构架、工具方法,甚至像本文所说的历史一样,仍处于演变的早期阶段。不过,尽管这门“跨学科”学科还在起步阶段,但其基础已经具备。
为了明确跨学科技能,IHBC创立了一个“保护周期”模型(图8),使评估人员能够评估跨学科技能的基本范围,包括本文开头概述的通用实践领域: 理解、维护和变化,或者用“周期”中的概念来说:评估、管理和干预。为了评估这些跨学科技能的能力水平,它采用了一个通用的同行评审系统——从“零”到“高”、从“外行”到“专家”——许多“爱丁堡协会”的保护认证计划也使用了这个系统。
独特的是,在IHBC中,对技能水平(或“能力”)的评估在整个保护技能范围内被正式地衡量,并与道德标准评估相结合。为了进一步根据保护成果——这种成果不是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衡量——而调整道德标准,IHBC有一个完整的、以遗产成果为重点的监管学科框架。[69]
通过IHBC的工作, 可以预见到21世纪英国的保护会有一个更加活跃、专业的前景,也会取得更广泛的成就:社会和社区的福祉,例如“生活质量、健康和幸福”;经济效益,例如因更新和提高而产生的效益; 以及环境效益,例如与良好的保护实践有内在联系的碳减排效益。
注释
[1]历史建筑保护学会(IHBC),英国专业的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保护研究机构,运用 “保护周期”来进行保护领域的一般性实践。该模型与 “实践领域的保护能力”:评估、管理和干预共同作用。详见下文,对IHBC的介绍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titute_of_Historic_Building_Conservation 和www.ihbc.org.uk.
[2]参见Http://www. iHBC.O.UK/GDPR/NETX.HTML。这一主张是在实践领域中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的,建立在英国独特的——以及全球公认有价值的——历史和历史环境保护历史上,正如结论中所讨论的那样。
[3]“ICOMOS关于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保护教育和培训指南,国际古迹和遗址理事会的大会,ICOMOS,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召开的会议,1993年7月30日到8月7日的第十届会议“。更多背景参看Jukka Jokilheto,2018年5月,IHBC https://ihbconline.co.uk/newsachive/?p=19045.
[4] ICOMOS Guidelines, para. 4.
[5] Jokilheto, loc. cit.
[6] ICOMOS, 1993, para. 5.m: “保护主义者”应该“……在跨学科的小组中工作”。参看Bernard M.Feilden的 “在英国古迹、群体建筑或遗址保护项目中合作的职业的概要简介。”《基于ICOMOS保护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保护教育和培训指南上做出的英国文物保护工程多学科合作培训意见》http://cif.icomos.org/pdf_docs/Documents%20on%20line/cotac.pdf
[7] ICOMOS, 1993, para. 5: … to produce”conservationists who are able to undertake the 14 tasks identified under para 5“.
[8] ICOMOS, 1993, para. 7: Practitioners must”act competently“
[9] ICOMOS, 1993, para. 5 (i): Practitioners must‘make balanced judgements based on shared ethical principles, and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ong-term welfare of cultural heritage’
[10] Egan观察到:“……这些职业的广度和不同的培训和认证过程使得现有的机构很难向所涉及的每一个人提供必要的技能……”和“CPD是由专业机构认可的。我们建议雇主与这些机构合作,考虑如何在通用技能和跨学科工作中给予最佳培训“。 Sir John Egan, ‘The Egan Review: Skill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DPM),2004:53. http://ihbc.org.uk/recent_papers/docs/Egan%20Review%20Skills%20for%20 sustainable%20Communities.pdf.
[11] Egan, op. cit., p.10.
[12] Egan, op. cit., p.11.
[13] Egan, op. cit., p.16.
[14] 事实上,ICOMOS指南指出保护应该处于可持续的目标之内:“可持续的变革管理策略……需要与当代经济和社会目标相结合“: ICOMOS, 1993, para. 2.
[15] BS7913:2013《历史建筑保护指南》,英国标准协会(BSI),2013。1998英国保护标准之后的版本都未得到共识,但2013版本是不同的。这一版本与BSI标准的框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具有权威性,并在建设和发展部门中处于更为核心的位置。See also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IHBC’s own cobranded pint run, available through the IHBC at https://ihbc.org.uk/bs/.
[16] BSI, 2013, op. cit., para. 5.6.1.
[17] 历史城镇和乡村论坛(HVF),一个联络民众需求的机构,为当地公民信托、积极的社区机构,进行联系的机构,
[18]‘Conserv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Principles’, HTVF, IHBC and Civic Voice, 2017.See http://ihbconline.co.uk/toolbox/docs/Conservation%20Professional%20Practice%20 Principles_A5%20FINAL%20May%202017.pdf.
[19] HTVF, IHBC and Civic Voice, 2017, S. 3.1, p.13.
[20] Ibid.
[21] Introduction, p.2.
[22] Ibid.
[23] Planning (Listed Buildings and Conservation Areas) Act 1990 (P(LBCA)A), chapter 9: ”一项旨在加强与建筑物和特定建筑或历史价值领域有关的特别管制法令,并执行法律委员会的建议。1990年5月24日“, and in Scotland, ”The Planning (Listed Buildings and Conservation Areas) (Scotland) Act 1997“. 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通过这项立法,遗产管理的过程更加脱离主流的规划法,如下文所讨论的,对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4] P(LBCA)A 1990, S.66.
[25] There is s a substantial body of research by the IHBC on such services, with key papers linked from https://www.ihbc.org.uk/skills/index.html and http://www.ihbc.org.uk/page55/ihbc_research/index.html.
[26]‘Planning and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Planning Policy Guidance (PPG) 15, DOE & DNH(TSO?), 1994. Download available at https://www.cheltenham.gov.uk/downloads/file/692/planning_policy_guidance_15_ppg15_-_planning_and_the_historic_environment.
[27] PPG 15, Introduction, paras 6-7.
[28] 这种双重作用与1990的立法密切相关。1990年的立法已经发展为“城乡规划法”,但在1990法案中,”保护“单独作为一个“章节”,专门用于管理发展环境中的文化优先事项。
[29]中央政府规划部门监督地方政府部门保护官员的工作,事实上,主要监管机构是中央政府的文化部门。
[30]The online archive of the IHBC’s membership publication, Context, offers substantial resources on this wider history, available at https://ihbconline.co.uk/cont_arch/. See especially the commemorative issue, No 100, at http://www.ihbconline.co.uk/context/100/.
[31] See the discussions around the IHBC’s Competences and Areas of Competence at http://www.ihbc.org.uk/resources/MembershipStan dardsandgGuidelines0308.pdf and as listed in membership guidance at http://ihbc.org.uk/membership/docs/Approved_Comp.pdf, and, for the ‘Conservation Cycle’, Note 1 above.
[3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Summerson 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kolaus_Pevsner.
[33] John Summerson, ‘William Butter field; or, the glory of ugliness’, pp.159-76, in Heavenly Mansions and other essays, W. W. Norton, New York, 1963,p.173. See also John Summerson, Georgian London,1945 and later editions (1945/49).
[34] 这一事件被描述在《爱尔兰建筑》(都柏林卷)中: “……最臭名昭著的破坏,就是沿着菲茨威廉街(城市中格鲁吉亚风景区最长的一部分)一处400英尺(122米)长的扩建”,后来被萨默森删改为: “一幢又一幢简单糟糕的房子!”。See Christine Casey,‘Dublin, the City within…,’ Buildings of Ireland,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2005, p.76.
[35] Ruth Adams, ‘John Betjeman, the Euston Arch, and the Fight to Save London’s Industrial Heritage’, published on ‘POLITIQUES DE LA CULTURE’: ‘1994,历史学家Dan Cruickshank在东伦敦里亚河畔的河床上发现了4000多吨拱门中的60%。其中一部分柱子被从水中打捞。据透露,这些瓦砾是1962年被购买来填补河床的裂痕。CurksHink发现,尽管在河床底部沉睡了30年,这些石头基本没有风化。因此他认为重建拱门仍然是有可能的。从河里甚至打捞出一个有凹槽的柱子,在那里也找到了用金字记号了“尤斯顿”的石头。 (https://chmcc.hypotheses.org/2663).
[36] 一群年轻的建筑师曾试图通过攀爬拱门周围的脚手架来拖延拆除,竖起一条50英尺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拯救拱门”的字样。约翰.萨默森爵士也出席了示威游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ston_Arch
[37] https://www.victoriansociety.org.uk/about/history-of-the-victorian-society
[3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Pancras_railway_station.
[39] https://stpancras.com.
[40]https://www.victoriansociety.org.uk/about/history-of-the-victorian-society
[41]有趣的是,这一现象在苏格兰遗产保护协会也出现了,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HSS)源自于“爱丁堡格鲁吉亚协会”,并在1956年会议后成立了“苏格兰-格鲁吉亚协会”。See https://www.ahss.org.uk/who-we-are/history/.
[42] Sean O’Reilly, ‘The arts of inference,presumption and invention: George Edmund Street rebuilds Christ Church.’ Gothic and the Gothic Revival.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21 February 1997: “斯特里特认定原本存在一个很壮观的立面,因此他设计了一个华丽的双重门。在建造过程中,在墙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框柱。幸运的是(斯特里特写到)这“完全合乎我的设计”,因为石头是“及时发现被使用的”,于是就“安放在新的门上”。(Street &Seymour,1882,P.117)“没有比这个原状和修复更统一的设计。”
[43] See current controversies over proposals for new build at Edinburgh Royal High School, e.g. at https://www.ahss.org.uk/saverhs/.
[44]“舒适性”指历史建筑、历史环境的特征、外观、布局等方面给人带来的舒适、愉悦的生活感觉。
[45]例如,IHBC的行为准则规定,“历史建筑保护学会所有成员的职责是促进和保护这一已建成的遗产。 See https://www.ihbc.org.uk/resources/A4-Code-of-Conduct.pdf.
[46] 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Contrasts : or a parallel between the noble edifice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corresponding buildings of the present day; shewing the present decay of taste.“, 1836.
[47] William Morris, ”The Manifesto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The SPAB, 1877; see https://www.spab.org.uk/about-us/spab-manifesto.
[48] Ibid.
[49]”A Thing to Mind: The Materialist Aesthetic of William Morris“, Jerome McGan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 55, No. 1 (Winter, 1992), pp. 55-7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50] See for example ”British Planning History, 1900-1952…“,at http://www.rtpi.org.uk/media/828289/british_planning_history_1900-1952.pdf.
[51] Anthony Sutcliffe, ”Britain's first town planning act: a review of the 1909 achievement“, Town Planning Review,Volume 59, Issue 3.
[52] Edmund George Bentley, and S. Pointon Taylor,‘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 Act, 1909, a practical guide… with a foreword by Raymond Unwin’, London,1911, p 129, Appendix B, ”PROCEDURE REGULATIO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OARD, MAY 3, 1910“, Article XIII: “关于准备或采用方案,地方当局应认真考虑任何有兴趣或受影响的人或委员会,包括代表建筑或考古学协会或其他人的书面形式提出的所有异议和陈述”。
[53] Ibid., “Author’s Preface”, p.vii.
[54] Ibid., with the transcribed text broken into paragraphs here to highlight the content themes.
[55] See http://www.jcnas.org.uk.
[56] 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trick_Geddes.
[57] See, for a practitioner’s take, e.g. https://www.ads.org.uk/outlook-exploring-geddes-in-the-21st-century/.
[58] This also anticipated the conservation model of“Evaluate, Manage, Intervene”used in the IHBC’s Conservation Cycle, discussed apart.
[59]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67/69
[60] Lucy E. Hewit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ivic Society Movement, Civic Voice, 2014. Quote taken from a speech made by Duncan Sandys at the Civic Trust Conference on the Civic Amenities Act, 27 October, 1967 (Civic Trust Archives).
[61] Dr Deborah Mays, “The History of Listing”,unpublished paper, Historic Scotland, 29 May 2008. Based on “Listing in Scotland: Origins, Survey and Resurvey”,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ncient Monuments Society, Vol.38, 1994:32-94.
[62] See “COTAC Half a century on”, downloadable at http://ihbconline.co.uk/newsachive/?p=2252.
[63] For “Edinburgh Group” resources see http://cotac.global/edinburghgroup/ http://www.understandingconservation.org; and http://www.understandingconservation.org/content/conservationaccreditaton.
[64] Bernard M. Feilden’s Draft “outline profiles of the main professions who may be asked to collaborate in a project for conservation of a Monument, Ensemble or Site,in the UK. ”COTAC Conference on Training in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Conservation Projects in the UK Based on ICOMOS Guidelines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Conservation of Monuments, Ensembles and Sites” .http://cif.icomos.org/pdf_docs/Documents%20on%20line/cotac.pdf.
[65] See https://www.the-nhtg.org.uk.
[66] NHTG, 2005: “TRADITIONAL BUILDING CRAFT SKILLS,Assessing the Need, Meeting the Challenge; Skills needs analysis of the built heritage sector in England 2005”.See https://www.citb.co.uk/documents/research/nhtg_skillsresearch_england_report2005_tcm17-6857.pdf.
[67]“The Context for Skill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John Preston, in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JAC),Vol. 12, No 3, Nov 2006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Ed. Vincent Shacklock, Donhead Publishing Ltd,:35-48,38.
[68] See http://ihbconline.co.uk/context/1/. For the full online archive of Context see https://ihbconline.co.uk/cont_arch/.
[69] For full details of the IHBC and its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resources, see links form http://www.ihbc.org.uk.
图片来源
图1:作者提供
图2:作者提供
图3:http://ihbconline.co.uk/toolbox/docs/Conservation%20Professional%20Practice%20Principles_A5%2FINAL%20 May%202017.pdf
图4: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uston_Arch_1896.jpg
图5: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File:Stpancras.jpg# filelinks
图6:https://ia801403.us.archive.org/18/items/housingtownplann00bent/housingtownplann00bent.pdf
图7:http://ihbconline.co.uk/context/1/
图8: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