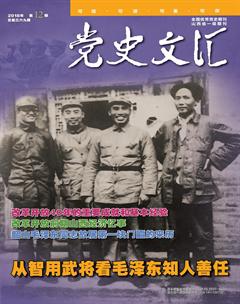读书人
屈戎
《读书》杂志2018年第7期的封二上,登载了一篇署名王蒙的配画文,《戏子》(以下简称《戏》文),画是康笑宇所画,题曰“尊重”。文章主要有两个意思。
一是因“有关部门对于演员的收入做了些规范规则规定,网上出现了一批大骂表演艺术家的言论”。什么言论呢?说:“演员在旧社会称作‘戏子,如何如何没有道理。”于是,引起了《戏》文作者一番严厉指责。
《戏》文作者谓,由于“长期绝不公正的封建等级观念”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仍然根深蒂固,又“死灰复燃”了。因此判曰:这是“野蛮丑陋”“乖张暴戾”。进而申论:“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尊重艺术劳动”,是“先进文化”。而“污辱文艺行业,污辱表演艺术”,正说明“这种人是多么可怜”云云。
固然,发论者将现今的文艺工作者与旧社会的戏子作简单比附,确实不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叫“读书人”。在封建社会的某些朝代,比如说元朝,“读书人”的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据有关记载,元朝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在乞丐之上,娼妓之下,所谓“八娼九儒十丐”嘛。如果因此就说新社会不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还应该将他们放回到元代的地位去,那就更是大谬不然了。
因此,《戏》文作者就此提出批评是对的。不过,对归对,但逻辑上却不是那么严谨。《戏》文中,出现一些概念,诸如“演员”“明星”“表演艺术家”“艺术家”“文艺行业”“表演艺术”以及下文“艺术工作者”等概念。凡概念,都有其一定的内涵与外延(比如,读过《读书》的人,和“读书人”就不是一回事了,如果不加区别的混用,便很容易出现逻辑上的错误)。比如,“骂”个别演员,不能就说成是骂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想来发论者一定是有所指,由于笔者未见到过网上这类文章,不好判断所指为个别“演员”,还是所有艺术家。如果指的是前者,则显然没有波及到整个艺术家群体。更不能由此推断出是污辱文艺行业,污辱表演艺术。
鲁迅曾在《论辩的灵魂》一文中谈到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曰:“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倘若进一步推断:“中国人从事各种行业,有企业家,银行家,艺术家,理论家……你罵中国人,就是骂各个行业,就是骂各个行业的什么家或从业人员。”如此推断,可乎?!
《戏》文的第二个意思呢?是在对一批发论者严责之后,继而提出几个问题:一、“我们的一些演员的自尊自爱自强做得如何?”二、“为什么有的艺术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变得那样不堪?”三、“艺术家的基本品德、基本素养、基本面貌到底是不是出了某些毛病?”
对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没说原因。对于第三个问题,到底也没说清毛病出了没有。问毕,认为上述演员或曰艺术家“也许这里有可以反求诸己的地方”。按,是“也许”,尚不一定。
看起来,对发论者和某些演员或曰表演艺术家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对待两方面的区别是明显的。对于前者责之偏严,而对于后者则大都用不确定的设问,似有过轻之嫌。须要知道,前者观念落后,可以说服教育。而对于后者,如果像有关方面披露的那样,该纳的税变着法躲避,那损失的可是国库里白花花的银子,由此而对社会风气产生的负面影响尚未计算在内。这已不是轻轻一个“反求诸己”即可了事。要求这些人照章纳税总不算过分吧。但《戏》文中只字未提,是不是可以算作一时疏忽呢?不难看出,虽然同样是五十大板,对前者是举起来着实落下,对后者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如此一来,畸轻畸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逻辑归逻辑,《戏》文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那就是:发论者的“本事与处境距离‘戏子们十万八千里。”可以说,两者各方面的差距确实不小。仅就收入一款,与那些明星们比起来,恐怕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实属可怜。但是说差距大“才会恨得牙根疼”,则不竟然,至少不全都是。至于“以为明星会被收拾得与发论者一样惨淡”,这是发论者“以为”,错了。我可以回答,这绝对不会。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面对不合理的现实敢怒不敢言,即使愤满至极,为了远祸保身,也只能如元代张可久在一首散曲中写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今天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新时代,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保障下,对一些不良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是非明确、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的评说,应该不是难事。假设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是否该和元朝那位张先生商量,把他那句曲语改一改:一声长叹读书人。
顺便申明一点,这里的“读书人”是特称,绝没有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表示失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