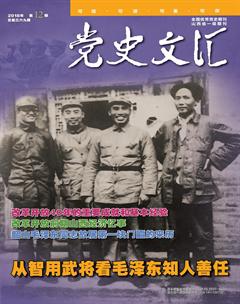改革开放前期山西经济忆事
吴达才
笔者原先在省化工厅工作,1983年春进入省级班子,故对参与较多的改革开放前期山西经济情况忆之。
能源重化工基地的规划与实施
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需求,解决能源保障成为迫切和十分重大的议题。山西作为我国最大的煤炭产区首先得到重视。1979年秋薄一波来考察调研后,向中央报告提出建设山西煤炭能源基地。1980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尽快把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随后,国务院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编制六五计划(1981—1985)时明确提出要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进而批准由马诰带领国家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开展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综合研究。参与者有国内著名专家(含中国科学院、社科院所属有关研究所,若干著名大学等)近300人,省内专家及科技人员八九百人,马诰提出了总指导思想:方针正确,结构协调,布局合理,资料可靠,论征科学,措施得当,切实可行,经济效益良好,使人民能得到实惠。应该说,这个提法是正确的。其核心思想是:国家应支持充分发挥山西的煤炭资源优势(当时执行的尚是计划经济体制,列入计划以取得国家支持是首要前提),把山西建设成为“以煤炭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我受化工厅党组委托,负责主持化工部分的规划。省计委、煤管局、电力局、铁路局、化工厅、水利厅、交通厅等都投入大量精力从事规划事宜。在国家层面,国务院组建了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由国家经委资深副主任郭洪涛任主任,我省副省长郭钦安任副主任。
全省上下,对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抱有高度热忱,非常积极地投入。然而也遇到迷惑费解之事。当我赴京向有关部委请示汇报时,他们对山西的煤炭增产及外运极重视,包括化工部对供应全国不少化肥厂所用的晋城无烟块煤都很重视(乃至珍视);而对重化工则很冷漠且没有具体概念:是重工业加化学工业?还是化工行业内部相对于日用化工、食物添加剂、油漆等轻工而言的重型化工?都不了解且未接到上级指令不作答复。此时,我们还认为,待国家批准了山西的规划、纳入全国统筹安排后就可获解决。但当省里把规划正式上报后,国家并未正式批复,只电话回答说:原则上可以照此安排工作,不再正式批复了;大型建设项目可按规定程序分项逐个申请报批。
回顾10多年来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出,仍是突出发展了煤炭生产及其外运能力;电力有发展但达不到基地水准;重化工则更差,下边略加评述。
煤炭无疑最受重视且高速增长,从1980年的1.21亿、1990年2.86亿吨、1994年3.24亿吨,相应地调往全国各省(市)的煤量分别为0.74亿、2.03亿和2.24亿吨,约占全国跨省(市)调运量的76%至78%。这就为支持国家发展有力地提供了能源保障。这除国家兴建的大型矿井外还得力于乡镇村等集体所办和私人煤矿的发展。这些煤矿的产量从1980年的4800万吨跃增到1996年的1.63亿吨,即占了全省产煤量的半壁江山,对提高农民收入起了极大作用。期间,焦炭产量急剧增加,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焦炉虽并未增加多少,1980年之后只投产100余万吨/年,但总产量从1984年的400万吨/年激增到1994年的3500万吨/年,所以,直到90年代中期所增加的产能主要是土焦和改良焦的能力,引发不少问题。除全国钢铁产量跃增对焦炭需求旺盛和山西的焦煤储量多(占全国一半)、质量好、炼焦工艺短等直接原因外,還与山西原煤的外运能力不足也有关连(炼焦可减少运出量)。
为此国家下大力气搞铁路公路建设,除对在80年代原有的石家庄—太原及太原—焦作、大同—风陵渡这三大干线进行双轨及前两条的电气化牵引改造外,还先后兴建了大同—秦皇岛、陕西神木—朔州—阳泉—涉县—黄骅港等3条运煤专线,尤其大秦线是我国首条重载列车双轨电气化运煤专线,初期运力4000万吨/年,现已达1亿吨/年,为全国专线运力之首。同时还兴建了多条公路,打通了与外省的10个出口,公路货运量(含省内运输)从1980年7004万吨增加到1985年1.3071亿吨、1990年2.6706亿吨和1995年3.9776亿吨。
发电是煤炭的主要用途,增值也较明显,山西省由1980年的248万瓩发展到2000年的1275.64万瓩,发电量占全国4.85%、第8位。发电能力虽显著增加,尤其是前期向京、津送电的大同、朔州的大型电厂(附相应输电线路)和90年代下大力气建起向江苏输电的阳城电厂等大型项目,但在全国不到5%的占比和第8名的占位还达不到“基地”的称号。至于“重化工”则更未引起重视和列入国家重点安排,1982年化工部表示对山西主要有两条要求:将早先就已安排的建于潞城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煤制大化肥引进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建好(1983年夏开工);山西应保证供应每年1000万吨的晋城无烟块煤。此外,其他新项目主要依靠山西自行安排,依规定程序报批。
作为化工部分规划的主持人,我组织有关人士分析评估了国内外煤化工发展动态和供需趋势,结合山西已有化工产品结构分析,在规划中除适当安排传统化工基础产品如化肥、煤焦油加工利用等外,重点推介安排了国际新型煤化工趋向且其技术已基本成熟、可以实现大型化、国内科研单位已做了较好基础性研发的一碳化学(C1)或甲醇化学的煤炭转化新路线,即将煤炭在新型氧化装置中气化、净化,制得主要成份为一氧化炭和氢(CO+H2)的合成气,然后通过先制取甲醇再将其加工转化或不通过甲醇直接制取,可得到合成燃油、乙烯、丙烯(烯类原先均需由石油裂解制取,再加工制成一系列纤维、朔料、橡胶、涂料等,称为石化工业),就可成功实现煤化工与石油化工的对接,从煤炭制得大吨位的有机化工产品和合成材料产品。我国多煤少油,通过煤取代石油或从煤制取油品是现代煤化工的主流。陕西化工厅当即派专家来太原与我们交流并先于我省付诸实施。这个在80年代初提出的新型煤化工(过去固囿于煤制化肥、电石及煤焦油的加工等)路线,当时既新又大胆。但因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国家对山西主要要求保证煤炭供给,对兴建大型新煤化工装置暂时未列入议程。新开发的陕蒙宁煤炭基地投产后因其与沿海主要耗煤区的运输距离远长于山西且一般均要通过山西地域方可运出,因而对该地区煤炭就地加工的迫切性远大于山西,加之神华集团等央企的优势,自90年代以来30年间,国家在该“煤炭金三角”地区建设了10多个巨型的采用上述C1路线的煤化工项目,如年产百万吨级的甲醇及下游加工,百万吨级煤制烯烃、煤制合成油、煤制甲烷(即合成天然气)等;其中百万吨级煤制合成油投产时,习总书记曾亲自发了贺电,可见国家重视程度之高。此C1路线在陕蒙宁接壤区大规模实施开花结果,我作为始作俑者非常高兴,但山西首提此路线却还未启动,又未免使人怏怏。从陕西调来的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到任不久就在讲话中指出了山西在这些大型煤化工发展领域的滞后差距。当然因这些项目动辄耗资数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没国家支持很难兴办。近10多年来山西一些国企民企兴建了些10多万吨至五六十万吨级的C1煤化工项目,少数已投产,多数尚在建。虽起步晚了但要比不动好。至于省内对此方面的科技开发则集中于扶植由中科院煤化所进行的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即煤先气化后由一氧化碳和氢气合成燃用油。该所还分别在代县化肥厂、晋城化肥厂进行了百吨级、千吨级再后在潞安矿业集团十万吨级的放大试验,再在此基础建成百万吨级的巨型装置。其荣获习主席的电贺,新华社对此报道时专门提到这是在煤化所的技术基础上建成的。
回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实际依然是“挖煤为主,一煤独大”,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给山西带来很严重的不良影响。晋煤约70%左右、个别年份达80%是原煤调出,一方面在省内没有下游产品的增值链,不产生除了运费以外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国家对调拨出省的煤价又管制很严。因此,山西人民在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未能得到应有的实惠,反而在全国占位从居中降成下游。统计显示,在1980年至1995年间,国家对山西省的投入从全国3%降为2.5%;到1994年,山西GDP总量占全国比重从2.4%降为2.2%;人均GDP与全国人均差距由19元扩大为900元,1994年山西城乡居民收入都远低于全国水平,分居末位和第26位,都比1980年明显后移。由于采煤对水资源、尤其地下水破坏很大,排出污水量大而难以利用,使许多著名泉水的涌出量骤减,如神头泉、娘子关泉水、辛安泉等皆然,特别严重者如晋祠难老泉。采空区塌方时有发生,农民概括了8个字:井干、树死、地陷、群裂,可见一斑。发电方面,那时对所排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都未处理,污水、煤灰的排放也很随意,有顺口溜道:烧了煤留下灰,排气呛人耗掉了水。而且电力管理体制也损伤了山西的利益。大型电厂都是央企,由华北电管局统一核算。山西电厂送往京、津的电由华北局按企业内部价付款,起初只有每度9分,后经几次争取才上调到每度1角2-3分。发电厂资金由华北局另拨。京、津用电价当时为0.5元/度上下,旧京、津的电费是华北局收取,连税金(跟售电走)也交给京、津的税务局,这种方式实在对山西太过刻薄。另外,当时山西新装十万瓩以上机组大多是国内刚制成或东欧国家供应的产品,不太成熟,故障较多。为保证京、津用电,出故障后只好压减省内用电而保输出电量,故在80年代山西常停电,农村电网尤其严重,老百姓戏称:农民买彩电,就是看不见,刚刚来了电,很快就再见(电视终播时说再见)。
开发区的创建与坚持
我省到1990年一个开发区都没有。结合当时国家号召关注新技术革命、注意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的情况,我向王茂林、王森浩两位主要领导提出创建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议,得到同意。于是组织有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到国内外相关单位参观考察,选拔物色恰当人选,开始组建开发区。在征得国务院开放办公室和国家科委同意后,我们先选定基础条件较好的长风街南、中辐院西的一块空地起步,开始招商。形成现在太原高新区的基本格局。一年内,就有激光全息摄影防伪商标、铂系三元催化网及铂灰回收、高纯钨棒、新型油墨等企业入区并投产,初步站稳脚跟。1992年冬,被批准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我省首个国家级开发区,给了相关工作人员很大鼓舞,大大增强了信心。时任太原市领导的王昕、王晓林等对高新区的建立和发展贡献良多。此时各地(市)也纷纷要求建立开发区,经新到任的省长胡富国批准,设立了山西省开发区工作协调领导组,我任组长。批准省内首批8个省级开发区(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临汾、长治、风陵渡),其中长治申报为高新区,其余都是经济开发区。我数次召开领导组会议,对各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功能、土地工商税收等优惠规定、管委会的级别待遇等作了规范,以正式文件下达。还确定由省体改委的一个处联系各开发区的日常工作。这8个开发区的起步都不错,太原市更领先些。每个区产出逐年以20%以上速度递增,远高于所在地(市)的平均水平,而耗费的政府投入却并不高。国家主管开发区工作的开放办主任胡光保来晋考察后表示肯定和支持。
1994年开始,国家针对各地设立开发区过多过滥、良莠并存的情况下令整顿。我省有跟“风”者提出要制止和除去一些开发区,我不同意。恰好此时,新任国家开放办主任胡平来晋听了汇报、看了几个开发区后明确指出:“山西对外开放起步晚、步伐慢,开发区建设尚属初创阶段,谈不上过多过滥过热,关键是下大力气把开发区搞好搞大,推动开发区的发展,增强其活力和对当地经济的推动。国家除要抓好沿边沿海的加快开放外,对内陆地区沿交通干线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山西的开发区布局符合此要求。”由此打消一些人的疑虑,不仅保留了各省级开发区,还放手促其发展壮大。虽各地财政投入很有限但各开发区的成长速度都很显著,高的达年均50%左右。1995年后,我转任省人大职务后主动辞掉开发区协调工作领导组组长、煤化工发展规划领导组组长,退出此项工作。
骆惠宁、楼阳生出任我省党、政主要领导后,对开发区工作十分重视,并将之与国务院批准的能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紧密结合起来,大手笔地把太原市和晋中市的几个开发区、大学新校区、机场保税区等统筹整合,形成大开放、大改革的综合发展试验区,这必将大大改变我省开放的后进面貌、促进转型创新的步伐,实现弯道超车,为调整我省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加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科技为经济服务
1、省筹资金选派出国留学人员
针对改革开放需要,提高教育与科研、农业、卫生等领域的技术人员水平、更新并吸收新知识,以及时跟进世界前沿,十分必要。由于历史原因,国家统筹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中山西能得到的名额很少,远不能满足需求。1984年,省里决定,每年从地方留成外汇中拨出100万美元连同配套的人民币(后增为150万美元),派遣中青年骨干作为省派留学人员,出国攻读学位或进修提高。此项工作受到省内热烈反响和全国好评,一直延续至今(从90年代起此专项基金内有一部分改为资助归国留学人员改善其科研和工作条件使用,以更好地吸引他们歸来)。1985年至1993年共派出648人次,对提高我省教育、科技水平,作用显著。如彭堃墀、谢克昌分任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并分别当选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谢还出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李悦娥、侯晋川、聂向庭、祁寿椿、赵国浩、张少琴等都成为著名教授并出任所在院校领导,卫小春成为著名骨科专家,他们中绝大多数还成为省级领导成员。
2、启动对外科技交流
1984年冬,为执行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中能源项目名下的洁净煤小组的技术合作商讨,国家科委指派该小组中方负责人、煤炭科学院院长范维唐,国家科委二局高工范铭义与省科委主任的我赴美商谈合作并参观访问相关科技开发单位。我国科技及环保人士虽知原煤直接燃烧的污染较大但对其危害的严重程度缺乏感性认识且对洁净煤(CCF)技术尚较生疏。在商谈煤炭利用时中方提出过多项建议,美方(美国科学院与工程科学院牵头)均不感兴趣,坚持要以洁净煤技术(CCF)为合作主题。现在回想,美方很有远见,前瞻性很强。因他们看准中国20世纪内仍将以煤为主要能源,而当使用数十亿吨/年的煤直接燃烧将带来极严重的环保困境,非走洁净利用方式不可。进入新世纪后习主席很重视此工作正大力强化中。
11月抵美后,我们考察了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匹茨堡能源研究中心、位于加州的世界首个燃煤联合循发电、位于北达科他州的世界首座工业化规模的煤制甲烷气工厂、肯塔基州的煤矿及矿井安全示范技术、肯塔基大学等。与美方组长、肯塔基大学采矿系主任任纳德教授,副组长、贝克特尔工程公司(美国十分重视从科技合作走向工程合作,该公司规模巨大,时任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均出身该公司)副总裁高斯等会谈。商定下次会1985年在太原召开,开启山西与美国科技交流序幕。为作准备我启用了洁净煤技术的一个形式,即利用煤制成的甲醇以15%至20%直接掺入汽油(另有少量增溶剂)供汽车运输使用。由国家科委拨款,省科委会同交通厅共同组织,在长治运输公司和临汾运输公司各指定一个车队,在之前两三年10多辆车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投入475辆货车大规模试运行,运行一年的重载实验测试,并由省交通科学研究所进行室内台架全方位测验和对载重车队的跟踪配合与相关测定。一年的运行正常、成效良好;节油及降低成本均较明显,达到预期效果。这为我省在90年代后在长治和晋中推广甲醇—汽油燃料和纯甲醇汽车打下良好基础。试验资料在1986年于巴黎召开的国际醇基燃料会议和1993年在匹茨堡国际煤炭大会上交流。1985年在晋祠宾馆召开了中美第二次洁净煤技术交流会,上述山西的甲醇—汽车燃料试验由中方着重介绍,与会代表到汽运公司现场观摩,获得肯定。这是在山西首次召开的国家级科技交流会议,主管外事工作的白清才副省长很重视,曾特指定一位副秘书长对会议全程驻会安排好后勤事宜,会务则由省科委负责。
在软科学研究方面,国际上有个著名机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即在70年代作为东西方合作桥梁由美国、苏联、西德、英国、东德、波兰等两大阵营共17个国家联合组建起来。1985年,该所所长、美藉华人李天和博士访华,与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签署了合作协定,将首个合作项目选定为“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决策应用系统”;后因基础资料不足,改为“决策支持系统”,由该所承担。中方派有关专家赴维也纳到该所参与合作研究。国家科委决定由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著名电脑应用专家王众托牵头,其余参与研究人员由山西派遣。我省从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省自动化研究所、省科技战略研究所、省计委计算中心、太原理工大学及省科委机关等先后派出约20名科技人员(包括后来出任省级领导的谢克昌、王昕和出任山大校长、省科委主任的李镇西等)前往,分别进行3个月到1年多的合作研究。虽因前述过的基地规划目标内涵不明朗、基础信息又严重不足,该课题完成后的可应用程度不够,未能提供实际应用,但确实为我省培养了一批电脑的开发、应用人才。80年代中期后,科教对外开放、交流逐步进入正常轨道,不再赘言。
3、改革科技工作服务方向
早在改革开放初1978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此后又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与现在国家强调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实现弯道超车一脉相承和完全一致。可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科技工作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却并未这样明确,除国防系统较好外其它领域经济与科技脱节严重。在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即资金、劳动和技术进步中我国的技术进步曾长期滞缓。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占比达70%以上,中等发达国家一般为50%左右,而我国占比更低。经济与科技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亟待改进。
因此,科技改革重点须放在突出面向经济建设这个基点上。当然,对省级科研工作而言,也有少数具有较好基础应予支持的基础科研项目,如山大的光电子实验室。但对多数省份来说此类基础性科研很少,仅北京、上海等极少省市的比重稍大一些;对多数省市尤其是山西这样中等偏下的地方占比极小。工作重点更须放进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对某些特大型企业如太钢、太重、大同柴油机厂、六大矿务局等,主要鼓励其建立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等,自主或与设计、科研单位联合搞技术开发,取得很好成效。如太钢在80年代初自主开发的氧炉冶炼不锈钢、压制特薄不锈钢片,太重不断开发大型和特大型挖掘机、油膜轴承制造等。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开发也得到显著提升,如支持盂县永磁材料厂开发了稀土永磁材料并不断推广,使山西成为全国稀土永磁基地,成品远销欧美日本。从80年代初起,山西焦炭产能激增,从1984年的400万吨增至1994年的3500万吨(21世纪初一度达到1亿吨产能)。但增加部分大多為民营企业,缺投资、缺技术、规模小等,第一桶金大都来自坑式土焦或所谓萍乡炉,烟雾弥漫、污水横流,有些地方一度成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极大浪费了宝贵的焦煤资源,破坏了环境。但因这是农民的初级致富之途,一时尚无法硬令禁止,只好逐步引导。我们投入资金和组织科技力量不断引导它们改造升级。从吕梁炉、XX炉、75炉、JHK炉再过渡到大型机焦。其中JHK炉无论在煤耗、环保、焦炭质量等方面均可达到甚至个别优于大机焦,与90年代中期美国阳光煤业公司开发的热回收(只回收热量,不回收化工产品)相似,而建设投资只有大机焦的15%左右,曾由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和国家环保局准予推广和推介。在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方面,大力推行星火计划,即以实用技术推动农业、养殖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支持并增加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此文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回忆》编委会荐稿〕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