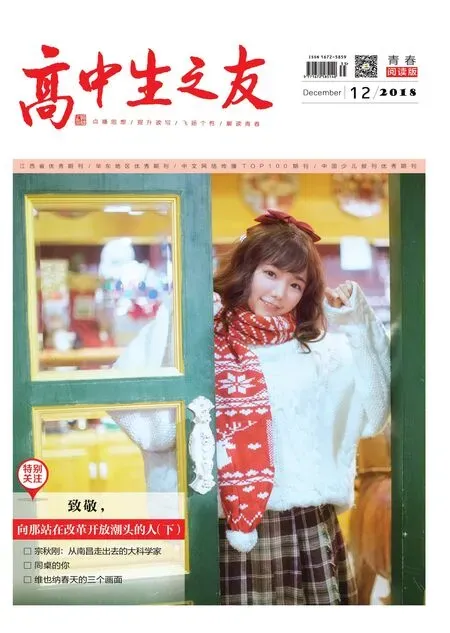吕本中《采桑子》:以俗蕴雅,以拙藏巧
○彭洁明

古人写月,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表乡思,如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之“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或写爱情,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或抒怀抱,如阮籍《咏怀》之“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凡此种种,给“月”这一意象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不过,我们如果略作浏览,便不难发现,在写月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是将其作为思念的维系。古往今来,以月为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如何能在众多同题之作中独具一格,脱颖而出,也成了作者们着意的问题。吕本中的《采桑子》,无疑是一首别出心裁的成功之作:
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吕本中是两宋之交的著名文人,诗近“江西诗派”,词则专精小令,风格清新自然,有学者认为其词与韦庄词有相似之处,不事雕琢,别样风流。此词以月写相思,虽句句不离月,但句句用意皆在相思而不在月,以月为宾,而以相思为主;以“恨”为宾,而以“恨”字背面的“爱”为主,在思妇词中堪称佳作。上阕云“恨君不似江楼月”,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人和事物——心上人和月相比,恨其“不似”,原因何在?因为月影随人,万里无违,而自己与心上人则聚少离多。下阕云“恨君却似江楼月”,从表面看,它与上阕表意完全相反,但若细品我们就能体会到,两部分立意完全相同,都是以宾陪主,正话反说。为何“恨君却似江楼月”?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间无常,与之相似。
这首词表面写月,实际上落点在相思。此词言“月”,言“君”,并不直言“我”,而“月”下“君”前,那个大写的“我”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是寂寥的、怅惘的,同时又是满怀期待和热望的,这种带有苦痛的企望、不因无常而停止的爱,其张力和生命力,自然能够深深地触动同怀之人。
此词调寄《采桑子》。词为双调,上下阕各四句,为“七—四—四—七”结构,押三平韵,上下阕同。此调特殊之处在两个四字句,有时可采用叠句,均入韵。这种完全重复的叠句,使得此调天然带有类似于民歌的风格。而吕本中此作,在采用叠句的同时,又设置悬念,先出惊人之语,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再揭示原因,巧妙扣合。上下阕句意表面上相反,实则具有内在一致性。
苏轼的《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上阕云:“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词作以雪与杨花的相似性,关联起别时和别后这两个场景;又以“雪似杨花”和“杨花似雪”的类比,注入今昔的感慨,将沉重的时间感寓于轻盈的民歌风格的譬喻之中,奇正相生。吕本中的这首《采桑子》,或许就受过苏轼此词的启发。
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首词是典型的结构具有对称性,意义具有对比性,但又用一条意脉贯串的作品。辛弃疾写作这首同调词,也许就受过吕本中的启发。
我们不难看出,吕本中写作此词,是运了不少巧思的。而细读他的其他作品,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同样有民歌风格的作品,譬如以下二词:
踏莎行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
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减字木兰花
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 故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去年。
况周颐《蕙风词话》云:“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二词就是以情驭景、景在情中的佳作。作者有意运用了对比、回环的手法,加以浅近的语言,自然流丽,读来口舌生香,似乎毫不用力,却绝非庸手能办。
不止吕本中,不少文人创作诗词,都曾有意借鉴民歌的手法,包括叠字、顶真、双关、谐音、复沓、对称等手法。饶有趣味的是,在历代不同的批评家对此的态度中,有的竟完全相反:褒扬者称其清水芙蓉,得趣天然;贬斥者称其东施效颦,惺惺作态。其实,就文学史的发展而言,各种文体在初兴时,都是发源于民间的,但自成形至繁盛,往往都经过了文人化、案头化的过程。虽不必刻意强调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分野,但两者无疑已有了不同的审美范式,读者阅读时,其心理预期也有所不同。所以,雅俗之际,巧拙之间,能够游刃有余,非易致也。
大略而言,初学者不宜求巧,取法须高,入门须正。在熟练掌握了文体的审美特性并积累了比较深厚的创作经验之后,可以尝试突破。或求巧,或求拙,法虽殊途,旨则同归——其一,此乃自我突破,创新尝试,并非常法,往往可一不可再;其二,倘若还未到圆转如意之境,则宁拙毋巧,宁重毋轻。此外,再好的“巧思”,也有其局限性:初见惊艳,再觏转觉寻常,事过回想,则往往略无遗韵。究其原因,在于过“巧”则伤气,过“工”则伤韵,过于经意,往往不够深情,而深情和气韵,本比精巧的结构更加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