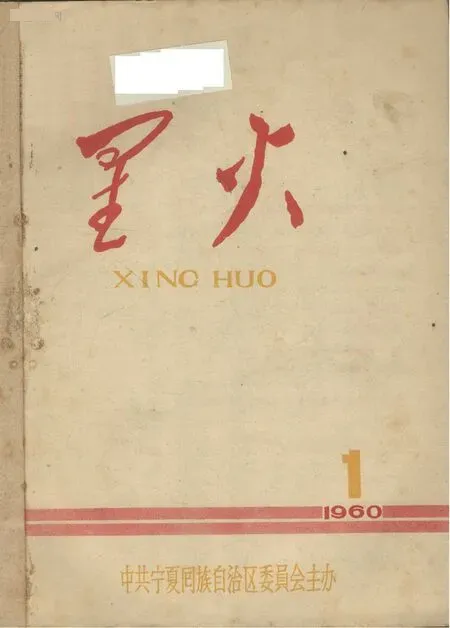今夜,风将抵达你的唇上(组诗)
○诺苏阿朵
今夜,风将抵达你的唇上(组诗)
○诺苏阿朵
请 求
此刻醒来的,干净的四野
请嚼着草,像嚼钻石上的光芒
能阅读,能开花
让那些藏在石头里的额头
提着灯盏,回到密集的寺庙
如果没有嚼到钻石上的光芒
嚼到黄沙,那也要感谢饥饿的天空
留下了星斗,抬头就看得见
自己在自己的命里磕长头
四野要是继续醒着
那嚼嚼风,嚼嚼摇晃
嚼嚼嚎啕大哭
嚼嚼最后一次相遇
实在嚼不动了,就让
云朵跪在地上
请求穿红色袈裟的僧人
赐一个完整的灵魂
继续爱着人间
我有高原上的孤独
在风尖上
太阳被两个人溺爱
天空像哑巴
独活着舌头上的大海
石头永向苍穹
搅碎远方
芨芨草赤脚
在霜雪上洗一遍穷苦
干裂的嘴唇
与情歌相依为命
死在眺望里的悲伤
和野花一样好看
一列火车要到哪儿去
这清晨的轨道
顺着二月的天空
飞出鸟鸣般
长调
这绿色的骨头
活在赤裸裸的高原上
遥远又迅速
这明媚的腰身
挎着路人
缝隙
远方和与你有关的黄昏
今夜,风将抵达你的唇上
风姓滇西北的姓氏
裹着月光煮雪的气息
夜色正紧
我需要七双靴子
一条缰绳
拉走所有的隘口
风要从什么地方来
我喜欢风从马背上来
突然拿走你唇上的
空旷四野
那时有一定数量的爱情
簌簌落下,惊动心跳
让舌头更加靠近
戒 指
一定是一封没有邮址的信件
套在我的无名指上
燃烧了一次黑夜之后
徘徊过的挣扎
屹立成
雪山
靠过来
一片一片
银质的疼
被清晨喜鹊的叫声遮蔽
与你有关
每一个岔口像极你的背影
连踉跄的月光,滑倒的花朵
都像极了。
你去过的北方呵
就这样盘踞于此
入夜后
哦,仅凭山鹛鸟发出的声音
我会泪水盈眶
也会
挑选一场大雪
在头颅上洁身自好
劲 敌
和一根草较量
我可以死一次
而它,年年复活
占据天空
但也,不要用一片草滩
挑衅我骨头中的跃跃欲试
在这里,绿过鬼魂的雷电会击中我
我不翻身下马,也
决不坠入马腹之下
我的死要悬于蹬
梦里敲门的人
吃完了所有的灯盏
夜打着响鼻
惊醒一双白天的眼睛
梦
明明死过一千次了
而我们的对视
在热爱过的事物里
再次起身
你说过的梅花
从冷下来的那个月份开始
粉色的雪
请一朵一朵地开
不深不浅地开
这样我可以不用光
贴着爱慕
读一封二十年前的信
黄昏平坦
山岭高高跃起
更多的天空围拢过来
十万公顷的暗香
在两个人之间
若无其事地
轻轻脆响
风吹着风
风吹着风
碱地上
盐贩,捏着烈日
停止叫卖
想起愿望
他用眼神拽下一根青草
担住
痛哭的生活
风吹着风
我在教堂忏悔
又和信仰
讨价还价
千里之外的大海
扔出腥味
嘲笑,一圈又一圈荡开
一只猫走过,从不正眼
看我
交 出
我交出朗读,老鹰放下盘旋,一条蛇在寺庙外,
庄重转身。我交出祭奠,有死去的人,
在赤脚走过的民间,复活。我交出财物,
二十四节气,让一个火命的人,在
薄薄的纸张上,春种夏收。
我交出城市里的爱和恨,故乡
才允许我,抚摸一次
核桃大的灵魂
我在岸上养鱼
没有湖泊,没有水溪
没关系,岸上有草,有虫鸣
有咬住耳朵的花蕾
有温顺在怀里的月亮
有蓝得倔强的马背
旷野,更像少年
仿佛,这岸上
藏着整个西藏
有时
我只抽出一个拂晓
慈悲就叮当作响
何况
我的心口,还有一层鳞
对阳光,恭恭敬敬
有了这些
我多么容易
就听见
一条怀孕的鱼
回到岸上产卵的声音
从春天开始失明
从春天开始失明
花就开在我摸得到的地方
窗台,旧藤椅,收音机
茶杯边沿和一只猫的耳朵尖上
深一脚浅一脚
而风也必是饮尽一蓬蔷薇,半坡荞花
暗合我眼中黑夜的酥软
慢慢加深整个身子里
蹲在地上那部分的斑斓
我听清了
一片最小的阳光
含着苞
微微鼓起桃唇
忍着小欢喜
像正在走过来的一个旧人
轻易的
我摸到所有死去的形态都活过来
鼓
一定要敲出声响,我的骨头上还有一粒孤独
孤独里有雪山
雪山里还藏着长刀
耳朵酥软
常常取走刀鞘
一定要用力适当
若敲破我的铁石心肠
这个世界上只剩下
一张牛皮眺望一亩地的信仰
黑井,前生的雪
盐可以落在这里
雪也可以
只有飞来寺
未落下
这样多好啊
低着头
也接得住黑暗
还能
化解拂晓
内心的盐,像雪一样白
供我舔舐大海

诺苏阿朵,本名普蓝依,彝族,出生于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有作品发表于《解放军文艺》《陕西文学》《云南日报》《滇池》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