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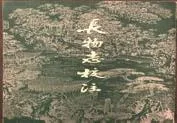
长物志校注
作者:文震亨 原著;陈植 校注;杨超伯 校订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长物志》:一部明代园林与生活美学读本
在中国古代造园著作中有三部最为系统,即《园冶》《长物志》《花镜》。其中《长物志》叙述较简略,但涉及范围最广。《长物志》成书于造园学说兴盛之明末,与《园冶》并称为“古代造园艺术双璧”。书名“长物”,取“身外余物”之意,本于《世说新语》王恭故事。《长物志》作者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明末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曾祖文徵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共同被称为“明四家”。震亨少而颖异,天启元年(1621)以诸生卒业于南京国子监,后因琴书知名,崇祯中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文震亨一生著述颇丰,计有《琴谱》《开读传信》《长物志》等,但很多遗稿散佚。
《长物志》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年),全书十二卷。分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类,各为一卷,包罗万象,用现代学科来说就涉及建筑、园林、植物、动物、矿物、艺术、园艺、历史、造园等各方面知识。《长物志》对晚明士大夫的生活日用文化及其精神追求,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概要,比较全面地表现了晚明文人生活美学观念,是研究晚明物质文化、建筑营造、文人生活、造园艺术的重要资料,也是古代造物艺术理论的代表。相比于大约同时期的《园冶》,《长物志》更多地注重于对园林的鉴赏品读,《园冶》更多地注重于园林的技术实施。《长物志》与《园冶》文体略有不同,但均有明代时文清言小品的特点,采用散骈文互融、长短句兼行的方式,文字对偶整齐、声韵协调,既有准确的叙事,又有华彩修辞和丰富的情感表达。正是这种文本,今天看来尤其珍贵,它们准确再现了明代器物美学与生活环境,具有某种特殊的史学价值,成为今天研究明代建筑、园林和工艺美学的重要资料。
《长物志》的版本,旧版有十数种。三种为明代木版,其余是清代及民国所印,如乾隆年间手抄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版、《奥雅堂丛书》版(清咸丰三年)等。明版书定稿者都是当日蜚声文坛的有名学者,脱稿之后曾由当世名儒为之审核定稿,其郑重可知。且该书印制发行,都是在文震亨生前,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版本。近年来的新版有十数种,刊自广陵书社、中华书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以不同旧版为底本。其中最值得推荐的读本当属1984年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长物志校注》,由著名园林学家陈植先生(养材)校注、杨超伯校订、陈从周作序。卷首保留沈春泽原序,卷后有伍绍棠原跋。
《长物志》涉及到的学科门类之多,加之明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差别,以及版本的错误,读者直接阅读原书会有很多错误理解,因此,对其进行校注就显得十分重要。《长物志校注》一稿的完成,是陈植继《园冶注释》之后对造园文献理论上的又一重要贡献。《长物志》是明代著作,很多词条不能按照今日用词来理解,比如卷一“照壁”一条,陈植注释,照壁是指,按照明、清堂、轩斋建筑,明间后方多用屏门,窗格或木板为虚壁,非指门外之照墙而言。《长物志》所述动植物、花卉、器具、书画等,种类繁多,各类品名与今名又各有差别,考证工作和典籍加注有很大难度。如花草、树木、鸟类名称等,都是注者几经考证,并咨询各门学科专家后才得出结论。对有关植物名称还补充描述,加注科、属名称。《长物志校注》,几乎为每一卷每一条词条做了详细注释,仅两页的原序言,就做了多达69个注释。全书引用参考文献多达500余种,令人叹为观止。校注延续了清儒乾嘉考据学风,堪称治学典范。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写到:“余恭奉其书,肃然起敬,喂然叹曰:前辈治学之谨严,用力之勤笃,足为楷模。先生六十年来,致力于我国造园事业,为海内所宗仰”。亦师亦友两位学人,对推广和普及中国造园文化作出巨大贡献。□(撰文:周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作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这是一本自然科学相关专业的大一新生所必读的参考书之一,但作为工科的建筑学人士却很少涉猎。这本书引导了一次科学哲学界认识论的大变革,为我们明确界定了科学的发展过程,而这也有助于我们厘清建筑学这一学科与科学的距离。
在本书的绪论中作者首先质疑了一个被大部分科学家所接受的常识: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事实、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被加入到科学知识的堆栈中。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作者提出范式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一法则能吸引一批坚定的科学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第二,这一法则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待解决的种种问题。由此,作者将常规的科学研究界定在基于某范式基础上的理论和实验活动,包括确定重要事实、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等三方面的内容。并在第四章中着重强调常规科学的研究是解谜,也就是在范式不变的基础上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度。
第六章到第九章是对科学革命过程的描述,在常规科学研究稳定的扩展其学科的广度和精度的过程中,自然界违反了常规科学范式所做的预测,通过调整范式理论也无法使这一“反常”与预测相符。面对这一危机,只能改变范式才能使自然界的这一事实成为我们所能描述的科学事实。这一新的范式并非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处理了之前旧范式研究成果,通过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这就是科学的革命。
最后四章作者更多是对科学革命的诠释以及意义的表述。作者认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范式的转化是不可通约的。并在最后以革命的进步为题比较了科学与艺术、政治理论或者哲学的不同发展,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原始开端出发的演化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朝向任何目标。
这一比较也为我们认识建筑学与科学的差异提供了标尺。其一,范式。自然科学是存在范式的,它没有竞争且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是研究者从事本专业研究的世界观的基础。建筑学缺乏一个范式,任何一种建筑学理论都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解释建筑空间完成建筑设计的方法论,所以我们还处于一个前范式阶段的百家争鸣时期;其二,科学共同体。科学研究是限定在一个有限团队按照一个共有范式进行研究活动,由于统一的标准,因此其进步是被科学共同体所承认的,但建筑学还存在于一个前范式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个体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创作,也没有稳定的科学共同体;其三,创新。技术强调创新,但常规科学研究不是以创新为目标而是强调在范式的指导下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有更高的契合度,但建筑学的创新强调对时代的表达,建筑师通过建筑语言对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进行艺术表达;其四,决策方。科学研究者所在的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封闭性和专业性的小环境,他们的成果由这个共同体自己进行认定和评价,他们坚定的原则是科学问题禁止诉诸政界和社会大众进行决策,而建筑学却是一个开放的大环境,无论是客户、政府、大众都可以加入到建筑学的评价和决策中,而且很多时候比建筑师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造成了建筑学人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较弱;其五,学习方式。自然科学的学习在于教科书,由于新老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每一次范式革命后都会重新编排教科书,按照新的范式指导研究者进入该学科领域,教科书的意义远大于历史某个经典作品或实验的意义。但建筑学的学习在于历史作品,更加注重建筑学个体在每个时代创作的作品和其内在的人文价值,这种学习方式更像艺术专业的学习,而非科学研究,因为缺乏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向读者们推荐这本书,也是希望大家能转换一下范式,从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下的建筑学,更全面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和这个行业本身与科学的距离。□(撰文:刘海洋,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文旅院副总建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