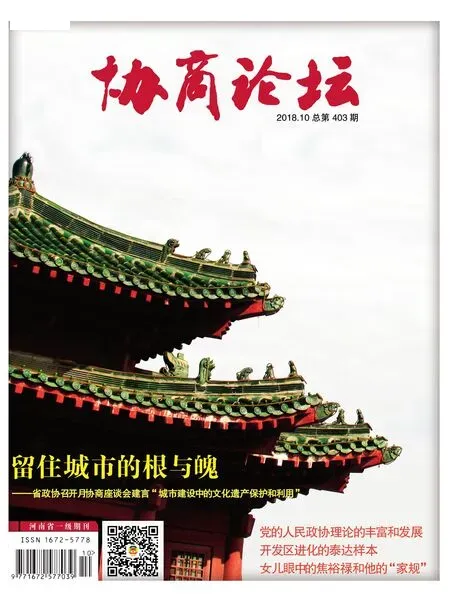守法不阿张释之
┃熊君祥
张释之,字季,西汉堵阳(堵zhě,今南阳方城县)人。他博古通今,秉性耿直,汉文帝时官拜廷尉,掌管刑狱,位列九卿。《史记》 《汉书》对他均有高度评价,有“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之赞语。他率先提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至今被法学界沿用。
在张释之任职廷尉的十三四年间,不但要求天下老百姓做到有法必依,就是帝王将相,也要求率先依法行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弘扬张释之法治文化和精神,对于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廉洁高效的法制政府,尤为值得提倡与借鉴。
张释之的精神和作风历来为人们称道,特别是任廷尉期间的建树,其精神可以概括为“执法公允,刚直不阿”的法治精神;“克己奉公,忠诚担当”的为官精神;“尊老敬贤,务实为民”的亲民精神。
执法:秉公断案,依法不依势
执法公允、刚直不阿是张释之法治精神的精髓。
张释之任公车令(负责皇宫正门警卫、传达事务的卫尉属官)时,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一同乘车入朝,行至司马门时却不下车,张释之阻止二人进宫,并弹劾他们违反了《宫卫令》中所规定的“凡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的人都必须下车”的律令。薄太后听说后批评文帝“教儿不谨”,并派使者给释之送来赦免太子和梁王的诏书,张释之才放了他们,虽然得罪了太子和梁王,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张释之任廷尉期间,有一次他跟随汉文帝刘恒出巡,来到渭桥时,有一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惊了文帝的驾。文帝将其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审问后得知这个人属于无意惊驾,便上奏文帝:其人触犯清道的禁令,应判以罚金四两的处罚。文帝认为处罚太轻,发怒说:此人惊吓了我的马,幸好这匹马温顺,不然岂不让我受伤?张释之抗辩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日此事按法就该这样判,若随意加重,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取信于民。况且,如果当时皇上立即杀了他,也就不再说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廷尉本是天下公平论理的代表,一旦有所偏颇的话,各地的官吏在行使法令时,会随意轻重,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希望陛下体察。文帝深思良久,同意了廷尉的判决。
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张释之耿直无私的禀性,执法严明、不徇私情的品格。在法律面前,他没有屈从皇帝的意志,不怕得罪储君,这是常人做不到的。
为官:力谏汉文帝主张薄葬
张释之在任中郎将(掌管皇帝侍卫的郎中令属官)时,随文帝视察正在兴修的霸陵。依制,古代皇帝登基,便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所需之费用,往往要占国家税赋的三分之一,修陵的时间大致等于皇帝执政的时间。
刘恒望着自己千秋之后的归宿——高高的陵山,不觉油然感伤,便让宠姬慎夫人鼓瑟,自己依乐作歌,音调哀伤,凄怆悲怀。但又见陵山巍峨,稍可宽慰,便止歌向群臣感慨道:以山为陵,以石作椁,绝对坚固无比呀!大臣们都纷纷附和。只有张释之上前对文帝说:如果陵中有让人贪婪的宝贝,就算铁铸南山,再坚固也会让盗贼有空可钻;如果陵中没有让盗贼想偷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也不用担心被盗!

文帝非常佩服释之的远见卓识,不觉点头称善。临终遗诏:“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史记·孝文帝本纪》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结果是仅仅过了一百余年的莽新后期,赤眉军入关,诸陵被掘,霸陵因释之一言而得以保全。
张释之反对厚葬,力主薄葬,影响深远。在汉代推崇厚葬,不惜倾家荡产之风盛行之时,张释之见解独到,反对厚葬,不仅需要大智大勇,更重要在于他以天下苍生为念。君王厚葬,敛于百姓,君主薄葬,惠及天下。汉文帝能够顾及民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达到“文景之治”,张释之的薄葬主张功不可没,后世多持此说。薄葬的观点得到上至君主下到平民的推崇,张释之的薄葬思想泽被千秋万代。
礼贤:结袜王生,名重天下
不只执法做官垂范世人,张释之还因尊老礼贤 “结袜王生”而名重天下。
在汉景帝即位不久的一次朝会上,一个年迈处士王生忽然说了声“我的袜带松掉了”,并转过头对九卿之一张释之说,“你为我结上袜带!”张释之在众大臣的注目之下从容走了过去,单腿跪在地上,俯身为王生系上了袜带,然后走回九卿之列。
作为重臣的张释之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一个无官无职,只是为皇帝讲些黄老之术的读书人跪地结袜,这不啻为一种污辱,然而张释之能从容做到这一点,更加彰显了他尊老敬贤的高尚节操。自卑者人敬之,他当时不以此为意,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原来,当时的情况是景帝即位,对曾经得罪他的张释之极为不利,或遭贬或被杀都有可能。这位处士王生出于对张释之的敬仰,想在张释之危困时帮他一把,便效黄石公让张良纳履之典故,故意松开袜带,让释之来结。张释之并未觉察,而是出于本能为王生结袜。其收效是,王生此举为别人所不平,事后,不少人责备王生道:你这个老头,为何敢在朝堂当众羞辱张廷尉到如此地步!王生这才解释道:我一个既老且残的无用之人,自思终究不能做对张廷尉有益的事,正因为张廷尉是天下名臣,我才让他结袜,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其后朝野闻之,果然称王生贤而推崇张释之的品行,也缓和了张释之与汉景帝的矛盾。
立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
纵观千年史章,我国古代具有系统法学思想的,首推张释之。他的法学思想吸取了法学“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观点,表现了古代法官追求的最高执法境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立传的最高司法官员。
司马迁在《史记·张释之传》中赞道:“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班固在《汉书》中赞道:“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释之典刑,国宪以平”。现代史学大家卢敦基先生说:“西汉前期,名臣辈出,然读史、汉诸传,使人心悦诚服,肃然起敬的,似乎只有张释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