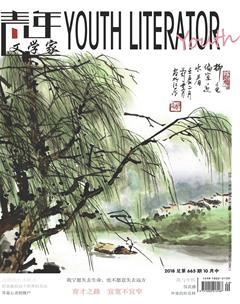从太宰治到纪伯伦
彭丽娅
我并不是有意将《人间失格》同《先知》放在一块儿看的,它们的相遇更像是宿命般的相遇。
你能听见太宰治在这头低语:“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对人类极度恐惧,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人类死心。”同时,纪伯伦又在另一侧呼喊,“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难而险峻。”
从太宰治到纪伯伦,此时不过是两页纸的距离。但这两页纸让他们分道扬镳,走向各自的祭坛。太宰治或许是自卑而屈辱的,但他同时又必定骄傲着,因为他用一种惨烈的方式完成了他的献祭。纪伯伦则拜倒在美和真的脚下,像个真正的圣徒。事实证明即便同样是求爱,也能走两条背道而驰的路。
“我现在是个疯子。”
这句话使我颇有些凄惨之感,惨戚戚。你瞧,世人觉得我是个疯子,我已是个疯子了。围墙外是正常的人,围墙内是疯了的人。我终于丧失为人的资格。
这样的疯,这样的叙事,太容易想到《狂人日记》。一句“救救孩子”,要一个世纪了,到如今也未曾实现。要救的或许早已不是孩子了。
我不愿意否认《人间失格》,正如我不愿意否认肉眼不可见的苦难。我也不愿意承认它,因为这病态和绝望一层一层叠得太深了。我甚至不愿意也不敢怜悯它,我只但愿我给予的是爱、宽容和幸福,而不是冷漠的怜悯。
阅读这样的小说仿佛令我见到卡佛和卡夫卡的影子,艾略特的诗歌也掠过眼前。我总觉得水土不服,远不比钱钟书、沈从文亲切。我在西方哲学精密繁细的论证里常常会怀念老庄,他们像清隽的影子,风也抓不住。读西方小说时又常常思念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小说,因为它们老像朴素的诗。我在后现代主义的迷宫里打转,整个人也像被割成了碎片,每一块碎片都在格格不入地抗争。可我其实愿做朴素的诗,不愿做碎片。我虽相信怪诞的一切,但我也相信美好的一切。就如我相信地狱,同时也相信天堂。
我一直热爱那些已被埋葬或正在被埋葬的。可这不是守旧,也不是传统,至少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传统。我爱那些古老的意象,像是一挥而就的意气,还有在朔风里飘零的情怀。中国文学靠情串起来,这情雅致,也广阔。这样的情有时让人觉得可爱可笑,比如老头子们喜欢拍着胸脯自夸,咿呀学语的小毛孩竟然会说起报国的志向。
在如今,那些像是带有仪式感的郑重情感好像远了,连带着游人的呓语也远了,但文字上的远却能抵达生活上的近。某天瞥到一句“稚子敲针作钓钩”,心头自然涌上如同归宿的欣喜,之后見到前头的“老妻画纸为棋局”,就像重新发现了生活。这一切都使我相信,生活是有情的。我无法想象缺少情的生活,这必定是上天开的最残忍的一个玩笑,一个偌大的悲剧。
可是《人间失格》就是这样的悲剧。叶藏在以自己的方式暗暗斗争,太宰治也在默默抗拒,唯独缺少这一味“情”,最终只能各自枯萎。如果有爱存在,它势必凌驾于肮脏之上。
我曾经在见到《二十二》时沉默不语,几个月后却在和母亲的谈话中大哭。那个晚上,我像是第一次见到苦难。我以为我见过它许多次了,实际上我不过是抓住了它透明的尾巴。我曾经像所有无知的人一样,以为苦难总会过去,也以为苦难总离不开诗意。可我看见了那些疲老的皱纹,那无措又悲痛的神情,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子,我再也没忘记了。它们显得那样真实,又那么粗粝,远离我生活的所有。我对母亲说:
“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还有这样的荒芜。它是诗意根本透不过的水泥板,寸草不生,像个黑洞一样,生产绝望又吞噬希望。”
苦难虽然让人感到绝望,却也最容易使人见到羁绊的情感。这是生活的魔力。就像余华说的,人本身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为别的。老人说到曾经会落泪,我们也会落泪;老人也会在现在的日子里微笑,我们也因之微笑。如果叶藏,或是太宰治哪怕只和一个人共同流过一次泪也欢笑过一次,我不信“世人”依旧是洪水猛兽。太宰治将自己封锁在套子里,但时不时还要钻出套子看看。被自己封锁的人如同一张被榨干的纸,所有的风吹来都是痛苦。
我曾经遥远地领略过人类造成的苦难的威力,也曾模糊地见到人与人之间的空洞。但我始终被爱,也始终在爱。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幸福。或许读了这样一本书后,我们才知道爱是多么伟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