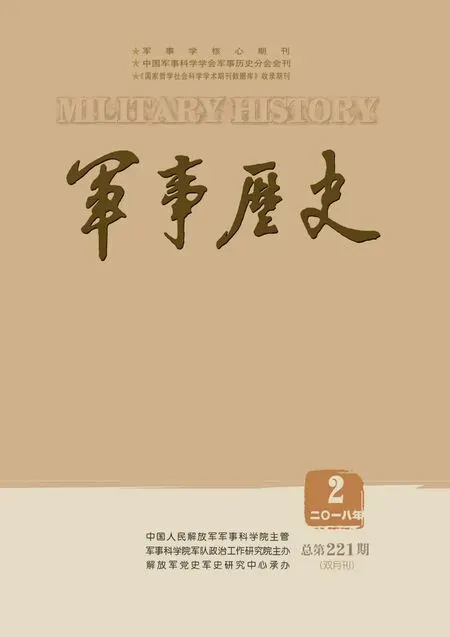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
★ () ()
1950年夏天,我谢绝导师玻恩教授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750英镑的待遇,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我先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两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我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南京大学的教授很少,学校把我当作归国高级知识分子,给我定为二级教授,但在填表时,我坚持只领三级的薪金。在南京大学,我听从组织安排,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和核物理两个教研室。1956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秘密使命
1960年夏的一天,郭影秋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报到,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我没有多问,第二天就动身。按照纸条上写的地址,我来到二机部一个搞煤炭的地方,却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圈电话询问下来,他们让我去城北某地报到。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那里有两栋普普通通的红砖小楼,一栋四层的灰楼是九所的办公楼。土城墙外有条护城河,后来成为小水沟。周围是大片空旷的土地,没有什么人。据说,当时为建灰楼,二机部的领导和钱三强、邓稼先等许多人都来参加劳动,聂荣臻、陈赓、张爱萍、宋任穷、万毅等一些开国将帅也到过工地搬砖、和泥、推车。
我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到了所里,吴际霖副所长跟我说:“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与南京大学商调你,南大不放,你先两边兼着。”实际上,我回学校工作总共也只有一次。1961年,我正式调入九所,开展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南京大学接到调我的调令,不想放。他们召回在北京学习的刘圣康,要让他代替我去二机部,二机部不同意。于是,核物理教研室的党员向系党总支申请,要学校出面申请免调我,还找到校长郭影秋。郭校长来南大前是云南省省长,他是主动申请来教育战线的。郭校长说:“你们要服从国家需要,以后会知道程开甲调去从事的工作。他今后工作的成就,也是南京大学的光荣,你们要把眼光放到年轻人的身上。”
就这样,我改行进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后来,我才知道,调我参加原子弹研制是钱三强点的将,邓小平批准的。
说起来,历史还曾有一些机缘巧合。我在英国留学时,曾因与美国从事原子弹内爆机理研究的福克斯有过一次短暂接触,因此曾被怀疑跟踪过。没想到10多年后,我还真的搞原子弹了。
福克斯是玻恩的学生,我的师兄。1949年11月14至16日,在爱丁堡召开的基本粒子会议上,我见到他。玻恩为我们作了介绍,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谈得很投机。当时美国政府正对有人将原子弹的核心机密泄露给苏联的事进行调查,福克斯在被怀疑之列。他倾向共产主义,被怀疑向苏联人泄露原子弹制造技术,卷入间谍案。会后不久,他就被捕了。开会时就有人监视他,而因为我们是师兄弟,我又是中国人,也受到了怀疑。我去法国的时候也有人跟踪我。他们将原子弹机密—福克斯—程开甲—中国共产党—红色苏联联系起来,跟踪调查我。事后,导师玻恩将这段离谱的插曲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将福克斯当间谍逮捕了,当初他们怀疑与福克斯联系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玻恩后来说:“我的许多学生,奥本海默、卢森堡、海森堡,福克斯、彭桓武,程开甲……都去搞原子弹了。”
二、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原子弹的研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知道参与这项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这项工作与我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但我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更重要的这是国家的需要。
我从事如此绝密的工作,根据国家保密规定,对外只允许说我在研究核反应、加速器、反应堆等。有一次回南京大学,同事们要我说说工作情况。在核子组我就讲核能、原子核的输运、中子输运等。我懂得一些,总可讲一点,但到底不是做这方面实际工作的,讲得不好,内行的施士元觉察到了,他感到奇怪。
原子弹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二机部九局负责。局长李觉,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7月,九局在北京建立二机部九所(1963年改制扩编为二机部九院),李觉兼任所长。最初确定研究所的任务是接受、消化苏联专家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以及调集、培训人员。苏联毁约停援后,研究所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工作。
我到研究所时,李觉所长还在“招兵买马”,做大量的协调和后勤保障等工作,两位行政副所长吴际霖、郭英会全力协助他。我与朱光亚、郭永怀同为技术副所长,朱光亚是技术总负责人。
最初的探索工作大致是围绕着理论设计、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引爆控制系统、结构设计等几个方面进行。我的任务是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
当时,我有许多东西不懂,尤其是爆轰实验。但工作分下来了,也就硬着头皮上。后来,王淦昌、彭桓武来了,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我们又走到了一起。由于王淦昌是搞实验的,所以爆轰物理研究的实验工作他就接了过去,我专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及其他一些工作。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对于这样的军事绝密,当时的有核国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为泄露了一点秘密,受电刑处死,福克斯也因为泄密被判了14年监禁。中苏关系蜜月的时候,聂荣臻元帅和宋任穷部长去苏联参观,也只能在厂房、车间外面透过玻璃窗看看,不让进去。来中国的苏联顾问常是不念经的“哑巴和尚”。有一次,面对中国专家,一位顾问想念一点点“真经”,但顾问团的领导一声咳嗽,就把他的话打掉了,可见其戒备之深。那个时候,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所需的仪器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1960年1月,二机部在“科研工作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我们的事业完全建立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自己研究,自己试验,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装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同年8月,二机部向所属单位发出了《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指出: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三、解决一个大难题
九所一室是理论研究室,室主任邓稼先原来是研究场论的,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物理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主攻方向。高温高压下状态方程组有胡思得、李茂生等几个年轻人,他们在求解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状态方程时遇到了困难。
核材料中的状态方程,无论对象、温度和压力范围,都不同于普通的状态方程。当原子弹中的高能炸药爆炸时,原子弹中的各种材料就处在与常温常压极不相同的极高温度压力状态。核反应起来后,介质的温度可达几千万度,压力达几十亿大气压。当时,国内没有实验条件获得铀235、钚239的状态方程,国外视此为绝密,我们只有靠自己摸索。
用什么方法求得核反应起来后介质的状态方程呢?托马斯-费米理论能够描述在极高密度和压力下的介质状态方程,但它是一种统计模型,不能用于千万大气压以下的范围。对这个理论各种各样的修正,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都不能彻底解决低压范围的使用问题。邓稼先主任曾去请教过当时在研究所里的苏联专家,得到的答案是:托马斯-费米理论包括它的修正在内,只能用于研究像中子星一类极高密度的天体物理,在核武器物理中用不上。尽管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有所保留,还是缺乏理论上的自信。
我到研究所后,状态方程小组负责人胡思得向我详细汇报他们已经做过的工作,也讲到利用托马斯-费米理论的担心。我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不时与他们讨论。有些概念,例如冲击波,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好在我在南京大学时研究过托马斯-费米理论,1958年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TFD模型方面的文章。当时,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没有学过固体物理,更没有学过类似托马斯-费米统计理论。为了让大家掌握托马斯-费米理论及相关的修正,我给他们系统讲课。系列课程讲完后,又追加了固体物理方面的内容,还帮他们复习了热力学、统计物理方面的知识,指导他们查阅国外文献资料。事实证明,这些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业务基础,也使他们能在更高的理论平台去开展研究工作、攻克难题。
大家对新任务都很陌生,所以我们经常召开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人人都是权威。即使刚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提出的稚嫩想法,也会受到关注和鼓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都被激发出来。
那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思考和计算,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有时在吃饭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会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公式帮助思考。
后来,别人常说起我的一个笑话。一次排队买饭,我把饭票递给窗口卖饭的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卖饭师傅莫名奇妙。邓稼先排在我后面,提醒我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
经过半年艰苦努力,我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即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
拿到结果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对我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我们在理论上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但原子弹起爆条件,必须进行炸药爆轰实验。这种没有核材料的炸药爆轰实验,称为“冷试验”。
当时,我们在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官厅水库旁的一个沙漠地带,借助工程兵试验场一角,建立了爆轰实验场,称为“17号工地”。为了解实验开展情况,我和郭永怀有时来这里,在帐篷里讨论问题,在野外吃带沙粒的饭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连饭也吃不饱,但积极性很高。让我们犯愁的是实验仪器的落后和技术方案的确定。那时化爆场只有0K-15、0K-17两种阴极示波器。针对实验测试的需要,我担心性能极差的两台阴极示波器会影响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1960年10月,张爱萍将军来研究所视察,听完汇报后,他提出去爆轰实验场考察。张爱萍、我、郭英会、郭永怀等人一起坐军用吉普车去17号工地。一路上,我们向他汇报爆轰物理实验场的情况。到了实验场,我让技术人员向张爱萍现场演示了两台阴极示波器的工作状况和性能,张爱萍问得非常仔细。趁此机会,我向他提出需要性能更好的示波器,他当即表态,“我回去后立即解决。”
在回北京的路上,我们乘兴在官厅水库游玩。我和郭永怀、郭英会3人乘船来到水库中央,突遇狂风,船差点被打翻,3人狼狈而逃。在岸的张爱萍,挎着相机一直在官厅水库拍摄,目睹了我们几个遇险的过程。经过八达岭,我们还下车与张爱萍一起合影留念,可惜这张珍贵照片现在我已经没有了,九院办展览借走后就没还给我。
张爱萍是位一诺千金的将军。不久,我们实验急需的先进示波器就运到了实验场。正是这次考察,张爱萍将军朴实、随和、敬业、尊重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的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由于工作过于紧张,我病倒了。1960年冬天,我不得不中断工作回南京养病。为早日康复,我想尽办法,向物理系魏荣爵教授学打太极拳、练气功,我学会了,一直坚持。
另外,我还决心戒烟。我抽烟始于抗战流亡年代,后来每天要抽两包。这次为了工作,下决心不再抽烟,成功地戒掉了。
我的夫人高耀珊一直精心照料我,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我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有她的一份功劳。平时我吃饭时考虑问题经常走神,她就剔净鱼刺,把鱼肉放到我碗里。回到南京养病,她每天陪我走到中山陵。当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为给我补身体,她想方设法买高价鸡煲汤,全给我吃,孩子都没有吃。她特别能吃苦,剩菜、剩饭都自己吃,水果烂了削削自己吃。
1961年初,春节一过,我就立刻赶回北京。这年夏天,所里派人到南京帮忙,把家搬到了北京,老大、老二仍留在南京上学。从1969年到1985年,我们一直生活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
到1962年夏,在我接受主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任务时,虽然炸药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的理论研究已经突破,但还没有通过实践验证。后来,青海的原子弹研制基地进行了多次化爆验证实验(化爆冲击压缩ND3出中子),我则一直紧张地准备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无法参加。而我在九所时从事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攻关,又兼任九所副所长(后九院副院长),所以,关键的最后一次化爆试验仍然通知了我,我也立即从新疆试验基地赶到研制基地,参加试验。当炸药的冲击聚焦最终得到引爆原子弹的条件时,我们都十分激动,十分高兴,因为原子弹研制的最后重要一关终于突破。
四、一碗红烧肉
1961年下半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都陆续展开,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也初步搞清,有的已经突破和掌握。正当我们力争加速进程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上出现了有关两弹的“上马”“下马”之争。后来是毛主席下的决心,结束了争论,并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灾害饥荒严重,广大科技人员也每天饿着肚子。电力供应不足,经常点着油灯查阅资料,不分昼夜工作。聂荣臻了解到这种情况,曾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给科技人员补助,并以个人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副食品。各大单位在物资同样紧缺的情况下,省吃俭用,慷慨相助,保证为我们每个月提供两斤肉和带鱼。北京军区打了一些黄羊,也拿出一部分送给17号工地。这在那时都是极其珍贵的。国家对科学家如此关心,大家很感动。
1962年春节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招待我们,桌上有大碗红烧肉。席间,总理谈笑风生,对科技人员十分关怀,亲自过来敬酒,让我们感到总理的谦和。当时,我和朱光亚、王淦昌、李觉、吴际霖在一桌。总理到我们这桌敬酒后,国防科委二局的刘伯禄说:“总理坐中间,左边是钱学森,右边是钱三强,你们看出怎么回事了吗?一看就明白中央搞两弹的决心,两样都要上。”他是说钱学森代表导弹,钱三强代表原子弹。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周总理,第一次是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在怀仁堂接见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科学家,并合影留念。那次,周总理宴请大家,亲自走到每一席和科学家握手,感到他是那样地关心和尊重科学家。这次宴请,让我再次感受到周总理的厚爱和重托,特别是那大碗红烧肉,在当时真是十分不易,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让我记了一辈子。之后,随着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推进,我前后向周总理汇报和受到接见有十次之多,每次的感动和感受都不同。
五、 转入核试验
1962年夏,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理论研究和制造技术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自行设计的原子弹理论方案也接近完成,爆炸试验问题提上了日程。此时,九所正为原子弹研制全力以赴,没有精力另外开辟原子弹爆炸试验新领域。经研究,李觉、朱光亚等人提出建议,钱三强同意,组织专门的试验研究队伍,由我代表九所开展工作。
随后,吴际霖副所长找我谈话。他说:“研究所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集中精力继续把这些工作做好,而对下一步要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也需要有专人来考虑。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由你专门考虑试验的研究与准备。”他还说:“你先去,我们后面来。”之后,他和我一起去国防科委,与二局局长胡若嘏见面。当时二局统管全国原子弹研制及试验。
胡若嘏局长开门见山地说:“程副所长,军委分析了国际局势,要求我们加紧试验准备。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日程表,提出具体进度,确定大致的试验时间。尽快拿出试验技术方案。”
我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但组织上决定要我去搞原子弹爆炸试验,我坚决服从。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就这样,我又一次转变专业方向,转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由于这项工作与九所的弹体研制本身暂时关系不大,研究所也根本没有精力考虑下一步的试验工作,那时的我真可谓“光杆司令”。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科研管理模式,我的工作也没有定制的上报程序。朱光亚是所里全面负责技术工作的第一副所长,我们俩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他都会问我工作情况,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打算与他交流。比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爆方式来试验,首先应采用地面静态试验方式,以后再用空爆方式;比如,我认为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还有对核试验研究所的组建与各类技术人员需求的考虑,等等。我根据进一步的分析与计算,明确提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采用塔爆方式。我的每一步工作思考,都及时与朱光亚交流,他都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1962年9月14日,朱光亚起草了《第一种试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草稿)》(简称《计划纲要》)。我提出的有关爆炸试验研究就成了1962年的《计划纲要》中核爆炸试验部分的内容。草稿完成后,他专门征求李觉、吴际霖和我的意见:“计划纲要(草稿)已写出。(1)不知问题和看法反映的全不全?对不对?(2)好几个数字,不知是否估得恰当?……请审阅修改。如果不合用,当再写合用的。”
大家都很赞赏朱光亚科学、民主的工作作风,而我与朱光亚之间则一直互相关心、信任、支持,保持着珍贵的友谊。
随后,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注:名称为《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上是给中央立下了军令状。这个“两年规划”得到中央批准。
1962年10月16日,在国防科委大楼,张爱萍、钱三强及二机部九局的领导进行工作协调。钱三强说:原子弹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爆炸试验靶场开展的技术项目就很大,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工程建设。这样,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队伍,立即着手研究立项。张爱萍提出,可以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专门从事核试验靶场技术工作的研究,请钱三强同志提出一个方案并推荐专家。钱三强同志表示赞成,并推荐我负责靶场技术工作。
1962年10月30日,张爱萍主持召开国防科委办公会议,要我参加。他希望我就试验靶场的技术准备问题进行汇报。在会上,我谈了关于试验技术方面的研究思考。我说:“关键是人,要有一支队伍尽快开展工作,提出研究课题来。”
张爱萍说:“好。三强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他推荐你来主管这个研究机构。”
我的工作早已调整并转了过来,我说:“请给我调人,我们马上投入工作。”
张爱萍说:“马上投入工作很好,也是必要的。不过,要房子暂时没有,仪器无法马上买到,机构短时间内也难健全,但研究工作要立即开始。”
11月初,吕敏、陆祖荫和忻贤杰来了。他们3人经常挤到我在九所的办公室里,研究讨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理论、方法和工程技术研究中的问题。
吕敏,我在浙江大学教书时,他是学生,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2年回国。陆祖荫,是钱三强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毕业,分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忻贤杰,浙江大学时是王淦昌实验室助教,动手能力很强,从王淦昌那里继承了许多好作风。他们后来都成为有名的核试验专家。不久,又调来了哈工大的孙瑞藩和北京航空学院的董寿莘。其他技术骨干,基本上是我提出的专业要求和人选,由邓小平同志批示,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从全国全军各地选调来的。选调时,各单位全力支持,点名要谁就给谁。先后调来的技术骨干有:理论计算专业的乔登江、谢铁柱、白远扬;放射化学专业的杨裕生、高才生、陆兆达;力学专业的王茹芝、俞鼎昌;光学专业的赵焕卿、杨惕新、李茂莲、张慧友、徐世昌;电子专业的龙文澄、史君文、于冠生、李鼎基、庄降祥、曾德汲;机械专业的傅燮阳、沈希轼;地下试验相关专业的宁培森、张忠义、丁浩然和核物理专业的叶立润、钱绍钧等。他们是重要的技术力量,结合每人的专长,我安排他们在研究所中分别担任各级技术领导。
1963年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批学生提前毕业来报到。夏天,又有100多名全国各重点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
根据核试验研究的需要,经过论证,我们很快提出了研究所学科专业需求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研究所下设5个研究室,分别为冲击波研究室、光测量研究室、核测量研究室、自动控制与电子学研究室、理论计算研究室,同时还有资料室和加工厂。之后,为开展地下方式的核试验,又增设了地质水文研究室。理论计算研究室(五室)室主任,在1963~1970年间一直由我兼任。
事实证明,研究所的设置完全符合核试验任务的需要,是科学合理的。后来,除分出放化分析研究室外,最初设置的体制一直延续了20多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后,我们研究所成为全军最大的研究所。
1963年7月12日,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大会,命令由林彪签发,大会由张爱萍主持,所长张超,政委张少华,我和董寿莘任副所长,我负责全面技术工作。成立大会上,张爱萍将军、刘西尧副部长等与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这样,我不仅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也兼任九所副所长,1963年九所改制为九院,兼任九院副院长,直到1977年我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免去九院副院长。
作为九院的领导成员之一,我对产品情况是清楚的,每次试验产品的参数和设计都会专人告知我,产品进入试验准备前的会议,也会通知我参加讨论。武器设计的检验必须通过试验,根据试验和测试为武器研制提供有价值的各种数据,提出有实际意义的建议,改进设计,解决问题。
我的双重角色,使我不仅能更好地完成试验任务、检验产品设计,还能从试验测试的角度对设计提出看法。例如,一次试验中,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没有测到某重要数据,我带着理论研究和测试人员反复查找出现问题的原因,指出这是弹体设计问题。于是提出改进建议,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这大概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试验之间的一种特色关系。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走出了理论、试验、设计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环之路,这种研制和试验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一般研制单位与靶场之间没有的,对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改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建所初期,没有自己的办公和实验地点,开始时,在总参谋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半年后,搬到通县仓库。我仍住在二机部九所宿舍,每天来回跑。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后,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搬到新疆红山,我把家也搬到那里,直到1984年调回北京,为了中国核试验,我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