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民企控制权转移现象
文=郑志刚
据《证券时报》(2018-09-03)报道,“包括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在内的‘国资系’主体正在参与或已经完成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国旅联合、三聚环保、华塑控股等20余家民营上市公司,均正在或已经完成相关股权转让事项,且均有国资接盘方,受让股权合计超过30次,交易金额超百亿。其中,三聚环保、新筑股份、金力泰等民营公司更是彻底变身为国营企业”。该报记者用“国资抄底”、“国资开启‘扫货模式’”来描述近期发生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公司控制权由原来的民资控股转向国资控股的现象。
容易理解,控股股东将对公司未来治理构架和发展方向选择上打上深深的印记,因而控制权转移对一家企业而言举足轻重。特别是,以往围绕控股股东性质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与企业会计和市场绩效统计上显著负相关。国企治理构架下常见的所有者缺位和长的委托代理链条问题,被用来解释二者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近期发生的民资控制权转为国资现象,是否意味着原本盈利动机明确的、民资主导的治理构架,重新退回到国资主导的、所有者缺位和长的委托代理链条的治理构架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近期发生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述独特现象呢?
首先,近期发生的民资控制权转为国资现象,只是民企为了缓解资金链紧张而完成的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民企从自身面临的困境出发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很多人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仅仅与以引入民资背景战投为目的国企改革联系起来。殊不知民企在陷入财务困境时同样需要引入战投来缓解现金流紧张,建立更加合理高效的公司治理构架。看起来促使不同所有制同时存在,从而形成所谓所有制混合局面的“混改”,其实质是引入战投。因此,我们可以把近期发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民资控制权转为国资现象概括为“民企的混改”。
第二,对照此次“民企的混改”与一些已经或正在进行分阶段引入战投的国企混改,我们看到,二者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借助二级资本市场控制权转让来完成“民企的混改”,不仅效率高得多,成本低得多,而且以一种资本市场所特有的公开透明方式。尽管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存在这样那样的批评,但上述事实一定程度表明,资本市场经过长期的建设发展已经具备基本的资源(重新)配置功能。它给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的一个启发是,未来如果借助资本市场控制权转让进行混改将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第三,此次“民企的混改”为国资管理体系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自然转化上了生动的一课,为未来相关国企其他领域混改的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知道,国企混改一个明确的方向是从原来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按照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的描述,所谓管资本就是改革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由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专项价值形态转为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有良好流动性、可以进入市场运作的国有资本。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构代替实体企业成为国资委新的监管对象后,经过“国有投资运营机构的隔离”,国资委与实体企业“不再有直接产权关系,也无权穿越投资运营机构干预其投资的公司,政企分开顺理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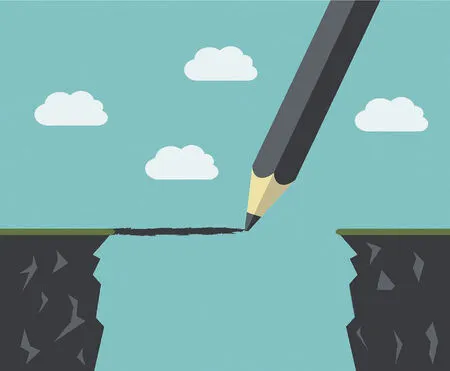
对于经过分阶段引入战投进行混改的国企而言,面临的挑战显然是如何摆脱一股独大下形成的治理惯性。这表现在不仅在董事会组织中大包大揽,而且用代表大股东的董事长一人之意志代替全体股东的意志。而对于这些通过资本市场控制权转移完成引入战投的企业而言,新入主的国资必须按照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则和全体股东的意志,通过与各方的协商完成包括董事会等在内的基本治理制度的构建。因而,民资的混改向这些获得控制权的国资提供了如何从股东的角度来参与公司治理,从原来的“管企业”转变为现在的“管资本”这一难得的学习契机。上述经验无疑将反过来帮助相关国企在其他领域混改推进中,清楚股东的定位和职能,不再越俎代庖去从事超越一个股东行为的工作。
第四,无论控制权从民企转到国企,还是从国资转到民资,都是资本市场中司空见惯的控制权的转移,并不值得媒体和公众大惊小怪。以2015年万科股权之争为标志,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低于三分之一的相对控股权的临界值,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并购行为将随着资本市场分散股权时代的来临,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甚至不惜以相对极端的“野蛮人闯入”和控制权纷争面貌出现。毕竟由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下降,接管商发起并购的门槛降低了,需要付出的成本降低了,并购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
近期发生的民资控制权转为国资现象事实上只不过是上述趋势下的反映。如果我们非要按照控股股东的性质来考察控制权转移,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借助二级市场进行控制权转移的既有从国企到民企,又有从民企到国企,当然还有从民企到民企,从国企到国企。只不过一段时期国企变为民企的多一些,而在另一段时期,民企变为国企的多一些。
第五,如果说此次“民企的混改”经历的控制权转移有什么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本轮“国资系”频繁入主,与“去杠杆”和股市调整所带来的很多民企资金链紧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债务难题密切相关。
由于金融收缩政策,与共和国长子的国企相比,民营上市公司更频繁地遭遇到期续贷时,临时要求增加担保物,提前还贷,利率上浮等要求,这使民营上市公司与同类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现金流更加紧张。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上近期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其实并非国企真正前进了,而是在歧视性的金融收缩政策下国企退出得较民企慢,看上去给人一种“国进民退”的错觉。因此,我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控制权转移究竟由国资转到民资,还是民资转到国资,而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包括歧视性金融收缩政策的不平等发展机会。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曾经指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再继续严格界定国有和民营已经失去了意义,政府应该弱化直至取消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促进实现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我们对此观点深以为然。
我理解,如果新入主民企的国资不能仅仅完成角色的转化,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早晚有一天,会把曾经吃下去的再吐出来,把控制权重新让渡给更有效率的民资。这是我始终坚信的信条: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一旦植入市场经济的基因,虽然在短期内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但从长期看,经济的逻辑一定会超越非经济的力量,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方向。
那么,混改的民企应该如何建立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呢?我们看到,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混改,它们需要共同遵循的原则是通过引入战投,形成权力制衡,避免监督过度,实现合作共赢。在混改引入新的战投后,平等地集体享有所有者权益成为一个全体股东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如何建立各方激励相容的治理构架,使参与各方群策群力,合作共赢则不仅既是混改的出发点,也是混改的最终归宿。
[小贴士]
民企易主国资长期占主导
统计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中,上市公司控制权性质从民资控股转为国资控股,或者从国资控股转为民资控股的事件共发生458家次,其中,8年间控制权从民资转为国资共计264家,占到全部控制权性质变更的57.64%,略高于控制权从国资转到民资的42.36%。而从2015年开始到2017年12月底,控制权从民资转为国资共计242家,占到全部控制权性质变更的83.16%,远高于控制权从国资到民资的16.84%。
从2010年开始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民营资本上市的快速增长期,到2017年底,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占到全部上市公司的70%。逻辑上,由于民资控股上市公司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围绕民资的控制权转移,甚至控制权由民资转为国资的案例多一些,也属于正常现象。更加重要的是,对于到今年7月底上市公司数量达到3551家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几十家至上百家的控制权转移应属正常范围。近期频现的民企转国企,由于是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的控制权性质转变,属于市场行为。
资本市场民企并购融资仍为主流
数据显示,目前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和直接融资中,仍以民营经济为主流。
2017年全年,境内上市公司共实施并购重组2765单,交易金额1.87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共发生并购1967单,交易金额9786.45亿元,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占比分别为71.14%、52.20%,民营经济借助资本市场实现了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2017年,证监会共核准交易204单(含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33单),交易金额5727.1亿元(含配套募集资金1194.96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共123单,交易总金额合计2917.79亿元(含配套融资692.64亿元)。
2018年1月至7月,民企在资本运作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A股上市公司实施并购重组2377单,交易金额1.36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共发生并购1835单,交易金额9795.45亿元,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占比分别为77.20%、71.76%。
同期,证监会共核准交易102单(含要约收购27单),交易金额3654.98亿元,配套融资439.81亿元,交易总金额4094.79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共52单,交易总金额2106.39亿元。
——省委宣讲团走进国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