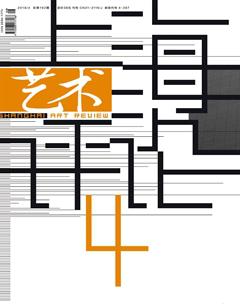让戏剧增添城市的魅力
丁罗男
戏剧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发挥着何种文化功能?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需要,是仅仅为了满足大众的娱乐休闲,还是城市文化品质构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什么“上海文创50条”中会提出“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和要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演艺业态与模式?这些都是值得深长思考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五月,上海的戏剧舞台上可谓好戏连连,热闹非凡。大大小小的剧场里“你方唱罢我登台”,着实让上海观众一饱眼福。其中,静安现代戏剧谷俨然成了申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上海的广大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精神食粮。
静安现代戏剧谷创办于2009年,区政府联合相关单位,利用地处中心城区剧场林立,各种演出团体、艺术院校和文化机构齐全的优势,每年都举办各种戏剧活动。今年趁着“撤二建一”的机遇,在“国际静安,全城有戏”的口号下,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现代戏剧谷掀起的“看戏热”确实令人惊喜,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这一点,从观众的踊跃、媒体的关注和其他文化产业的跟进中,都得到了印证。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戏剧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发挥着何种文化功能?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需要?是仅仅为了满足大众的娱乐休闲?还是城市文化品质构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什么“上海文创50条”中会提出“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和要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演艺业态与模式?这些都是值得深长思考的问题。
被激活的城市文化记忆
了解一点上海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座城市开埠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戏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市民大众的视线,或者说,戏剧始终是上海文化成长的一种叙事话语。
早在19世纪末,上海的舞台就曾出现“中西杂糅”的学生演剧,进而演变为文明戏,成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发祥地;同时,晚清的戏曲改良之风吹到上海,结出了奇异之果—“海派京剧”,它与沪上绘画一样,都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京剧作为北方剧种,却是在上海的剧场中跨出了现代化演剧与经营体制的第一步。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等一大批京城“名角儿”,曾争先恐后地来到上海这个码头献艺,而且越唱越红,以至于北京京剧界流行“不到上海不算红”的说法。更何况上海本身还孕育了一代京剧宗师周信芳。所以,那时候在上海,“看话剧”“听京戏”就是一种流行和时尚。
甚至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上海的戏剧,尤其话剧的职业化进程也未受到影响,反而在“孤岛”和沦陷时期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演剧的繁盛景象。过去的史家往往将其视作“畸形的繁荣”,然而从城市文化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抗战爆发使得上海业已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发生一时的萎顿,在电影和出版业遭到钳制和破坏的情况下,话剧这种原本带有精英文化性质的形式,以它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迅速的收益,很快填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市场空缺,并且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被赋予了一种更为通俗的大众文化性质。与此同时,对备受物质和精神双重困苦的上海市民来说,到剧场这一独特的文化交流空间去看戏,得到了某种压抑情绪的自由释放。以今天的西藏路、南京路“黄金十字街”为中心,周边的大小剧场多达数十家。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戏剧是民族文化凝聚、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文化血脉最为彰显的部分,戏剧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历来扮演着主唱的角色,而最近上海重现的演剧热潮,无疑激活了深藏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这份记忆。有研究者曾经指出,“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其背景与支撑,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与艺术活动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1的确,一座城市的艺术水平高低,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是城市形象、城市品质的标志性参照系之一。城市文化并非只是物质文化,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生活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建设,文化并不是为了给经济“搭台”唱戏,如果把发展经济作为最终目的而忽视精神文化,要保持上海国际一流大都市的地位是不可想象的。
戏剧在打造“新海派文化”中的功能
说到上海城市文化的特点,人们都会想到“海派文化”一词。作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海派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甚至存在褒贬不一的评价。它在商业都会、移民城市、租界社会等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趋时求新、多元包容的特点常常受到称道,而它的重商意识、市民趣味又多遭不同程度的贬斥。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所谓的优点、缺点,在一种文化形态中往往是掺和在一起,难以切割的,海派文化更是如此。比如,艺术领域里最早的代表—海派绘画与海派京剧,从好的方面说是打破陈规、敢于创新,风格上杂糅中西、不拘一格;从不好的方面说是着眼生意、媚俗小气,做派上炫技争奇、光怪陆离……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海派文化的传承时,用一种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作分析批判,去芜存菁;而不是笼统地肯定、否定,如同历史上有过的京派、海派之争;或者各取所需,就像这些年有些文化产品常用它来做一块块金字招牌。
二是唤醒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忆并不等于“怀旧”。传统的海派文化无疑是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可贵资源,但我们不能不跟随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去创造新的海派文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海派文化似乎被符号化、刻板化了,好像只有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些老弄堂、石库门、月份牌、香烟盒、花园洋房、西装旗袍等,才是海派文化,而真正的海派文化核心和精髓却不见有多少传承和发扬。怀旧当然可以,但作为一座鲜活的、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的城市文化怎能定格在那个年代?
所以,打造新的海派文化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和任务。那么,戏剧在这一任务中担负怎样的角色呢?如前已述,以戏剧为中心的演艺市场曾经是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戏剧在上海,不同于乡间的社戏或村落的庆典,更非私家的堂会,它属于都市文化大众聚集的公共场所,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教育的、宣传的、审美的、娱乐的。尤其在当今传媒盛宴的时代,除了传统的报刊和影视外,数字化的网络新媒体无孔不入地包围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一切商品交流、讯息交换都可以在网上完成,由此也培养了无数的“宅男”和“低头族”。但是,人归根结底仍需要精神与情感的交流,享受一种集体性的共鸣体验,剧场就提供了这样的空间。无论这种现场交流是仪式性的,还是游戏性的,演剧艺术总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整合著社会的价值观念,陶冶着人们的思想情操。这也就是许多人愿意离开身边的电子屏幕而赶到剧场里看一场戏的原因。
回到本届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弘扬和重塑海派文化的努力。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色能够说明。
首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特点。如同经济、科技领域不断地向国际最先进的水准看齐,新上海的演艺文化理应有更大的气魄和更高的眼界,瞄准世界一流的戏剧奋起直追。这些年北京、天津,以及乌镇戏剧节陆续邀请了一些欧洲名剧来演出,但从规格与力度上说都不如本届现代戏剧谷引进剧目来得强大。这次上海邀请的是具有262年历史的俄国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的两台戏和同样出名的立陶宛VMT国立剧院的三台戏,如此集中地展示国际著名剧院和导演大师的高质量作品,以及一流的表演艺术、舞台设计,真让我们的创作人员和观众大呼过瘾,也看到了差距。比如,《哈姆雷特》大家都不陌生,也欣赏过许多版本,但瓦列里·福金导演的作品依然那么具有吸引力,该剧没有胡乱的“解构”,而是在基本遵守经典文本的基础上新意迭出、令人深思。同样,图米纳斯导演的《三姐妹》和《假面舞会》,居然把兩出难排难演的戏呈现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具有现代感,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高水平的舞台演出。其实多元化也是以质量上乘为前提的,戏本身的艺术水平不高,再多样的题材与形式也吸引不了观众。因此,广收博取,拒绝平庸,这应该是建设新海派文化的方向。
其次,在创新中求发展,才能以文化的独特性占据制高点。文化产业的生命在于“创意”,这些年我们却普遍存在同质化的弊病,许多作品大同小异,互相复制,如此下去势必难以持续发展。今年戏剧谷的展演剧目特别强调了原创性和首演率,据统计比例高达80%。即使普及版块“市民剧场”与往年相比也有一定突破,不仅普通市民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而且也不乏新的创意。比如饶有情趣的儿童互动剧目,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一条“国际范”的戏剧大道,请来世界各国的街头、公园表演艺术团队,戏剧、音乐、曲艺、杂耍应有尽有,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往的上海一直是各路演出艺术的大码头和集散地,连越剧、淮剧、评弹等来自浙、苏地区的艺术品种,也是到了上海才逐渐成熟,走向巅峰,成了上海市民十分喜爱的形式。所以说,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文化发展的活力。当然,在当前艺术原创力普遍羸弱的情况下,邀请各地名剧仍是主要的手段,相信今后逐步形成文化品牌后,将会有更多来自国内外的优秀演艺团体和人才,主动到上海来展示他们的新创意、新作品。
第三,新海派文化应当在商业与艺术两者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过去海派文化最受诟病的恐怕就是商业化引起的媚俗问题。本届戏剧谷活动就比较注意对市场的引导,一方面以精品佳作提升观众的欣赏能力,甚至专门设立了“学院奖”鼓励新人新作;一方面从资金、政策上加大对高端艺术扶持的力度,用政府补贴票价的方法使更多的观众有机会共襄戏剧的盛会。在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中,不断提高文化产业主体的素质是必须的,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也不可或缺。同时,专业的艺术评论也应当跟上,不是一般的营销宣传,而是实事求是的批评,这方面仍需加强。
探索“演艺之都”的独特模式
“上海文创50条”谈到加快建设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时,提出“形成一批主业突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创意企业,推进一批创新示范、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文化创意重大项目”的目标。静安现代戏剧谷作为上海首批15家文化产业园区中唯一以戏剧等演出娱乐类为主的产业园区,非常需要总结创办9年来的经验与不足,进一步明确自己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定位与发展模式,探索“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未来之路。
国际上大型的城市演艺产业,大致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模式,它们都是以商业和金融中心为背景的超级大都市,具有深厚的、闻名世界的演艺文化传统,因此能在区域集中的剧院群落里,进行长年不断的商业戏剧演出。另一种演艺形态则是各种各样的戏剧节(或称艺术节),其中以英国的爱丁堡、法国的阿维尼翁和柏林戏剧节最为有名,号称世界三大戏剧节。一旦成为文化品牌,其影响力和辐射力相当强大。
从城市的规模、历史与综合实力来说,上海完全具备打造百老汇、伦敦西区那样的大型演艺中心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历史断层等原因,目前我们的演艺文化产业和市场尚未成熟,还需要在创作演出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剧场建设等各方面进行努力,所以只能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当下正在做并且能够做得更好的就是完善戏剧的节庆展演活动。每年秋季举行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有了近20年的历史,作为国家级的大型对外文化交流节庆活动,它的宗旨是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艺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显然,国际艺术节展演的节目范围更大、品种更多,而且着眼于国际交流。那么,作为区域性、文化创意园区式的静安现代戏剧谷,除了集中于戏剧方面和春季开展活动外,应该如何彰显不同的个性特色呢?
首先,现代戏剧谷设计的三大板块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但是,在高端型的“名剧展演”与普及型的“市民剧场”中间,是否可以再给年轻的戏剧创演者们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爱丁堡戏剧节又称“前沿剧展”,它基本不设门槛,世界各地的戏剧人都可以自带新作参加演出,因此剧目之多令人瞠目,去年一届就演出了3000多个作品。柏林戏剧节则门槛较高,每年正式邀请的剧目仅10部左右,他们的口号是不求“最好”,但求“最值得关注”,由7名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从上一年度几百部德语戏剧中精选出来,要求在思想或艺术上独具新意。于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戏剧家的新作屡屡被选中,尽管每一届总有戏引起争议,很是热闹。对于我们来说,爱丁堡模式也许鱼龙混杂,过于庞大;柏林模式又失之苛严,过于专业。相比之下,阿维尼翁模式倒是值得借鉴,它分为“内”(In)、“外”(Off)两个单元,“内”单元是经过挑选邀请来的;“外”单元则是开放式的,一切经费自理,内容形式五花八门,以青年人的新作为主,但演出被限制在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剧场一天最多可以演到10出戏。由此看来,欧洲三大戏剧节几乎都是向年轻人敞开的,强调创新性、实验性,这的确也是戏剧的活力所在。这一点能否为我们的戏剧节借鉴,在制作经费上给以适当的支持,特别鼓励那些跨国、跨界的合作。
其次,现代戏剧谷每年都会提出一个展演的主题,这个做法很好,但还不够集中和鲜明。如果每年选邀的剧目围绕一个专题,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思考,也避免国内许多戏剧节的雷同化倾向。比如,今年的“名剧展演”就设了“节中节”,集中演出立陶宛的三台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主题或主题模糊的戏剧节,会让人觉得主办方缺乏精心设计,请到什么戏就上什么戏,“拣到篮里便是菜”,效果就会打折扣。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上困难很多,姑且作为今后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本届静安现代戏剧谷落下了帷幕,上海的观众已经在翘首以待明年的戏剧谷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可以预见,随着一批有影响的老牌剧院(如上海大戏院、中国大戏院、长江剧场即卡尔登大戏院)的修复开张,以及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揭幕在即,上海的舞台将有越来越多的好戏登场,久违了的戏剧繁盛景象将会闪亮重现,为我们这座伟大的城市增光添彩,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旭光:《文艺繁荣与城市文化之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