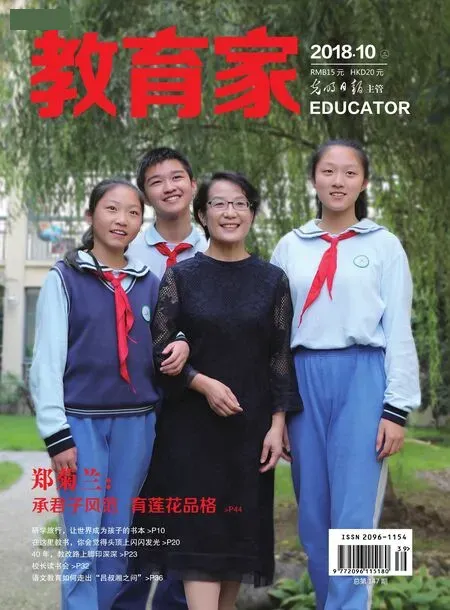语文教育如何走出“吕叔湘之问”
1978年3月16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文指出:“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吕叔湘之问”批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效果不佳。此问发出至今的四十年间,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改革,推出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取得成就和收获也不少。然而,仍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当年的困惑和疑问并没有真正解决,“吕叔湘之问”依旧悬在头上。
适量与慢读
如何才能走出语文教育的困境?著名学者温儒敏提出:提高语文教学效果最管用最有效的办法是读书,是培养读书兴趣,这是关键,是牛鼻子。如何抓住这个牛鼻子?温儒敏先生主张语文课要教读书方法,默读、浏览、快读、跳读、猜读、互文阅读、“连滚带爬”地读,以及如何读一本书,如何进行检索阅读等等,各有各的技巧方法,都要有意识地教给学生。
对于“连滚带爬”地读、读整本的书、海量阅读等提升语文能力新途径,有业内人士则忧心忡忡,以为这会使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学生雪上加霜,难以承受。针对学生负担过大的现状,有人建议,应当理性而精当地确定阅读范围,不必将诸多经典与好书提前纳入中小学生必读或建议阅读的书目中。要让孩子适量适时阅读,而不是大量超前阅读。
学生疏于阅读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课业负担太重,挤压得学生几乎没有整块的闲暇时间。也有人认为是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负面的影响过多,从手机网游“王者荣耀”到短视频应用“抖音”“快手”,学生所受诱惑五光十色,不胜枚举。因此,有学者提出,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精读、研读,而不是泛读、快读。我们在中小学阅读教学中应重点引导孩子学会慢读,学会沉浸阅读、专注阅读,不应过多添加阅读任务,以免干扰阅读过程,妨碍孩子聚精会神读书习惯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建议,在语文课之外单设一门阅读课程,这门阅读课程每周只开设一两节课,每学期只读一部经典,让老师和孩子们一同研读,慢慢读上一个学期,重在疏通字句,把握精义,平时没有作业,也不让孩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彻底抛弃语文教学现在的应试模式,索性让孩子每周在学校和老师无功利自由阅读一两个或两三个小时,期末只作简单测试。
此外,强调阅读方法的训练,也担心可能会将阅读教学变成应试教学。异议者认为,在各种模拟考试与正式考试中,由于题量已经很大,孩子们很早就在老师反复训练下学会了快读、跳读、猜读与互文阅读,甚至是“连滚带爬”式阅读方法。当今中国人的阅读弊端正是不停地刷屏、刷百度、刷朋友圈这样的快速阅读、海量阅读,现在最需要提倡的应当是慢速阅读、精当阅读。将学习重点不放在阅读名著本身,而放在读书方法上,这是一种舍本求末、买椟还珠的行为。
减负亦有迷途
训练阅读方法与增加阅读量是否会加大中小学生的负担、重回应试教学的旧路,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在当下的教育背景之下,强调增加阅读的“量”与“时”及方法训练,如何才能不给孩子们再加重负?如何不令那些方法的训练成为应试的法宝?如何不令那些一套套教材及辅助读物成为商人牟利的工具与学生们做题的材料?这一连串的问题,很难有谁能给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在我们的教育深深为应试所绑架的背景之下,哪个教育主管者、哪个老师、哪个家长、哪个学生都很难不关注分数。分数与孩子的前途有关,与老师的绩效有关,与领导的政绩有关,与学校的声誉有关。分数的枷锁不除,恐怕很难有真正的减负,确实不容易有真正且持久的“阅读”。
适量与慢读,进而为孩子减负,这是个非常好的愿望,听起来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是现实执行又如何?孩子的负担真的减了吗?即使学校教学时数少了,孩子们的作业减了,就能保证孩子去读书、去发展各种素质?那为何有那么多的孩子离开课堂后就无所事事、无所依归,那么多孩子沉溺于网络与各种游戏?还有校外的各种辅导机构的蓬勃兴起,孩子们从这个校门又进了那个院门,那里的学怎么教,读又怎么开展?谁又能给予保障和监督呢?他们不同样会陷入应试的模式或商人盈利的怪圈之中吗?
倘若只将减负当作口号流于言语,而不考虑如何做到减量提质,无疑是饮鸩止渴的错误行为。孩子爱玩的天性与生俱来,周围眼花缭乱的环境中有许多“玩物”和“玩机”足以使他们流连忘返,如果孩子没有健康的指引,他们的健康成长并不一定就有保障。
语文及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加强
笔者注意到,不少学校的语文教育弱化,孩子的人文素质令人担忧。在近些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有不少大学毕业生甚至连一些基本常识都搞不对,说不清张飞、鲁智深出自哪部名著,写起汉字来歪七扭八竟像外文,令人十分痛心。这样的结果是不少大学忽视《大学语文》等人文类课程所致,也与他们在中小学就没有打好基础密切相关。语文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如果弱化语文教育,一味降低对语文的学习与要求,致使孩子内在精神气质里已很少有本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样的“孩子”还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存在吗?
回答“吕叔湘之问”,学生、家长、学校、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笔者以为把减负流于口号,并奉为教改第一要务,有取媚于学生及舆论之嫌。减负已成共识,如何减负才是重要课题。关照孩子的阅读兴趣,在早期教育阶段中家庭教育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幼儿阶段,孩子与家长共同建立良好的亲子阅读习惯,为孩子种下一颗喜爱阅读的种子,让阅读成为孩子通向成长的一架桥梁。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改革和课堂改革,也要保护孩子的自主性,在兴趣和爱好的主观驱动下,阅读自然不会是一种负担。
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强调训练阅读方法与增加阅读量,还是有较大意义与可行性的。当然,究竟如何才能实现倡导者的初衷与我们语文教育的目标,应需在推广过程中切实地加强指导、管理与监督;同时,也要积极追踪和调研实际效果,注意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更新与完善,以避免继续被绑缚在应试机制的车轮上,给学生们带去更大的负担,堕入到人们所担心出现的新困境中。
如何真正引领语文教育走出困境,并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吕叔湘之问”,至今仍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归根结底,不管强调快,还是慢,量多还是量少,都需以提高语文教育质量和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旨归,且不能以给学生增加负担为代价,如此而进行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才能够真正持久和有效果。
——吕叔湘中学的成长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