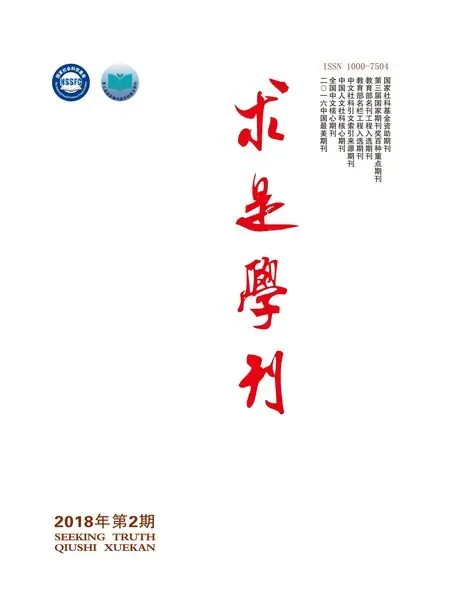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刘永祥
晚近以来,在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下,传统史学开启被动转型的艰难历程。与之相适应,历史编纂学领域也呈现一些新气象,如中外边疆史地记载的兴起、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繁荣、世界意识以及近代意识的增强等。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历史编纂体系,但未实现根本性突破。推动历史编纂学完成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者,正是梁启超。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以此为标准重估、整合传统历史编纂学,而且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然而,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中的承上启下地位和总设计师角色,以往被大大忽略了。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教。
一、以西律中:重建历史编纂理论
梁启超逃亡日本后迅速舍经入史,广泛摄取西学资源,首倡史界革命,试图建立与中国传统史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新典范,从而打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框框,吹响文化救国的号角。①赵少锋:《略论广智书局的日本史书译介活动》,《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他之所以选择史学作为突破口,从主观上讲,是出于实现学科对接的考虑,在他看来,“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而从客观上讲,则是晚清以来“通史致用”取代“通经致用”成为时代主潮的直接反映。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①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开启了史学近代化这一新时代”。②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494页。自此,史学的中心从历史编纂逐渐转向历史研究。以往学界的关注点大都放在史学理论的转移和重构,却无意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即梁启超输入“新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页。“五四”以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批判陷入琐碎的史料整理和考订之风,提倡整体性的历史书写,认为,“一般从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68页。换言之,在梁启超以日本为媒介引入的新史学话语体系中,传统史学几乎等同于以正史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由此切入,我们对于“新史学”应当有新的定位,即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并表现出前期重“破”、后期重“立”,前期重理论、后期重方法的阶段性特征。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梁启超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新史学”是以救亡为旨趣的政治史学,梁启超提倡编纂全新中国通史的深意在于,将书写中心从封建王朝转移到民族国家,重塑大众历史记忆和政治观念。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根本性的一次转折,影响至深至远。当然,这一重构过程自始至终皆以西学为主导。
首先,确立进化史观在编纂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历史编纂的核心,是史家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而时空跨越使二者之间的对话带有鲜明的解释学特性,即使纯粹的事实罗列也是一种意义的表达。因此,史家对客观历史演进的理解,就成为编纂思想的核心。中国史学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史义的传统,这也成为区分历史编纂层次的主要标准。章学诚就将浩如烟海的古今史著独创性地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层次:“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⑤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书教下》,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6页。对于史家主观解释与客观史实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援引西方历史认识论加以重新论述:“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显然,在他看来,历史编纂是主客观的有机结合,两者缺一不可,进化论和因果关系则应成为史家认识和解释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论指导。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中包含朴素的历史进步观,但最为盛行的仍是与王朝更迭相适应的盛衰循环论。梁启超试图打破旧式的朝代观念,极力主张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观察。他明确批评在编纂过程中孤立考察历史事件或简单堆积史实的行为:“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4—35页。自梁启超将进化史观引入历史编纂领域,无论是清末的国史重写运动,抑或民国前期的通史、断代史、专史编纂,无不以此为理论指导,直至唯物史观兴盛,势头才有所减弱。
其次,以国家主义、社会视野重新厘定历史编纂内容。从理论上讲,一切与人类有关的历史活动都应被纳入编纂范畴,中国古代自司马迁《史记》就已形成多维度叙述历史的优良传统,章学诚称之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⑧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申郑》,仓修良编注,第249页。但整体而言,以政治史为中心是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特征,并呈现出重朝廷、轻国家;重个人、轻群体的思想倾向。对此,梁启超运用西方国家主义和社会学知识加以批评,并重新厘定了历史编纂的范围和内容。
西方近代国家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朝代观存在根本区别,强调国家和民族至上。梁启超以此为标准,严词批评旧史家犯有“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弊病,重新厘定“正统”的含义:“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突破种族限制,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力倡新型通史编纂应以叙述“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为主体。①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21、26页。此后,历史编纂无不以民族、国家统摄朝代,实乃一大进步。
社会学则在方法和视野上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和群体性,将观察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梁启超据此批评旧史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并对历史编纂范围做了新界定,认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页。换言之,个人活动是否影响历史演进成为判定其应否被纳入历史编纂范围的标准。他进而率先提出“整个的”概念,主张史家必须具备把握历史整体性的能力,认为“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后能提挈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18、104页。这一“治史尚整全”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提要”,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页。的系统理念,表现为突破政治史范畴,力求反映社会生活全貌。梁启超以独到的学术眼光将人类社会生活径自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类,认为:“这是很近乎科学的分法,因为人类社会的成立,这三者是最主要的要素。拿人的生理来譬喻吧。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髓神经才能活动思想。”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23页。这种划分方式最早见于其1918年所撰《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分为政治之部、文化之部、社会及生计之部(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第15页)。他将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引入历史编纂学,涵盖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方面,便于形成清晰的层次,展现彼此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奠定了通史和断代史编纂的基本框架,由政治—经济—文化组成的三位一体模式成为此后史家最常用的著史格局。⑥值得一提的是,王朝意识的破除以及国家、社会视野的确立,还引起历史编纂中分期观念的变革,即以重大社会变迁取代一朝之兴亡。梁启超指出:“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为研究便利起见,挑出几样重大的变迁,作为根据,勉强分期,尚还可以,若不根据重大变迁,而根据一姓兴亡,那便毫无意义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5—36页)
再次,突出国民意识,转变历史编纂的价值取向。梁启超“新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旗帜鲜明地倡导史学致用,反对“为学问而学问”,实现的主要途径即为编纂新式中国通史。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尚书》即已明确总结“以史为鉴”的思想,并表现出“敬天保民”“敬德保民”的民本倾向,但其服务对象是统治者,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成为时代主题,建设新体制、新文化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关键在于提高民众素质。梁启超以国家主义为依托建构“新民”理论,形成强烈的国民意识,并将其引入历史编纂领域,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就已表现出对史学功能的高度关注,明确区分君史与民史。接受西方文明史学观念后,他将史学置于培育“新民”的主导地位,明言:“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批评旧史虽外貌发达,但陈陈相因,“未闻有能为史界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进而大声疾呼,“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⑦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2、7、11页。显然,历史编纂的价值不再体现于为统治者提供“殷鉴”资源,而是激发普通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为现实及未来生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当然,倡导史学致用并不意味着历史编纂可以降低“求真”的要求。梁启超明确指出:“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1页。显然,他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历史编纂中实现史观、致用与求真的有机结合。
二、对历史编纂形式、方法等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从理论到形式再到方法自成一脉,在世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学者评价说:“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页。对于这份丰厚的史学遗产,梁启超的态度前后发生巨大转变,由最初近乎全盘否定(过度批判)到后来进行系统总结(理性重估)。有趣的是,两者皆以“新史学”理论为思想主导。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就梁启超自身而言,是早期重在破除旧历史观念,采取无差别攻击策略,后期淡出政治、游历欧洲,改变了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并受到整理国故思潮影响。
首先,对传统史书体裁予以批评、整合。作为历史理论展示的主要途径之一,史书体裁绝非简单的技术问题。不同的体裁形式,折射出史家在历史进程和历史结构理解方面的差异性,也直接影响所能容纳的内容深度和广度。外部体裁的变更,常常意味着历史序列的重新整合,所呈现的面貌亦迥然而异。对此,梁启超有清醒认识,曾谓:“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比如,《汉纪》以《汉书》为蓝本,“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虽“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9—20页。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体裁。梁启超以“新史学”理论为标准,对诸种体裁的优劣展开批评,并大胆糅合其中符合现代史学精神者以成“新综合体”。
与人类社会生活由简单向复杂逐步演进相适应,历史记载亦由单一视角过渡到多重视角,先秦时期史书体裁已具备时间、人物、典制及社会情状等不同维度并呈现综合趋势,至司马迁乃编纂集大成的纪传体《史记》,一举奠定此后两千多年的正史典范。梁启超充分肯定《史记》在史书体裁发展史上的转折性地位,认为“诸体虽非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同时总结其优、缺点,谓:“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6、19页。事实确是如此,纪传体将编纂范围大大拓宽,内容包罗万象,能够将历史予以立体化呈现,但同时又无法彻底克服一人、一事分见数篇甚至重复叙事的弊病。
能够反映历史进化大势及社会整体情状并发挥教育功能,是梁启超评价史书体裁的主要标准。因此,传统史书体裁中,除纪传体外,他尤为看重纪事本末体,明言:“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0页。他将这一体裁等同于西方章节体,但同时指出其存在事件之间互不统属、记载范围狭窄的缺陷:“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页。“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1页。上述极具卓识的看法迅速成为晚清学界的共识,并影响了民国时期史家对两种体裁关系的认知。以同样标准审视编年体,则其强于史料储备,弱于历史大势及因果关系的呈现,显然与史学致用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未获梁启超青睐。
批评的目的在于创造。梁启超重建历史编纂体系时基本以西学为标尺,但因将章节体等同于纪事本末体,认为它同样存在弊端,因此在编纂形式上并未做简单移植,而是以崭新的史学理念辨析传统史书体裁优劣,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与现代史学精神更为契合的新体裁。其基本理念从上文批评中已可窥见端倪,一言以蔽之:糅合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创造出“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体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显然,他充分吸收了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同时又对纪事本末体加以创造性运用,明确以“载记”为主干,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而打破了纪传体以帝王为中心的“众星拱月”格局,彰显出新的时代精神。②关于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可参阅陈其泰的《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其次,探索再现历史的多种途径。“五四”以后,随着历史考证风气的兴盛,以及学科化和职业化的初步确立,中国史学开始向专科化迈进,反映到历史编纂领域,表现为通史编纂的一统格局被打破,专史编纂日渐兴起。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梁启超再次以超前的学术意识扮演了时代潮流引领者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猛烈批判,折射出思想文化界蕴积已久的激进心态,并掀起一场“重写国史”运动,试图实现对全部中国历史的重写,但历史观念先行、事实考辨滞后的现实使得这场运动最终未能完成既定目标,即使最著名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带有较重的模仿痕迹,这也是新历史考证学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考史”对“著史”的反动)。面对这一境况,态度日渐趋于理性的梁启超,在经过实践后,深刻认识到通史编纂的困境,并毅然开始探索历史书写的新路径。他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5—36页。梁启超充分意识到“精密研究”对于历史编纂的重要性,尝试克服早期“宏博而不坚实”④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60页。的弊病,并参照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对历史内容加以分类,将历史编纂区分为专史与通史两大阶段和层次。不过,后来他的态度略显消极,将两者关系简单化了,认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历史本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分门别类的专史研究和编纂,目的在于为通史编纂奠定坚实基础,然真正高明的通史绝非专史之和,应以史识统摄全局。
梁启超对专史的规划并非简单将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照搬过来,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史学再现历史的多样方式,共分为“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其中,“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在专史中最为重要”,分为政治的专史、经济的专史、文化的专史,文化的专史又分为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思想史再分为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等。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2页。这种将体裁与学科加以整合的方式尽管并不十分合理,却首次在理论上将西方分科方式引入历史编纂领域,极大地拓展、细化了历史书写内容,丰富了再现客观历史的途径和维度。此后,史家沿着这一方向开拓出无数新的研究领域,编纂出大量风格各异的专门史。金毓黻就在1928年日记中写下对当时史学界的观察:“国人厌为饾饤之学,好为瀚大无边之哲学史、法律史、学术史以自号一家言。”①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8年7月2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2128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确是对新史学“著史”风气的一种反动,但不能就此说“考史”取代了“著史”,只能说形成了并行之势。这与梁启超的大力倡导显然存在密切关联。
三、广开门径:诸多领域的出色实践
梁启超自1918年起专力从事著述和教学,仅十余年间,其著述即达30余种,约几百万字,涉及诸多学科,而最钟情于史学。姚名达曾谓:“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姚名达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77页。梁启超虽一度对考证多所倡导,但其史学主体仍在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显示出恢弘、博大气象。其历史编纂带有开拓性和指示门径的作用,以独特的学术风格、深刻的论述和精湛的见解成为无数后来者的学术明灯。许冠三赞其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而且也是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③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提要”,第1页。可谓恰切。
(一)通史编纂的成功示范
鉴于断代史乃与王朝更迭相适应,无法给人以贯通性历史认识并发挥史学社会功能,梁启超力倡将编纂通史及现当代史作为重要任务加以落实。其理论建构、体裁创新等皆统摄于通史编纂,即使后来转向专史,最终目标仍指向通史。早在《东籍月旦》中,他就以文明史学为标准批评中国没有合格的通史:“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④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9页。他之所以尽力从事新史学理论建构,目的正在于改变中国史家掌握史实而理论陈旧的现状,将编纂新式通史以培育“新民”视为己任。1901年,梁启超所撰《中国史叙论》实为《中国通史》的叙言部分,后在《三十自述》中又谓:“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⑤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9页。此宏愿因卷入政治旋涡被搁置多年,直至1918年,他方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尽管梁启超由于自身及外在原因最终未能编纂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但他按照“新综合体”所编纂的部分篇章尤其是《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仍为如何把历史写活做了绝佳示范。他在致梁仲策的信中说:“《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446、448页。对此,张荫麟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而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来、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⑦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李红岩:《素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94—195页。
(二)突破学案体格局:两部清代学术史
“学术史”这一近代概念虽非梁启超最早提出,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已突破传统学术史“以人为主”的书写格局,代之以“以学为主”的编纂范式,“第一次给人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⑧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第105页。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誉史坛,影响深远,无疑开近代学术史之先声。
梁启超自幼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亲身闻见考据派耆宿的治学风范和方法,他本人也是晚清今文学派和输入西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中西交汇的学术背景和特殊的时代条件使其能够居高临下,俯视过去的学术递嬗之路。概括来说,《清代学术概论》重“论”,贵在梳理和点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重“史”,贵在系统和翔实。二者互相发明,前为奠基,后为夯实,交相辉映,实可视为一体。梁氏曾总结读史的两种方式,认为:“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24页。若用最扼要的话来概括其清学史编纂特点,应该是:既能从纵向上梳理清代学术的演进历程,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时代条件、学术特点和整体成就,又能从横向上铺陈清学各个领域、不同流派以及众多学者的学术成就和特色,充分做到纵横论列,气势非凡,巨细兼顾,分析精当。
(三)当代史述·长篇传记·文化史编纂
自《春秋》《史记》至《国榷》《圣武记》,许多史家有重视当代史记载的传统。梁启超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撰成《戊戌政变记》《欧洲战役史论》等重要的当代史著述。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撰有多部长篇人物传记如《李鸿章传》《王荆公》等。这些篇章在论述范围上虽然无法与大规模的通史、专史同日而语,却将历史事件、人物书写首次从国史编纂体系中独立出来,自成系统,从而构成新的历史编纂形式,同时被灌注以新的史学理念和时代精神,成为中国历史编纂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影响并不亚于其通史、专史编纂。
事件、人物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两大重要元素,但一般作为国史编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少有独立成篇者。尤其是,传统的记事与史传采取“寓论断于序事”②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1年第4期。的方法,而梁启超的相关著作显然受到西方史学影响,不以栩栩如生的描述见长,主打汪洋恣肆的宏论,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学开始从传统描述型向近代分析型的叙事模式转变。梁氏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序例》中明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1页。显然,他“无心走中国传统的记事性史传的正道,却开启了中国阐释性传记的先河”。④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梁启超极为注重历史编纂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无论记事还是记人,无不以贯通眼光梳理演化过程,以开阔视野探寻事物联系,而在叙述范围与内容方面远远超过了古代。比如,他在《戊戌政变记》中结合自身体验,总结了维新变法逐步萌发、推动的过程,划分为道咸间开始萌芽,同光间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中法战争后西学传入较多,至甲午战争后掀起高潮四个阶段,概括了19世纪后60年间对西方的认识,从了解其枪炮、技术,到学习学术、制度的历程,论述客观而中肯。换言之,其编纂目标在于以事件、人物反映时代和社会,皆灌注着强烈的经世精神和爱国情怀。
梁启超还是中国文化史编纂的早期开拓者,曾在《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中规划了包含朝代篇、种族篇、地理篇、政制篇、法律篇、军政篇、财政篇等28篇异常庞大的规模,⑤这一设想直接影响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编纂,可参见王家范在《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一文中所列的对比表格。这充分折射出他力求描绘社会整体情状、关注普通大众生活面貌的史学理念。已编成的《社会组织篇》作于1927年,在广泛搜集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上婚姻、宗法、社会等级、都市、港口等均有论述,堪称对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史做了初步勾勒之作。本篇在研究方法上尤具特色,运用近代社会学、民俗学知识对古代资料做出新解,一些以往学者不甚注意的材料,经他诠释,使人感到新鲜而有趣。
结 语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西学传播的不断扩大,史学经历了长达60年的自我调适后,在今文经学助力下,终于迎来一次总爆发,其标志即为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历史编纂学的转型与史学的变革无疑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史学科学化、学科化、职业化尚未形成之前,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典范尚未确立之前,二者实可视为一体,“著史”仍然占据着主流。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显然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不仅援引西学完成历史编纂理论的重构,而且以“新文体”编纂了多部带有标志性、启发性和开拓性的历史著作,使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改造虽然在整体上以西学为标尺,但自始至终皆非简单移植,而是创造性地将二者加以融合,只是前后期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实则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其“所有的引进和输入都是基于‘中国视角’而且伴随着浓重的‘中国情结’进行的”,亦即“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继承性和中国文化的自身规定性等方面,来审视西方学术文化”。①宋学勤:《“梁启超式的输入”的真意义——兼论中西史学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这是梁氏之学能迅速风靡的主要原因,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恰恰是其在历史编纂上的成功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他所建构的历史编纂体系不仅直接掀起了清末国史重写运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开史学界无数法门”。②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学衡》1929年第67期。许多史家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索,既不断创新历史编纂理论,丰富历史编纂形式,又成功编纂出蔚为大观、风格各异的历史作品,如吕思勉、周谷城、萧一山、张荫麟等都受到梁启超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