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故事:小小幻灯放映室
孙晓鸥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文革”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人们不光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同样十分单调。当时的文艺舞台和银幕上除了那清一色的八个样板戏之外,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那时学校又不怎么正经上课,风华年少又精力过剩的我,由于整天无所事事而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
过一过撒传单的瘾
几年前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大街小巷抛撒传单,这些人传单撒出而被人瘋抢后得意洋洋的样子让我很是羡慕,总想着自己也能过过居高临下撒一把传单让众人哄抢的瘾。我当时手里正巧有一本木刻版毛主席像画册,而我又曾不止一遍地看了长篇小说《红岩》。书里所描述主人公之一成岗自编自刻自印《挺进报》的情节,让我觉得成岗这一英雄形象既高大又神秘。于是便萌发了向革命烈士成岗致敬,自己印制毛主席画像的想法。
我从大院儿的木工房找来废旧的三合板擦拭干净,把需要复制的画像先用白纸拓下来再贴在三合板上,然后用铅笔刀一刀一刀刻下来,最后再用细砂纸和橡皮仔细研磨,一个可以用来印刷图像的木刻印版就制成了。我又找来白纸和墨汁,将墨汁均匀地涂抹在印板上,然后翻过来像盖图章一样小心翼翼地按在白纸上,一张木刻版的毛主席黑白画像瞬间诞生,连我自己都惊叹这神奇杰作。之后我如法炮制继续印制,很快手头便就有了几十张这样的画像。到哪里去抛撒呢?当然我不可能跑到大街上去抛撒,只能在大院里进行,抛撒对象只能是我们家附近那帮同样无所事事整天游来荡去的孩子们。
为更好地完成和见证这一壮举,我找来楼里邻家一个发小来做搭档。这小兄弟搞创意和具体制作不行,但他很会招呼人,用现在的话讲叫忽悠。巧了,他们家还真是东北人。那会儿部队大院儿里楼房都不高,我家住的楼房只有两层,我俩的家都住二楼,最适合抛撒点什么。
这天,小搭档“砰”地一下推开我们家门(当年我们小伙伴之间串门从不敲门,都是破门而入),跑进来挥着手一脸兴奋地喊着:“都来啦!都来啦!快开始!快开始!”我很诧异。他打开窗户向我示意,我伸头一看,妈呀,景色太壮观啦!楼下翘首以待站着十几个孩子,个个眼睛里透着期待和疑惑。我知道是这小哥们儿把这帮傻小子给忽悠来的。顿时,一种救世主般的神圣感在我心头油然而生。我俩先就每次抛撒一张还是多张画像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临时磋商,最终决定每次只扔出一张。因为一次性把画像都扔下去,虽然哄抢场面很壮观,但却只热闹一次;而每次只扔一张的话,这帮傻小子就会反复哄抢,自然我们就可过多次过瘾。主意一定,我立刻拿起一张画像扔到窗外,那张白纸在空中随着风向慢慢飘落时,下面那十几双如饥似渴的眼睛,便随着那张白纸的飘移方向转来转去。白纸刚一落地,大家便蜂拥而上乱成一团,抢到者立刻跳出人堆,得意地把纸举在手中蹦跳狂喊着。此情此景,令坐在二楼的我俩无限惬意和满足!什么叫成就感?不就是这个吗?
幻灯片诞生记
虽然那会儿人们尤其是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单调之极,但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住口。没多久,领袖画像没人抢了。望着空空如也的楼下,我俩十分沮丧!总想着还得整点什么花活打发时光啊!我又想起当年在幼儿园看幻灯的那些场景。那幻灯机射出的长长光柱,以及白色墙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图像,特别是幻灯机的片夹在换片时发出的咔咔声响,神秘而令人心动。于是我俩开始了新的项目。研究制作幻灯机是技术活,当然由我来承包,小兄弟还是负责忽悠人。老爸还真支持我的事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五合板和油漆。我把板子按照书上提供的样式和尺寸锯开并钉好,再刷上油漆,非常漂亮的幻灯机箱出现在眼前。我又按照制作书里的零件要求跑到西单商场去买镜片。当时聚光镜镜片1.4元/个,一对镜片2.8元,再加上一个放大镜七毛钱,全部开销3.5元。虽然觉得太贵,但还是狠狠心将其拿下。其他零部件全部自己制作,基本就没再花钱。
如果说幻灯机算硬件,属一次性投资。那么幻灯片无疑就算是软件,那可就是无底洞了。我跑到文化用品商店和新华书店一看,那些讲故事的幻灯片,有胶片和玻璃的,也有可供自己绘画的胶片和透明颜料,但价格全都不菲。买是不可能了,只能自己制作。人在被逼急了的时候,往往会别出心裁想出很多自己都不曾想到的鬼点子。某天我突发奇想,能否在白纸上直接画画做成幻灯片?从理论上说,白纸不透明,不可能做幻灯片。但我反复实验发现,如果在薄一些的白纸上用黑色毛笔画上图画,然后用特亮的灯泡再通过聚光镜聚光,其亮度就可以把白纸上的图像模模糊糊地映在白墙上。虽然亮度很差看着费眼睛,但这可是幻灯啊!别说我们楼里,就是全大院的家属楼里也没有啊!
于是我马上开始进入正式创作。绘画内容是当时国内最热门的话题:黑龙江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那是在60年代末国内各主流报纸以及电影院里反复播放的主流新闻。我根据电影画面和报纸所讲述的内容,用毛笔描绘出祖国领土珍宝岛的历史,以及当时苏联军队在边境的挑衅行为,还有我人民解放军与侵略者展开的殊死搏斗!画儿是我画的,解说词也是我自己撰写的,真正的自编自导自演,因为播放幻灯的还是我。
“少年私营影视公司”开张了
经过数日奋战,我们的小小“影院”终于开张。我那搭档还真能忽悠,第一天晚上就来了很多本楼的邻居孩子。那年头部队大院家属宿舍大都是简易的筒子楼,而且谁家住房都挺紧,不可能把那么多人乱哄哄请到家里看幻灯。所以我们因地制宜,把幻灯机架在我那搭档的家里作为放映室,然后打开屋门,把走廊对面的白墙当银幕,走廊也就成了观众坐席。那会儿大院宿舍用水用电都是供给制,不按照实际用电量收电费,所以电可以敞开用。我那小搭档也不善,不仅把观众都给忽悠来,还担任片子的播音员。为使播音效果更逼真,他用手捏着鼻子以模仿出成年播音员那种瓮声瓮气的效果。幻灯机光柱通过屋门映射到对面墙上,精彩的节目加上我那小兄弟抑扬顿挫的播音,哈哈,我们那节目相当火爆!大家看了还想看,于是我又继续创作。什么《鸡毛信》《董存瑞》《小兵张嘎》之类。这些片子不光孩子们爱看,连那些大人也三三两两来凑热闹。每天晚上,我们还没吃完饭,“放映室”门口已经坐着很多等着看幻灯的人了,甚至还有人提前摆好马扎子占地儿!有时我正在家吃晚饭,便有观众代表破门而入问我今晚演什么?我说今天不演,新片还没画出来呢!他们便可怜巴巴地央求说,那就把旧的再演一遍呗!我们还想看。说实在话,虽然我经常板着脸和他们讲话,但此时心里这种被追捧的感觉牛极了,这些观众不就是我们的粉丝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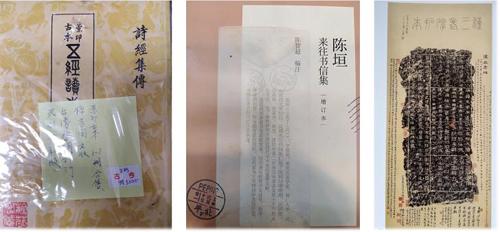
要说当年支持我播放幻灯的是我老爸,那后来断送这事的还是老爸。当他得知我们的幻灯片播放如火如荼时,便在某天晚饭后也来观看。谁知不看则已,一看立马大怒。因为老爸发现这些观众不是美滋滋坐在那里欣赏幻灯,而是个个都像鸭子一样使劲往前伸着脖子瞪大眼睛,几乎把脸贴到墙上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这“白纸版”幻灯亮度太差。不是光源不行,而是幻灯片几乎不透亮,那模糊的影像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老爸看到这景象当即叫停,然后把我带回家好一通严厉批评:“你要干什么?你就给大家看这个?你想让全楼的人都变成近视眼?”我申辩到:“那、那不是真正的幻灯片买、买不起吗?”我意思是,老爸你要真支持我,就给点钱让我去买真幻灯片啊?谁知老爸说,那就别弄这个了,有那时间看看书多好!得,从此以后,我那被人追捧的小小幻灯放映室就此关门!
在后来的生活中,我那退役了的幻灯机一直被扔在角落里。终于有段时间我有能力买来一些真正的故事幻灯片了,可楼里孩子们早已对这玩意儿失去了兴趣,我的幻灯片也只能在家里自己给自己播放了。唉,要多无聊有多无聊!
别了,我的幻灯机幻灯片;别了,那曾经给我带来人生极大满足的小小幻灯放映室;别了,我那曾自创自制自导自演幻灯的家属宿舍“少年私营影视公司”……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一种电影考古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