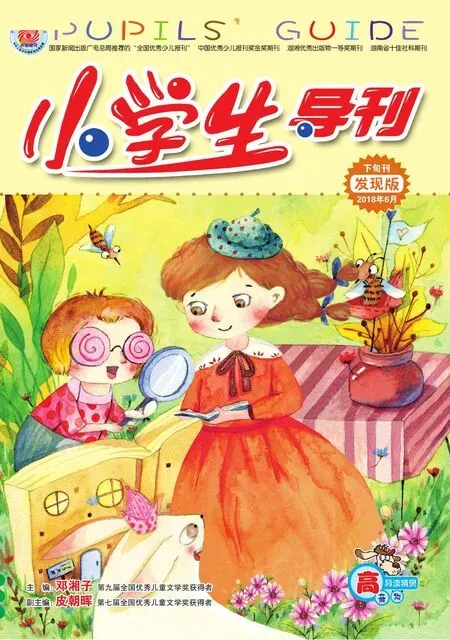第21碗馄饨
廖小琴
古街的馄饨摊只在黄昏时出摊。摊主是个头发花白、腰身佝偻的老头,姓徐。大家都叫他徐阿伯。徐阿伯刚一支摊,古街的人就会迫不及待地拿出早已备好的碗,排在他的摊前。也有心急的,早早就等在设摊的古榕树下。
徐阿伯才不管有没有人等,总是不慌不忙地放担、架火、熬汤。慢吞吞地,时间被他拉得长长的,好像那用棒子骨熬好的汤,可以再次熬到天荒地老。
没有人抱怨。
汤“咕咚咕咚”在大铁锅中沸腾,惹得大伙儿的口水都快流出来时,徐阿伯才将准备好的皮和馅从担中取出。
别人包馄饨,就像摘胡豆,动作干净利落。徐阿伯包馄饨,却似在雕刻,馅轻轻地放,皮轻轻地捏,口轻轻地收。他的馄饨皮薄得透明,能将里面藏的馅料瞧得一清二楚。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擀出这些皮的。
有人问他。他说,只要慢,自然能擀出。
皮虽薄,却从未漏过馅,等放进嘴里,滑溜溜的。
而那些馅就更妙了,都是时鲜菜蔬,红萝卜出来就做红萝卜馅,白菜出来就做白菜馅,没有一样不鲜。馅剁得细碎,将藏在汁液中的香味儿全都剁出来了,被馄饨皮包着,被骨头汤泡着,再拌以相宜的香葱、酱、醋,只是闻着都满足。
古街的人喜欢徐阿伯的馄饨,连猫啊狗啊都喜欢蹲坐在他的摊前。但他脾气怪,每天只做20碗。
为什么呢?
他不肯说原因。
几十年过去,他一直守着这个秘密,无人知晓。古街的人也慢慢习惯,在他的摊前只排20位。
可是,这一天,他的摊前却多出了一位。那是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孩。
“他只卖20碗。”男孩前面的老婆婆好心提醒道。
男孩不吭声,头垂得低低的。
“有许多人都想吃到第21碗,但他只卖20碗。明天来吧。明天早点。”老婆婆絮叨又热心。
男孩仍不吭声。就有那更前面的人,想要看清他,问问他从哪儿来。古街是没有这样一个男孩的。
可是,男孩索性将整张脸都缩进了厚重的大衣里。
大概是从山上来的。据说,那里搬来一位护林员。男孩大概是他的孩子吧。
馄饨陆陆续续出锅。
起风了,很冷,大家捧着热气腾腾的馄饨陆续回到有炉火的家。
“他真的不会卖给你馄饨的。”老婆婆又回头讲。她叹了口气,若不是孙女等着,她真想将自个的那份馄饨让给男孩。
男孩的脑袋仍藏在大衣里。
徐阿伯将最后一碗馄饨捧给了老婆婆。
馄饨一个个卧在碗底,弯弯的。馄饨肚里的翠莲白,使得它们像是一只只晶莹剔透的小绿船。
老婆婆叹了口气,低着头,走了。
徐阿伯准备熄火,取锅子,收馅盆。
男孩站在他的面前。
一阵寒风跑过大衣上的破洞时,男孩打了个哆嗦。
“我每天只做20碗。”徐阿伯说。
男孩犹豫片刻,这才从大衣中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他大而鼓的眼中有一大包眼泪,只要轻轻一戳,准会像雨水哗啦啦落下呢。
“我只做20碗馄饨。”徐阿伯重复。
“我爷爷……”男孩取下口罩,露出一张毛茸茸的脸。
徐阿伯拿馅盆的手停了下来。
“我爷爷,病了。”男孩仰起头,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他很想吃一碗你做的馄饨。”
徐阿伯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古街有馄饨店还开着,你去那边看看?”徐阿伯试探道。
男孩摇头:“爷爷说了,只吃你做的。”
“我每天只做20碗的。”
“都怪我慢,在路上耽误了。”男孩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在大衣上流出一条小河。
“你爷爷究竟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男孩抹着眼泪说:“爷爷没说什么,只说他很想念你的馄饨味儿。”
这么说,男孩的爷爷是吃过徐阿伯的馄饨了。
“是在什么地方吃过呢?”
男孩想了想说:“爷爷提过,是在一个叫灯镇的地方。”
徐阿伯听了,心里一惊。灯镇,距离古街很远呢。三十年前,他走了几个月,才走到这条古街的。他将那男孩毛茸茸的脸看了又看。
在灯镇时,他也遇到过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那时,徐阿伯还不叫徐阿伯,叫徐大,腰没佝偻,头发还乌黑。不过,他那时也卖馄饨。
卖馄饨前,他做过竹编,卖过草鞋,帮人干过苦力。
一天,他背着沉甸甸的盐,停下休息。但坐着坐着,他居然睡过去,醒来时发现一张毛茸茸的脸凑在面前。
他吓了一跳。那张毛茸茸的脸却笑了。
“蛇。”他对他指了指草丛。
他低下头——脚旁,有条蝙蝠蛇,拇指粗,已被石头砸死。
原来,他坐的枯木洞旁就是蝙蝠蛇的家。蛇被挡了路,准备袭击徐大,却被蹲在树上一直好奇瞧着他的家伙发现了。
“谢谢你。”徐大很感激。
被蝙蝠蛇咬的人都必死无疑。他死不要紧,家里还有老爹呢。
毛茸茸的家伙瞧着分明是猴子,但言行举止又和人无异。徐大猜想他大概是云猴。他曾听老人讲,这类猴极其聪明。
毛茸茸的家伙自称卜哒哒。
“谢我什么呢?”卜哒哒歪着脑袋问。
“你想要什么?”
“还不知道。”
“那这样吧,你慢慢想,我这段时间都在这条道上帮人背盐,明天还会经过。”徐大说。
第二天,他又停在那里时,卜哒哒果然出现了。
“想好了吗?”徐大问。
卜哒哒搔头,说还没想好。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并且慢慢熟络起来。
不背盐了,徐大又挑着担,叫卖起馄饨。
“卖馄饨哦,好吃的馄饨来了。”他有副好嗓门,将“馄饨”二字叫得像是蘸着糯香。可是,他的生意却不好。
天气渐冷,一天他正瞅着担里的馄饨发愁,却听头顶有人说:“给我来一碗吧。”
他抬起头,看到卜哒哒正骑在树上。
卜哒哒吃完馄饨,抹着嘴说:“这馄饨真难吃,难怪你生意差。”
徐大听了,很不好受。他不是心灵手巧的人,能包出馄炖,已经不错了。
不过,从那以后,只要徐大经过那棵桐树,卜哒哒都会说:“给我来一碗吧。”
“味道比上次好一点吗?”徐大总会问。
卜哒哒就回答:
“没有,更难吃了。”或者“恩,就是皮太厚了。”“馅味太重了。”
慢慢地,徐大形成习惯:无论如何,每天都给卜哒哒留一碗馄饨,听听他的意见。
渐渐地,他做的馄饨味道越来越好,生意也逐渐好转。后来,他索性在那棵桐树下支起一个小摊。
吃客多了,卜哒哒却很少出现了。
“他怕人呢。”徐大猜测。
冬天时,老爹的病愈加严重,需要更多的钱抓药。徐大只好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将摊摆得很晚。
寂寞的夜里,孤单的炉火挡不住一阵接一阵的寒气。
“给我来一碗吧。”那时,卜哒哒却会出现。
“馅有点咸了。”
“皮再薄点,就好了。”
……
吃完后,他总会和他聊上几句,或者就干脆那么默默地陪他坐会儿。
炉里有橘黄的火,寒夜有人陪,这令徐大觉得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老爹去世后,徐大准备投奔姑爹。
走之前,他给卜哒哒做了一碗菜心馅馄饨。卜哒哒吃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其实有一个做馄饨的秘方。”
他将秘方告诉了徐大。
徐大听了,想笑,什么馅皮要用面杖擀999下,馅料要剁1999下,大骨汤要熬足5小时……
这不像秘方,像是临时胡诌的。
“我保证你做的馄饨比谁的都好吃。”卜哒哒却信誓旦旦地说。他还强调:“不过,每天你只能卖20碗哦。”
“为什么?”
“因为若是超过了,秘方就不灵了。”
徐大说:“好,我记住了。”他并没有当回事。
到古街后,他原本准备和姑爹学做生意,没想到遇上兵祸匪患。姑爹走了,姑妈走了,世界上又只剩下徐大一个人了。
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重新卖馄饨。
只是因一时好奇,他才将馅皮擀999下,将馅料剁1999下,将大骨汤熬足5小时。没想到味道却出奇地好,好像那真是秘方了。
馄饨越卖越好。他的日子也渐渐好转,娶了媳妇,有了仨儿子。当儿子们都像他当年那么大时,他也就慢慢变老了。
仨儿子开了三家馄饨店。他却到古榕树下支了摊。
皮,擀999下。
馅料,剁1999下。
大骨汤,熬足5小时。
每天,只卖20碗。
儿子们劝他休息。他说,你们不懂。
他们也问他,为什么只卖20碗。他也不肯说。
他原本固执,孩子们只好随他,但都在背后笑话他。
“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呢?”徐老伯问男孩。
“3天前。”男孩说,他爷爷原本想亲自来的,“但他病得严重。”
徐阿伯看着挑里。30年,无论是走巷窜户,还是在这古榕树下,他的挑里始终都会剩下1碗馄饨的皮和馅。
他重新将炉火拨旺。胖胖的馄饨,在白色的汤里上下翻腾,像波涛起伏的大海上归来的小船。
做好后,他将馄饨放入事先备好的保温食盒,撒上葱蒜,浇上酱油、醋、麻油。
“走吧。”他拎着食盒说。
“我可以一个人回去的。”男孩说。
他不吭声,朝着通向山林的那条路走去。身后,炉火还在噼里啪啦地熬着那锅汤。
无论在什么地方,卜哒哒只要打听哪儿有只卖20碗馄饨的摊,就知道他在哪儿。这就是他这么多年,坚持只卖20碗馄饨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