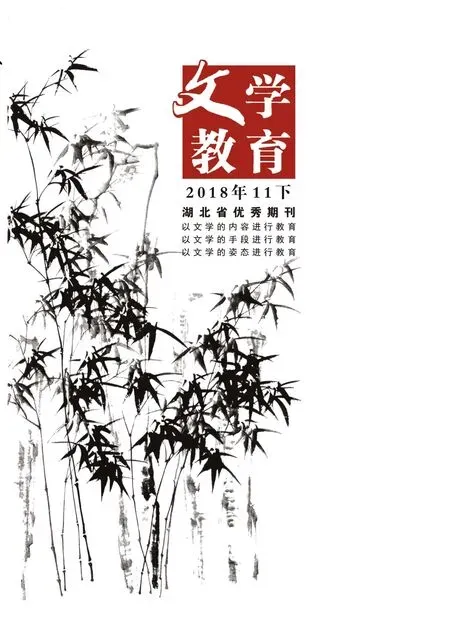论《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的叙事建构
刘侃如
在过去的人类文学创作中以游魂、亡魂世界为主要叙述内容或是背景的虽不多,却也不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神曲》中的地狱、炼狱、天堂,《浮士德》中的魔鬼,《哈姆雷特》中老国王的魂灵,《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甚至《野草》中的幽灵……他们或是快乐的,或是忧郁的,或是黑暗的,或是充满着诱惑的。因着对《圣经》的挚爱,在小说《第七天》中余华索性就“明目张胆”的仿其片段进行创作构造,从第一天起、第二天、第三天……七天的故事,采用了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围绕游魂杨飞作为链接人物展开叙述。第七天,很显然文章的重心是放在最后一天,在字数不足十分之一的“第七天”里,那些游魂,消逝了所有的灰暗,在“死无葬身之地”得到了身心的安息。文章描写了游魂世界,各色游魂穿插在整个叙事中,现实世界倒成了倒影。
一.死亡意识的持续
响了一宵的拆迁声在“我”开屋门时突然消失,“我开门的动作似乎是关上轰然声的开关”。一道门似乎阻绝了生与死,开始了死亡后的世界,却也让我们开始体味着余华笔下的幽灵世界。
在小说创作中,死亡意识从早期的死亡仪式描绘,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将死亡与苦难与人性结和进行透析,死亡似乎有了更广阔的叙述天地。在余华笔下死亡是他极其“喜爱”的一个叙述内容,从早期的先锋实验就可看出。死亡体验、死亡仪式成为了他一直以来叙述的重心之一,他习惯通过对死亡赤裸裸的描述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对文章主题产生异样感,并进而突显出先锋要求。即便是其后的《活着》,也不乏对死亡的描绘。凤霞难产大出血而死、家珍病死、苦根吃豆子撑死……;《许三观卖血记》中虽没有如此明显的叙述,但小说反复提到的“血”又不得不说确是死亡的隐性代名词;《兄弟》中刘山峰掉入粪坑淹死、宋凡平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等等,这些死亡写的直截绮丽澎湃,充满了作者独特的自我感受。
而在《第七天》中“死亡意识”被直接明目张胆的放到了整体叙事题材之中,更加具化、深化,以游魂串接生前身后之事。余华很善于在自我的世界中去体认现实,体认死亡,体认生命的苦难。因此,《第七天》并非是新闻素材的堆积,而是像余华所说“我写《第七天》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实世界里的事件只是小说的背景,死无葬身之地才是小说的叙述支撑。”“死无葬身之地”成了温暖、和谐的代名词。
小说围绕着“死无葬身之地”展开叙事,这是作者对“死亡”更深层的体悟,通过各种死亡方式的叙述,反照着现实,又渲染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虚无意象的含义。女儿坐在废墟上懂事地边做作业边等着父母来找她,却不知道那永远等不来的、因暴力拆迁而死去的一对夫妇早已与她阴阳两隔;杨飞的乳母李月珍发现了在河水里漂浮着的,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引产的二十四个死婴,在多次上访无果后被宝马车撞死;当地的一家商场发生火灾,死亡三十八人,为了不影响市长书记们的仕途,政府方面瞒报死亡人数,通报只有死七人,死者家属受到威胁拿到封口费然后此时不了了之;在警察的残忍逼供及死者家属的不依不饶之下,丈夫被迫承认是自己杀死了精神病妻子,并被执行了死刑,可笑的是其后妻子却又归来;警察张刚在他走出警校后第一次的审讯中踢中了男扮女装卖淫的李姓男子的睾丸,李姓男子在多年申诉未果后刺死了张刚;漂亮的鼠妹如许多和她怀着对爱情美好憧憬的女孩子一样,深爱着她的男友,在一次男友给她买了假iPhone4S后,因为在意被欺骗赌气爬上了楼顶不小心坠楼死亡……在《第七天》中死亡意识不再作为仪式而被详细描述,它是分割线,分割着悲凉与温暖,仇恨与情谊,穷困与和谐。“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连着游魂,也安息了,安息在了这片“死无葬身之地”。
二.片状人物速写
这七年磨一剑的《第七天》自问世后着实让很多论者“失望”了一番,有评论认为这部作品人物形象过于单薄。实际上我们纵观余华其他作品不难发现,人物不过就是他笔下的一类素材,就犹如环境、场景的使用。从早期的先锋实验,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鲜血梅花》、《兄弟》,余华所关注的重心始终都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他就是那么直白的将人性赤裸裸的表达出来,也因此的他笔下的人物是充满着苦难的,苦难的人生,苦难的人性,挣扎在生死的边缘。即便是在《活着》中,劣迹斑斑的富贵形象也没有多么的丰满,他是为“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的主题服务的,整个篇章的人物关系围绕着富贵展开,他既是纽带也是核心人物,因此笔墨较多,着墨如此多地让人体味着他那复杂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而生的生命领悟。
在《第七天》中文章采取串珍珠式的结构,每一章节独立成篇,并由游魂杨飞串联而成,因其涉及人物较多,所以在有限的篇幅内描绘的比较简省,无论是肖像、动作、语言等均是为突出人的某一质性而出现的,他们围绕着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被叙述着: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没有办法表述的人类其他情感,成为了《第七天》的中心。作者试图在小说中涵盖现实中所有的“人之性”,并且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虽驳杂,却环环相扣,丝毫没有给读者任何勉强之感,每个重要人物出场的机会均等,为了小说主旨的塑造,作者截取了片段式的人性、片段式的叙述进行阐释。余华笔下的小人物大多是善意的,鼠妹为了爱情心甘情愿地跟着她爱的人,即便穷困潦倒,她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欺骗,而他的男友伍超则在鼠妹死后为了给她卖块安息之地选择去卖肾赚钱;善良的杨金彪为了捡来的孩子杨飞终身未娶,把所有的父爱都给了杨飞,在重病后为了不拖累孩子离家出走死在了一场火灾之中……作者选取了片状式的人物个性,鼠妹的不离不弃,李月珍的视杨飞如己出,杨金彪的如山的父爱……片状式的对他们进行描写,他们是爱情、亲情、友情的载体。而这些,正是那方游魂世界,尤其是“死无葬身之地”所要叙述的内容,在那里没有了欺骗、没有了误解,更加淡漠了欲望。
三.荒诞:真实的堆积
《第七天》的叙述秉承着余华一贯的叙事风格,将荒诞、讽刺进行到底。余华的荒诞是突兀的、直楞的,没有丝毫的含蓄。就那么活生生的将生活中我们认为的“不可能”,我们无法接受的“可能”,“如实”地摆在读者面前。他的视角是奇特的,他总能捕捉到“粗俗”的生活,并且进行“真实”的再现,如《活着》中富贵骑在妓女身上路过老丈人门口还要打声招呼,荒诞至极却又让人禁不住唏嘘。似是采用了古典叙述的方法,将叙事策略与叙事内容进行了分离。也就是“站在说真话的姿态上说假话”。在余华笔下荒诞的叙事就是一个个的巧合,也就是“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七天的遭遇就是荒诞的真实,所有的死者或是生前或是死后被“七天”安排在了主人公杨飞身边,和他有着若近若离的关系,刚刚变成游魂后的杨飞目睹了一场车祸,而车祸中死去的男性则是鼠妹男友的好友肖庆,游魂肖庆向鼠妹娓娓道来了她男友伍超在她死后的生活;游魂杨飞在遇到了已死的乳母李月珍后才知道了杨金彪的行踪,也才与父亲相认,认出了那个最疼爱自己的父亲。一切都太过巧合,作者将“无巧不成书”表现到了极致,加之整部小说并没有多么厚重,平均分配角色也就难免有让读者有单薄之感。
小说的叙述内容是荒诞的,具讽刺意味的:为了烧市长的遗体,这个城市大面积的交通阻塞,焚化炉有进口与国产的区别,殡仪馆有贵宾候烧区域和普通候烧区域;杨飞的母亲在火车上上厕所时生下了他,李姓男子将自己打扮成女孩的模样从事卖淫,一年多来接客超过一百次,竟然从未被嫖客识破……叙述语言也不时的荒诞:“我的右眼还在原来的地方,左眼外移到颧骨的位置。接着我感到鼻子旁边好像挂着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的就是鼻子,下巴下面的就是下巴,他们在我的脸上转移了”。极具恐怖性的先锋叙述手段放在虚空的世界中,一切就变得这么的合情合理。“她双手伸过来,小心翼翼地把我掉在外面的眼珠放回眼眶里,把我横在旁边的鼻子移到原来的位置,把我挂在下面的下巴咔嚓一声推了上去。”洗脱了先锋的主体叙述风格,但在死亡与黑暗面前仍然保留着余华早期的叙事习惯,“椅子好像要塌了”,“过一会儿就好了”,“不会塌了”,“好像坐在一块石头上”对话的荒诞意味也为行文钩织了情感铺叙。即便是小说的中心———死无葬身之地,无处安息即是永生,又是多么的荒诞,荒诞的名称却又消解了原本的含义,让人不禁唏嘘如此颠倒的世界。这些荒诞、讽刺的小说叙述正是真实事件真实语言的堆积及放大。
在《第七天》里,“死无葬身之地”的幽魂世界与现实世界互为影射,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禅悟或许能在此解释的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