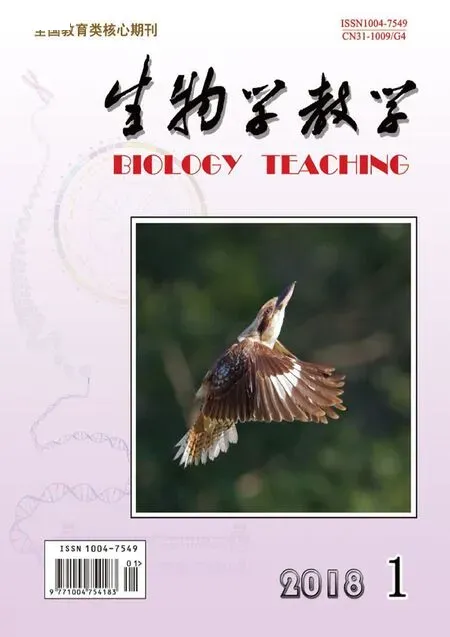中国近代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评介
付 雷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金华 321004)
1 生物学知识的排列
对于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知识的排列,近代主要有系统排列法、共存体排列法、季节排列法、难易的排列法等多种: ①系统排列法,先介绍具体的自然物,又根据生物类群的排列顺序,分为由低等到高等的原始的排列法和由高等到低等的经验的排列法。这种排列法主要是考虑生物学的内在逻辑和生物的演化,不太注意学生的经验。②共存体排列法,将生活在同一生境的生物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介绍,如春之庭园、夏之水边、秋之田野、冬之森林等。这种排列法主要是考虑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但是却忽视了生物学的内在逻辑,而且对于中学生而言,也很难完全理解所谓的共存体之间的关系。③季节排列法,将动植物的生长繁殖与学校教学的时间相协调来安排教材内容,如春天讲授植物开花、秋天讲授植物结果。这种排列法主要是方便学生对自然界及生物现象的观察,但是会显得知识支零破碎,学生对于整个生物界难以有系统的认识。④难易排列法,将较为简单的知识放在低年级的教科书中,较难的则放在高年级。这种排列法是考虑儿童的认知水平及其变化作出的安排。
这四种排列法中,系统排列法和共存体排列法主要是从生物之间的关系考虑的,季节排列法和难易的排列法则主要是从儿童的学习与认知水平考虑的。
在小学的博物或自然教科书中,各种排列法的教科书都有,尤其是季节排列法。但是对于中学教科书而言,则很难只是按照一种排列法组织知识,通常是以一种为主,兼顾其他。最常见的是系统排列法,在具体介绍时,往往选取一种或几种模式生物做代表详细介绍,然后再对类群做总体概括[1]。考虑到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作者在编写教科书时,没有局限于哪一种排列法,因此本文也不硬性将其归类。
2 近代中学植物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
清末民初的植物学教材一般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即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有的教科书称为内部形态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分类学。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各教材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例如,杜亚泉的《共和国教科书植物学》将植物生态学和应用植物学作为单独的两章进行介绍;文明书局出版的华文祺译《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则分为四章,即形态及生态、解剖及生理、分类、分布及应用;黄明藻的《应用徙薪植物学》和马君武翻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大部分内容都在介绍植物的主要类群,而对于形态结构与生理言之少略。还有的教科书则不受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分类学这样的框架约束,而是将其杂糅在一起。如王明怀的《中学植物新教科书》和杜就田、孙佐的《新编植物学教科书》主要是根据植物开花的先后安排各种普发,基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落实,根据生物学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打破模块的限制,将必修和选修课程进行整合,开设适合学生学习的校本生物学课程。从而使学校学科特色更加鲜明,真正体现多样化,满足学生“选择性”的教育需求。
3.3 加强生物学科组建设 由于选课走班教学,打破了原先的行政班,甚至会打破年级制,取而代之的是教学班。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校更要加强学科组的建设。生物学科组教师要精诚团结,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特长,共同进取。学科组要有计划地、扎实地开展主题式校本教研,潜心研究生物学核心素养,提升教师自身的课程开发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学科教学能力。思考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从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传递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需要教师整体备课,思考学科知识的教育价值[3]。
通植物,并穿插介绍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最后集中介绍植物的解剖、其他生理、分布、应用等知识。这一时期的植物学教科书没有太多生态和应用的内容,更没有植物遗传与变异的内容。这些教材大都编译自日本,明显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影响。
到了民国中期(1922年以后),由于出现了综合的普通高中生物学教科书,再加上课程标准颁布的影响,植物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教科书已经注意打破原来分开讲植物各部分构造与生理的传统。如杜就田的《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先讲普通植物,而后讲植物的形态、构造、生理、生态和应用,在构造部分介绍了细胞、组织和构造,在生理部分重点介绍了生长作用、运动作用和生殖作用[2]。在1929年暂行课程标准颁布后,有的教科书则重视应用植物学,如北新书局吴元涤和王志清的《初级中学北新植物学》只有一章介绍植物外形生理和构造的大概,根据植物的用途用八章篇幅分别介绍食用植物、工艺植物等,另有一章为植物学与遗传的关系。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徐克敏编《初中植物学》与此类似,这两本教科书是完全遵照课程标准编写的。彭世芳的《实用教科书植物学》将教科书分为普通植物示教、植物通说、植物之利用三大部分,既介绍了常见的植物、植物的一般知识,还突出了植物应用。
1932年正式课程标准对植物学的教学内容做出调整后,不再单独区分植物的形态、解剖和生理,而是将其融汇在一起,即介绍某一个器官的时候,就将其形态、解剖和生理一并介绍,至于分类则仍然独立。如童致棱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在“叶”一章,就介绍了叶的外形、叶脉的种类、叶的内部构造、植物的营养(含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水的蒸发、叶的变态、叶的繁殖作用、叶与人生等若干节。开明书店贾祖璋的《初中植物学教本》,正中书局王志稼和方锡琛的《初级中学植物学》、世界书局马光斗的《马氏初中植物学》等也是这样处理的。这些教科书在介绍植物分类上有一些差异,另外贾祖璋的《初中植物学教本》又单独一章介绍了变异遗传与进化,马光斗的《马氏初中植物学》单独介绍了植物的生态。
综上,民国中期及以后的植物学教科书已经打破了原来分立的形态、解剖、生理,而是按照植物体的主要器官将其融汇在一起,另外对于植物的应用、生态、遗传也都开始重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清末民初,还是在民国中期,都没有将植物学实验作为单独的章节列出,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其他内容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在植物生理学部分,有的时候则是在附录中。
3 近代中学动物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
清末民初的动物学教科书一般包括通论和分论两部分,通论讲授动物的形态结构、组织、生理、生态及应用,分论则是动物的主要类群,只是不同的教科书侧重有所不同。商务印书馆黄英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动物学》、中华书局华文祺的《中华中学动物学教科书》侧重于分类,没有通论部分,直接讲授各类动物。商务印书馆徐善祥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动物学》则不同,全书分为六篇,分别是分类学、形态学、组织学、生理学、生态学和应用动物学,各篇比较均衡。曾经在英国学习动物学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民国新教科书动物学》中尽管同样将重心放在分类学上,但是在后面几章突出介绍了动物的分布、古动物学和天演(进化与遗传)。杜就田和许家庆翻译的《动物新论》则没有突出动物的类群,对于动物的解剖、组织、生殖、发生、生长、分布、体色等都分别以独立一章论述。
民国中期以后,在1929年暂行课程标准影响下,有的教科书突出了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如王志清的《初中动物学教本》,在该书的各论部分,将各种动物分为家养昆虫、害虫、益农动物、爱玩动物、家畜、寄生动物等。但是大部分动物学教科书并没有采取这种体系,而且1932年的正式课程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动物学教材的结构主要按照动物类群编排,只是增加了动物的遗传与进化、应用动物学、生命的一般特征、人类等内容。如周建人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动物学》。陈兼善的《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动物学》则在通论部分介绍了动物与人生、动物维持个体生命之方法、动物维持族种生命之方法及动物之进化。杜就田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动物学》在动物通论部分,不但介绍了动物的形态结构,还介绍了动物的生殖与发生、习性与形态、进化与分布、与植物的关系,并且将应用动物学作为单独一章。
与植物学教科书类似,动物学教科书一般将实验与课文融合,或者列入附录。
4 民国时期高中生物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
1922年施行壬戌学制改革,初中与高中分开,普通高中生物学教科书开始出版。与分科的动植物学教材不同,高中生物学教科书不再将动植物类群作为重点,转而介绍适合于所有生物的一般知识,即生物的共同特征,包括生物的构成(细胞、组织与器官)、营养与代谢、生殖发育与生长、感应与调节、遗传变异与分类演化、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生物与人类的关系等。但在具体内容的编排上,不同教科书仍有差异,体现了教科书作者不同的教育理念。
王志稼的《公民生物学》突出了实用主义,以培养公民为目标,因此教材的编排强调生物的生活与适应,特别是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抗战开始后的教科书补充了一些与发展生产有关的知识,如《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生物学》增加了生物的疾病、生物体与厚生的内容。
陈桢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是在其《普通生物学》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并增加了关于衰老死亡与寿命、性别决定、X射线突变等生物学进展,同时介绍了自己的金鱼遗传学实验内容[3]。
费鸿年为高中师范科编写的《新中华生物学》为了满足师范教育的需要,特意安排了“生物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一章,列举了进化论、生理学与教育学的关系,后天性质遗传问题;此外,还有一章讨论小学自然科的生物学教学法[4]。
5 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与课程标准的关系
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如何选择与安排,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生物学学科知识体系、教科书编写者对于生物学及中学教育的观念、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等。就生物学科知识体系而言,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知识体系的变化,反映了生物学从传统的博物学转变为现代生物学。不过,在各种影响因素中,课程标准的影响最大。课程标准的拟定者不只是教育部门的官员,更包括了相关学科的专家和中学教师,可以说课程标准是学科相关共同体对于该学科的性质、核心知识体系、教学方法的共识。课程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依据,按照近代的教科书政策,各出版商出版的教科书都要交给教育部门审定才准予发行;同时,出版社与教科书的作者也会突出强调其教科书遵循课程标准编写,以适应学校及教师的要求。不过,在具体编写过程中,教科书的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课程标准,而是有所发挥。
1913年的中学校课程标准最早对博物(包括动物、植物等)的具体内容作出要求。1922年壬戌学制后,初高中分开,但直到1929年才颁布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初中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教材大纲是以实用主义的观点编排的,尽管有一些教科书是按照这个教材大纲编写的,但是这种教科书所占比例不多。这种以习见动植物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固然能够让学生关注生物与人生的关系,且照顾到学生的认知水平,但是这样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让学生获得系统的生物学知识,呈现给学生的生物学知识是零散的。此后民国教育部门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在1932年颁布的正式课程标准中做了修订,初中植物学增加了植物根本组织及功用、各部形态构造与生活方法,而后才是分类大纲,分类部分尽管仍然沿袭实用主义的思路,但是总体上将植物分为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初中动物学则完全按照动物演化逆序,从高等到低等[5]。到1936年再次修订课程标准时,在分类部分,明确初中植物学按照从低等到高等、动物学从高等到低等排列,不再突出实用主义了,只是要求在涉及的地方随时提及[6]。可以说,民国中期的大部分教材都是按照这样的体系编写的,只是在具体的物种上有所差异。
在高中生物学教材方面,1929年的暂行课程标准就要求学生明了动植物与人类同为一生命现象,有基本相同处,受同一基本律支配,给出的内容标准包括生物体的构造、代谢、动植物营养、感应、生殖、生长与发生、遗传、优生、适应、天演、分类、与人类关系等十余方面[7]。尽管在1932年和1936年有过微调,但是总的课标变化不大。绝大部分高中生物学教科书也是按照这样的大纲编写的。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的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课程标准的影响,但是不同教科书的作者所受的教育及思想观念的差异,也左右了其对教科书知识体系的把握。同时也要注意到,当时社会动荡,教育主管部门对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不能施行有效控制,也在客观上弱化了课程标准对教科书知识体系的控制。
6 对当代生物学教科书编写的启示
中学生物学教材的知识体系是教科书编写者和中学生物学教师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知识体系的问题是教科书中安排了哪些知识、如何安排的问题;深层次来看,则是该学科的核心知识是什么、需要通过如何组织达成教学目标的问题。当前的中学科学教育,正在转向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是学生核心素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知识呈现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究竟科学知识中的哪一些是核心的,是对学生终身发展至关重要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还要进一步思考,这些核心知识该如何组织,形成一个怎样的知识体系,才能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思考并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一是从科学发展本身入手,具体到生物学而言,就是要思考生物学的核心知识有哪些,这些知识是如何构成的,相互关系如何;二是从人的发展和社会需要入手,就是思考哪些知识是人将来成为健全的人和合格的公民所必备的知识;三是从学生的心理发展入手,就是要思考知识的组织如何适应中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在基于“标准”的课改背景下,作为教科书编写依据的课程标准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制定和修改课程标准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宗旨,从而为教材建构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