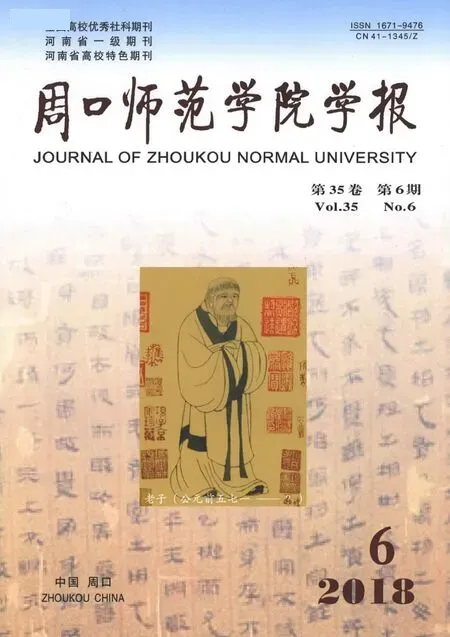乡村振兴战略下乡贤治理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兼对长沙市“新乡贤”评选的思考
匡立波,熊敏秀,周双娥
(1、3.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2.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的总体要求。在此指引下,新一轮乡村建设大幕正在开启,乡村即将迎来繁荣发展的时代机遇。乡村振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报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19,即这支队伍不仅要有一技之长懂农业,更要一门心思爱农村、一以贯之爱农民,不仅包括善于发展农业发家致富的能人,更包含对乡土具有深厚情感的贤人,他们与我国古已有之的乡贤群体有着高度契合之处。本文将从乡贤治理视角分析“新乡贤”的历史传承、当代特点和建构路径。
一、道义共同体:传统乡绅治理的运转逻辑
今天盛行的“乡贤”一词在古代的通常说法是“乡绅”,乡绅即乡村绅士。对于绅士,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张仲礼有较为宽泛的界定:“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则自然属于绅士集团成员。”[2]3费孝通认为官员和其家族集团都属于绅士范畴,“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廷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有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3]6。吴晗强调绅士的在野性,“官僚、士大夫、绅士是一名同体的政治人物……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时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的离职、退休、居乡(当然居城也可以),以至于未任官以前的称呼”[3]37。几位学者对绅士界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界定中有一个共同点:绅士是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或有科举功名之士。以此类推,乡绅包括居住在乡里有功名的读书人、退休官员、有儒家知识的地主和宗族领袖,还包括少数通过纳捐、保举获得功名的商贾之室,总之,乡绅是一个以知识和功名为表征的乡村精英集团。
乡绅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与欧洲农村的庄园制和俄国、印度农村的村社制不同,中国农村不是以集体农庄为基本单元,而是以分散的家户制为根基,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如何对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进行有效统治?其秘密就是乡绅治理。费孝通认为传统社会是“皇权不下县”的“双轨政治”:整个社会有两条并行的治理轨道,一条是在县级以上由专制皇权进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另一条是在县级以下由地方权威即绅权进行自下而上的自治[4]152。皇权与绅权,分别保有不同的治理领域,从中央到县衙是皇权的范畴,由国家官僚统治;从县衙门到家门口的这一段属于绅权的领地,由地方绅士自治。黄宗智则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他认为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政治体系由三部分构成:顶部小块是国家的正式机构,底部大块是社会,两者之间的是大小居中的“第三领域”,“第三领域”是国家官吏与士绅领袖合作维护地方公益的地方[5]。无论是“双轨政治”的二分法还是“第三领域”三分法,都说明乡绅是传统社会权力体系中沟通皇权与民权、链接官与民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大一统皇权对分散小农进行低成本治理的密码。
乡绅治理得以有效运转,重要原因是乡绅对公共事务的承担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一是主持修建地方公共工程,如修路造桥、开河筑堤、兴修水利等。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研究》中,列举了绅士主建的大量公共工程。在道光朝,有陕西华州一生员“捐万金,凿山开路百余里,行人便之”[6],嘉庆时浙江衢州有一生员花银一万四千两,用于筑桥。这些由绅士私人操办的工程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如果工程涉及区域很大,就由若干绅士集资合力规划实施。光绪五年安徽庐州绅士合力建闸,使庐州“七邑田庐生民计数百万得以保护,帑课计数十万得以保证”[7]。二是主持地方福利事业。地方志中记载的绅士发起和建立慈善组织以及个人做善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如《龙安府志》记录了绅士在嘉庆五年地方叛乱时输谷米赈济、施棺收骸的义举。至于济贫、义葬、育婴堂等慈善组织由官吏批准,经费和管理由绅士承担。三是调解地方矛盾。绅士没有皇权正式授予的司法权,但却是解决地方矛盾最重要的仲裁人。据《保定府志》载,当地一生员极善调解纠纷,他老家的各村庄很少有诉讼案件。《湖南通志》载一贡生调解纠纷十分明断,十余年来他所在的村庄竟无讼案[2]50。四是宣传儒家价值观念,如维护寺院、私塾、贡院,宣讲“圣谕”,编纂地方志等。此外,在近代,由于国家政局混乱,有的绅士还负责训练地方团练,成为地方武装组织的军事首领。总之,乡绅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公共职责的承担使得乡绅获得了乡村治理的权威基础。在民间遇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大事时,普通百姓以请到乡绅主持为荣;进行买卖交易时,契约上有乡绅做“保人”买卖才会可靠;在日常的纠纷矛盾处理中,绅士虽然不是国家正式权力的代表,但其调解意见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当事人双方愿意遵从。乡绅与平民之间,除了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被剥削”对立关系,还存在斯科特所说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相互协作关系:乡绅为平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私人保护,平民为乡绅承担徭役和部分税赋,二者按照不同的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形成了乡绅权威与平民依附的二元互动。我们常认为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其实,传统社会小农并非一粒粒沙子,而是在乡村精英黏合之下的一团团泥土[8]。以乡绅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不仅连接了国家与社会、农村与城市,更黏合了乡村内部千千万万的小农,使之成为一个运转有序的整体,庞大的封建国家因而能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长期对基层无为而治。乡绅治理的运转逻辑就是在乡绅的黏合下,乡村精英与一般农民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道义共同体:该共同体以道德规范行为,以伦理调节秩序,人与人之间互动互惠的行为结成一张张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网络内部,社会矛盾自我化解,公共产品自我供给,公共秩序自我整合,因而看似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能绵延千年,具有持久坚韧的生命力。
二、双重脱嵌:当代乡村的治理困境
清末取消科举制度后,以儒家教育为依托的绅士阶层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高人一等的精英身份渐次衰落。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下沉,因战乱频仍对底层社会资源的汲取力度猛增,苛捐杂税盘剥不止,原德高望重之绅士纷纷隐退,地痞恶棍掌控乡政,土豪劣绅横行,乡绅从“保护型经纪”蜕变为“赢利型经纪”[9],借国家权力之手对普通百姓索取无度,致使民不聊生,“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均衡格局被打破,精英与平民的道义共同体不复存在,基层社会坍塌,国民党政权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合作化运动和集体化时代的土地归公,绅士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制度土壤,被划分为地主、富农成为批斗的对象,“在新型的村庄权力格局中,绅士主导的柔性权力被国家主导的刚性权力所替代,内生的文化权威为外来的政治权威所取代,权力运作的伦理道德取向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所取代”[8],乡绅作为一个国家正式权力之外的农村精英阶层被整体消灭了。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国家政权上收到乡镇一级,村庄实行了村民自治,国家与千万分散小农之间的中间地带(“第三领域”)得以重现,但是,乡村精英与普通民众互动互惠的道义共同体并没有得到重建,反而是精英不断“脱嵌”于村庄和村民,多数村庄陷入一盘散沙之中。
一是城市化加速了人才外流,使乡村精英与村庄脱嵌。在传统社会,人才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一批批青年才俊走出乡土,或科举致仕,为官为吏,为国效力,或行商坐贾,积累财富,发展经济,晚年都叶落归根,告老还乡,以一身荣耀与成就成为乡绅,兴办公益,调解纠纷,教化乡里,成为农村秩序的维护者。这样一批批人才走出乡土,一批批官商回归故里,如此往复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10]。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村庄由封闭走向开放,乡村优秀人才通过务工、升学、参军、提干等方式大量流出村庄,乡村精英流失严重。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使乡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的第一波民工潮,1亿多农民流向乡镇企业。90年代初随着“三来一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进入珠三角,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离土又离乡”的第二波民工潮出现,孔雀东南飞成为潮流。改革开放的迭次推进让农民工越走越远,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长三角到京津冀、从沿海到内陆、从国内到国外,一波又一波的农村人口走出乡村流向城市,流到世界各地,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2.82亿[11]。这些农民工是农村最精壮的劳动力,是农村精英的重要来源。除了农民工以外,农村流失的还有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入伍军人等,这些外流人口是农村最有文化、最有见识、最有能力的精英人才,进城以后他们的工作重心和生活重心都放在城市,而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陷入“空心化”困境。
二是市场化侵蚀了村民互惠关系网络,使乡村精英与村民脱嵌。除了大量外出精英,乡村还有一批留在当地有能力、有见识的本土精英,他们或务农或务工或经商或担任村组干部,为何他们也没能在村庄形塑出一个道义共同体?这就是市场化的社会变迁所致。在传统村落社会,农民比邻而居,孕育出了熟人社会互惠协助的分工与合作传统。如在生产环节,农作物栽种和收割时,农户之间互借农具,彼此换工,轮流收种;在生活领域,每逢农户婚丧嫁娶的大事,邻里之间共凑碗筷桌椅,义务帮工;修桥补路时,乡绅捐资,对内对外组织协调,村民出工出力彼此配合,共同完成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彼此协调配合中,村民积累了共同的生产经验和生活体验,产生了对村庄共同体的高度情感认同。在现代乡村,市场经济促使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取代了乡村守望相助的互惠合作习惯。农忙中的亲朋不再彼此换工,雇佣收割机可以解决劳动力的不足;红白喜事时无须邻里互凑桌椅碗筷,亦无须帮工,只需聘请专业厨师团队,相应的人员和设施一应俱全;在路塘堰坝等基础设施建设时,村民不再出工出力,聘请的建筑公司很快能完成工程。市场化、专业化侵蚀了村庄内部的协作系统,催生了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算计代替了温情脉脉的互惠互助,村庄精英不再像传统乡绅一样热衷于承担公共职责为地方谋公益,而是各显神通埋头于个人发家致富,乡村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的抽样统计,我国农村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累积收入之比为10.19∶1,也就是说最富者和最贫者收入差距已有10倍之多[12]。贫富分化使乡村精英日益成为一个有势力的独立阶层脱嵌于普通村民,村庄公共事务缺乏带头人推动,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从一团团泥块重新打散为一粒粒沙子,乡村原子化了。
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发现,中国农村有三个为地方治理提供资源的领域:“公”“共”和“私”领域。三者代表不同的资源供给原则:“公”代表着政府的“再分配原则”,“共”是社区的“互惠原则”,“私”是市场的“交换原则”。在国际比较上,“共”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而农村精英历来是“共”的主要承担者[13]。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精英渐次与村庄和村民脱嵌,公共产品自我供给和公共秩序自我维护的社会机制瓦解,道德伦理滑坡,农村矛盾增多。市场的“私”领域越来越强势,村落社区“共”领域的优势在丧失,“公”领域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日益加大。湖南省长沙县信访局曾对2010-2013年全县的所有信访案件做过统计,发现信访中真正为缠访闹访的不合理诉求只占8.1%,还有91.9%的因山田水土分割和邻里纠纷等引发的矛盾完全可以在村庄和乡镇两级消化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村庄和乡镇基层治理得力,需要县级政府处理的矛盾不到信访总量的1/10。乡村治理如果全靠政府的“公”领域,无论是从人员、从财力还是从精力上看,基层政府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所以,我国的乡村治理还是要复兴“共”领域(第三领域)的传统优势,发挥乡村精英对乡村社会的黏合与带头作用,在村庄中重建道义的共同体。
三、双重认同:新乡贤重构的精神纽带
近年来,各地政府重新审视传统乡贤资源的社会治理价值,大力弘扬乡贤文化,继浙江上虞、广东云浮、浙江德清、贵州印江等地掀起乡贤复兴浪潮之后,湖南省也开始重视乡贤资源的挖掘。长沙市从2014年起在各地掀起了乡贤评选活动,宁乡县、长沙县、开福区捞刀河街道、望城县东城社区通过群众推荐、基层推报、候选人确定、联合审核、实地走访、网上公示、组委会定选等多个环节,各地群众相继从228名候选人中评选出了34名“新乡贤”。《湖南日报》从2017年6月13日起每期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分两季连续推出“寻访新乡贤”系列人物报道共14篇,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赞誉。
何谓新乡贤?从评选结果来看,基层政府和群众对“新乡贤”的界定比较宽泛,从地域来看分布广泛,既有返乡精英,也有本地精英,还有外来精英;从职业构成来看身份多元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村能人,如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企业家,还有普通工人和农民(见图1)。入选者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在工作或生活中为所在村庄付出了巨大努力,为村民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如黄龙新村退休村支书王再德,他倾尽半生心血,历尽艰难将贫苦落后的“三靠村”建为总产值达到6.8亿元的富裕文明村;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文莎,驻扎乡里创办了知名的“薯夫妻”红薯粉品牌,为村民创造了近500个工作岗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罗锡军,先后为村广场捐赠了几十万元的设备设施,常年扶危济困,热心公益;年过八旬的张秀英,多年来致力于调和邻里关系、关爱弱势群体,被楚江村近3000名村民称为“老管家”;乡亲健康的守护者董国安,数十年来坚持上门给孕妇免费体检,上门为残疾人免费诊治,逢年过节看望老病号,被称为“妙手仁心”的乡村良医。这些“新乡贤”并不是当地最能致富、最有权势、最有知识的高大威猛型精英,有很多是平凡的老百姓,是一心为乡民服务的“贤者”,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评价。可见,新乡贤与乡村精英并不等同,不是所有的乡村精英都能称之为“新乡贤”,乡村精英是指来自乡村的杰出人才,有致富精英、技术精英、权力精英、文化精英,侧重于个人才干,属于“私”领域;而新乡贤强调个人对乡村社会承担的公共责任,侧重于对村庄的价值,属于“共”领域。

图1 长沙市“新乡贤”构成状况
在市场经济时代,推动乡村精英从“私”领域走向“共”领域的动力在哪里?传统乡绅治理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旧乡绅有土地供养,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获得功名后与官府有密切往来,享有不服徭役、免纳丁税、减免田赋等特权,受到官府的特别器重和法律的特别保护。卜正民认为,传统乡绅致力于建设学校、修筑堤坝、疏浚湖泊、树立牌楼等地方公益事业是为了获取威望等“象征性资本”,是一种“把纯粹的经济手段转变成更抽象的权力形式的方法,有助于把他们的统治客观化成在地方观众看来是精英力量的权利”[14],传统乡绅与普通平民建立的保护与被保护的依附关系实质上是国家臣民文化在乡村的复制版,二者是不平等的,旧乡绅是特权精英。
现代的乡村已经不再具备人与人依附关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不论财富的多寡、文化水平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他们与普通民众在地位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新乡贤属于平民精英。他们不再有旧乡绅的特权,也不一定担任行政职务,但仍然对当地的乡村发展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源自于中国人对地缘和亲缘的高度认同。首先是地缘认同。地缘认同是指人们对祖籍或故乡的心理共识和文化归属感。在长沙市评选出的34名“新乡贤”中,企业家有8名,其中在外发展回报家乡的企业家有6名;60岁以上的老人有21人,返乡的退休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共有20人。这些在外的企业家为家乡捐钱捐物,献计献策,返乡老人退休不做“闲人”争当“贤人”,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割舍不下的乡土情怀。传统中国以农业文明为主,定居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了人们对故土家园的深厚情感,“从农民一朝的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柩回乡止,那一套所系维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4]173。这份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就是我们常说的“乡愁”,在“乡愁”的感召下,人们愿意抛开理性算计,用乡土情义促进家乡发展,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其次是血缘认同。血缘家族是中国人“差序格局”中的核心圈层。韦伯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对血缘家族的依恋是中国人最深沉、最核心的情感。对外出精英来说,他们从农村到城市发展,个人实现了空间位移或身份转换,但大部分亲戚还生活在农村,对这些亲人的牵挂便成了退休返乡的最大动力。对本土精英来说,热心公共事务,推动村庄发展,既是对集体的贡献,也是对宗族的贡献,居乡的族人乃至子孙后代都能享受到红利,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他们能从自我付出中得到巨大的精神满足。作为中国人,浓郁的乡情、深厚的亲情是千年传承的文化基因,是让我们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重建新乡贤文化的重要纽带。
亲缘和地缘相当于传统社会的互联网,回答了“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属问题。即便在人口高速流动的今天,乡村精英的足迹遍布五湖四海,故乡的村落和亲人仍然是他们内心最深的牵挂,巨大的文化惯性让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地缘和血缘认同也越来越强化,每年“春运”的大迁徙便是对这两种认同的集中表达。无论是外出精英还是本地精英,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是他们的“根”,村落的亲人是他们萦绕在心灵深处的“魂”,对村落与亲人的高度认同凝结成了为家乡谋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重建村落的道义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双重再嵌:道义共同体的再造与新乡贤治理的当代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懂农业”意指有发展农村、农业之才干,“爱农村、爱农民”意指有服务农村、农民之品德,这种才德兼备的人才就是新时代的新乡贤,他们是发展农村的领头羊,是凝聚农民的黏合剂,是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从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乡贤文化的复兴才刚刚起步,在长沙市评选的新乡贤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乡贤占了总数的91%,青壮年乡贤比较稀缺,而实际上乡村精英以青壮年为主,他们有干劲、有知识、懂技术,是发家致富能手。这些有才干的乡村精英如何成长为愿意为家乡出力、为村民服务的新乡贤,积极主动地从“私”领域走进“共”领域?地缘和血缘认同为新乡贤重构提供了心理基础,但心理认同与现实行动之间还需要具体的平台和载体作为桥梁。如前所述,新乡贤重构有两大现实困境:一是在乡村精英外流的较多,精英与村庄脱嵌;二是乡村的互惠网络断裂,精英与村民脱嵌。根据各地乡贤治理的经验,本文认为,要实现乡村精英到乡贤的转换,再造出精英与村民连接紧密的道义共同体,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成立乡贤组织,促进乡村精英与村庄“再嵌”,形成乡村振兴的整体合力。目前农村年轻人迫于生活压力大多流向城市谋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成为为家乡做贡献的乡贤,灵活的制度建设与现代技术力量结合可以加强外出精英与乡村的关联。
成立正式的乡贤组织,构建“村(组)委会+乡贤会”的治理模式。乡贤是“共领域”(第三领域)的主体,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利用社会力量进行乡村建设的必要性,纷纷将乡贤聚集起来成立乡贤组织。其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在村一级成立乡贤组织,如广东云浮的“乡贤理事会”,浙江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贵州印江的“乡贤会”;二是在组一级成立乡贤组织,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廖晓义在重庆巫溪、湖南长沙县等地进行的“乐和乡村”项目建设,重要切入点就是在小组成立“互助会”,互助会理事由愿意为小组事务出谋划策带头做贡献的乡贤构成,再有湖北秭归创建幸福村落,也是在小组成立“理事会”,由村民选出“一长八员”[注]小组理事会由村落理事长和理事(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维权员、管护员、环保员、张罗员等“八员”)组成,简称“一长八员”。在具体实行中根据小组情况进行配置,如果小组精英较多可以“一人一职”,如果小组精英较少可以“一人多职”。。无论是村级乡贤组织还是组级乡贤组织,其共同做法是将扎根本土的典型人物、经商致仕的外出成功人士、投资兴业的外来创业者纳入其中,成立理事会,建立章程,出台兴办乡村事务的行动方案。乡村精英加入乡贤组织以后,为村里谋福利的积极性大增,他们利用自己的见识、技术和人脉为村庄带来大量资源,如德清县莫干山镇燎原村的乡贤帮助联系了9家企业开展“帮扶共建”,引进了22个合作项目,推动落实资金970万元,吸收87名村民进企业就业,结对困难户12户,极大促进了村庄发展[15]。成立乡贤组织可以将村里各类精英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村庄建设合力,让精英的个人发展与村庄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为精英从“私领域”走向“共领域”提供平台。
建立网络村庄的虚拟乡贤组织,开创“互联网+乡贤”的治理模式。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无法分离,“‘什么时候’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16];在现代社会中时间与空间分离了,从而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即“脱域”,并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17]。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使农民的脚步越走越远,他们从传统村落社会地域性的时空中脱离出来融入全球化过程,早期他们只能通过汽车、火车、电报、电话来维系与乡土社会的“弱联系”,而现代高铁技术的普及缩短了人们回乡的时间距离,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拉近了人们与故乡的空间距离,农民与故乡的联系加强,社会关系得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障碍重新组织,为外出乡贤振兴乡村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湖南省桃源县三红村1000多人,村里常住人口只有400人,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在外务工或经商,村支书将外出人员中的30多名精英分子组织起来建立了“世外三红新乡贤”微信群,让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乡贤齐聚微信群共谋村庄发展。该群建立以后,村里在外打拼的青壮年都为家乡献计献策,捐钱捐物,半年内筹集到了20万捐款,修建了风雨桥、村活动广场,正在筹划修建村医疗室、戏台,开展助学扶贫等事务。贵州印江县针对乡贤人士外出较多、难以集中的问题,充分利用新媒体覆盖面广、互动及时等特点,搭建乡贤论坛交流、乡贤文化演绎、乡贤商会融合多个平台,打破时空界限,建立乡贤与村委会日常沟通联络机制,实现乡贤与村庄“零距离”沟通。现代技术让乡村居民的社会互动从时空中抽离了,但现代技术的进步同样可以将抽离的时空重新“连接”起来,外出精英与村庄的关系可以通过技术发展重新勾连。
其次,发展村庄公共事务,促进乡村精英与村民“再嵌”,挖掘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市场化加剧了农民的个体化和农村原子化,原子化的村庄能否重建精英与村民的连接?吴理财认为,公共性建设是医治中国乡村个体化病变不可或缺的良药,激发村落社区居民的公共行动,在公共行动中孕育、产生村落社区的公共性,最终实现村落公共产品的自我生产或自主供给[18]。村庄公共事务是黏合精英与普通村民的最好载体,农民合作是再造村庄互惠共同体的最佳途径。
发展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发挥乡村精英的组织动员作用。公共性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村民自己的责任,而现在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基本都是政府买单,市场兴建,与村民无关。“干部跑断腿,堵不住群众埋怨的嘴”,政府大包大揽效率高,但新农村建设因此成了外在于村民的事,村庄内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反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和农民需求错位,村民的满意度并不高。公共建设可以转变方式,大型设施由政府统一兴办,小型建设可以适当放权,由政府按照财政实力全额或部分拨款,由乡村精英自己组织村民差额筹款并修建。长沙县乐和乡村和秭归县幸福村落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在长沙48个“乐和乡村”项目试点村中,每个村民小组都成立了互助会,互助会理事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村民兴办小组公共事务。如长沙县惠农村村委拨给罗家组10万元修建一条2公里长的组级生态路,由互助会牵头组织、理事监工、组员出工、全组共建,在修建过程中,理事们尽心尽责,严格把关建筑材料和施工的每一个细节,组员分工协作,理事带头义务劳动,带动所有组员都出义务工,结果大大节约了修路成本,原本计划2公里的生态路最后建成了4公里,村民皆大欢喜;秭归县成立了互助会“一长八员”制度带调动群众公共建设积极性,郭家坝镇百日场村在几位理事的带动下集资220万元,新修了18条田间路,总长达23公里,解决了柑橘运输难和田间管理难题。实践证明,体制外乡村精英的动员和组织效果要优于体制内的乡村干部,将“公领域”的部分事权让渡给“共领域”,充分发挥社会精英的作用,有利于挖掘村庄建设的内在动力,让原子化的乡村能再现勃勃生机。
开展村庄公共文化活动,重建乡村精英与村民的互动互惠网络。公共文化建设门槛低,互动性强,是再造精英与村民连接更便利的纽带。近年来长沙市农村基层积极开展了公共文化活动:一是进行道德文明人物评选,很多村庄开展新乡贤、好媳妇、好婆婆、好孝子、文明家庭的评选,还有的村创设了道德银行,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这些先进人物在乡土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垂范引领作用,促使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也促使新乡贤队伍不断成长和壮大。二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和传统节日举办传统文化活动。长沙“乐和乡村”项目的小组互助会非常重视在传统节日节气开展活动,理事们在春节积极排练文艺节目举办农民春晚,在谷雨组织村民采春茶,在端午节组织村民集体包粽子,夏至日开展煮面条,冬至日开展包饺子等民俗活动,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村里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村民其乐融融。开慧镇葛家山村以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动远近闻名,通过广泛的文化参与村民的联系越来越多,关系愈来愈亲密,村里的道德风尚逐渐向好。2016年该村李大爷因家里起火被烧伤住院,病愈回家后发现他不在家的两个月家里饲养的鸡、鸭、猪和种植的蔬菜都被精心照料,长势良好,原来是小组的几位乡贤发动全组组员轮流帮他照看的结果,这样的守望相助在葛家山已经越来越普遍。以先进人物为核心,以公共文化为依托,村落社会能够涵育出文明乡风,重新编织出一张张互惠互助的人际关系网络。
新乡贤评选在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乡贤治理正在大力复兴和重建。新乡贤治理实质就是将有才干、有情怀的乡村精英从“私领域”动员进“共领域”,甚至吸收进“公领域”,让乡村精英嵌入空心化的村庄和原子化的村民中,发挥乡村内部的示范引领和组织动员作用,以乡贤对公共职责的担当再造出富裕的村庄共同体、道义的村庄共同体,让乡村振兴不仅有发展的速度,更有道德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