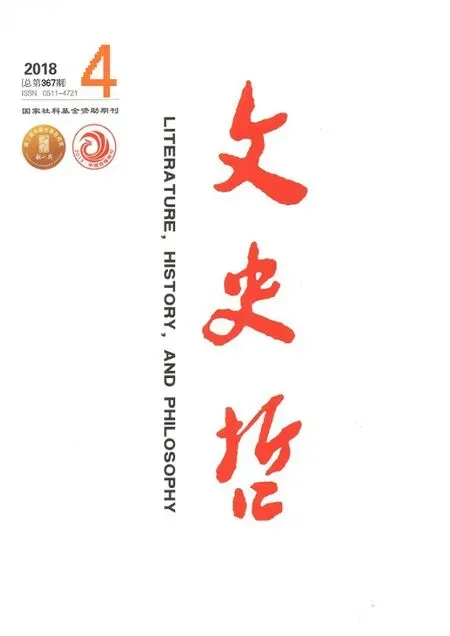“两极相联”与中西之间
——论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儒家哲学元素
张允熠

一、哲学思想的中西际会
中国哲学何时传入欧洲?虽然在16世纪之前,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中国思想文化西传欧洲的涓涓细流,但利玛窦于1594年用拉丁文翻译《中国四书》,以及罗明坚、金尼阁等人的此类著述,应被视为中国哲学西传欧洲的正式开始。至18世纪末,大量中国经史典籍已经被介绍、翻译到了西欧。美国学者埃德蒙·莱特斯指出:16至18世纪随着耶稣会士往来中西之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为18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书志编纂学者对这些书信集散布的状况加以研究(研究的项目包括:购书者系何人,收藏这些书信集的是哪家图书馆,哪些书商),结果显示散布之广相当可观——从波兰到西班牙都有所发现”*[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其中16至26卷约11卷是从中国寄来的*贾植芳:《序》,朱静:《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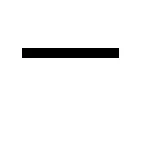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然而,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中国哲学毕竟只有融入欧洲哲学语境或通过欧洲化进程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中西之间的历史性际会来分析两种哲学的异同,并考察欧洲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和中国哲学融入欧洲的途径。
(一)中西哲学的异同。毋庸置疑,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除通常认为西方哲学有逻辑体系而中国哲学缺少逻辑之外,人们还认为西方哲学有本体论而中国哲学无本体论,西方哲学有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无形而上学,等等。差异固然存在,却也被夸大了。实际上,二者异名而同指。中西哲学邂逅和交流,最初遇到的是语言和翻译问题。翻译外来名词和术语,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借词,一种是译词。对于一种指称对象,如果人有我有,就用译词;反之,就用借词。一般说来,一个文化势位高的民族,在翻译外来语言时必然译词多于借词。相反,则是借词多于译词。对于物质名字,无论人有我无或人无我有,翻译上较易对应,歧义不大。而对于一些抽象名词,尤其是对于哲学范畴,就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词,这样,歧义必然发生。例如,像being这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术语,有学者指出:“对于西方哲学这座大厦来说,具有奠基石的功效,对于我们追溯西方哲学思想方式来说,又有行经走纬的作用。”*俞宣孟:《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及其思想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解读和辨析being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在西语体系中争执了数百年;引进汉语世界时,更难寻到一个与之百分之百确切对应的同义词,一般所谓的“是”、“有”、“在”、“存在”等不同译法,对于理解西方哲学的本质常常会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应。诸如philosophy(哲学)、ontology(本体论)、metaphysics(形而上学)、logos(逻格斯)、nous(理性)等哲学范畴,在翻译和理解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正因为在西方来华人士的眼里中西各有其“哲学”,所以他们才致力于在两种哲学之间寻求可以充当最大公约数的译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借词。如,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既用了译词又用了借词,他界定“理学”说:“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意]艾儒略:《西学凡》,《天学初函》明刻本。这样,艾儒略就在“格物穷理”和形上形下的意义上把西方哲学(斐禄所费亚之学)与中国哲学(义理之学)等同起来。在葡萄牙人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名理探》中,Philosophia(斐禄所费亚)一词还获得了“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等译名*[葡]傅凡际:《名理探》,李之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页。,其中“爱知学”比西周的“哲学”译名更贴合“斐禄琐费亚”本义。在诸多译名中,“理学”流行较广:中文叫理学,西文就叫“斐禄琐费亚”,反之,西方人叫“斐禄琐费亚”,中国人就叫“理学”。
有学者坚持认为:西方哲学又称“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本体论”(ontology),而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中西哲学之间的意译或通约的误区。所谓“形而上学”,即追求形上的终极和超验“本体”的学问,而所谓“本体论”,古希腊哲学中并无此概念,它实为一个德文词汇(ontologie),是莱布尼茨学派的沃尔夫最早命名的——就字面而言即关于系动词的学问。实际上,该词在从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等印欧语时早已出现了歧义,再将它译成汉语时,其争议之大更可想而知了。于是,便出现了“万有论”、“存有论”、“存在论”、“本体论”等多种关于ontology的中文译名。
孰不知,“本体论”一词在汉语中被普遍使用恰是出于中国哲学语境自身的理解,因为对“本体”的研究实为中国哲学固有之问题。例如,儒、释、道三家都讲“道”,“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本体,围绕着何者为“道”以及如何得“道”,中国哲学内部有长达两千年的争辩,在魏晋时期,是关于“有”、“无”的争辩,在宋明时期,是关于“理”、“事”或“心”、“物”的争辩。把“有”看成本体,“有”就是“道”;把“无”看成本体,“无”就是“道”。宋明理学诸大师虽然都把“理”作为本体,但认为最高的本体是“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意。而心学家们则把本体安置在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之中,如王阳明反复强调“知是心之本体”,“本体”就是一种自我意识,“致良知”也就成了认知本体的内省功夫。可见,把“being”理解为“本体”,用“本体论”翻译ontology,尽管并不合西方哲学原意,但却打通了中西哲学各家各派的话语通道,从而使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西方哲学范畴禀赋了中国属性。
对“逻格斯”(logos)、“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解读同样如此。“逻格斯”在汉语中被译成“道”、“理性”或“宇宙精神”,但无论怎样译,这一外来的抽象语汇很难确切地呈现原意,致使如今仅把它作为一个借词使用。“逻格斯”通常也指“本体”。“形而上学”这一译名,源自对《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事,中国古代哲人关于“道器”、“理气”、“心物”、“体用”、“本末”、“知行”、“天人”、“动静”等对立范畴的辨析,就包括着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的思辨,它们构成了中国哲学的轴心话题。由此来看,中西哲学都有对本源性、至上性实体的追求,基于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本体论”来翻译西方的ontology、metaphysics、logocentrism,确为异名而同指、实同而名殊而已。
强调中西哲学“名异而实同”,并不是说二者毫无差别。首先,两者在形式和方法上有异,即西方哲学更强调“道”、“器”二分,由此形成了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认知论路线;中国哲学更强调“道”、“器”的合一,由此形成了重整体和动态平衡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一元论传统。其次,在“道器”、“本末”、“体用”、“主客”、“心物”、“天人”、“动静”、“知行”等诸多范畴的“合一”中,中国哲学强调“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相互包含性,这赋予了中国哲学以辩证的特色;出于逻辑规律(不矛盾律)的思维定势,欧洲哲学的“二元对立”通常指两种性质相反事物的对立,如“此岸”与“彼岸”,这种对立终难统一。而中国哲学的“对立”指的是同一事物正反(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所谓“一物两体”,“两体”本来就是“一物”。其三,中国哲学重视现实世界,而西方哲学重视此岸与彼岸的分野,否则,就不可能有精神超越,从而不仅限制了对超验的信仰本体的追求,也限制了对科学理性的知识本体的探索。因此,西方哲学排斥“绝对的”统一观,中国哲学缺少“不矛盾律”的逻辑认知论。
(二)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16、17世纪,继希腊哲学被重新发现之后,儒家哲学西传,进一步点燃了欧洲启蒙主义的火种。罗博特姆写道:“当一位支持者大声说道:‘如果柏拉图从地狱中出来,他会发现他的理想国在中国实现了!’他的话表示承认在欧洲思想解放的使命中,孔子和柏拉图在两次运动中担任着相同的角色。”*Arnold H. Rowbotham,“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 4, no. 3(1945):242“两次运动”指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者受益于希腊(柏拉图),后者则得力于中国(孔子)。莱布尼茨的《论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中国哲学家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沃尔夫的《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伏尔泰的《论孔子》、魁奈的《论中国的专制主义》等著作,都是这个时代著名欧洲启蒙哲学家对儒家哲学传入后所做出的回应。


(三)中国哲学融入欧洲哲学的主要路径。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认为,17至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有两条线索可寻——“一条是由莱布尼茨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密到休谟”*[美]N·P·雅可布逊:《休谟哲学可能受东方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就第一条路向来说,莱布尼茨旅居法国时与唯物主义哲学家培尔因观点不同发生过辩论,费尔巴哈曾说:“正如莱布尼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万能的天才,是一个在各门科学中都有所建树的天才,培尔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不是在同一规模内——包罗万象的批判家。”*[德]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史著作选》第三卷,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6页。培尔批判了莱布尼茨哲学中的经院哲学遗痕,但却把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的“自然神学”视为与斯宾诺莎无神论一样的典型。至于休谟,其《人性论》一书就是在法国完成的,休谟明确承认其学说与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人的观点有密切关联:“休谟对斯宾诺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比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中的有关条目。休谟步培尔的后尘,主要考察了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和属性的学说,并与培尔的观点如出一辙。”*周晓亮:《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8页。莱布尼茨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休谟既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同时又受斯宾诺莎的影响,培尔则发挥了中介作用。
就第二条路向来说,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首领魁奈是18世纪欧洲宣扬中国思想文化的又一重量级人物,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深受其影响。亚当·斯密又是休谟的忘年交,两人自1752年之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周晓亮:《休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斯密的两部名著《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都是在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道德哲学原理与休谟的《人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性论》成书的时间早于斯密的两部著作,应该说休谟影响了斯密更符合逻辑。

二、中国原理被纳入欧洲的思维形式
由上文可知,中欧哲学的对译和中国哲学的西传,实起因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所引发的两大文明系统之间的邂逅性相遇。就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来说,“伟大相遇”的史实仅为外证,内证则需要从对中国哲学融入西方哲学学理内部的分析和论证中开显出来。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的实体就是“自然神”,“自然神”是隐蔽的无神论。这源于斯宾诺莎与笛卡儿共同的学术师承,即自幼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们的哲学以浓郁的“东方余风流韵”。笛卡儿从8岁到16岁在耶稣会学校中接受了8年教育,这影响了他的一生,致使“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80页。。人们从笛卡儿学派的实体论中,不难看到儒家哲学实体的身影,那就是“理”或“道”。


(二)朱熹哲学与“有机论”。当代哲学界一般把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为“有机哲学”。然而李约瑟却认为: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中国哲学是“有机论”,尤以朱熹哲学为代表;在西方哲学中,莱布尼茨是“有机论”,而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有机论”哲学体系*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1.II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6):500.。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受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朱熹哲学的影响。
正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把朱熹哲学推介给了欧洲思想界。该书在《导言》中说:“儒家自汉代以来,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明代就集中表现在将程朱理学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非朱之言不尊’,‘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吴孟雪:《柏应理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秋之卷。《导言》还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太极”概念,指出:即便朱熹本人也承认,无论伏羲还是文王、周公,都没有使用过“太极”这一概念,“太极”一词只是孔子自己在《易经》的“附录”*指孔子作的《易传》,即“十翼”。中写上去的。“太极”即是一个包括着阴阳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体系,朱熹认为,自太极至万物化生,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达用,从微至著,内含着对宇宙生成的见解。基于这一点,李约瑟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所谓“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在朱熹之前,中国哲学的全部背景都是如此,在朱熹之后,则有莱布尼茨的哲学如此*[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4页。。

(三)“理”、“道”、“性”与“理性”。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它把儒家的“理性”概念介绍到了欧洲。如《大学》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而该书的拉丁译文意为:“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精炼或改进我从上天汲取而来的理性(rationalem naturam),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唯有扫除了蒙于其上的邪欲瑕疵,才必然会恢复它那无比的清澈。(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 ando seu reparando),当然,要依靠他们本身的榜样和规劝。(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立场坚定,保持最大的德行。”这里,“道”译成为“理性”。再如《中庸》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哲学家孔子》译为:“上天置于人们心中的东西叫做理性。这种用理性造成的、并对之加以模仿的东西,叫做法则,或叫做和理性的一致。反反复复、勤劳不辍地按照这种法则实践并亲身遵循之,那就叫做教育或善德之学问。”*上述译文转引自吴孟雪:《柏应理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秋之卷。这里把“性”译成“理性”,把“道”译成法则,并认为其与“理性”一致。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的“理性”从传入欧洲起,就被纳入了欧洲化思维的进程,成为欧洲近代哲学“理性”概念的重要源头之一。
实际上,早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利玛窦等人在16世纪就把中国哲学的“理”与“道”译成了西文的reason(理性)。17世纪,欧洲哲学界开始广泛使用“理性”,到了18世纪,“理性”成为整个思想界所高扬的一个名词,就像一首乐章中高亢的音符——这是时代的最强音。18世纪的欧洲进入了一个理性的时代,“理性”一词在欧洲虽然有着本土的思想来源,但随着中国哲学的传入,中世纪“理性”(神性)发生了质变,出现了取代上帝的一种“纯粹理性”*莱布尼茨曾把朱熹的“理”称为“至上理性”,所谓“至上理性”即超越任何经验的纯先验的理性,这是“纯粹理性”的第一层含义。“纯粹理性”的另一层含义是不掺杂任何神性的理性,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说:“经过宗教原则的彻底转变和市俗化,中国人的意识完全避开了宗教过程,并在一开始即达到了其他民族经过神话过程才能达到的纯理性的境地。”([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0页)从莱布尼茨到谢林,欧洲哲学家曾把这种“至上理性”和“纯粹理性”追溯到中国哲学那里。。所谓“纯粹理性”,一是不受“物性”羁绊,绝对超验;二是不杂任何“神性”,绝对纯粹。而在此之前,欧洲的理性皆不纯粹。谢林说:“我们一定能够——以便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找到一种上帝的替代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原始神明的替代物。”*[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第138页。欧洲人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才认识到了“纯粹理性”的存在,而中国却很早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理性”在希腊和基督教哲学传统中大致有三个用词,一是reason,二是nous,三是logos。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多是用nous和logos,它们都没有脱离“神性”,甚至等同于“神性”,如《圣经》上说“道(logos)成肉身”,nous被理解为“宇宙灵魂”,等等。而reason一般被理解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把“道”翻译成拉丁文rationalem(理性)的同时,还用了另一个拉丁字naturam,即“自然性”。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儒家的“理”张扬了一种“自然律”(natural law),即“天道”,也即“理性”。如:“孔子所说‘天’,即为自然;所说之‘天道’,即为自然的道理;所说‘顺天而行’,即为按自然的道理来行。自然的道理,即理也。”*宋晞:《中国文化与世界》,第22页。埃德蒙·莱特斯认为在欧洲人吸收儒家思想的学术背景后面,“透过两大学说之间的争论而尤为突出。一派学说是基督教主张的启示说;一派主张18世纪所谓的‘自然道德律’或‘理性’说,此说可溯其源古典希腊罗马。这个争论是西方本土固有,但这个本土争论却为吸收中国思想预先铺设好路途”*[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可见,欧洲人是基于欧洲固有的“理性”范式来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学之“理”的。
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的流行表明过去被视为“万恶之源”的无神论合法地楔入了欧洲思想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2页。这里所说的“清一色的无神者所组成的社会”就是指的中国社会。笛卡儿学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马勒伯朗士写了一篇《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学者的对话》的冗长文章,对话中的一方“基督教学者”可视为马勒伯朗士本人,对话中的另一方“中国哲学家”可视为朱熹的化身。马勒伯朗士把中国哲学的“理”界定为无神论,反对把“理”说成是“上帝”,因为“理”没有脱离物性。马勒伯朗士对朱熹“理”的“物”性认识与莱布尼茨把“理”比拟为“神”的做法从相反的方向上接近了朱熹“理”的本色。因为在朱熹那里,“理”一方面是超验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6页。,另一方面,“理”与“气”又是不可分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4页。。莱布尼茨与马勒伯朗士都是有道理的。马勒伯朗士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所以在18世纪欧洲,变成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变成革命的哲学,这一位笛卡儿(按即笛卡儿)中派的麦尔伯兰基(马勒伯朗士)的解释,对于法国百科全书派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四)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罗博特姆说:“柏拉图曾传授过道德法则,但是,柏拉图是理论化的和形而上学的,而孔子则是实践的,却是更重要和更成功的(后来,当伏尔泰对希腊的形而上学抱着嘲笑和鄙夷的态度而转向儒家的实践人文主义时,他支持了这一观点)。”*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4, no. 3 (1945): 239.16世纪中国哲学初传欧洲时,利玛窦最早把它界定为一种“道德哲学”。到了德国哲学始祖莱布尼茨那里,他对中国的“实践哲学”十分推崇*[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张允熠编:《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237页。,莱布尼茨逝世之后,沃尔夫的哲学统治德国思想界近半个世纪*康德从幼年时就跟随弗朗茨·阿尔伯特·舒尔茨(Franz Albert Schultz)学习,1732年,又进入舒尔茨任校长的腓特烈学院(Collegium Fridericianum)学习拉丁文。而舒尔茨是沃尔夫的学生,因此,康德算是莱布尼茨的三传弟子。,沃尔夫在1721年7月发表了一篇给他带来了厄运的演讲,题目就是《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沃尔夫说:“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令人钦佩。”“在我们眼中,孔子常常被看作如此伟大的智慧的始祖。这种看法恰恰表明了对中国情况的一无所知。早在孔子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已经为自己拥有最卓越的法而自豪了。”这种“法”是什么呢?他认为,这就是“至善的准绳”,是“正派高尚的品德”。沃尔夫宣称:“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德]沃尔夫:《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张允熠编:《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第255、267页。即使在因宣扬中国哲学受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和中国哲学的正面评价,事隔24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一个哲学王治理下人民的真正的幸福》的文章。康德作为沃尔夫的再传弟子,虽然开始贬低中国哲学,然而尼采却把他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三字实指“孔夫子”。因为在当时欧洲的语境中,孔子常被称为“中国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7、713页注18。。马克思在提到“中国人”时还把他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相并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2页。,这里,“完善的中国人”即指孔子。

不过,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吸收了中国哲学思想要素。在哲学史上,除马克思公开承认他继承了黑格尔又批判了黑格尔之外,主动承认吸收了别人思想的哲学家微乎其微。尤其是康德,他“相当自信地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任何其他思想的翻版,而是自成一家的创造。所以,他的道德哲学不提卢梭的贡献,当然也没有必要提及中国儒家思想的贡献”*谢文郁:《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代序)》,[美]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14页。。理性的先验性和至上性、道德的形而上性和实践的自律性以及“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正是康德哲学能够打通中西的主要隧道。
三、中国哲学与黑格尔
以上我们撮要讨论了中国哲学被纳入欧洲思维形式进而转化为欧洲哲学理念的若干内证,实际上,中国哲学(包括佛、道哲学)对近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渗透远不止这些。单就17世纪以来中欧哲学的融通而言,最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哲学,而黑格尔哲学又是德国近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因此,我们有必要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个案提取出来给予专门剖析。
(一)黑格尔哲学的实质。“绝对精神”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着基督教的logos、新柏拉图主义与斯多葛派的nous的痕迹,然而,它更依托于笛卡儿、斯宾诺莎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之“实体”论的基础和莱布尼茨以来德国唯理论哲学自身的土壤。马克思曾经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跟前辈们的“实体”论不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纯粹逻辑概念的推衍,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辩证否定的对立统一。“绝对精神”在经过了一系列辩证发展的过程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它是“理性”的最高阶段。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来没有“无”这个范畴,正是黑格尔首先把“无”纳入了他的思辨哲学体系。直至后来,海德格尔的“无”也是其存在论中的重要范畴。黑格尔之所以批判康德,是因为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悬隔于感性与知性之外。而在黑格尔这里,“物自体”不仅是可知的,而且是能动的、生生不息的、终极的本体——这就是“绝对理念”即太极。
“有无变”、“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等等,这些辩证命题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指的同一事物两种属性的相成相辅,这是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欧洲传统哲学最显著的地方——在欧洲哲学史上,我们绝难发现“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命题的前迹,但对于熟知中国儒、道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却丝毫不陌生。欧洲哲学的实体论渗进了中国哲学元素,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中有着中国式的思维逻辑。要深入探寻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无视中国哲学在近两个世纪期间对欧洲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不能忽略从莱布尼茨以来儒家哲学对德国哲学的渗入。斯宾诺莎的“神”、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物自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人们从这些众多的“实体”论背后能看到中国哲学“理”、“道”、“心”、“性”、“诚”、“太极”等概念的身影;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到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我们在这种德国式的思辨形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的特征。为此,我们有必要揭开黑格尔“西方主义”的面纱而窥其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
(二)黑格尔西方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费尔巴哈说过:“谢林学派对东方向往,乃是这个学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向往西方贬抑东方,即是黑格尔学派的本质特征。”*[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页,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实际上,知识渊博的黑格尔从来不否认东方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他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造的地方。”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样,“精神的光明”也从亚洲升起,而它大放光芒却是在欧洲,“前亚细亚最为特异的,便是它没有闭关自守过,将一切都送到了欧罗巴州。它代表着一切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的开始,然而这些原则的发扬光大则在欧罗巴州”*[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他甚至用“盲人”来隐喻中世纪的欧洲,后者既然得到了启蒙,周围的一切都看清楚了,那么,他现在就要“转而思索它自己内在的东西……他重视他自己内在的太阳,更过于他重视那原来的外界的太阳”*[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0页。。这就是黑格尔强调的“自由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正如太阳自东向西运行,中国是“最东方”的,相当于人类的幼年期,接着是希腊,代表着人类的青年期,罗马是人类的中年期,而以日耳曼为主的欧洲则是人类的老年期。太阳运行的轨迹,也就是“精神”从“一个人”的自由(东方的君主专制)向“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世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东方……历史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着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0页。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追述,东方是起点,作为“最东方”的中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正像黑格尔所说,东方这个“外界的太阳”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他“内在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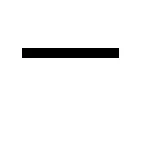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有趣的是,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曾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费希特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而最早注意到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极其相似的人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曾写道:“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和祆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5页。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一篇《国际述评》中再次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既然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共同之点”,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公开回应却是一种极力贬低的评价呢?这也是发人深思的。对此我们可以这么看:
首先,黑格尔成长于欧洲“中国热”流行的时代,他的前辈们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正负两方面评价在他的思想中都有体现。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借用了别人的说法。其次,“中国热”的消退归根到底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和中国国势的急剧跌落,黑格尔逝世不久,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时过境迁,西方人很少再会赞美自己的“手下败将”,相反,侮辱、贬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西方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成为时尚,黑格尔的中国观不可能脱离这一时代背景。例如,他读过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使华的笔记和1798年出版的该使团副使斯当东的使华纪实,这对当时欧洲的“中国迷”可谓是当头一瓢冷水,“中国热”沉寂下去,批判甚至抹黑中国之风一时流行起来。

四、结 语
始于四百年前的中西哲学的“两极相联”和“伟大相遇”,以及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对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显著标志便是在哲学领域用“理性上帝”取代了“神本上帝”。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正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中国,他们运用来自中国的“理性”和无神论哲学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在此过程中,西方思想家所看重的中国哲学“原则”,逐渐融入新生的欧洲哲学范畴,被纳入西方的思维形式,中国元素被深深嵌入了西方语境的深处。

西方哲学无疑有着自身的大本大源与发展理路——这主要得力于希伯来文化即“犹太基督教”传统,但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的输入,则与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希腊思想共同形成了理性时代“两个平行”的推动力,致使欧洲思想界执牛耳的重要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及其后学以及伏尔泰等人“都毋庸置疑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4, no. 3 (1945): 242.。“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是要在中国发现普世主义的内容,是要从犹太——希腊——基督教传统之外汲取榜样。他们了解中国并非出于自我兴趣,而是要从中国文化中挖掘资源来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第174页。美国学者孟德卫说,启蒙哲学家们认为诸如基督教那样依靠神的启示和信仰的宗教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祸根所在,因此,“启蒙思想家寻求用自然神论(理性宗教)来替代基督教(启示宗教)”*[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第169页。,中国哲学便成了他们的依皈。“启蒙哲学家们赞美儒家道德,认为它无须借助宗教便能教导人们是非对错。事实上,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作他们的圣人。”*[美]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第174页。
欧洲的启蒙哲学家们还认为,中国的基于道德理性的政府正是欧洲中世纪世袭领主制所最缺乏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平民无法进入政治圈子,反观中国,官员皆由考试录取而来,官员即学者,学者即官员,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平民进入统治阶层铺设了通道,这种官僚科层体制是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首创,因此,他们高度赞美中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儒学体系中最让欧洲人感到欢欣的要素之一就是学者在中国的地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们的这种共识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启蒙运动开始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就被视为是一块摧毁了政治家和学者之间樊篱的土地。当伏尔泰在政治改革的领域中小心翼翼地探索时,他把‘哲学家’做王的中国作为理想国,并以此提议选拔‘启蒙哲学家’出任内阁部长。伏尔泰被称为‘费尔梅的孔夫子’,这只不过表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内心中的一种向往而已。”*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4, no. 3 (1945): 241.当我们发现文官制度在19世纪的英国突然平地而起,知识分子以平民身份也可“封官加爵”时,我们就更不能忽视中国元素对欧洲文化的实质性渗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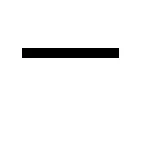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然而,从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又出现了新的危机。理性主义复兴导致了欧洲近代哲学革命,它的进一步发展则走向了反面:传统形而上学被强力“拒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思潮泛滥,哲学本体论已不再具有知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预告了哲学的终结,进入20世纪,许多知名哲学家都相继从各自的学理角度进一步断言哲学终结,如海德格尔所言:“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然而,与西方相比,中国始终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在西欧尚处在神学(宗教)时代之际,中国则已进入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时代。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讲,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看就是一个以哲学代宗教的文化,“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其实,19世纪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德国哲学家谢林就曾断言中国人因为避开了西方人经过宗教的曲折历程,才获得了纯粹理性。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达到顶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现代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峰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积弊之重延宕至今呈现出深层次危机:要么以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物化思维、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体现人的“在场”,要么以张扬唯意志论、直觉论、“现象学”的“存在”还原意识之人,甚至把哲学碎片化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分析工具,等等。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中把真正的哲学抛弃了,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大道理没人讲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哲学被解构得不再是哲学了,以至于其解构主义也不是哲学,只能算作一种“思想”了……*杜小真、张宁肯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人们开始呼吁“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在场,三百多年来,从莱布尼茨到海德格尔,相当一批欧洲主流哲学家无不把欧洲思想界寻求支援力量的关注目光一再投向中国,试图从跨文化角度汲取东方的智慧和营养。
然而,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我们应着眼于人类理智共性的“普照的光”,而不是拘泥于对中国哲学文本所谓绝对正确、无误的理解或诠释。且不说当年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以及他们的后来者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异质文化的隔膜下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儒家的经典,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又何尝能够真实无误地完全理解自己祖先的坟典呢?中西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古今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日耳曼人的近代欧洲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因此,跨文化的哲学交流,重在思想的启蒙、启发、启示。跨越沟壑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既为一种同质的共求,更是一种异质的互补,唯有如此才能对人类的文化总量有所增益,对其品质有所提升。由此来看,欧洲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需求不在于原汁原味地照搬,而在于后启蒙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理,当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吸收,也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