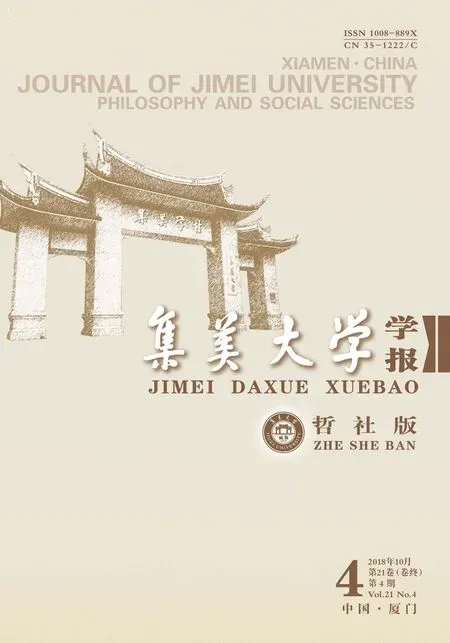汉字意象系统的传承与更新
——以“火”为例
郭 菁
(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引 言
现代两类“意象”术语运用广泛。一种是“审美意象”,“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象显现。”[1]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应属此“意象”的早期使用。另一种则用为认知语言学基本概念“image”的中译。王作新指出:“思维活动中的意象,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觉形象,它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其本源基础是客观外物,而结果则是如‘格式塔’心理学所言,经知觉进行积极组织、建构的‘形’(或‘象’)。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具有意象形质。”[2]
汉字兼有文艺审美、语言认知两方面的功用,汉字意象也就包容着两种内涵,参考上述两类定义,笔者将“汉字意象”定义为:人们认知客观世界并运用想象力创造汉字,汉字所反映出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形象就是汉字意象。
造字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汉字系统是持续更新的,在汉字的历史演变中,传承与更新交织,循变与异变错杂,每一个汉字的历史都是经过许多变化的历史;同样,汉字的意象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呈现着不同的面孔。汉字意象有个体的,也有系统的,具体某个汉字的意象是个体的汉字意象,多个彼此关联的汉字意象的集合是系统的汉字意象,如“火”关联着从“火”之字,这些“火”构字的意象集合就是系统的“火”的汉字意象。如果对一定范围内全部汉字彼此关联的意象进行整理,就可能得到该范围内全部汉字的汉字意象系统。
汉字“火”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火”认知的知觉形象。客观世界里作为基本物质与人类文明标志的火,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极其重要、无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这种重要性反映在汉字中,“火”具有“字原”的性质。张标指出字原部首有6个特征[3],所举之例正有“火”。赵静莲[4]、树炳妍[5]、史天兰[6]等,都说到“火”构字乃至构词反映出的文化蕴藉十分丰富——包括饮食、祭祀、农耕、照明、取暖等方面,他们主要着眼的是构字字义到文化的生发贯通,而汉字以字形为本,义由形生,象形字“火”的意象生成也以形之象为基础。那么,从“火”构字字形出发的系统考察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考察的构字包括现代构字与历史构字两个部分。现代构字是在《通用规范汉字表》[7]一级字表(3 500字)范围内穷尽,得到以“火”“灬”为形旁的构字63个:火、灭、灰、伙、灯、灸、灶、灿、灼、灾、灵、炬、炒、炊、炕、炎、炉、荧、炭、秋、炼、炸、烁、炮、炫、烂、耿、烤、烘、烦、烧、烛、烟、烙、烫、焊、焕、焚、焰、焙、煤、煌、熄、熔、燎、燃、燥、爆、煽、点、热、烈、羔、烹、庶、煮、焦、照、煎、熬、熙、熊、熟。历史构字难以穷尽,特选取6个:光、赤、票、尉、叟、粦,它们的现代字形没有“火”“灬”,但都曾经是“火”为形旁的典型构字。两部分构字合计69个,这些构字中有关“火”的意象彼此关联补充,宜视为一个整体,笔者就此作历时考察。
二、殷商西周:多样的火,火在物下
“火”的意象发端于殷商西周时期,“火”字的初文意象,是观察“火”汉字意象系统的核心与起点。甲骨文“火”像火焰上升,与山峰耸立之形的“山”形体非常接近。李宗焜在《甲骨文字编》将“火”与“山”邻列,收二者字形如表1所示:[8]
表1 “火”“山”的甲骨文字形

从字形比较可知,甲骨文“火”“山”形体相似、容易混淆,“火”较晚出的第二种字形,附加了描摹火星的点画,使得二者得以区别,因此加火星之点的火形,是“火”具有区别特征的典型字形,也是后世“火”传承字形所本。董莲池指出:“(火)字见甲骨文,写作、、诸形……是火焰的象形文。后偶或加点,以与‘山’形相别,作……西周承之写作(令簋‘炎’所从)、(令簋‘炎’所从),线条化作(王盉‘’所从)、(此簋‘赤’所从)。”[9]季旭昇也说:“甲骨文与‘山’不易区分,大别为‘火’有两点,‘山’则无。但‘火’字亦常不加点。”[10]董季所言甚是。
结合“火”的构字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概括起来,殷商西周“火”及其构字所反映出“火”的意象包括了两方面的特征:

其次,“火”在物下的构字意象极为常见,这说明人们对火的使用在脑海中所投射出最鲜明的知觉形象正是火在物下。在火上烧林木是(焚),拿来小羊火上烧烤是(羔),秋天烧去蝗虫是(秋),火上烧鸟过头是(焦),烧热石头来烙烤食物是(庶)。

三、秦小篆:形态规整,火居左超过居下




四、隶楷阶段:“火”“灬”分流与分工


字形与意象的分化看似新生,但早在初文时代就已经蕴含着可能性了。如前所述,殷商西周时期的“火”在构字中就是灵活多变的,兼有带火星之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的不同形态,这两种形态正是隶变中“火”分流的远源。
其次,分流后剩余的“火”大部分居左。前述居下之“火”的构字“灾”“焚”“荧”“灰”“炭”“灭”等,数量远远少于居左之“火”。而“灬”形体与“火”差异明显,位置固定,成为火居下这种意象特征的主要承载者。至此可以说“火”隶变后的分流,使火在物下这种典型意象传统转移到了新生的变体“灬”之上了。
发展到楷书时期,随着字样研究、雕版印刷的兴盛,至《康熙字典》时楷书的字形大为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到《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4)公布以来,楷书字形的稳定与规整程度为历史最高。隶变时“火”“灬”还可出现在一字异体中,而到楷书时期二者则是泾渭分明。除了分流更加显著彻底之外,楷书的“火”居左及在“炎”上时要改变笔画——末笔捺要改为点,前者是为了“让右”,后者是为了“避重捺”,结果是“火”内部也有了形体的分化——都是“火”,但居左和居下的“火”形体并不相同。而“灬”,与隶书时期四点方向不定,有省写一点或将点连写的情况不同,楷书“灬”只能写作四个点,四点的方向也只能依次为左、右、右、右。
总之,在隶楷阶段“火”完成了其字形及意象系统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次转变,殷商西周时期多样的“火”是这一转变的远源,带火星的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的意象分别由“火”与“灬”传承,这是意象的分流。另一方面,“火在物下”的位置意象并没有随着居左的“火”占优势而消弭,而是通过固定居下的“灬”承担起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火”意象的生成与更新过程,或许可以这么说——从殷商西周的斑斓多姿,到小篆的统合一形,再到隶楷的分流分工,“火”的意象演变是一个“分——合——分”的过程,但在变化的意象中又蕴含着不变的意象特征——带火星的火焰形与点点火星形,同时火在物下一直是典型的意象。
五、部件变形对个体汉字意象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上“火”的变化纷繁复杂,但就演变的结果来说,现代常用字中所见“火”都来源于真的“火”,是一个单源的部件,而“灬”则是以分流之“火”为主,又混有其他多种形源的多源部件。
从“火”之字演变中部件混同与分化并存共现,所以在认识“火”及从“火”之字的意象时要注意排除那些似火非火的情况。部件变形给构字理据与字形意象所带来的影响多半是破坏性的,如“光”“尉”“叟”“票”这些历史构字,如果不追根溯源地考察初文与本义,就无法看出它们的意象与“火”有关。
六、“火”汉字意象系统传承与更新的动因
通过对“火”与从“火”之字字形演变的推究,以及对这历史过程中汉字意象变迁的考察,笔者认为“火”汉字意象传承与更新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们认知“火”的烙印深度决定了“火”意象的传承力度。作为基本物质的火在人脑中投射的意象扎根极深,火可以照明取暖,可以烹饪食物,可以威慑野兽,可以刀耕火种,使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走向越来越舒适丰盛的文明社会。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祭祀、占卜多用火,但火也可以引起灾害,造成毁灭,《说文》声训释火“火,燬也。”[12]因此火给人留下既敬又畏的心理烙印,可谓刻骨铭心。这就使得带火星的火焰、点点火星两大意象穿过历史洪流,继续表征在现代从“火”之字中。同时,火在物下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关于火的位置的意象,无论何时总是一种极具标志性的置向,尽管这种意象受到了左形右声的冲击,比重已经略低于火居左;而在“火”“灬”分流之后,火在物下的意象更多地转由“灬”来承担。其次,汉字字形规整的需要两次推动了“火”意象的更新。小篆自是因“书同文”的需要而推动“火”在构字中形体的高度一致。隶变时分流出现的“火”“灬”在楷书时期由于字样学与雕版印刷的兴盛,以及新中国的现代汉字整理规范工作,终于各自实现了再次的高度规整。再次,形旁居左大势所趋,“火”居左取代居下成为“火”在构字中的典型位置。汉字系统内部的左形右声大趋势对不同的偏旁都发起了类化作用。有些传承构字通过改变部件位置而变得左形右声,有些新造构字按趋势、按习惯就把形旁放在左边。其他如“木”“禾”“土”“女”“口”“日”等等比较典型的形旁,虽然构字时的位置并不唯一,但居左都是最为常见的。正是在这种左形右声大潮的推动之下,“火”原本具有的火在物下的优势置向被火居左所超越,物下之火也就被迫向分流的“灬”大转移。
七、余论:其他汉字意象系统的传承情况
“火”初文意象在演变过程中得以延续传承下来,这并非个案,在其他常用部件的演变中也能看到同类现象。如“宀”“皿”“门”“囗”等部件也甚为典型。“宀”甲骨文像尖顶的房屋;“皿”甲骨文像敞口有座的容器;“门”甲骨文、像包括左右两扇的门;“囗”小篆为,像围起来的一块地方;“雨”甲骨文像雨自天空落下。这些字作偏旁构合体字时,位置都是唯一的、固定的,且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原本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宀”房屋形略去了墙体,保留带尖的屋顶形,因房屋类建筑可以无墙,但必须有顶,构字时固定在字形上部,合于“上有屋顶”的认知意象。“皿”简省了上部敞口外沿,下部的底座形保留,末笔横拉长后呈现出向上承托的结构趋向,在构字中固定居下,很好地反映出人们对于容器认知的“承载托举”的意象。“门”简化后门的两扇隐含了,然而外廓上仍贴合门框的外形,构字时位置固定,呈向下包围的结构趋势,与人们对于“门”认知意象一致。“囗”变化很小,只是外廓更加方正,构字时固定在字形外部,将内含部件全都围住,体现了它给人们带来的“围”的核心意象。“雨”现代字形中天空形不显,外廓变得像窗户,保留下来的是雨点,整体像窗户上有雨点,可看作偶然形成的理据重构现象,在构字中“雨”主要居上,应是对初形天上下雨的传承,也是人们对“雨”构字多与天象有关的认知反映。


上述这些例字也都可以作深入的历时分析,讨论它们汉字意象的传承与更新情况。显然,关于汉字意象系统的研究还大有可为,对汉字意象从系统出发的把握,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汉字本身的认识,而从认知角度来说,也可促进我们对于汉字的人脑认知特点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