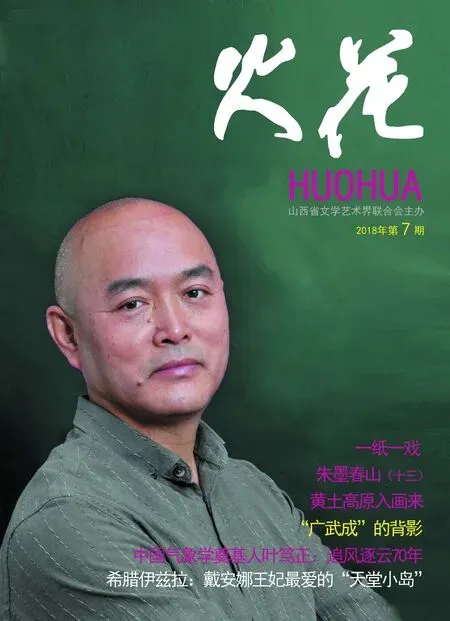草木缘情
周寿鸿
野菜与乡愁
《诗经》三百零五篇,是从野菜开始的。第一篇《关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是当时人们采摘野菜的场景。“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荇菜,就是乡间常见的水浮萍,形似睡莲,开黄色的小花,是河塘、沟渠的一道风景。
荇菜所居,清水环绕。真没想到,它也是一种古老的野菜,而且还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古代玫瑰”。
《诗经》里提到的可食用野菜多达二十五种。从农耕时代到现在,采摘野菜一直伴随我们的生活,这些先民们行吟的诗歌,传递着生活的质朴与美好向往。
早春二月,天气还冷,但地气已经回暖,野菜正在返青发绿。这是一年里野菜最嫩最具营养的时候。与往年一样,母亲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又种下了菊花脑。菊花脑,又名菊花郎、菊铧头,即野菊花的嫩苗。菊花脑枝叶繁茂,成熟时黄花匝地,也可作花卉观赏。菊花脑生长很快,且随摘随长,可一直长到秋季。整个夏天,我们的餐桌上都弥漫着菊花脑微微苦涩的清香。
离乡既久,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野菜。有人说,野菜没有故乡,只要有阳光、水和土地,就是野菜的家乡。其实,一方水土长一方草木,草木有春秋,乡土寓情思。每一个从乡村成长的人,都有对家乡野菜的记忆。没有了故乡的野菜,乡愁就少了寄托。
故乡地处苏中里下河水乡,野菜品种很多。春天起,房前屋后、田塍沟埂,随处可见野菜的身影。至今,我还能记起一些野菜的名字:黄花菜、白鼓丁(蒲公英)、马齿苋、马兰头、猫耳朵(鼠麴草)、灰条、剪刀股(苦荬菜)、碎米荠、蒲根菜(香蒲)、茭儿菜(野茭白)、枸杞头、野芦蒿……有些吃过,也有些只识其形不知其味。
故乡稻麦两熟,野菜也分两季。春天的荠菜、麻菜、黄花菜等等,与小麦同季越冬;入夏的野菜,如马齿菜、菊花脑与野苋菜,夏秋两季生生不息,霜降之后则陆续枯萎。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荠菜是春天的使者,率先报告春的信息。家乡的作家汪曾祺在《故乡的野菜》中写道:“荠菜焯熟剁碎,界首茶干切细丁,入虾米,同拌。这道菜是可以上酒席的。”俗话说:“吃了荠菜,百蔬不鲜。”我忘不了荠菜的清香,那种春天的味道和喜悦。
小时候最喜欢的野菜,是红花草和黄花菜。红花草学名紫云英,过去用来沤肥或作猪草。花开季节,状如蝴蝶摇曳多姿,连绵不断如同紫色云海,又似铺展的地毯。放学回家,我常常停下脚步,到红花草田里奔跑、打滚,然后躺在草地上仰望天上的白云。黄花菜又名金针菜、黄黄子,跟红花草一样都是牧草。它花冠如钟,色泽金黄,食之清香。黄花菜无人播种却生命力极强,喜欢在红花草田见缝插针悄然疯长,不经意就会占领一大片地盘。
这两种野菜都是被贱视的植物,但我却极喜欢。它们的嫩茎或花冠爆炒后味极鲜美,只可惜过于费油。母亲看我喜欢吃,虽然心疼油,仍常常给我炒上一碗。
长大后得知,黄花菜又名忘忧草,是中国古代的康乃馨。它还有一个非常典雅的名字:萱草。《诗经·卫风·柏兮》有咏:“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朱熹注曰:“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谖、萱同音,谖草就是萱草;“背”与“北”相通,指母亲所居住的北房。诗意是:我到哪里去找到一枝萱草,种在母亲的堂前,使她从此再也没有忧愁呢?
每到春天,当鹁鸪的鸣声掠过城市的天空,我就会遥想故乡的野菜,又开始恣意生长。那里白日青云,红花草和黄花菜开满了田野。
城市的枸杞
我家餐桌出现一道凉拌野菜,色呈翠绿,已经用水焯过,切碎成末。尝一尝,入口嫩脆,微微苦涩,再品,悠悠的清香从味蕾散开,萦绕在齿颊间。
这是什么野菜?枸杞头。母亲告诉我,明月湖畔的绿地长了一丛枸杞,竟然无人发现,她约了邻居姚婆婆去,采摘一大包回来给我们尝鲜。
在乡间生活多年,我当然知道枸杞头。家乡的田边河坎、村路旮旯,经常可见枸杞的身影,三五尺高的枝条,长着小刺,叶似石榴。春天枝繁叶茂,立夏过后,茎叶间开满紫红小花,随后结果,红珠点点圆润鲜亮;大暑叶落,到了秋天又生一茬绿叶,再度开花挂果。经常有人采枸杞子泡茶,说可以清热明目、消暑解毒。而其枝叶因为多刺,喂猪不宜,砍作柴火也嫌麻烦,这反倒让它活得滋润,越发蓬蓬勃勃。
惭愧的是,我过去竟然不知枸杞苗叶也可作蔬。可能是乡间的春天草木繁盛,蔬果丰富,没轮到枸杞头上餐桌的机会。不过对于经历了饥饿岁月的父母,枸杞等野菜却是救过命的食粮。母亲三岁就离开了娘,没上过一天学,很小的时候就打猪草、干劳活。乡间各种野菜,是陪伴她长大的伙伴,她清楚记得每一种野菜的模样和味道。
有一天午后我发了闲兴,去踏访被母亲发现的那丛枸杞。绿地四周被步道包围,香樟茂盛,小径积满落叶。因为人迹罕至,野茼蒿、野菊花、丝荞荞、地锦等葳蕤生长。枸杞隐藏在一片冬青树的后面,稀疏的几棵枸杞并不醒目,显得有点寂寞,苗叶依旧葱葱郁郁、青翠欲滴。
我记得几年前,这片绿地原本很大,在国展中心二期建设后,绿地退缩到了路边。其实再早几年,这里原本就是乡村,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长出了高楼、马路,农村人成了城里人,野菜野草变成了城市的流浪者。
枸杞树泼辣易活,生长极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它列为本经上品,说:“春采叶,名天睛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籽,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王磐将之列入《野菜谱》,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里,它是救饥的珍馐。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还保存着几棵千年枸杞,至今枝繁叶茂,花红果累。《小雅·杕杜》有咏:“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这里的解民之饥的“杞”,就是枸杞头。从《诗经》开始,野菜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看着这几棵孤独的枸杞,我想到了父母的身影,还有少年时的同伴们。老家现在已经冷冷清清,年轻人纷纷去了城市打工、定居,老年人也有不少跟着子女进城生活,还留守在乡下的已经不多了。他们迁徒到了城市,心却还留在乡村。父母已经随我在城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却依然保留着乡村思维和习惯。一遇到不开心的事,就发狠说要回老家,其实乡下的老屋已经快要倒塌了。他们就像长在城里的野菜,不习惯高楼和车流,无时无刻不想念乡间的田野和风雨。虽然已经回不去故乡了,仍然一次次梦见乡下的老屋。
采薇采薇
到了小满,一年就下来三分之一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麦秸泛黄,田间作物渐至成熟,瓜果蔬菜进入快速生长期。小满而未满,这是一个充满期盼的时节。
犹记儿时,我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田野,在紫云英地里打上几个滚,在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奔跑,追赶蝴蝶和蜜蜂。童年无忧无虑,与春夏的草木虫鱼一起,快速而快乐地生长。
想起童年,就想起了“荞荞子”。这种麦田伴生的杂草,是乡村孩子最好的玩伴;清脆悠长的荞哨声,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荞荞子”是麦田的守望者,与小麦一同生长,当小麦抽出麦穗时,它就从麦根爬上来,亲热地攀附在麦秆上,柔柔的藤蔓、长卵形的细叶,开紫白色的小花,楚楚可怜地在微风中摇摆。小麦灌浆了,越长越高,“荞荞子”也挂上了一排排小豆荚。这时,小心翼翼地剥开豆荚,去除细籽,再掐掉豆荚的一角,含在嘴里就能吹出声音来,还可以吹出各种音调。我喜欢荞哨,薄脆而清亮的声音是那么的美妙。四野俱寂,只有清脆的荞哨声飘过麦田、水面,在天地之间悠悠地回荡。
“荞荞子”的豆荚,形似缩小版豌豆,还是乡下孩子的美食。它是麦田的杂草,我们会毫不留情地连根拔除带回家,将豆荚摘下,洗干净放锅里去煮,就像煮盐水毛豆一样。不一会儿锅里的水滚了,再稍微焖一下然后起锅。翠绿色的豆角饱含水分,在盘中格外清香诱人。捏住一角,用牙齿轻轻一扯,细嫩的籽粒就落到了嘴里。这种野生野长的食物,有点甜又微微有点苦,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独特的味道。
过去了好多年,我一直不知道“荞荞子”的学名。有一次读到《毛诗品物图考》,上面注有:“薇,巢菜,又名野豌豆。”书中有图,那一片片椭圆形的对叶,正是记忆中“荞荞子”的模样。“薇”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诗经》中的《小雅·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充满故国情思,而《史记·伯夷传》所记,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又显示出品性高洁。
“荞荞子”这种乡间野草,就是著名的薇吗?
我有点半信半疑,在家乡,茎叶粗糙的“荞荞子”只作猪草,从未有人采食。还是向李时珍请教吧!翻检《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薇生麦田中,原泽亦有。故《诗》云,山有蕨、薇,非水草也。即今野豌豆,蜀人谓之巢菜。蔓生,茎叶气味皆似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在《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三卷》,还记有“又有野豌豆,粒小不堪,惟苗可茹,名翘摇,见菜部。”为什么叫翘摇?李时珍的解释是:“翘摇,言其茎叶柔婉,有翘然飘摇之状,故名。”原来,荞荞子又叫野豌豆,一名巢菜,古代也称为薇、翘摇。翘摇之名,倒与家乡的读音相近,或许是因为太过典雅,被乡人们渐渐读走了音。李时珍称“苗可茹”,翘摇是古代著名的野菜,嫩叶亦可做羹,过去的人们是采食其茎叶的。
比起文雅如诗的薇、翘摇,我还是愿意称呼荞荞子。阳春四月,正是家乡的田野最欢乐的时节。闭上眼,它那柔婉的茎叶翘然飘摇,仿佛在向我微笑,耳边有悠悠的荞哨声飘过……如今,乡间的野草已经很少了,荞荞子成了遥远的记忆,但是那种微苦的味道还存留在我的脑海里。
苔花如米
草木知春秋,每一个低微的生命也都想开花。苔作为一种低级植物,生长在阴暗潮湿处,生命同样在萌动,到了春天一样拥有绿色。花虽微小,但是生命力顽强、旺盛,努力去染绿一片生机;花虽平凡,也要像牡丹一样,把最美的瞬间,展现给这个世界。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袁枚的诗。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袁枚辞官后定居江宁(今南京),在小仓山下购筑“随园”,自号随园主人,优游其中近五十年,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在某个春夏之日,袁枚闲庭信步时,瞥见了背阴的墙脚或者潮湿的石头上,有一汪苍苔鲜亮耀眼,他忍不住俯下身来仔细端详,发现这苍苔之上,布满了米粒一样的小花。他被苔花的隐忍和坚持,被这样一种细碎之美、自在之美深深地打动了。
在中国古诗词的意象中,苔藓常被作为环境清幽的衬托和超然物外的象征。袁枚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苔花,自是独出心裁。他还写过另一首咏苔诗,从另一侧面悲悯青苔未见斜阳之美:“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青苔没有见过斜阳,但并不怨艾,坦然接纳了生命的不完美。它暖凉自知,顽强生长。
春天正摇摇晃晃地从青苔中走出来,我想起了故乡广阔的田野,和绿树掩映下的村庄。在我的老家,雨水充沛,植被茂盛,小溪边、井沿上、河滩中、墙脚和树下、潮润的石阶上,随处可见苔的身影。苔以绿色为主,也有青、紫等颜色,紧贴地面生长,所以也叫“地衣”。在微微的细雨中,在地气的蠢蠢欲动中,布谷鸟的鸣唱划过潮湿的天空,那些花儿草儿,包括最不起眼的苔藓,在蛰伏了漫长的冬天后,正攒着劲儿往地面钻呢,“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向阴而生,这是苔的命。在它落地生根的一刻,它的生命已然注定。但是每一个平凡、朴素的梦想,都可以在日积月累、日拱一卒中开花结果。太阳照不到我,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理想。
青春自来,苔花静开。顾盼和领悟之间,苔花让我对于生命中的快乐,有了重新的理解。快乐并非一个定义,而是一种角度。苔花与牡丹不同,正如小草与大树不同,生命同样美妙和多姿。我们每个人,各有各的人生履迹,对于快乐的感受,自然也是各有角度。我们不妨学那小如米粒的苔花,生命给予什么,就坦然接受什么,尽自己的心力,开自己的花,寻找自己的快乐。
甚至,哪怕没有开花,只要尽了心力,也能平静而坦然地面对,就像“苔花”。你见过青苔开花吗?苔藓是隐花植物,也就是不开花的植物。它只有扁平的叶状体,没有真正的根和维管束,其根也是茎,其茎也是叶。据说,人们所见的青苔开花,只是附着在青苔上的孢子而已。
但我宁愿相信:青苔是开花的。我相信,每一个低微的生命,都会开花,也都能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