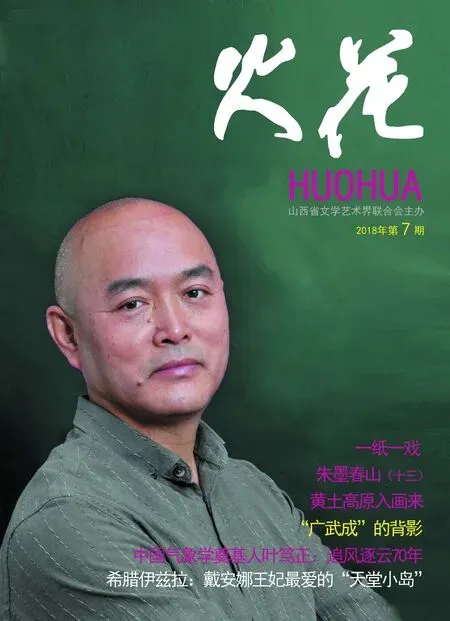有女仳离
郭玉琴
故事从泪水泛滥的兵荒马乱的饥荒年代开始谈起。
姑姑爱哭,天下的女人多数都爱哭鼻子,但没见过我姑姑这么爱哭的。一把年纪了,每次回娘家都还要哭一场,我爸骂她是号丧鬼投胎的。奶奶在世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就对自己的母亲边哭边抹眼泪,奶奶过世后,她没亲人哭诉了,每次回娘家就跑到我奶奶坟头上哭。她的眼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水汪汪的,没见一天干过。因为她老爱哭,我父亲对她非常反感,先是和她发生龃龉,不许她哭,后来她不听,姐弟之间的关系就闹得很僵,索性我父亲霸道地不许她回娘家,让她没地方去哭。她没地方去,就跑到离我奶奶坟头近的村子里的三叉路口哭,一直哭到家里有人去把她连拖带拽硬拉回来为止。
小的时候,记忆中有一次是我奶奶的周年祭奠日,姑姑从她的婆家一个人回来了,是步行回来的。她来之前,我们村里就有族叔来我家和我爸劝和,调解姑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希望父亲看在已故爷爷奶奶的份上,让她回来参加祭祀活动。其实那时候我还小,只有七八岁的年纪,根本不懂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只见父亲脸色难看,脾气倔强地和村里的族叔们理论着,最后在一番争论后达成一个协议,姑姑可以回来,但不许进门就哭,要哭就在路上哭。于是姑姑第二天得到允许从五六里路的婆家赶回来,一双小脚没进门就先坐在三叉路口的路上哭起来了。我母亲是心细的人,懂得大姑的心思,知道她嘴上答应不哭,一到家门口老毛病肯定又会犯,于是就早早地安排我和大我两岁的哥哥,让我们兄妹俩一大早就等在三叉路口迎接姑姑,嘱咐我们劝她不要哭。
姑姑哭的时候,不像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张口就哇哇大哭。她那天早上在三叉路口的路上哭的时候,更像唱一曲悲歌,数成花哭成串的,一边哭着一边讲述着自己的心事。她有什么心事呢?她有什么心事,我也不懂啊。我只是个小屁孩,只听懂她哭的时候总是不忘说上一句,妈妈,我将来就是死也不闭眼啊。那天早上她坐在三叉路口的路上,哭足了尽兴了就起来了,也不需要我和哥哥两个人上前去拉和拽,不但没让我们去拉她,还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一包小饼干,分给我和哥哥两个人吃,这真出乎我们意料,高兴死了。因为我比哥哥小两岁,那天早上回来时她就一边抱着我一边用手搀着哥哥,姑侄三人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平静地回了家。进了家门,因为之前她已经哭过了,所以就有模有样地和大家打招呼,帮母亲择菜,洗碗,干活。
姑姑虽然是我父亲的姐姐,但是她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祖母了,因为她比我父亲足足大了二十岁。姑姑今年下世已经二十年了,父亲今年六十八,她若活着,就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了。记忆中的姑姑,总是迈着一双小脚,母亲说那小脚走路还凑合,下田干活是不行的。所以姑姑从不下田干活,她在活着的时候,只是每天在家里的院子里外主持家务。姑姑做饭的手艺非常好,她蒸的馒头又白又大,吃起来很香甜。她炒的菜也色香味俱全,每次家里办红白喜事,她都要上锅前去炒菜,比我妈的厨艺精湛多了。姑姑的针线活也很好,她会裁剪一家人的衣服,做鞋子,纳鞋底,还会给我和哥哥织毛衣,要知道这些女工都是我母亲做不来的,我母亲只会干田里的庄稼活,对家务事不太擅长,为此我们都感觉很遗憾,身上穿的衣服从来都不是慈母做的,而是我妈买来布匹请大姑缝制的。
姑姑虽然迈着一双小脚,却读过书,认得字。这在我们村子里老一辈人眼中,是个稀奇的现象。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姑姑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里,我奶奶与我爷爷成亲的时候,家里有一百多亩地,全是靠雇佣佃农来耕种的。姑姑是我奶奶的第一个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在富裕的环境下,很受宠。爷爷奶奶不但让她读书,还让她裹小脚,学女工,做各种饭菜,就是想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培养她,好让她将来顺利进入大户人家当媳妇,寻一门门当户对的好亲事。奇怪的是,我奶奶生了我姑姑之后,在那个没有任何避孕措施的年代,就再也没有怀孕过。后来听老一辈的人讲,我奶奶着急请了个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是主宅不好,主吉凶上的人丁单薄,于是我奶奶就和我爷爷商量卖了主宅,搬了家,重新到一个新的宅基地上盖了屋子,于是后来才有了我父亲。这其中间隔了二十年,我奶奶得了我父亲像宝贝一样疼着,但是没想到的是,我父亲出生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爷爷是个赌鬼,成日在外面赌钱。但是幸亏他在外面赌钱,早早就闻到风声,悄悄地把家里的一百亩地一口气都给卖了,只留七八亩口粮地,对我奶奶也瞒着说是输钱抵押给人的,这才逃了一劫,没有成为地主成分,被划为贫下中农,平安度过文革的那段动荡岁月。
姑姑是在文革之前出嫁的。姑姑出嫁的那年,只有十九岁,上学才上到小学四年级。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上学的人年龄普遍比较迟。姑姑当时不想出嫁,但是亲事是我奶奶的堂兄给保媒的,她不敢违拗家里父母的意见,就只好上了花轿。我奶奶的堂兄是个开药房的老中医郎中,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既然是我奶奶的堂兄保媒,那么这桩婚事应该不会太差才对。事实上这的确是一门好亲事,但是我姑姑嫁过去之后,只能怨她自己福薄命薄。姑爷是个读书人,当时还在上高中,正在求学。姑姑婚后与姑爷虽然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但是感觉很幸福。姑爷很喜欢我姑姑,两个人婚后恩爱好合,从来没有红过脸,只是有一点遗憾,姑爷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是他的嗣母,生母与我姑姑之间倒没什么疙瘩,就是嗣母从我姑姑一进门就不喜欢这个媳妇。姑爷的家世其实还不如我们家,他是遗腹子,亲生父亲在他没出生时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母亲带着他寄居在他的大伯母家。他的大伯父也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因为大伯母没有生养,就两个寡妇合力抚养一个儿子。姑爷的大伯母娘家有钱,也是地主家庭,还开了个油坊,赚钱得很。姑爷和他亲生母亲为了讨生活寄人篱下,给人当儿子,凡事都忍气吞声,不敢违拗半句,就是娶亲花的聘礼钱也是嗣母出的。当初我奶奶的堂兄保媒的时候,只说这一户人家有钱,是大户人家,有一个儿子是读书人,年龄和我大姑相仿,并没有和我奶奶细说他是过继给人家的嗣子,所以我奶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女儿嫁了过去,本以为是寻到了一门好亲事,没想到后来成了推自己女儿进火坑的间接刽子手。
姑姑的亲婆婆是个老实人,遇事能忍,不吭声。名义上说和她的妯娌是平起平坐,实际上就像给人当帮佣一样,端茶倒水,侍候一家人起居,不辞辛苦,从不敢怠慢。我姑姑原以为嫁到人家去是当现成的少奶奶,等嫁过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是给人当使唤丫环的。姑姑在家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哪受过这等委屈,她性子刚烈,没事就和她的那个嗣母婆婆发生龃龉,先是小吵小闹,接着就是互相谩骂,发生肢体冲突不断。矛盾升级,姑爷和他生母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知道自己的女人受了委屈,可是端人碗服人管,那时虽然成亲,但是他上学的费用都还要靠嗣母的油坊赚钱来供养,根本没有能力自立门户。
所谓发生肢体冲突绝非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媳妇和婆婆可以造次互相动手,而是婆婆点上一炷香,放在堂屋的案桌旁,然后对我姑姑进行家法惩戒。她先是叫我姑姑跪在地上,让她用鸡毛掸子打在身上,等她打累了,就让姑姑不吃不喝跪在那里,跪多久也是有规定的,等到一炷香烧完就可以起来去干活侍候一家老小了。
姑姑起先为了家庭和睦,隐忍不发,可是后来看到她的这个嗣母婆婆越来越变本加厉地刁难她,她就不服,和她顶撞反抗起来。一次蒸馒头,姑姑和她的亲婆婆两个人蒸了一天一夜,嗣母婆婆只给她们婆媳两人每人一个馒头,剩下的都藏起来留她自己吃。姑姑不服,赌气扔了馒头,她就罚她跪,她就是不跪,再打她骂她,她也就不依不饶地和她回骂。老太太一看媳妇敢骑在她头上,顿时使出了杀手锏,将姑爷和姑爷的生母叫到房里说,我现在给你两条路走,一条是休了她,我重新给你再娶一门亲事,聘礼还是由我来出;另一条你不休她也成,从今往后你上学的所有费用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另外还要将你们分出去单过。姑爷自幼长于两个妇人之手,又是个文弱的书生,听这么一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可是那时候我姑姑过门没多久就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即将临盆待产,他怎么能做出这种无情无义的事情呢。于是他夹在两边左右为难,只能一味地给嗣母磕头赔罪,请求嗣母给他时间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姑姑过门一年后,在婆媳失和的矛盾中生下我的大表姐,还没满月,姑爷的嗣母就找到她娘家的人为她主持公道,到法院为自己的嗣子起诉离婚,在我姑姑连出庭都没出的情况下,就把判决书硬判下来了。判决书上明文写着,婴儿处于哺乳期,暂时由母亲抚养,直到六岁后可以转交男方抚养。在婴儿六岁期间,抚养费暂时由男方出。姑姑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当日,就伤心绝望地趁着姑爷外出有事时在家里拿了一根绳子上了吊,幸好命不该绝,姑爷去赶集买东西半途又想起忘了带钱返回来,及时将气绝半路的姑姑抢救过来送到医院,从阎王爷那儿捡回了一条人命。
姑姑这一闹,原本以为怕出人命的姑爷一家人会收回心意,接纳她,没想到他们一家只是威慑于当时危险情形,暂时妥协了一下,和我爷爷奶奶达成协议,让他们单独过,但是法院判决书并没有收回。他们等我姑姑情绪稍微稳定后,没过多久就又开始闹腾了起来。这一次闹开之后,姑爷亲自跑到我家央求我奶奶和我爷爷做我姑姑的思想工作,让她搬回娘家住,等他学业毕业了再来接她们母女回去。考虑到姑爷的难处,我爷爷和奶奶答应让姑姑搬回娘家住,但是要求他每个月必须给两块钱的生活费。姑爷回家后又和我姑姑好生商量,软磨硬泡,姑姑一想到两个人的感情那么好,也就心软服从了他的安排。哪知道姑姑这一走,就再也没有等到回去的机会。姑爷将姑姑和大表姐送回后,自己就回学校继续去求学,每个月到月底,姑姑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去他上学的学校去要生活费,他就把嗣母每个月供给他的生活费挪出两元钱来分给我姑姑买口粮来喂大表姐。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后,我们家的日子也日渐中落,不如从前,又加上乡里经常闹饥荒,常常饿得上顿不接下顿,奶奶实在没办法就把自己碗里的饭省下来给我大表姐吃度命。即使我奶奶为了节省口粮,后来在有一年,自己饿得面黄肌瘦,嘴里淌黄水,家里也还是难以维持生计。爷爷生气,急得催我姑姑去找姑爷多要点钱,说每个月两块钱根本不够买米喂孩子的,可是姑姑死活不肯去,一来是因为她知道姑爷在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嗣母知道他把钱贴给大表姐用,一再克扣他的家用;二来他本人也在学校饿得身体羸弱,让姑姑看了就心疼。先前还能每个月拿出两块钱给我姑姑,后来渐渐的日子久了,连两块钱也不能按时拿出来了,到最后没办法我姑姑只好放下表姐给我奶奶带,自己去给人做徒弟学裁缝,赚点零钱养活自己的女儿。
姑姑的女儿和我父亲差不多大,舅甥两个同时去上学,我奶奶为了让我姑姑放心在外面学手艺赚钱,硬是狠下心肠,让父亲每天把从学校食堂饭票换带回来的仅有的一个馒头,拿回家换锅里煮的山芋稀饭吃,让大表姐吃馒头。父亲为了省给大表姐吃,时间久了,患了胃炎,一直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都没有再痊愈,现在一提到山芋稀饭,他就直摇头说,那个年代把这个食物都吃伤了,看见就害怕。大表姐在我家一直过到十二岁才离开回到她亲生父亲的身边。在姑姑离婚后的第六个年头,其实姑爷就毕业分配工作了。姑爷从淮阴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乡下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他参加工作后有能力养家糊口了,但是并没有履行承诺来接她们母女俩回去,而是一直保持沉默,僵持着。尽管毕业后他没有提出复婚的请求,但是每个月他都会按时把生活费送到我们家来。在这六年离婚的期间,家里有不少亲朋好友给我姑姑重新物色对象,但是都被我姑姑一口回绝了,姑姑坚信她的丈夫既然当初答应会接她们母女回去,就一定会来接,只要熬到她的丈夫参加工作有自己的工资不需要寄人篱下就行了,甚至幻想着一家三口幸福团圆地分灶单过,尝尝没人管束的小家庭生活,甚至她还想着要接自己守寡的亲婆婆一起回来,好好孝敬她,不让她也仰人鼻息地过日子,给人当奴才。
可是人生都是充满变数的。离婚的那些年,姑姑和姑爷也常常见面,他们见面也都很平心静气地说话,像没有离婚时一样,互相关心着彼此,嘱咐对方好好生活,坚强过下去。但是令姑姑没有想到的是,她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好不容易盼到姑爷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年尾,却盼来了姑爷的变心。姑爷在没参加工作之前,每次要生活费,都是姑姑亲自跑到他的学校去拿的,等到姑爷毕业的第一个月,他就兴高采烈地把工资里的钱匀出一半亲自送到我姑姑做衣服的裁缝店。他每次来送生活费,也会坐在裁缝店里和姑姑家长里短地聊些家常话,感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姑姑在晚年还是一直坚定地说,他对她很好,他们之间感情没有任何裂痕。但是我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姑姑是一根筋的人,太相信感情这种事了,人心昼夜转,天地变化一瞬间,离婚那么久,离皮离骨地过着,时间久了,感情再好也消耗掉了。最后一次来姑姑裁缝店的时候,姑爷不但送来了生活费,还送来了几尺布,跟姑姑说,他想做一身中山装,他说这是自己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衣服。姑姑不明就里,高兴地替他裁剪着,她干活,他还是照常陪她说话,聊着女儿的成长中一些有趣的话题。聊着聊着,他就突然伤感起来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们母女俩了,我将来到死也是怀有愧疚的。姑姑宽慰他说,你有难处,我能理解你,孩子大了,将来也会理解你的,我们娘俩都不怨你。姑姑这样一说,姑爷就更难开口了,他支吾了半天说,我马上要结婚了,这套衣服是留着我结婚时穿的。他这样一说,正在缝制衣服的姑姑就停住了干活的动作,愣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犹如晴天一个霹雳。过了老半天,姑姑才强忍着泪水问道,对象是哪里人,她好吗?是干什么的?于是姑爷一一照实回答说,女方是拖拉机站的一个会计,我们领导保的媒,领导说如果和这个姑娘成亲,将来就提拔我做教导主任。姑姑听了什么也没再问下去,就静静地缝制着那件衣服,一直等到衣服缝制好,姑爷穿上身,问我姑姑合适否,姑姑才回答,真合适。于是姑爷就又开口了,我这一次来,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以前我们俩虽然离婚了,但是没有人管束,还可以到一起说说话。以后等她过门了,估计就没那么方便了,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们就只能避嫌了。只是有一点你放心,孩子的生活费,我一分也不会少。本来现在我就该接女儿回去的,但是我考虑了很久,觉得女儿还是暂时放在你身边抚养好,一来怕她过门,孩子受晚娘的气;二来她是个姑娘,一进门就给我的孩子当现成的娘,我怕她不高兴,影响我们夫妻感情。我的婚姻已经失败一次,被人破坏一次了,我不想这一次再有波折。这些年苦了你,是我对不住你,下辈子我再补偿你,就算我欠你的。你有合适的,趁着年轻,就赶紧找吧。说完,姑爷抹着眼泪穿着我姑姑缝制的新衣服回家成亲了,而我姑姑在他走后,伤心得滴水未进,两天两夜哭红了眼。好不容易在我奶奶和众亲戚邻居的劝说下,才想通了,收藏起悲伤,继续过日子。
姑爷成亲后,姑姑就一个人带着大表姐搬到集市上的裁缝店里住。我奶奶让她回家来住,她不肯。她说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老住在娘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我父亲一天一天也大了,以后还要娶媳妇,都团在一起过,开支大,家里没有余钱怎么行。姑姑搬到裁缝店去住后,奶奶在家整日以泪洗面,舍不得我姑姑和大表姐,没事就迈着一双小脚往集市上去送吃的东西。家里亲戚朋友磨破了嘴皮,都说孩子的父亲已经另娶他人了,这下子你该死心趁着年轻再找一个男人成家吧。可是姑姑执拗地说,我就当是寡妇守丧,靠女儿过,娘俩慢慢熬。爷爷不同意,他说你靠女儿怎么能靠得住,别看抚养权是归你的,这抚养权是暂时的,等孩子一大就会被带走,她到底是人家的孩子,现在只是碍于面子不敢带回去,等后娘过门久了,做通了思想工作,人家找到恰当时机就会来要人,你那时就是替人带孩子啊。爷爷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姑姑都听懂了,可是真要她舍得放下自己的女儿,她哪里肯呢?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掉下来的啊。
姑姑后来还是改嫁了。大表姐十二岁那年,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打扮时尚的陌生女人出现在了姑姑的裁缝店里。她来了之后,开门见山地介绍说,她是我姑爷的妻子,来的目的是和姑姑商量大表姐的抚养权问题。她说,如果姑姑愿意把孩子交给她和姑爷抚养,必须答应一个条件,在大表姐出嫁之前,不准来探视;如果不答应,以后抚养费将终止供给,并且断绝父女关系,孩子有任何事都不准再来纠缠他们。姑姑当时没有马上答应,说容她考虑一天时间,再给她答复。姑姑回来之后就跟我爷爷奶奶和我族里的叔叔婶婶们商量。姑姑的意思是舍不得给,给了之后母女很难再有见面机会,可是不给吧,又担心大表姐将来读书的费用成问题。爷爷是当家的男人,他考虑问题比较理性,他对我姑姑说,趁着这个机会把孩子给他吧。孩子已经十二岁了,以后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没有钱你拿什么供养孩子。不供养孩子上学,她将来就找不到好婆家,你是愿意短痛还是长痛?做父母的不能不为孩子长远做打算啊。照我们现在这家庭,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哪供养得起她读书,况且你弟弟和她差不多大,现在我们也自顾不暇,哪有她那父亲吃皇粮的硬气,好歹他自己也是教书先生,孩子带在他身边,不会不用心培养的。姑姑和奶奶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决定忍痛割爱,将大表姐送给她后娘带回去了。大表姐走后,害得姑姑又伤心地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对我奶奶说,妈妈,我的人生走到这一步死也不闭眼啊,丈夫被人夺走,连孩子也被人夺走了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辈子迈着小脚的奶奶,除了后悔自己当初看走眼,许了这一门冤孽的亲事,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
表姐走后,没多久,姑姑就在奶奶的堂兄做媒下,又找了一个男人,就是我现在的姑爷。原来的姑爷姓丁,我们晚辈都叫他丁姓姑爷,现在的姑爷姓沈,我们晚辈私下称他为沈姓姑爷。俗话说得好,好人不当二房狗,半路夫妻怎比得上结发夫妻情义深。沈姓姑爷家的条件比起丁姓姑爷家差得远了,简直不可比拟。沈姑爷是做石匠的手艺人,大字不认识一个。他原本有一个妻子,妻子有一次在他外出干活时在家和婆婆拌嘴,因为婆婆说了句等我儿子回来找你算账,就这么一句话,一气之下拿根绳子在柳树下吊死了,死时留下一个男孩才三岁。因为女方娘家没有哥兄,只有一个老妈妈,所以死了就死了,连来为她伸冤的人都没有。姑姑过门后,他家也吸取了教训,和婆婆分开单独过,并且让前妻留下的孩子给他母亲带,他母亲一直把孩子带到十岁过世后才又转交给我姑姑带。我姑姑离婚后改嫁也是给人做后娘的。但是做后娘和做后娘的处境也大不相同。姑姑的继子长大到十岁,正是淘气又长心眼的时候。姑姑过门后,很快就接二连三地开枝散叶,生了好几个孩子。有一年姑姑做月子,生我四表哥的时候,她的继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不高兴,故意把姑姑给他做的棉袄里的棉花给掏了出来。那天我奶奶刚好买了鸡蛋去送给我姑姑吃,见到孩子的棉袄坏成这样,赶紧拿出针线要给他缝补起来,可是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就是不肯把棉袄脱下来,还对我奶奶说,不要你缝,我就要故意把棉花露出来给邻居看,好让大家说我妈是后妈,对我不好。我奶奶回来后就跟我爷爷叹气说,给人当后娘,前一拖后一块的,真不好过。
姑姑在这头日子不好过,大表姐回到后娘的家里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大表姐的后娘给大表姐定下规矩,在满十八岁之前不准去见自己的亲娘。这个规矩虽然很苛刻,但是寄人篱下,为了有书读,大表姐也不敢违拗。但是她离开我们家时已经是个十二岁记事的孩子,亲娘晚娘这一点她也是分得很清楚的。有一次她中午偷偷地跑到我姑姑家,见了我姑姑就抹着眼泪哭诉道,妈妈,她对我一点都不好,我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蒸的馒头就不给我吃,只让我吃山芋叶稀饭,她和我弟弟两个人吃馒头,这不公平啊。那馒头是我爸爸的工资买的,我凭什么不能吃我爸爸的东西,我是我爸爸的亲生女儿,每次我告诉我爸爸,她就指责我说谎,还撺掇我爸爸用扫把打我。大表姐边哭边说,姑姑听了心像刀绞一样疼。她拿出家里仅有的做月子吃的鸡蛋和馒头放锅里煮给我大表姐解馋,可是一顿饭刚吃完,我的沈姓姑爷就对我姑姑说,吃完赶紧让她走,免得她后娘发现找上门来吵架。既然答应给人家带,就不能留在家里,万一被发现,人家不要她了更麻烦。就这样,大表姐吃完饭就被我沈姓姑爷赶走了,我姑姑难过地躺在床上淌了一个月子的眼泪。
姑姑改嫁的沈家和原来前夫的丁家相距不远,两家只隔着一条宽宽的河流,那条河在乡下当地人口中叫三涧河。饥荒年代,姑姑在大表姐走后做完月子,家里的米缸就空了,一出月子不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连烧锅草也没有了。无奈为了度命维持生计,姑姑带着几个大的孩子,背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四表哥,娘几个一起去河边树下拾草叉鱼。就在姑姑弯腰拾草的工夫,不巧那天又遇见了那个阴魂不散的克星,我姑姑的前夫嗣母。老太太一脸刻薄相,露出鄙夷的神情说,怎么出来拾草了,难不成你家连烧锅草也没有了?呦,你这是米箩又掉进糠箩里去了,日子不够过的啊?我还以为你能找到比我儿子还好的男人呢。真可怜。怪可怜的呀,难怪你连闺女都养不起,送回来了。就这样,老太太的一番刻薄话说得我姑姑一口郁闷气憋心里去,回家倒头就睡了三天三夜没起床,我奶奶知道后,只好让我爷爷和我爸爸去拾草,然后把拾的草用手推车送到姑姑家,让她在家烧饭用。
苦尽甘来,大表姐十八岁成人之后,终于获得自由身,可以光明正大地来看自己的亲生母亲了。十八岁的大表姐,不仅获得了自由身,母女得以团聚,还毕业参加了工作。她读的是卫校护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医院的药房上班。她有固定的工资,终于可以每个月拿出一点钱来贴补我姑姑。我姑姑看到大表姐来看她,心里也很高兴。爱屋及乌,大表姐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和丁姓姑爷的爱情结晶。在姑姑的心目中,男人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大字不识的沈姓姑爷永远比不上儒雅有学问的丁姓姑爷,况且他们俩才是结发夫妻,是在家长专制下被迫仳离的。可是女大不中留,大表姐参加工作后,很快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的父亲为她物色了一位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小伙子长得英姿飒爽,姑姑看了之后也很满意。婚期到了之后,大表姐的晚娘提出来,大表姐的嫁妆得由我姑姑买,她已经尽到了抚养她到十八岁的责任了,没有义务再为她置办嫁妆。可是姑姑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三男两女,且都未成年,家庭经济负担太重,哪有能力承担置办嫁妆的钱。姑姑没办法,带着大表姐来我们家,和我爷爷奶奶商量。奶奶心疼姑姑,同时大表姐小时候在我们家也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很心疼,于是就给她买了一个红漆木箱子,又将家里屋檐前后的树锯掉几棵打了一个桌子和写字台,给她当体面的嫁妆。大表姐出嫁后的第二年,我奶奶就患了癌症,病倒了。奶奶在临终前很想见大表姐一面,那时又没有电话,我姑姑知道后,就让她的几个孩子去找他们的大姐,将这个消息告知。可是去了几趟,她都推脱说工作太忙,走不开。最终我奶奶在没有见到大表姐的遗憾中撒手人寰了。
我奶奶过世,大表姐没有来披麻戴孝,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在丧礼中。我爷爷和我父亲问我姑姑原因,姑姑一再解释说孩子工作太忙,吃公家饭,端人碗服人管,请不到假。于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也就不再追问。可是事隔很多年后,姑姑才在家族亲戚中透露,大表姐之所以不来,并不是因为工作忙,而是她晚娘让人给她带了话,如果敢来我们家给我奶奶披麻戴孝,就证明她不是丁家的姑娘,既然不想做丁家的姑娘,以后就不准再回娘家,也不准再去找她爸爸。表姐懦弱又无主见,自小在离异家庭里长大,她不但胆小还势利眼,知道跟着自己亲生母亲过以后会没有前途,姑姑在沈家生的几个孩子就是她眼前的一面镜子,因为贫穷一个个都没念什么书就中途辍学了。她不想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也穷怕了。所以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抱着晚娘的大腿不放,深怕被父亲的那个重新组成的家庭给遗弃。
表姐出嫁后,在城里安了家,两个人都是吃皇粮的人。姑姑体谅女儿,就像我奶奶当年体谅她一样,家里的米和面、鸡蛋和蔬菜,不停地派自己的几个儿子去给大表姐送去,生怕她的日子不够过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姑姑疼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挖出来掏给她吃。尽管家族里一直有亲戚责备姑姑说没教好大表姐,让她变得连一点亲情都不顾了,外婆死了都不知道来奔丧。但是姑姑不这么想,她一直为自己的女儿袒护说,这不能怪她,她有自己的难处,夹在两个家庭里里外不是人,谁都不把她当自己家的孩子疼。姑姑的护犊情深,过度的袒护,终于给她晚年的人生也造成了死不瞑目的遗憾。姑姑不知道,大表姐即使出嫁后,每次来姑姑家,也是瞒着自己家的晚娘的。她出嫁后另立门户,晚娘当然不可能像她做姑娘时有机会天天盯得死死的,一步自由路也走不了。可是纸包不住火,姑姑在六十三岁的那年,身体也在家庭的重担负荷下垮了,她患了心肌梗塞和脑血栓,躺在床上不能生活自理了。大表姐在姑姑奄奄一息的时候来了,她坐在姑姑的床头抹着眼泪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啊。我不能够天天待在你身边侍候你啊,我是忤逆不孝的女儿啊。姑姑闭着眼睛不说话,但是她有清醒的意识,大表姐边哭边说的时候,姑姑紧闭的眼里溢满了泪水。母女感情是天性,也是相通的。表姐哭完最后一次附在姑姑耳边说,妈妈,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啊,我晚娘又说不让我来奔丧了,我真是左右为难啊。大表姐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没有别人,没有人给她出主意,而唯一能和她商量的人,我姑姑那时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
姑姑咽气后,四表哥派自己的堂兄弟去大表姐家报丧。那是一个冬天,三涧河的水都结冰了。数九寒冬,姑姑尸骨未寒地躺在地下的冷铺上。大表姐得到噩耗,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她表情平静,不说话,只是流泪。过了半天,她对报丧的人说,你先回去,我考虑考虑再做决定。我猜想大表姐那次还是挣扎过一次的,并没有像我奶奶过世时那样避而不见。因为听我表哥说,后来大表姐来了,但是走到姑姑当年拾草的那个三涧河边就碰到了站在那里等着她的晚娘。晚娘见了她说,你不能去,我帮你去把丧礼钱付了。我没有闺女,就两个儿子。你是我花钱培养出来的,我这几年的钱不能白花。等我百年之后,还等着你给我披麻戴孝,替我号丧呢。我不想和别人合用一个女儿,天下母亲不能有两个,我不能学你爸,认了两个母亲,结果一辈子活得窝窝囊囊的。你今天给我表个态,认我做娘就不准去奔丧,给你娘去奔丧就不准再喊我妈。不喊我妈以后你爸死了我也让我的两个儿子不准你回家奔丧。两条路给你选一个。就这样大表姐在她晚娘的淫威之下,经过一番威逼利诱的话,终于又翻了心思,打道回府了。本来村里人听说大表姐已经走在途中了,都已经派家里人去接,没想到家里人没接到大表姐,却接到了大表姐的晚娘,以及送来的二百块钱丧礼钱。气得四表哥当时就一把拉过大表姐晚娘的胳膊,把钱砸还给了她。姑姑生前就对我奶奶说过,她将来死后都闭不上眼,我想姑姑若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自己的亲生女儿连奔丧的权利都被人剥夺,也定然不会闭眼的。
姑姑下世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大表姐的消息。时隔二十年杳无音信,一直到今年,偶然的一次回老家,村子里有一个族叔告诉我,就在前不久他在街上碰到已经退休颐养天年的大表姐父亲了。从他口中得知,他的那个老伴在我姑姑去世三年后也得了癌症,过世了。过世时大表姐为她披麻戴孝,喊吹鼓手唢呐,风风光光地履行为人子女的责任,给她安排下葬了。虽然知道这个消息,我的族叔为我姑姑感到有点憋屈,但是恩恩怨怨都随着人的过世一起带走了,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人们向来只愿意谈活人的生活,哪愿意一直纠缠死人的过去。我的这位族叔问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前姑爷,大表姐现在可好?哪知道姑爷叹口气说,好什么好,大表姐也得了癌症,现在正躺在家里没人照顾呢,家里正商量着送她去养老院。我的族叔问她,大表姐家里现在还有些什么人?丁姓姑爷说,冤孽,和她妈的命一样的苦,她的丈夫在她五十岁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地跟她提出了离婚,在外面一直藏有情人和私生子,闹得不可开交,她这癌症病都是她男人给气出来的。现在婚也离了,身体也不行了,就一个女儿,还不愿意承担照顾她的责任,把她往养老院推。幸好她身上还有一笔退休金,能自食其力,不然她现在的日子连她亲妈都不如。丁姓姑爷的日子还好过吧,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我问我的族叔。他说,好什么好,都是不得好死的东西。他两个儿媳妇没一个愿意给他洗衣做饭,他都九十岁的人,还到处打听请人能不能为他再物色一个身体硬朗、能做饭洗衣服的老伴,最好还是要年轻一点的,既当保姆又当老婆的那种老实本分人。
这年头,人心向钱看,亲情单薄,上哪找这么贴心的人去侍候他?我不以为然地说。族叔说,有钱就以为了不起,成烧包了。没见他当年吃软饭时的那个怂包样!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回就该轮到他爷俩遭天谴报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