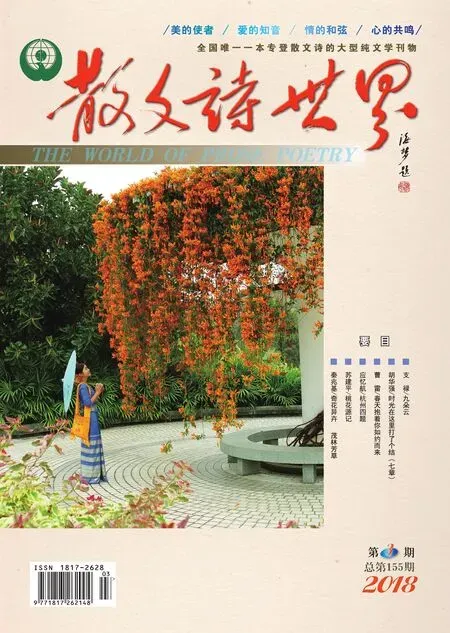我闻到岁月久窖的芳菲(五章)
安徽宣州孙埠高级中学 潘志远
雪就将远去
雪就将远去,我去送送它。
到野外田地里,河堤边,草垛旁,或一切朝阳的山坡……
雪无言。许是有千言万语卡在喉咙,或不屑于言说,或还没找到合适的言辞,或已根本不需要对我言说,但愿是后者。
雪很平静,也很冷静。从来的那一刻,一直保持着固有的生命的温度;提升,只能加速其逃遁。
雪明白:让人狂喜亢奋的日子已逝,厌弃产生,它被铲除到路边,被人反复践踏,被一次次泼脏水。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快离去。
雪一天天消瘦。消瘦也不改其白,不失其白。即便死去,也清清白白。
质本洁来还洁去。那些强加给它的玷污,此刻已经澄清、分离、沉淀。
滴滴答答的,是它流淌的欢笑。可意会不可言传,意中意,诗中诗,经得起揣摩。
随溪流淙淙奔腾的,是它的血脉,给大地输液,给江河补血。
雪的灵魂遁于无形又无处不在。
雪就将远去,我必须送送它。长城外,古道边,雪地有多辽阔,我送它的心,就有多辽阔……
老天的脸
一夜春雨,不,冬雨。
但已完全是春雨的阵势,叮叮咚咚吵夜,像发烧后患上百日咳的孩子;淅淅沥沥,淋漓个没完。总之,我没有好词汇,好的词汇,我留给真正的春雨。
早晨起床,拉开窗帘,见天光放晴,吃惊不小,如吃了兴奋剂,顿时提起了精神。
心头闪过一念,大寒第三日,总觉得哪儿不对劲。想到前两天在公交车上,一老人说今年还没有见白,如醍醐灌顶:老天给我们一个笑脸,暂且珍惜。
和睦的友好,笑靥的温馨,是人与人,也是人与自然,难得的情谊。
等到老天变脸,飞雨,飞霜,飞雪……再怀念它的温和、灿烂、善解人意,未免不是一种幸福。
飞雨,飞霜,飞雪……包括总是阴沉着,都是它的真面目,老天的脸有时比翻书还快。早已习惯老天的脸,看不够老天的脸,爱不尽老天的脸,哪怕它瞬息万变。
老天大发雷霆的脸,让我心里一颤一颤的,但我还是好奇地偷看;老天发火的样子,震怒的样子,就像普通人,甚至像个泼妇,它已完全忘记了它是老天。
矜持、威严、高尚、斯文……统统抛到了一边。
给一头老牛让路
回乡的土路上,我遇到一头老牛。我的第一反应是准备给老牛让路。
不是怕遭遇相持的尴尬,更不是怕老牛用角抵我。我知道,如果我径直走过去,老牛会很儒雅、很有风度的给我让路,让我人模人样地从它身边通过。
为避免这一幕发生,我提前让到路的一边,干脆下到麦田里,让出全部的路面。
这是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老牛。从不居功,从不埋怨牢骚,把劳碌草一样咽下,在夜间千百次反刍,津津有味地活一辈子的老牛。
老了,不能继续耕耘时将被宰杀,肉烧锅子被人下酒,皮做成一双双皮鞋在我们脚上锃亮生风,头骨挂在墙上坐装饰成为一门艺术……
想到这些,我的心微微颤抖……等老牛走过,我再回到路上,在它身后我行了一个长长的注目礼。
不是我有菩萨心肠,不是我有绅士风度,也不是我突然良心发现,而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和藉口
不给一头老牛让路。
我闻到岁月久窖的芳菲
冬的坚守者,一转眼成为春的代言和形象大使。
扎雪头巾的香樟,绿发钻出来,如心中燃烧的火焰,灼烫着我的目光。
穿雪婚纱的女贞子,多么拉风、拉眼球。
系雪围兜的矮树,我叫不出她的姓名。
到处都是冷酷的风度,到处都美丽动人……季节的主题充分彰显。无处不在的T型台,让每一个人走秀。
近看不如远观,你的婀娜多姿,咔嚓在我心灵的底片。
这一张,那一张……都各具魅力和神韵。
动辄分享,动辄晒,已成为这个时代浮躁浅薄的通病。我只爱珍藏,当一帧昔日的旧照,略显斑驳和发黄,我闻到岁月久窖的芳菲
在指尖,在鼻息,拂过,旋舞……
一棵老树
比较来,比较去,我还是觉得这一棵老树最值得信任和依赖。
当阳光雨泼下,它为我举起一把绿伞,迎我来,送我往,无怨无悔。伞一直撑在它手里,生怕我不期而至,伞不能及时打开……
风中歌唱,雨中也歌唱,只为消解我的落寞。
偶尔放飞一叶,旋舞着单翅,不是鸟,却有鸟的轻盈,自由落体的弧线,荡出一道虹……别人无所谓,我在心里一遍遍描绘。
触地的一刹那,我感觉到振颤和轰鸣,不绝于耳。
在水里,造一叶轻舟,划过鱼儿的头顶,每一尾鱼梦里都荡漾着彩色的涟漪。
当我疲惫的身子倚着老树的躯干,我的灵魂浪迹在千里之外。倚而不依,依而不倚,一棵老树在我精神的沃土挺拔。
它早已雄姿不再。西风飒飒,每天前来索要我的清泪……不给,就使劲吹,吹翻我的五味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