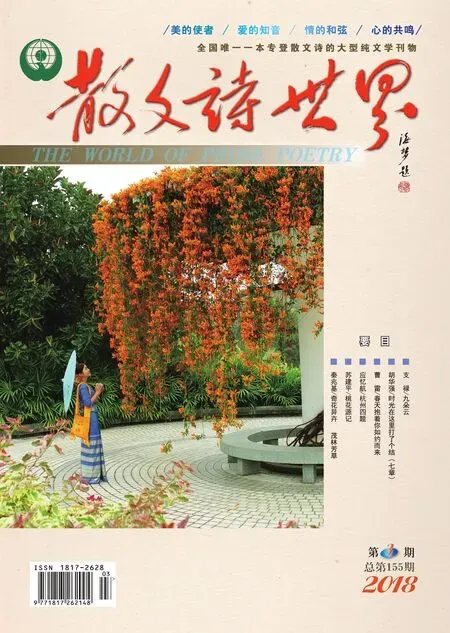年关·那村儿那事儿那媳妇儿
四川 余华君
1、山坳下那村儿
初冬的太阳在这个山坳,差不多每天都要跳出来几次,就像少女的身影,躲躲闪闪,羞羞答答地放不开热度,直到每一个梦醒时,又被痴情的相思羞红。
那村儿就在山坳下的河边躺着,岷江河水带着弓杠岭的冰雪,融化在这湾回旋,再流向成都平原,流进那个天府之国。
村儿也在镇上,青石板的小路就如老祖母弯弯的脊背,被阳光牵得很长。老外公咧嘴笑开的黄牙,像极了街道上那些歪歪扭扭要倒不倒的木板房,写满岁月沧桑的痕迹。
大黑、阿黄这些狗儿们,总是比村里人起得更早,朝雾朦胧里,在青石板路上,踩出了它们觅食的脚印。公鸡开始打鸣。大树下的牯牛开始咀嚼干草,反刍着那些成年往事。麻雀子叽叽喳喳闹了,开始成片成片地飞向田野地头,再一溜子排列在电杆子的电缆上歇脚。
农妇打开鸡笼,鸡飞蛋打的声响,彻底唤醒了村儿的黎明。勤劳的农夫开始备好农具,一声吆吼,赶牛儿下田。太阳晒到屁股后,娃娃们睡眼惺忪地起床了。小姨子长长的发辫子勾着魂儿地疯长,在小媳妇儿的心底挽上个结,老也打不开。
未嫁大姑娘的门前,总是有无数双眼睛在偷窥,布满墙角院后。唯独老祖母脸上的褶皱,不会划破孙女儿水嫩的肌肤。老爷子旱烟嘴燃起的青烟,缭绕在空气里,把日子熏染,也把心事明了。夕阳和朝霞都美丽得通红,足以温暖每一颗受伤的心灵。
岷江河的水清清,浪花一波翻着一波顺流直下,一去不返,把祖辈的欢乐带走,也把晚辈的忧伤送去。炊烟凌空,在浮云里飘动着村儿里的故事,储满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事。故事重复着故事,不变的依然是小村儿的风景和质朴的风俗。
冬日,阳光不暖,天很蓝,山坳下的那村儿,黛紫色的朦胧,不知哪家的女孩,又在春情萌动……
2、梨花的相思
落叶纷飞时,女孩的痴情在冬季里蕴藏,犹如梨树火红的蜕变,等待最后一片叶红绚烂时,好把自己也染红。
村儿在静静地呼吸着给氧,一如既往的梨花总会在三月里盛开,洁白得成林成片,铺满山坳。那时,女孩的初恋也该无拘无束地绽放了,把一冬的压抑奔放,好与那个邂逅的等待牵手,魂牵梦萦。
山坳间,羊儿咩咩地叫着,呼唤着女孩来年的春季,好让每一树梨花,都挂满洁白的相思。
那个心动的男孩千呼万唤不来,留下一双咄咄的眼眸,一箭穿心,直刺灵魂。女孩眺望远方,欲哭无泪,心底里千万次地呼唤着男孩的名字,呐喊已声嘶力竭:你就是我的天空,我的海洋啊,我的温暖,我想在你浩渺的胸襟里畅游,在你微笑的漩涡里曼舞,我想痛快地为你死去,再痛快地为你活来,直到我的血液被你一滴滴凝固,我的心扉被你一点点掏空,我的魂魄被你一丝丝定格。
女孩的相思疯长着,惆怅翻卷,不知疲倦。数着男孩归期的日子,就像这岷江河的波涛,翻山越岭,只为流去不返。
鹰在天空盘旋,山坳下那村儿,被梨花的洁白盖满,女孩的相思若隐若现。
3、邻家的新娘
幸福突然降临,仲冬的吉日良辰,邻家有女儿出嫁。
鞭炮还没有炸响,木芙蓉已开满了新娘的家。清晨,白花透着粉花儿开,午时,粉花儿变成了玫红花,这一日三变的花儿,就如待嫁女儿的笑脸,千娇百媚,闭月羞花。姐姐把鸳鸯对鸟和木芙蓉绣在妹妹的嫁衣上,天缘相配,夫贵妻荣,白头偕老。
村儿那头,他大哥的媳妇刚生了龙凤胎,不等满月就赶来祈福,为新娘铺床、挂帐、撒枣。闺房里的红双喜字刚刚贴上,娃娃们就争前恐后,一拥而上,呼啦啦追着新娘子讨喜糖。童年的毛根儿女友做了新娘的伴娘,喜出望外,好一番梳妆,打扮成一娇媚娘。
当迎亲的锣鼓唢呐由远而近,鞭炮震耳欲聋,小村儿也开始沸腾。镇子里的青石板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贺客,翘首期盼,望眼欲穿。当新郎背着新娘的迎亲队伍按时辰走过时,人如潮水一浪浪涌去,又戛然停止在新郎新房的门前。客人一阵阵哄堂大笑,顷刻又一阵阵鸦雀无声。
大红喜烛三尺长,照红新人照红堂,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爹娘,四拜姑舅,拜完亲友,再拜夫妻。万目聚视下,新娘羞涩在欢乐的漩涡里,大红大紫。
百桌喜宴,从村儿头摆到了村儿尾,请来了十里八乡的名厨子掌勺。柴火架大锅,杀猪炖肉蒸肥肠,炸酥肉,溜丸子,鱼虾王八全鸡鸭,红烧扣肉猪蹄花,腊肉排骨香十里。九大碗里有乾坤,饭饱酒足定终身。
酒客匆匆,吃过一轮又一轮……
4、婆媳的年关
天麻亮,婆婆的敲门声“咄咄”两下,媳妇就被惊醒了,男人的鼾声还在继续着他的节奏。媳妇一骨碌翻身下床,开门接过婆婆递进来的一小碗鸡蛋羹,这是给她男人补身子吃的。从嫁进婆家门的第一天开始,这每天一碗的鸡蛋羹就没有断过,也从来只有这一小碗,没有媳妇的份。
门关上,媳妇用脚踹踹男人喊:“起来吃起来吃”!男人迷迷糊糊撑起身来,咕噜咕噜几口吞下,仰头倒下又睡去。媳妇把碗往地下一丢,长长使劲地叹了口大气。这家族独根男人的特殊待遇,像一坨石头鲠在了媳妇心窝子,总是拿不掉,甩不开。
媳妇刚生下女儿才两个月大,没有给夫家生下男孩,就等于没有功劳也不算苦劳。这女人生下个女孩,就好比母鸡下了一只寡蛋,没用。婆婆的脸像秋茄子一样拉得又黑又长,满肚子不高兴,媳妇对婆婆也是满肚子委屈不敢说。婆媳心里,都在算计着各自的小九九。但对两个女人来说,有一点是相同的,生男孩的问题应该是女人天大的事情,没有停止只有继续。
冬日的阳光透过门缝和窗帘子,照射到灶台上挂着的那一溜子烟熏的老腊肉,金黄黄的,泛着黑烟熏过的油亮,一股股味儿散开,弥漫着浓浓的香气。这油亮亮的老辣肉,在媳妇的眼里,就像婆婆的身影,走过身边时,也总会散发出浓重的气味。
过年了,婆婆总要做她的核桃麻糖的,一年做一回。婆婆这远近闻名的手艺,还没有要传授给媳妇的意思,媳妇只有远远地站着偷看,悄悄记下制作核桃麻糖的过程。
婆婆把核桃仁、黑芝麻分别炒熟备用,再熬制麦芽焦糖。熬制麦芽焦糖是做核桃麻糖的关键,火大了很快会糊掉,火小了糖浆又不能牵丝。将精心熬制好的麦芽焦糖与炒熟的核桃、黑芝麻混合搅拌、搓揉、定型,凉冷后切片就可以食用了。一口咬下脆脆的,咀嚼后由劲道变柔软,满口浓香四溢,回味无穷。邻里亲友对婆婆的核桃麻糖赞不绝口,但婆婆就是不传授经验,只有每年春节初二三,亲戚邻里互相开始拜年走动了,大家才能吃到婆婆美味无比的核桃麻糖。
太阳快下山时,家里突然来了一拨远亲,说是进城购置年货路过,顺道来看看亲戚。亲戚们把小媳妇从头到脚看了个够,看得媳妇满脸通红,赶紧钻回了自己屋里,带小女儿去了。这小女儿也乖,正在这时候突然就哇哇哇哭起来。
听到婴儿哭声,亲戚们得知家里新添了小孩,非要看看是男是女。婆婆的脸一下子又拉长了,吆吼着里屋的媳妇把孙女抱出来。孙女儿见到陌生人哇哇哇哭得更厉害。婆婆突然瞪着媳妇骂道:“你不会喂奶吗,哭哭哭,生个赔钱货,一天就会哭!”媳妇抱着女儿正要回屋,婆婆又喊道:“就在这里喂奶呀!就坐这里喂!”
媳妇好尴尬,顿时脸蛋红一阵白一阵,不得不迟疑地掀开外衣,在一拨陌生亲戚的注视下,掏出奶子,将圆圆紫红的奶头塞进了女儿的小嘴里,女儿吞着妈妈饱满的乳汁停止了哭泣。而媳妇的泪水却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地砸在女儿的小脸上,泪水冲刷着小女人满腹的耻辱、辛酸和无助。
客人离去,婴儿熟睡了,媳妇悄悄冲出了家门,一口气跑到村头的桥上,痛痛快快放声大哭了一回,泪水如瓢泼大雨倾泻奔放。望着桥下流淌翻滚的岷江河水,媳妇真想一跃身跳下去,结束自己。
男人追来了,从身后一把使劲抱住了媳妇,用男人的体温安抚着媳妇忧伤、抽搐的身体。男人对媳妇说:“至于跑出来发泄吗?咱妈不就是想让亲戚们看看,女儿是我们亲生的骨血,不是捡别人的。”媳妇的心更凉了,一股寒气顿时透进了骨子里。婆婆这可笑的举动做足了夫家人的面子,当然也把媳妇彻底伤了心。
年关三十,瑞雪突然而至,小村儿的除夕夜色被片片飞雪妆点,时隐时现。村儿被百家灯火点燃,每一盏灯下,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人间故事,而结局都是一样,不是欢笑就是哭泣。午夜时刻,过年的爆竹噼噼啪啪地准时叫响了,像油锅里的炸胡豆,炸响了村镇,炸裂了小屋,把媳妇的心也炸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