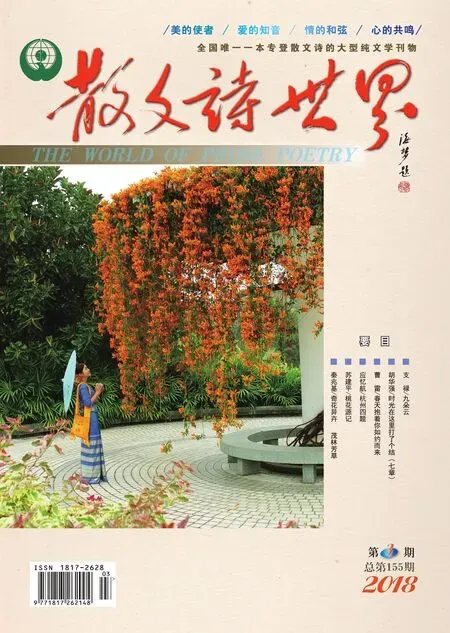九朵云
新疆 支 禄
1
破晓,一朵云来到窗口。
云,是从天上赶来的,心事重重地站在外边,既不进来也不离去,想要告诉什么的样子。
云,矮矮地站了好久。
最终,云什么话也没有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跟着风慢慢地走了。可云呆呆的眼神告诉:怕连累。毕竟天上的事殃及尘世,好事坏事吃亏的一定是凡人。
看来天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事的样子,云匆匆赶来报个信儿。话说到底,天上就是发生针尖一样大小的事,作为凡人一定帮不了什么忙!再别说地动山摇的大事了。
正午一过,天空已是电闪雷鸣,一直闹腾到黄昏。
电闪雷鸣的事,人间,实在一把忙也帮不上。
2
飞机“呜”一声穿过云朵,向天空飞去。
再高,再高,超过了天山;再高,再高,就到了天上。
天堂里的亲人们,过得还好吗?好久不见了,一定有许多想要说的话。闭上眼睛随心一想,怕一亲热,走的不让走,来的又忘记走了。
我还是想回来,在尘世,有许多事等着做呢!
当我睁大眼睛,下边,云朵海浪样翻滚,上边,剜心的蓝大锅一样扣在头上。
天上,什么也没有,一根针都没有。
那他们去了哪儿呢?又能去哪儿呢?
飞机,没有因一个人的想法而作停留。
窗外,一朵丢了魂的云,漫无目的地走着。天空太大了,云像是不停地想着:去哪儿歇会儿好呢?
一时间,面对无边无际的天空,云也丝毫拿不定主意。
先我到达天上的亲人去哪儿了呢?
云,慢腾腾地在散步,一点不关心的样子。
3
当我想起马的形状,云就变成马奔跑的形状;想起龙的形状,转眼之间,又变成长长的龙形,盘来绕去;想起了老虎,就变成老虎的样子,发起威风,啸声阵阵;想起鸟就变成一只鸟的样子,使劲地拍打翅膀,朝雨水丰沛的南方飞去,遥远的南方正值稻谷成熟,一派好年景啊!
……
云,应该变成一条回家的路,晌午一过,我就能赶回阔别多年的故乡。
朝着天空,我赶紧催着说:“变、变、变。”
云,最终没有变成,回家的路就这么难变吗?
或者变是变了,片刻,却让风吹得魂飞魄散。
4
大半天时间,一个人粮袋样搭在沙梁杆儿。
望着天空的云朵,猛想起年轻时,一起出力不讨好的五个人,上司一不高兴就喊猪脑子,那时,连尘世的一棵草也看不起我们。
一个个真的能行,帮老板赚的只只口袋鼓鼓的;更多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老板指天画星星说如此深奥的事,我们做起来简单的像个一,老板反复地用计算器戳捣半天的数字,我们总是脱口而出,让老板恼火不已,老板一出办公室的门朝太阳吼道:“研究生、大学生多得是!”
“啐”地唾了一团,我们也就不干了。
翻遍衣袋凑了钱,买了二锅头,几碟子小菜,在戈壁滩上大喝一场,然后,在茫茫不知所措地唱起西北花儿《冻死尕老汉的歌》,唱着唱着天就亮了,各奔东西。
从此,像撂进大海的针,渺无音讯。
如今,手掐指头一算,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不知道另外四个猪脑子过得怎么样?
而我不快乐的时候照旧让太阳拼命地晒着,一个人这样躺着谁都知道晒不出什么大名堂来,但风会把忧伤一点一点吹成无边无际的沙子,浑身上下轻松不少。
忽然,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一朵大小、形状、色泽,和一个猪脑子一模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探头探脑地在塔克拉玛干以北高高的云端,一下子让我看到了。
接下来,又来了三朵,张三李四王麻子,我知道是谁了。一个个怎么这么快就匆匆去天上了呢!
后来,一旦闭上眼睛,轰隆隆地,听到他们从头顶走过的脚步声。
5
一抱一抱的云着火了。云,燃烧得好厉害,从西面烧到东面。
黄昏,风一点都不大,让人纳闷的是:怎么发生火烧连营的事呢?
当巨大的影子在天空晃动。神,挽起袖子,开始扑火。
天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天上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呢?如今,天上发生什么一点音讯传不到人间。
以前,仙女下凡择婿,牛郎追织女去天上定居,吴刚砍桂花树……人间和天上亲戚一样来往,时不时,神提拔凡人得道成仙,比如铁拐李、关尹子、刘海蟾……多得数不完。
不知什么时候,神与人拒绝往来,别说提拔的事。
在人间,眼巴巴地望着燃烧的云,也就无处下爪。
不久,云烧成的灰从天空纷纷落了下来,暮色样,埋住了草垛子、村庄、大山。
月亮上来后,人间,才感觉轻松了一口气。
6
人不走,云就不走;人走,云就跟着走。
一朵云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头顶跟着我转悠了半天。那些日子,我无所事事,难道云也闲着没事?云,难道跟着看我的笑话?
也许,我接二连三地叹息声风听到了。风,稍稍劝了一下,云,就走开了。
在天空,云就听风的话。
其实,那时,许多风言风语,说的都不是鸡毛蒜皮的事。
7
一直以为云轻飘飘的,所以毫不在意云的存在。
那年,一年半载找不到活干,整天无所事事地躺在黄沙梁上,看蚂蚁搬家、黄蜂打架,七寸子上爬下窜,听麻雀子,一口一个日他妈。
河流,一袋子一袋子地把时光搬到远方,然后,码起来,成了高高的垛子。那些嫌时光不够用的人,一看到北方的天空下,已经堆放那么多高于大山的闲散时光,惊得目瞪口呆。
时光,又不能借着用一下。
他就蹲下来彻夜抱头痛哭,哭声,撕心裂肺,在大地蔓延。
闲着的时光满黄沙梁不停地流着,闭上眼,只要伸出手胡乱抓一把放开,依旧看到闲下来的时光;再伸出手胡乱抓一把放开,依旧看到闲下来的时光。
风,抓起一把时光撒向高高的天空,落下来就变成浩瀚无边的黄沙;再抓起,丢下来依旧是浩瀚无边的黄沙……
一朵云,飘在我的头顶,寂然不动。
当我斜躺睡卧在沙堆上。一朵云,就飘到我的心里。云,好重呀!巴掌大小的一朵云,竟然一大袋粮食样压得我半天翻不过身。
看上去轻飘飘的云,原来和大山一样重。
8
初春,一群羊卧在东天山谷口,漫无目的地望着。
雪山的光亮一把一把掏去目光,六神无主,变成空空的袋子。春天刚刚开始,大北方还没绿的迹象。一个冬天,草经常让北方的寒冷埋得不一般的深啊!
破土发芽一次,就是一个传说。
一阵老北风吹来,羊,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吹成天空的云朵,赶往有草原的地方。
一只羊心事很重,起初像是不想走的样子。
等风再来时,一个拱形的跳跃,也迫不及待追赶迁徙的大军。
荒凉漫过四蹄,羊不能不走。
风越来越大,吹得天空一丝不挂,羊,匆匆忙忙地赶着,那行色匆匆的样子像是体内有把鞭子在不停地赶着。绵密的蹄声惊醒沙坡上熟睡的闪电,粗声粗气地给西去的群羊出难题。有许多羊被敲打敲打成粉末,魂飞魄散,更多的还是跨过去,继续前行。
天边边上有伊犁大草原,我去过,整个夏天,羊荤吃海喝的,让日子过得肥肥胖胖。
9
一朵云,飘在岩画上。
雨,一刻不停地落下来,像是一袋袋米粒,从高高的天空倒了下来。
一撒,落了五千年。许多羊在岩面外,咩咩地叫着,不停地喊渴,就是不见雨从岩面流出来。
幸亏目光望不穿岩石,否则,岩面早已千疮百孔。
风沙稍微停了一下,一只跟着一只跳了上去,喝得酣畅淋漓。
好几年后,路过那块岩石,喝足的羊卧在岩面上的草丛中,又是一动不动,看得久了,一只只羊眼皮子稍微瞭一下,然后又是一动不动。
那朵云,一直下着雨,丝毫没有减小的样子。
羊喝足了,为什么不下来呢?
在戈壁,雨水就是羊的命。